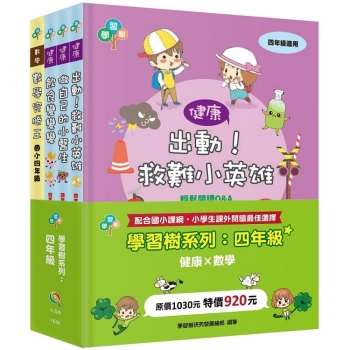小野洋子心中最真實的約翰藍儂!
他是搖滾樂史永不寂滅的風,
他是愛與和平的實踐者,
因為藍儂,我們從此有了作夢的勇氣。
一九八○年十二月八日深夜,約翰藍儂與小野洋子回到達科他大樓門前,一名瘋狂的歌迷朝這位搖滾巨星開了五槍,藍儂的生命在此終結,年僅四十。他的猝逝舉世震驚,搖滾樂壇失去一位最富傳奇色彩的巨星。
藍儂締造六○年代的搖滾神話,披頭四當時一季的唱片銷售量高達美國唱片總銷量的十分之四!但也許是盛名來得太快,他迷失在自己一手創建的披頭神話中。他高唱〈救命!〉,小野洋子聽見了。她是約翰的心靈伴侶,兩人創作大量音樂,並為世界和平發聲,呼籲「戰爭結束了」,用音樂與行動傳遞更深遠的影響,向那個年代的威權發出憤怒之聲。然而一聲槍響,中止了所有夢想。
藍儂過世二十五年後(原文二○○五年出版),未曾走出槍殺悲劇的洋子,選擇集結眾人的文字,包括藍儂的偶像、音樂同儕、貼身採訪過藍儂的記者、夫婦倆的密友等,以文字、照片、圖畫、詩作,甚至是解密的政府檔案,共同回憶這位巨星。書中收錄大量珍貴照片,包括德國攝影師艾斯翠克赫爾拍攝的年輕藍儂,及安妮萊柏維茲在槍響前幾小時留下的約翰與洋子相擁的珍貴鏡頭。
透過七十三位好友的真情告白,讓洋子獲得最大的安慰:「看著大家的文章,我笑啊笑的,然後哭了出來,一發不可收拾,而且最後一頁怎麼這麼快就翻到了……」
藍儂短暫卻燦爛的一生,觸動許多人的心,直至今日,無數人受到感動與啟發。無論是披頭四時期風靡世界的音樂,或是單飛之後所創作的歌曲,都為西洋音樂樹立無數的典範。我們不會因為他的離去停止想像,因為藍儂,我們從此有了作夢的勇氣。
【好評推薦】
◎「我深深被這本書感動!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約翰藍儂不為人知的丰采,你就應該閱讀這本書!」~美國舊金山讀者
作者簡介:
野洋子與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日本移民到美國,定居紐約。洋子在此求學,專攻哲學與音樂,一九六○年代初成為行為藝術家。一九六五年在卡內基音樂廳表演了她最著名的行為藝術「切片」,由觀眾用剪刀將她的衣服裁成碎片,直至赤裸。
一九六六年,她認識約翰藍儂,一九六九年成為夫妻,直到一九八○年約翰過世。他們合作耕耘革命性的藝術、電影與音樂企畫,並致力於和平與人道主義活動。約翰死後,洋子曾發行自己的唱片,音樂類別屬於實驗曲風與前衛搖滾,並持續推動所有藍儂的音樂發行及各式各樣的音樂活動。
二○○九第五十三屆「威尼斯雙年展」獲頒最高榮譽的「終身成就金獅獎」。如今她已七十六歲,仍持續在世界各地發表屬於自己的展覽與創作,目前定居紐約市。
章節試閱
想念約翰
那天晚上,約翰突然撒手人寰,我覺得自己也隨他去了大半。我全身發抖,膝蓋抖得尤其厲害,我得抓著一旁的友人,才能步出醫院。春天來了又走,夏天緊接著來,我很驚訝,縱使約翰已不在人世,陽光之下的綠葉依然燦亮,所有事物依然充滿活力,簡直是罪惡。美麗的秋天過去,冬季降臨,我才發現這季節對我來說,將會是多麼的殘酷。
二十五年過去了,當我和大家相處,和兒女在一起時,我很好。我會微笑,會開懷大笑,會抬頭看著天空,讓心飛揚。我擁抱孩子(正確說來是他們擁抱我,孩子都長得比我高大了),但當我獨自一人、當向晚的光線將天空染成粉紅色,在漆黑的深夜以及清晨時分,我的心依舊顫抖得難以停歇。
大家一直問我,什麼時候才要寫出我和約翰的生活,我總是說自己還沒準備好。我有可能準備好嗎?不太可能。當心還在顫抖,我不可能敞開那部分的心房。
這本書讓我覺得幸福。每篇短文我都很珍惜,大家真的很愛約翰,字裡行間機智幽默又充滿才氣,我獲得莫大的寬慰!我不敢相信我和約翰的朋友中,有這麼多人文筆都這麼好,我心裡不斷對他們喊話:「繼續寫,大家都是作家的料,現在開始還不晚喔。」他們讓我捧腹大笑,從伍迪艾倫最近一部片以來,我就沒這樣笑過了,想想還真的滿久了......我笑啊笑的,然後哭了出來,眼淚簌簌流下,一發不可收拾,看到最後一頁還在落淚,而且最後一頁怎麼這麼快就翻到了......
這本書是很棒的企畫,希望你們和我一樣喜歡。就像我們以前推出成功作品時(我們是這樣覺得啦),約翰會說,我們很快會再「生出續集」。我的朋友,感謝你們,願意與大眾、特別是我,分享這麼多深埋在心底的回憶。我真的很幸運。
小野藍儂洋子
二○○五年春
…………………………………………………………………………………………………
雙重影像 大衛葛芬
時至今日,即使那件事過了四十年,我只要聽到披頭四歌曲的幾小節,仍馬上受到披頭音樂永恆的悸動,想起他們所創造的傳奇。一九六三年第一次聽到披頭四的歌曲,帶給我前所未有的感受,從此一路聽了下去。我感覺到他們不只是樂團,而是真正的藝術家,不斷拓展自己的視野,用每一張專輯帶領我們這群深深受到感動的歌迷踏上新的旅途。
我投身音樂界之後,擔任很多歌手、詞曲創作者的經紀人,他們都大方承認熱愛約翰與保羅共同創作的歌曲,多數也認為自己永遠達不到披頭四的水準。一旦位居該文化的翹楚,你的影響力自然無法抹滅;披頭四的唱片雖然錄製於六○年代,其藝術性卻不因年代漸增而有所減損。
我第一次見到約翰藍儂是在一九七四年,他和菲爾史培克特正在A & M唱片錄製專輯。當時的他並不順遂,和妻子洋子正值分居狀態,無論是私人生活還是事業都一團糟。六年後,洋子再次介紹我們倆認識,與先前的他判若兩人。他變得沉靜,最重要的是,他和洋子升格為父母,孩子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對於自己的名氣,他從沒習慣、但也不會否認,根本是完全不理會;後來,家庭更成為當上父母的約翰與洋子生活的重心。
一九八○年,約翰和我都處於事業的再出發。我剛創立葛芬唱片,約翰則進錄音室,和洋子一起錄兩人的專輯《雙重影像》。我知道如果能簽下他們,一切就沒問題了,但我不覺得有機會。我寫信給洋子,因為她才是做決定的人,約翰對她有絕對信心,在事業上完全信任她。約翰錄製《雙重影像》的動機很浪漫,他想讓世人知道洋子的天分,讓她得到應得的認可。他希望光芒照耀在洋子身上。「我們要照顧洋子。」他會這麼對我說。「這是這張專輯的目的。」
不過,洋子卻是個實際派,她會跟約翰說,大眾想聽的是他的音樂,不是自己的。不過約翰不管。他是洋子的頭號歌迷。他們倆有著全面性的合作關係,互信互重成為兩人婚姻關係的基礎。我這輩子都和明星為伍,但從沒見過像他們這樣合而為一的伴侶。
最後我們合作了這張專輯。約翰與洋子對於專輯的成功大感興奮,很開心大家能接受他們的作品。然後,幾分鐘之後,在熙來攘往的紐約街道上,有個人從他們、從我們身上,奪走一切......
我不願回想或談論約翰被殺的那個夜晚。電話通知我到醫院去找洋子,因為約翰遭到射殺,我一度以為是惡作劇電話。會意到這個慘痛的事實後,我趕到醫院陪伴洋子。醫生要我告訴她約翰已經斷氣,但我說不出口,求醫生自己告訴她。
那晚,我們回到達科他大樓時,他們門口釘著一張雜誌上撕下來的告示牌百大排行榜,他們的專輯拿下第九名,約翰用筆圈了起來,還加上箭頭,指向第一名。當然,專輯在隔周就登上排行榜第一名。
經歷了那個可怕的夜晚,至今我仍是洋子的朋友和仰慕者。約翰的離去,讓我們都失去了一些東西。即使到現在,我仍想念他的音樂、他的精神,與他希望安身立命於和平世界中的強烈信念。約翰與他的兒子會是洋子永遠的最愛。我能夠確認的事,無論是他在披頭四時期的歌曲,或是詩一樣的〈想像〉(我的最愛),約翰的作品將永世流傳。
大衛葛芬:創立了「避難所唱片」與「葛芬唱片」兩大品牌,之後轉到電影製作,和夢工廠合作。約翰藍儂和小野洋子的《雙重影像》是葛芬唱片公司發行的第二張專輯,於一九八○年十一月發行。
…………………………………………………………………………………………………
藍儂回憶楊韋納
約翰是個暴烈的天才。他強烈的個性裡富含了力量、憤怒、激情、熱血等元素,想分析他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一次把他排上雜誌封面完全是個巧合。當時截稿日期迫在眉睫,亟需派得上用場的照片,我們手上正好有些理查賴斯特的電影「我如何贏得戰爭」,其中有張由約翰藍儂飾演的二兵葛維的劇照,看起來很酷,當期的封面就這麼決定了。有道是需求是發明之母,這件事完全不在計畫內,那只是我們手上最好、也最有意思的照片,原因就這麼單純,但事情就是這麼巧!他媽的可真巧!
我們的關係始於《童男處女》那張專輯,當年我才二十一歲,這張專輯當年是禁片。雷夫葛利森對我說:「嘿,有沒有辦法弄到那張照片?」我認識德瑞克泰勒,他和約翰的關係很好,都是有才氣又聰明的人。我寫信給德瑞克:「我們可以這樣做嗎?」當然,他們答應了,寄來《童男處女》的封面,正反兩面的。我們照原樣刊出,那是我們一周年的特刊,總期數第二十二號,上市後旋即售罄再加印。
「滾石」那時還是小雜誌社,這期成為創刊以來銷售量最高的一期,我們首度嘗到名氣的滋味。我記得很清楚,「舊金山紀事報」下了「裸體披頭危害舊金山」的標題,我心想,天啊,高明、高明、高明。在下一期的編輯室報告裡,我算是給讀者寫了封信:「這次讓我們學到教訓,刊出有名的包皮,全世界就會對你大加撻伐。」
約翰、洋子的裸體照登上雜誌封面引發軒然大波,是因為當時沒人敢那樣做,現在早已司空見慣。這個行動很了不起,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第一,正面全裸在當時前所未見;第二,他們是以明星的身分來做這件事,而且還是最有名的明星;第三,裸露的身體不是光滑無瑕的那種,他們昭告世人要有勇氣做你自己,心胸要開闊,要對自己誠實,你的模樣不管是如何都很酷,毋須是花花公子雜誌的兔女郎或是古銅色膚色的萬寶路牛仔;做自己就是酷的,他們要大家知道這一點。
從那時候起,我們就開始報導有關約翰與洋子的活動。當時披頭四還沒正式解散,但他們已各作各的,而約翰有點煩躁不安地急欲掙脫束縛。他一直說:「有一天我會告訴你我的故事,有一天我會說自己的故事。」
他們持續推動和平運動,一九六九年在直布羅陀成婚,去了阿姆斯特丹與蒙特婁舉行「床上和平運動」,同時,我們也報導洋子的前衛作品。我有個大學時代的好友住在倫敦,名叫強納森卡特,他十分了解這些東西,了解德國作曲家史托克豪森、古典樂與當代音樂,常常供稿給我們。他跟洋子相熟,透過洋子也認識了約翰,所以我們開始報導洋子的活動,還有約翰的近況。
我們決定支持和平運動後,有關約翰和洋子的報導更多了,我們戲稱這是「多倫多截稿日」,派出記者或自由撰稿者撰寫他們的行動。約翰、洋子會主動打電話給我們,我也會給他們撥電話,電話訪問一結束,旋即刊出第一手、最新的消息。當地的媒體或地下報紙偶爾會發一點消息,我們仍是他們與讀者聯繫的最大出路,彼此有點結盟的味道。
我人在舊金山,他們夫婦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倫敦。刊物的辦公室就設在印刷廠裡,辦公室有台電傳打字機,那是國際通用的私人電傳打字機,現在都丟到垃圾堆裡了。他們在亞斯各有一台,我以此和他們的助理連線、互傳訊息,有個資料夾就專門在收集這些,像是和雜誌有關的、他們對外的聲明等等。我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們把消息放給我們,提高了合法性,也有助於當時正崛起的「滾石」雜誌的知名度。經過一番來回,我們終於促成了那個有名的專訪,專訪內容在一九七一年由「滾石」雜誌出版成《藍儂回憶》一書。
我和約翰共度過最有趣的時光,是一九七○年春天他來舊金山的時候,他和洋子突然來電,說他們人正在舊金山,想來「滾石」雜誌辦公室走走。我帶他們參觀雜誌社,引起一陣騷動。他們下榻市中心的希爾頓飯店,我放下手頭所有工作和他們共度周末,幫他們找了更棒、更安靜、更隱密的旅館,用一個周末的時間陪他們看電影、逛舊金山市區還有一道用餐。親眼見到約翰的經驗非常有意思,近距離看著他的一舉一動,當時他才剛進行「原生吶喊」治療療程,情緒不太穩定,好的壞的一下子全都浮上檯面,但他選擇面對,不想繼續隱藏自己的情緒。如果有人靠近請他簽名,他會覺得被騷擾,馬上就變臉,他不再以禮貌的一面示人。我滿驚訝他對那些索取簽名的人口氣很差,直接簽個名不是比較簡單嗎?但他會說:「你沒看到我在吃飯!」或「沒錯,妳打擾到我了!」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當時他才二十九歲,還非常年輕,比較接近青少年期,而非成人階段。
所以舊金山之旅相當愉快,洋子有一小段童年時光是在舊金山度過的,我們兩對夫婦在城市裡觀光玩樂。他們從沒看過《讓它去》,電影在舊金山上映已長達三個月了。我們挑上班日的下午時段去看,一般人不會在此時進戲院的,裡頭空蕩蕩的,只有我們四個。看著一部描寫披頭四解散的電影感覺十分痛苦,他們在電影裡關係惡化,一直到影片結束都沒好轉。和披頭四的團長一起看這部電影感受格外深刻,我們四個人一走出電影院不由自主的相擁而泣。
我們正式進行專訪的時候,不是輕鬆地在家進行的,而是在艾倫克萊恩紐約辦公室的會議室裡進行,克萊恩準備了一台錄音機,我也拎了一台,洋子也在場。
在每個人心中,這都是件大事,因為約翰不曾接受這樣的訪問,從來沒有。他接受過零星的訪問,這裡一點、那裡一點,但他才剛脫離符合大眾期望的披頭四時期,十分期盼能一吐為快,好不容易有了機會能好好談談自己以及這一路走來的感想,這些在以前都是要被掩蓋或是淨化處理的,想都不要想。
幾年來,你注意到他的幾件新聞,他發表披頭四比耶穌還紅的言論,或者是和英國女皇有關的一些爭議,或是他的機智,但是他苦澀、嚴肅的一面卻沉寂多時,更不用說他對仍被視為披頭四的一員而深感不悅。瞧大家怎麼喊他的?聰明的披頭?其實回看披頭四一路走來的軌跡大概就能理解約翰的所思所想,這些從他在學時的成績單就能嗅出端倪。這次專訪前所未有,所以要問他的事情有一籮筐,像是:身為披頭四的一員是什麼感覺?那些歌是誰寫的?歌曲想傳達什麼信息?
當時我們都很年輕,我二十四歲、約翰三十歲,都是個性有稜有角、天真又自我的年紀。回想起來,當時的我訪問技巧仍待琢磨,策略也嫌生澀,我們的對話卻熱力四射,時而劍拔弩張但也相當誠實。這就是他的風格,首次以赤裸裸、未加修飾、誠懇的樣子暴露在大家面前,嘗試跟世人對話。
他和媒體的關係其實非常好,他與人為善,喜歡眾人的注意,不介意曝光,而且很想傳達某些事:和平運動。他愛談論,他的訪問出色且能侃侃而談。他喜歡唱片賣座,登上排行榜,這點他很誠實。他喜歡接受訪問,喜歡記者;他一點都不能忍受笨蛋,遺憾的是很多記者都是笨蛋,但他卻能迷住記者,當然,披頭四仍然是個浪漫、裹著糖衣的神話。「滾石」刊出的專訪,是第一次有披頭團員(更不用說是他們的創團元老與團長)走出被保護的世界,將所有的一切全攤在陽光下。我個人和「滾石」雜誌這份刊物清楚約翰的為人,他大可放心通盤說出他想說的。他說話很急卻非常自然,卸下心防滔滔不絕談論著從沒講過的重要的話題,充滿他處事一貫的熱情與智慧,少有藝術家的自我描述是這樣的,我從來沒有看過。
每個人都崇拜約翰,因而引來尼克森政府的騷擾,先前還有宗教狂熱份子的撻伐,大家自然會同情約翰,公眾曖昧的態度也讓約翰得到了好處。很多媒體認為「袋子運動」與「床上和平運動」愚蠢到極點,很多人心裡大概想著:「你知道嘛!約翰就是怪,反正也不會傷害到誰。」然而他們喜歡他。他不像別人會去爭,還假裝不想上報或不需要作公關,這類狗屁倒灶的事現在還是一大堆咧。
我確定他確實有些祕密,但他已經相當開誠布公了。他應該是覺得「有必要撒謊嗎?」他誠實、不隱瞞,不管會有多痛苦。他很情緒化、容易失控,對某些事情也會義憤填膺,痛恨偽善,要是讓他察覺絕對是一針見血加以戳破。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過程中他所忍受的痛苦有多巨大,他的感受力向來深刻,和平與愛對他而言非常重要。在披頭四時期,或是後來名氣更盛的時候,他的〈只要有愛〉道盡了「愛」這個經常被忽略的人生課題。他跟哲學家羅素、科學家愛因斯坦是同等級的天才,為了推廣和平與四海皆兄弟的信念到處奔走。
他走得太早,來不及看到他的信念發光發熱,但卻也為吉爾道夫與波諾等人架好了舞台。
他照顧西恩的那段時間,我們並沒有聯絡,但我可以想見這個世界懷念他,並不是因為他是個全心全意的父親。如今,父親積極參與育兒工作反倒流行起來,不管是不是單親爸爸。傳統的父親形象已有改變,現在的父親必須要肩負育兒使命,過去才不是如此,至少不像當時約翰那麼熱中。
他自痛苦中激發出更強烈的東西,反過來解決痛苦的根源。這顯然與他的童年有關,在利物浦長大的約翰,戰爭的陰影仍未退去還被父母遺棄。二次大戰後的利物浦十分封閉,注定不平凡的他受困其中,急欲掙脫。利物浦不是機會之地,對於從小就才氣逼人的天才如約翰,此處並非他的棲身之處。他這一生深受回憶所苦,與當權者的抗爭永不休止,他與打壓他的保守派人士搏鬥,那些吝於去愛、會說「不能做這個、不能做那個」的大人們,他是典型的反對派份子。
約翰無疑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曲家、流行音樂創作人,同時也是歌手與社會評論家。披頭四在現代傳播崛起的時代裡,在歌唱、曲風與詞曲創作這方面稱得上是絕對的天才,他們一向走在前端,也是第一個席捲全球的樂團。你可以說之前絕對出現過天才型的音樂人,像是吉爾伯特與蘇利文、羅傑斯與漢默斯坦、柯爾波特等等,但披頭四現象是前所未見,他們在特殊的年代崛起,以世界史的觀念來看就是戰後嬰兒潮。西方社會與受西方影響的社會,在二次大戰後人口暴增,披頭四道出了這群人的渴望,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他們代表了年輕人的文化,而這群人如今已成為主導世界的中堅份子。披頭四影響他們,為青年發聲,將那些價值觀付諸實踐,披頭四對世界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日。這些了不起的成就源自約翰的社會良心,是多年來在他的創作中不斷追求的,不管在錄音室裡,或延伸到錄音室外。
大眾記得的約翰是個愛好和平的殉道英雄,也是史上最偉大的搖滾樂手之一。約翰是聽貓王長大的,貓王是他的偶像,如果說有誰能超越這位身穿黑色皮夾克的搖滾大老,這個人非約翰莫屬。這樣的傳奇對約翰來說,比什麼都重要。
(此文為訪談整理)
楊韋納:「滾石」雜誌創刊時的總編輯兼發行人,他也是韋納媒體公司的董事長兼執行長,發行「US」與「男性時尚雜誌」,之後成立韋納出版公司。一九七○年曾與約翰藍儂進行長時間的訪談,內容刊登於「滾石」雜誌上。
想念約翰那天晚上,約翰突然撒手人寰,我覺得自己也隨他去了大半。我全身發抖,膝蓋抖得尤其厲害,我得抓著一旁的友人,才能步出醫院。春天來了又走,夏天緊接著來,我很驚訝,縱使約翰已不在人世,陽光之下的綠葉依然燦亮,所有事物依然充滿活力,簡直是罪惡。美麗的秋天過去,冬季降臨,我才發現這季節對我來說,將會是多麼的殘酷。二十五年過去了,當我和大家相處,和兒女在一起時,我很好。我會微笑,會開懷大笑,會抬頭看著天空,讓心飛揚。我擁抱孩子(正確說來是他們擁抱我,孩子都長得比我高大了),但當我獨自一人、當向晚的光線...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