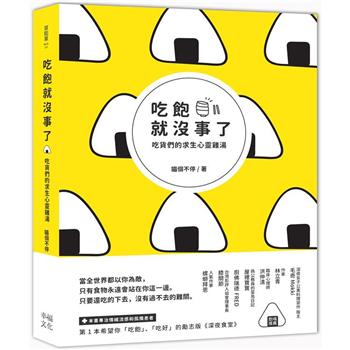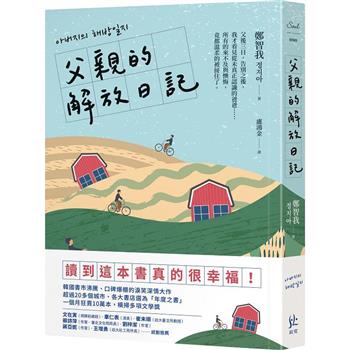藍儂第一位親密愛人的私密回憶!
一段成名前罕為人知的歲月,
從發光到殞落的傳奇故事,
映照出最真實的約翰藍儂……
一九五○年代後期是個夢想的年代,戰爭結束了,年輕人開始恣意揮灑青春。英國利物浦四個小夥子組成一個樂團,在當地的俱樂部演唱,他們的專輯迅速登上英國排行榜冠軍,接著向大洋彼岸的美國樂壇進軍,披頭四短短幾年內風靡世界,被推向世界流行音樂最高峰,創造了六○年代的搖滾神話。
這段藍儂由沒沒無聞到成為搖滾巨星的歷程,他生命中第一位真愛──辛西亞始終伴隨左右。她是約翰第一任妻子,和這個舉世聞名的男人共同生活了十年,陪伴約翰經歷樂團初創時的起起落落,見證披頭四崛起的那段關鍵歲月。
在世人為披頭四瘋狂的同時,約翰卻迷失在自己一手創造的神話中。盛名與毒品帶來了劇烈的轉變,然後他遇見了日裔前衛藝術家小野洋子,約翰與辛西亞的婚姻在一個苦澀的過程中畫下句點。他與洋子於一九六九年結婚,兩人創作大量音樂並鼓吹世界和平,他們的理念為這個世界帶來不一樣的夢想,影響了一整個世代的人,甚至是四十年後的今天。
但辛西亞與藍儂長子朱利安長久以來被大眾所遺忘:披頭四時期的飛黃騰達,她大部分時間只能隱身幕後;藍儂單飛時期的轟轟烈烈,更是莫可奈何地完全缺席。但這些都沒改變她對藍儂的款款深情。
一九八○年十二月,約翰在紐約自宅門口被槍殺。二十五年後(原文二○○五年出版),辛西亞不再保持緘默,她用最平實的文字,娓娓道出屬於他們的年輕歲月,追溯他從沒沒無聞到風靡世界的歷程,關於一個歌迷從沒有接觸過的年輕藍儂,勾勒出這位搖滾巨星時而殘酷時而風趣、才華洋溢且極端渴求關愛的深沉性格。書中收錄大量從未曝光的珍貴照片,包括約翰藍儂在藝術學院時期以及樂團剛起步時的照片,帶你重溫那個夢想的年代。
【好評推薦】
◎「所有披頭四的粉絲必讀的一本書!!」~美國加州讀者 Betty Dravis
作者簡介:
一九三九年出生於黑潭,在威拉爾半島長大。一九五七年自利物浦藝術中學畢業,同年進入利物浦藝術學院就讀,她在那裡認識約翰藍儂,當時他已因叛逆、善於譏諷的性格,以及對搖滾樂的熱愛而與眾不同。約翰和辛西亞在學院的第二年墜入愛河,於一九六二年結婚。一九六三年,他們的兒子朱利安出世,同年,藍儂一家搬到倫敦,之後定居於索立郡,在那裡度過披頭四全盛期的幾年。一九六八年,他們的婚姻觸礁,一九六九年離婚,朱利安由辛西亞扶養。約翰和第二任妻子小野洋子搬到紐約後,朱利安會到紐約拜訪他們。辛西亞現在與她丈夫諾耶爾查爾斯住在西班牙。
章節試閱
1
一九八○年十二月初的某個下午,安琪和我在北威爾斯一間我們共同經營的小酒館裡打點聖誕節裝飾。天候陰濕寒冷,室內卻充滿了歡樂溫馨的過節氣氛。我們開了瓶葡萄酒,將聖誕樹的吊飾一一掛起,牆上滿是聖誕節的圖畫。我們十分開心,隨意開了個彩球,裡頭的玩具掉到地上,我彎腰拾起,是把小塑膠槍。這讓我打了個冷顫,在滿屋子金箔與紙環裝飾品當中,這把玩具槍顯得格外突兀。
隔天我去了倫敦一趟,借住在我的朋友茉史達基那兒。聖誕節前夕是店裡的旺季,我根本抽不出空,但律師告訴我有些文件非要我的簽名不可。於是我搭上前往倫敦的火車,打算第二天就返家,我不在家的時候,店裡的一切由我先生跟安琪打理。安琪是保羅麥卡尼的弟弟麥克的前妻,她跟麥克離婚後就住進餐館樓上,與我一同經營餐館。
我很開心又見到茉,我們在一九六二年成為朋友,當時我正和約翰交往。年輕的時候,茉是披頭四的歌迷,她在洞穴俱樂部邂逅了林哥,兩人墜入愛河,在我和約翰結婚一年六個月後也步入了禮堂。披頭四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唱的日子裡,我們倆總是相互作伴。她的大兒子查克今年要十五歲了,朱利安則大查克一歲半,這兩個男孩從小就是玩伴。
茉和林哥在一九七四年離婚,當時的茉傷心欲絕,騎了摩托車一頭撞上磚牆,傷勢十分嚴重。茉在十五歲的時候就跟林哥相戀,所以當林哥帶著他的新女友、美國演員南西安德魯絲公開出雙入對的時候,看在她眼裡格外痛苦。
茉離婚時才二十七歲,之後她帶著三個孩子搬到梅達谷,查克、傑森、李分別是八歲、六歲、三歲,都還是孩子。車禍後,茉的臉部整形手術十分成功,反而覺得自己比從前漂亮,林哥也從她的生活慢慢淡出,後來還與喬治哈里森約會了一陣子,最後與硬石餐廳的老闆、百萬富豪艾薩克提桂特正式交往。
我抵達倫敦的那天晚上,茉的家裡跟往常一樣熱鬧,她母親弗蘿和她三個孩子再加一個保母與她一起住,她家的大門一向為朋友敞開。當晚一起共進晚餐的有我們共同的老朋友吉兒以及戴爾紐頓,保母準備的晚餐非常豐盛。餐後,我和吉兒、戴爾、茉琳開了幾瓶葡萄酒,聊起往事,沒多久話題就轉到梅爾伊凡斯的死,他是披頭四巡迴演出的經理,負責器材等事宜。梅爾人高馬大,為人慷慨大方又有副好心腸,早些年他在郵局工作,晚上在洞穴俱樂部兼差當保鑣的時候我們就認識他了。之後幾年,隨著披頭四愈來愈紅,梅爾開始替披頭四工作。
梅爾生前一直是披頭四們忠實的朋友,和約翰尤其要好,他與披頭四另一位巡迴經理尼爾阿斯比諾一起籌畫巡迴的大小事,解決許多突發狀況,保護、照料著大家。披頭四解散後,梅爾迷失了自我,後來聽說他搬去洛杉磯,還傳出酗酒、嗑藥的消息。
一九七六年一月四日,就在他洛杉磯的家,梅爾與女友發生爭執,女友打電話報警聲稱梅爾對她拔槍。警方趕到他的公寓,看見梅爾手裡有槍,槍口正對著警察,於是開槍擊斃了他,後來發現他的槍裡根本沒裝子彈。這是個悲劇,我們猜想他當時應該是嗑藥嗑到腦子不清楚了,因為我們所認識的梅爾絕對不會拿槍指人。無論如何,他的死帶給大家很大的衝擊。那天晚上,我們一群人圍坐在茉家的壁爐旁,話題全是梅爾,聊到他生前的好,不應該就這樣走了等等。
我們無法想像,死在槍下會是什麼情況,更無法想像這事就發生在我們的好朋友身上。
聊了一會兒我打算先去睡了,我知道大家會繼續喝酒聊天直到天亮,但隔天一早我還得趕搭早班火車回家,得好好休息一下。
我進客房沒多久,突然被尖叫聲吵醒,沒過幾秒,我聽出是茉的叫聲,她衝進房間:「辛,有人朝約翰開槍!林哥在電話上,他要和妳說話!」
我不記得自己是怎麼下床、怎麼下樓去接電話的,林哥在越洋電話另一頭邊哭邊說,他的一字一句我聽來清晰無比:「辛,我很難過,約翰走了。」聽見約翰的死訊我整個人都傻了,一下子反應不過來,我聽見哭泣聲,回過神來發現是自己在哭。茉從我手裡接過話筒,跟林哥說了再見隨即掛斷電話,她一把抱住我,邊哭邊說:「辛,我跟妳一樣難過呀!」
那時我腦中旋即浮現了另一個身影,就是我的兒子,我和約翰的兒子朱利安。他現在應該在睡夢中,我得趕緊回家通知他這個噩耗。朱利安當時還是十七歲的孩子,命運捉弄,我們兩代竟然同時在差不多的年齡失去至親,我的父親在我十幾歲去世了,約翰則失去了親生母親。
我撥了通電話告訴我先生我馬上趕回家,在這之前別讓朱利安知道他父親的死訊。當時我們的婚姻已經走到盡頭,但我先生仍在這關頭支持我,他說:「當然,我會盡力保守祕密。」
我著好衣裝,將行李打包完畢,茉叫了車堅持要帶查克陪我一起回去。她說:「如果朱利安需要避開媒體,就讓他到我家跟我們住一陣子。」
十二月八日晚間十點五十分,約翰在紐約遭槍擊,英國時間是十二月九日凌晨三點五十分,事情發生不到兩小時,林哥就撥了電話給我。我們一行人於七點上路,到北威爾斯約莫得花上四個小時。黎明天色灰暗,窗外景色不斷轉換,但我滿腦子想的都是約翰。
雜亂的思緒中,有兩個念頭不停出現,第一個是數字「九」,是約翰生命中別具意義的數字,他出生於十月九日,和他第二個孩子西恩同一天生日;他母親住的地方門牌號碼是九號,我們相識的時候,我家門牌號碼是十八(一加八是九);朱利安出生的醫院地址是一百二十六號(合起來也是九);布萊恩艾普斯坦頭一次看披頭四的演出是當月的九號,雙方在九號簽下第一份唱片合約,約翰也在九號與洋子相遇,這個數字以各種形式在他的生命中出現,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約翰寫了三首關於九的歌:〈九○九之後〉、〈革命九號〉以及〈九號夢〉。他在九號過世,真是驚人的巧合。
另一個念頭是,約翰這十四年都活在死亡陰影裡。一九六六年,他收到一封聲稱是靈媒的來信,警告他將會在美國遭到槍殺,我們倆因此惶惶不安,披頭四當時正要去美國進行最後一次巡迴演唱,我們認為這封信所指的就是這趟美國行。在這之前,約翰發表了「披頭四比耶穌還受歡迎」的言論,引發極大的騷動,充滿威脅、憤怒的信件如雪片般飛來,靈媒的死亡預言從此常駐在約翰心底。
儘管十分不安,約翰還是去了美國,但也心不甘情不願地為他的言論公開道歉,直到他安全抵達家門,心上大石才得以放下。但約翰沒有忘了那個警告,他不時會回頭張望,似乎在等著殺手現身。他常把「總有一天,我會遭到槍殺」掛在嘴上,多年後預言竟然成真。
我們在上午十點左右抵達魯辛,我的心旋即往下一沉。我先生不可能瞞得住朱利安,一堆媒體已經把原本應該寂靜的小鎮擠得水洩不通,廣場上、還有通往我家和餐館的街道,全被大批記者占據。
我和茉將車子停在幾條街外,從後門偷溜進屋,屋前的人群完全沒發現我們。一進門就看到我先生焦躁不安、來回不停地踱步,我母親則從窗簾後頭偷偷向外探,七十七歲的她患有輕度的老年癡呆症,我讓她跟安琪同住在餐館樓上,外頭人群讓她困惑,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我看著我丈夫,心中的疑問不言而喻,朱利安知道了嗎?目光看著樓上朝我點了點頭。不久,朱利安衝下樓,我張開雙臂緊抱著他,青少年特有的瘦長身體癱在我的腿上,雙手環繞著我的脖子、肩膀,我們母子倆抱頭痛哭,約翰毫無道理就這麼死去,讓我們悲痛逾恆。
茉燒了水泡茶給大家喝,查克靜坐一旁,不知道該說什麼,或幫得上什麼忙。大家邊喝茶邊討論後續事宜,茉琳提議讓朱利安跟她一起回倫敦,但朱利安說:「媽,我想去紐約,我想去爸爸倒下的地方看看。」聽得我十分不安,但我知道他的心意。
茉琳和查克分別擁抱了我們然後離開。我和朱利安進到臥室撥電話給洋子,電話轉到她手裡,她希望朱利安能過去一趟,可安排當天下午飛往紐約的班機。我告訴她我擔心朱利安,但洋子擺明了不歡迎我跟朱利安一起去:「辛西亞,妳又不是我的老同學。」這話說得直接。我很清楚,公開的哀悼場面不會有前妻的分。
幾個小時後,我和我先生開車送朱利安前往曼徹斯特機場,這下躲不過媒體了。我們神情哀戚,圍在門口的人群紛紛向後退,我很感激沒有人上前騷擾我們。兩個小時的車程沒有人開口說話,我的情緒震盪得太厲害了,幾乎撐不住,但為了朱利安我必須堅強,後面還有一堆事情等著我處理。
到了機場,我目送他隨空服員上飛機,朱利安垂著肩膀,臉色慘白。我知道飛機上乘客手上報紙的頭條,全都是他父親的死訊,那一刻,我好希望追上他。進登機門的前一刻,朱利安回頭向我揮揮手,他是那麼年輕、令人揪心,我捨不得讓他獨自從我身邊離開。
回到威爾斯,大批媒體仍然駐紮在家門口,鎮上旅館全數客滿。幾年後,曾跟理察麥德利一起主持「今日早晨」的茱蒂芬尼根告訴我,當時還是年輕記者的她也在人群裡:「那時候我真的替妳難過,妳看起來是那樣的疲倦。」
當天稍晚的時候,有個記者說服我丈夫讓他進屋來把我給惹毛了,他聲稱正在寫一本關於約翰的書,我根本沒有如此人後來聲明的接受過專訪,身心俱疲的我哪有閒功夫接受訪問。當晚,我身心麻木就這麼倒在床上,疲倦到連一滴眼淚都擠不出來。
我睡得很淺,突然傳來巨響把我驚醒,聽起來像是炸彈爆炸。我尖叫著從床上翻了起來,穿了睡衣死命往外跑。跑到屋外一看,原來是煙囪頂端崩落把屋頂砸了個洞,直往朱利安閣樓的房間砸,無緣無故颳起強風讓我有不祥的感覺。感謝老天,還好朱利安不在家。
隔天,朱利安撥電話告訴我他平安抵達,他和洋子、西恩以及好幾個工作人員一起待在達科他大樓,外頭擠了上百個人,而西恩還不曉得約翰的死訊,洋子說時機到了才會告訴他,一屋子的人只能假裝若無其事。朱利安聽來十分疲倦,說約翰的助理佛來德西曼到機場接他,而且對他很好。聽到有人照顧我的兒子,我才稍微安了心。
在威爾斯的日子還要過下去,酒館不能關門,我們需要收入。現在正值旺季,要是少了我這個人手,我丈夫約翰與安琪是忙不過來的。酒館恢復營業,我一如往常打掃、做菜、招呼客人、照顧母親,日常瑣事塞滿我的生活,但有時候還是會晃神。我得強壓傷痛才能繼續度日,約翰的名字天天占據新聞頭條,他的歌曲在榜上不斷攀升,關於他的種種,那些我們共同的日子、分享過的一切,不斷在我腦海裡浮現。我收到許多慰問卡片與致哀的電報,有的是約翰的友人寄來的,更多的來自不知名的陌生人,只因他們喜愛約翰以及他的音樂。聖誕節即將來臨的前幾個星期,我陷入空前的絕望,兒子不在身旁,婚姻瀕臨破裂,無力感吞噬了我。我曾經愛得這麼久、令我深深狂戀的男人,怎麼就這樣離開人世了呢?他是那麼富有創造力、總是與眾不同,怎麼會被個瘋子輕易地奪去性命?而且,他的兩個兒子需要他,他怎麼忍心丟下孩子?
1一九八○年十二月初的某個下午,安琪和我在北威爾斯一間我們共同經營的小酒館裡打點聖誕節裝飾。天候陰濕寒冷,室內卻充滿了歡樂溫馨的過節氣氛。我們開了瓶葡萄酒,將聖誕樹的吊飾一一掛起,牆上滿是聖誕節的圖畫。我們十分開心,隨意開了個彩球,裡頭的玩具掉到地上,我彎腰拾起,是把小塑膠槍。這讓我打了個冷顫,在滿屋子金箔與紙環裝飾品當中,這把玩具槍顯得格外突兀。隔天我去了倫敦一趟,借住在我的朋友茉史達基那兒。聖誕節前夕是店裡的旺季,我根本抽不出空,但律師告訴我有些文件非要我的簽名不可。於是我搭上前往倫敦的火車,...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