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勒卡雷、半希區考克式,」作者近年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驚悚小說——《紐約時報》書評家角谷美智子
教書事業一帆風順、外型帥氣,還是個運動好手的佩利格林•邁克皮斯,在他30歲生日那年開始思索,他是否想要一輩子都當個教書匠?在決定一腳踢開學術圈、決定奔向自由生活之前,他的女友葛兒•柏金斯也必須下定決心,是否該放棄即將展開的律師事業,追隨佩利去天涯海角?
作
出決定之前,佩利邀請葛兒,利用他繼承來的一小筆遺產,在豔陽天飛往安地瓜來場網球假期。
本該操心兩人未來的度假旅遊,另一種「未來」卻不請自來:矮矮胖胖、輕微跛了一隻腳,與佩利截然相反俄羅斯富豪狄馬、度假島嶼的半個主人,同樣也是網球愛好者兼好手,在目睹佩利的高竿球技後盛情邀他打上一場;無法拒絕也難以抗拒與高手過招的佩利,進入狄馬的私人球場後,同時陷入狄馬與他的家人的包圍——死氣沉沉的大老婆、美豔神祕的大女兒、一對神情憂傷的小姊妹與兩個正值青春期的兒子,外加兩名保鑣組成的觀戰隊伍。
輸得心服口服的狄馬進一步邀請兩人到島上的別墅作客,但狄馬把佩利帶開、讓大老婆把葛兒帶開,開始隱密地向這位英國教師求援:狄馬是俄羅斯最大黑道企業的白手套,專門負責在全球各地洗錢,如今他的地位及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他想要帶全家人投奔英國、想要佩利為他居中牽線……
渴望「新人生」的佩利一下成了半個間諜,連葛兒也一起拖下水。
「儘管不是喬治‧史邁利,作者卻在《我輩叛徒》中創造了近年作品中少見的迷人、立體的角色;讀者之福是,勒卡雷先生把教條的、反帝、反西方的意識形態擱到一旁,反而把重點放在有血有肉的狄馬與佩利,以及兩名負責此專案的英國情報局官員赫克特與路克身上」《紐約時報》書評家角谷美智子如此評論道,「而路克就像是勒卡雷的另一位『完美的間諜』——一個不完全確定自己身分、卻急於歸屬到一個比他自己更大的東西裡頭,一個在家庭中不夠自在、唯有工作時才是他自己的男人……
《我輩叛徒》中真正天才和令人心驚肉跳的,就是赫克特與路克如何周旋在狄馬與英國情報部門的交易之間……其成果便是作者近年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驚悚小說。」
名人推薦
作家/評論家 楊照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我輩叛徒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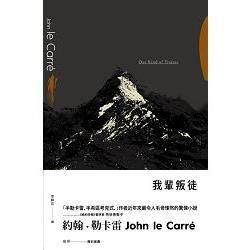 |
$ 284 ~ 324 | 我輩叛徒
作者:約翰‧勒卡雷 / 譯者:李靜宜 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15-06-03 語言:繁體/中文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我輩叛徒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生於一九三一,離開伯恩及牛津大學後,於冷戰期間於伊頓公學教書、服務於英國外交部,並在英國情報局任職的五年間寫下《死亡預約》、《上流謀殺》及他的第一本全球暢銷小說《冷戰諜魂》——被譽為二十世紀最了不起的小說之一。這三部小說塑造了喬治‧史邁利一角,他也出現在《鏡子戰爭》一書,也是「卡拉」三部曲:《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榮譽學生》與《史邁利人馬》的主角。過去五十五年他靠寫作維生,將自己的人生劃分為倫敦市與康瓦爾郡兩個時期。
約翰.勒卡雷最近出版的小說包括二○○八年《頭號要犯》(A Most Wanted Man)、二○一○年《我輩叛徒》(Our Kind of Traitor)以及二○一三年的《脆弱的真相》。
勒卡雷一生得獎無數,包括一九六五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的愛倫坡大獎、一九六四年獲得英國毛姆獎、James Tait Black紀念獎等,一九八八年更獲頒CWA終身成就獎(另分別在一九六三與七七年獲頒金匕首獎),以及義大利Malaparte Prize等等。至今已出版的二十三部作品,不僅受到全球各大媒體的矚目與讀者的歡迎,更因充滿戲劇元素與張力,已有十九部被改編為電影與電視劇。
譯者簡介
李靜宜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美國史丹福大學訪問學者。曾任職出版社與外交部。譯有《理查費曼》、《諾貝爾女科學家》、《牛頓打棒球》(牛頓)、《現代方舟二十五年》(大樹),《古烏伏手卷》、《法律悲劇》、《古典音樂一○一》、《直覺》、《奇想之年》(遠流)、《追風箏的孩子》、《史邁利的人馬》、《遠山的回音》(木馬)等。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生於一九三一,離開伯恩及牛津大學後,於冷戰期間於伊頓公學教書、服務於英國外交部,並在英國情報局任職的五年間寫下《死亡預約》、《上流謀殺》及他的第一本全球暢銷小說《冷戰諜魂》——被譽為二十世紀最了不起的小說之一。這三部小說塑造了喬治‧史邁利一角,他也出現在《鏡子戰爭》一書,也是「卡拉」三部曲:《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榮譽學生》與《史邁利人馬》的主角。過去五十五年他靠寫作維生,將自己的人生劃分為倫敦市與康瓦爾郡兩個時期。
約翰.勒卡雷最近出版的小說包括二○○八年《頭號要犯》(A Most Wanted Man)、二○一○年《我輩叛徒》(Our Kind of Traitor)以及二○一三年的《脆弱的真相》。
勒卡雷一生得獎無數,包括一九六五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的愛倫坡大獎、一九六四年獲得英國毛姆獎、James Tait Black紀念獎等,一九八八年更獲頒CWA終身成就獎(另分別在一九六三與七七年獲頒金匕首獎),以及義大利Malaparte Prize等等。至今已出版的二十三部作品,不僅受到全球各大媒體的矚目與讀者的歡迎,更因充滿戲劇元素與張力,已有十九部被改編為電影與電視劇。
譯者簡介
李靜宜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美國史丹福大學訪問學者。曾任職出版社與外交部。譯有《理查費曼》、《諾貝爾女科學家》、《牛頓打棒球》(牛頓)、《現代方舟二十五年》(大樹),《古烏伏手卷》、《法律悲劇》、《古典音樂一○一》、《直覺》、《奇想之年》(遠流)、《追風箏的孩子》、《史邁利的人馬》、《遠山的回音》(木馬)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