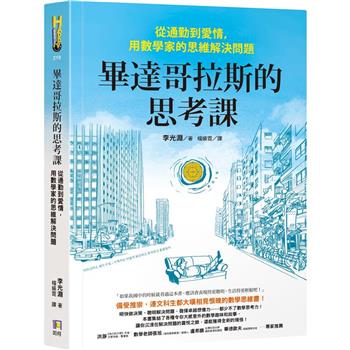序章 要求
車子攀爬在霧中的山路上。
FM的電波如我所預料,已經接收不到了。沒辦法,我只好將頻道切換成AM,雖然得聽著那像油炸食物般混雜雜音的廣播新聞。不過新聞的尾音偶爾也會消失,消失在我身後愉悅地微響著的氣冷式引擎聲中。車裡只有我一個人,我眼睛盯著前方,手握方向盤。
然而,當我想著這路途前方的某件事時,並不覺得不可思議,反而不知為何浮現一股懷念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會想起過去的事也是很自然的吧……我想,就算我已經可以駕輕就熟地單手解開女性背後的鈕扣,或者完全習慣了梳子掠過頭髮時那若有似無的抵抗感──也就是說,就算我已經是個成熟的紳士了,卻還是沒有辦法抵抗思念的心情。這也許是霧中山路所引發的作用吧!
當然,我是在出門工作的路上。適度而輕微的緊張感,像遍佈著細微紋路的銀箔紙般在我體內毫無偏差地均勻擴散。在工作途中的我看起來心情總是很不好,但我自己卻毫不自覺,甚至覺得自己很有活力,然而在旁人眼中,我看起來似乎很陰沉且心情惡劣。「從一早開始就這樣了,你為什麼那麼生氣啊?」這樣被說了好幾次之後,我才終於察覺到。人生中應該沒有比像這樣的忠告更珍貴的東西了吧!而我也只是瞬間擠出一個笑容回答:「沒啊,我沒有在生氣。」在我作出反應前那一點點延滯的時間裡所產生的精神效果,對我來說極為寶貴而且值得珍惜,要說有如沙漠中的綠洲也不為過。話說回來,我偶爾也會這麼問女性:「妳為什麼那麼生氣啊?」那幾乎都發生在深夜時分,而其所獲得的結果──得到一個笑容的機率,就連萬分之一都不到。這到底是為什麼呢?當然,一定是因為我不好,可是就算是我不好,要是其中有個人能微笑著對我說:「沒有,我沒有為了什麼在生氣。」這樣不是也很好嗎?
瀨在丸紅子就是唯一一個微笑著對我這麼說的女性。為什麼?因為那時她是真的在生氣。不過我當然也理解她為什麼會那麼做了,因為她就是那樣的女性,只是我已經想不起她為什麼而生氣。對自己不利的事就不會記得,這似乎是人腦組織中非常基本的功能,目的是為了自我防衛。因此,我只想起那明亮的光景,就是她那魅惑的笑容。至此,我才好不容易稍稍有了一點笑意,就像從一位令人懷念的朋友那邊寄來的信中得知他要結婚的消息一樣。
但是,我想努力地把它遺忘了。
美好的回憶,通常要趁還新鮮的時候迅速將它凍結起來,這樣它一定會在自己某天心情低落、非常痛苦還有即將死去之前發揮作用……不,我覺得以「發揮作用」這四個字來形容似乎和我想說的有些許細微的差異。而且我總覺得,像這樣打算為將來留下一些什麼的自己,似乎有點奇怪。到底事情的全貌是什麼呢?這下我又回想起過去,因而笑出口來。
引擎聲仍舊轟隆隆地追上我的思緒。當然,這是我的車子的聲音。車子奮力奔走在山坡路上,輪胎聲告訴我路面濕滑的情況。明明已經往上攀升一段路程了,卻還是沒有看到所在位置的高度標示。周圍瀰漫著白茫的空氣,車子應該已經被蒼鬱的森林所包圍了,但我卻沒辦法確認它的全貌。森林其中的某部分偶爾會顯現出來,就像透過碎裂的毛玻璃觀看一般。
從後方而來的大燈闖入那迷幻、孤寂的坡道。接著,我聽到低沉的引擎聲傳來,於是瞥了一眼照後鏡。是什麼時候被追上的呢?正後方有一輛車子緊追我著跑,雖然還保持安全距離,但仍與我非常貼近,讓我完全處於被追著跑的狀態。可惜我的金龜車並沒有配備一顆爆發力十足的引擎來克服這種狀況。在過了三個髮夾彎左右之後,我發現道路稍微變寬,於是將車子往左靠,拉下一半車窗把手伸出窗外,催促我後方的車子超車往前。
雖然我原本就覺得後面那輛車子的高度不高,但也沒想到那會是一輛紅色的法拉利。對方輕輕鳴了一聲喇叭,應該算是對讓車的我禮貌性地打個招呼吧!那低沉的引擎聲和圓形的尾燈隨即消失在霧中。
我從口袋裡拿出了香菸,用打火機點上火。此時的動作緩慢到連我自己都覺得厭惡,我想,我的祖先說不定是白熊。車窗維持打開的狀態,伴隨著最初的那口煙,我嘆了一口氣,那嘆息聲就跟我自己到目前為止的人生一樣長。接著,我腦中浮現從我的人生中擠出的潤滑油,於是將車子排進低檔,金龜車咔啦咔啦地發出乾澀的聲響,再度開始爬升。
這次的故事也許跟之前故事內容的旨趣完全相異,就好像一種進入動物園角落的昆蟲館或是蟲類館那樣的感覺。
先作個預告吧!以首要特徵(犯罪心理的部分)來說,偵探小說的犯罪原理中,應該沒有比這個案件的犯案手法更奇特的了,再者,表面上看起來也與之前的案件有所不同。
這次除了我保呂草潤平之外,平常會出現的那三個人並沒有登場,也就是說,這個案件是在瀨在丸紅子、小鳥遊練無和香具山紫子她們三人不知情的時候發生的,所以是根據我個人的觀察、蒐集情報所獲得的資料,再加上一如往常細微的安排來重現這個故事。雖然可以以第一人稱寫下這個故事,個人判斷也不會打斷到目前為止的故事流程,然而我還是想用以往慣用的手法(也就是所有的人,包含我,全都使用第三人稱的觀點)來描寫。使用慣用的手法就跟使用道具一樣,在不知不覺間已經用得很順手了,就先以這個理由當作藉口吧!
道具是一種奇特的東西,在使用它的時候並不會發現,然而當使用其他的東西時就會感覺到它的存在。在用過別的東西之後能再回頭使用自己習慣的道具,實在讓人覺得很舒適。在這層意義上,就暫時享受一下這一時的異樣感吧!
不只是道具,人的行為大多也是藉由種種非外顯的手法所支撐,而且那些手法是自然而然學習到,在不知不覺間建構出來,屬於自己的做法。那是無法替代的東西,通常在失去之後才會發現它的價值。
說起道具,讓我聯想到的是工具,特別是用來進行截斷或削切的各種小型工作用具。我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很喜歡這種東西。我是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喜歡這種東西,只記得要是有機會要大人買東西給我,我一定會拜託他們買工具,甚至不管什麼時候,我的腦中都有一張工具表,上頭寫著我想要的工具的先後順序。
好的道具會有一種讓人忘記它是道具的功能,那簡直就像是魔法一樣,讓人有一種錯覺,覺得使用它的人能力因此提升了。用到不好的道具時,人們就會察覺到正自己正在使用道具,並且發現因為道具不好,使得工作沒辦法順利進行。這個法則不論用在任何一種手法上都行得通,例如語言或規矩。更進一步說,用在健康或朋友,還有愛情或情人身上也都行得通。
有時,成就「人生」這個工作的道具就是個人的身體與頭腦,也就是說,我覺得我們的存在以及所有的一切都是道具。
雖然道具有可以選擇的也有不能選擇的,但至少能夠選擇的就應該去選擇,選擇一條對自己來說也許是最好的道路。另外,我們同時也會發現有我們無法選擇的道路,察覺到這點是很重要的。
我的一位老朋友會在這個故事中出現(雖然他應該不認為我是他的朋友),他是一個執著於一流的道具同時非常明理的人。我喜歡他,但這並非意味我對他懷抱著情感。光是觀察他,對我來說就很有意義,他的人生很值得玩味,這是我的理由,這和透過玻璃偷偷看著鬣蜥蜴的動機是一樣的。在某種意義上,他可以說具有強大的能力,讓人想去觀察他,而在另一種意義上,我無法不對那種能力抱著近乎尊敬的感情。總歸一句,就是因為如此,我才會想要進行偵探工作,才會去執行。
我的特質是決定下得太慢,行動得太快。我總是維持著這種步調,不論怎麼做我的行動都不可能比決定還要慢,所以只能說比起太早下決定而太慢執行的人來說,我是深深地受到神的眷顧吧!
可愛的是瀨在丸紅子。
在她面前我似乎變成一個正直的人,正直到幾乎只存在數學性的東西。如果我的存在是為了成為讓她使用的道具,那將是何等的幸福啊!
事後我跟她報告這件工作的成果。
於是紅子如此問我:「你確信你所完成的始終比你未完成的都還要有價值吧!」
「並不是這樣的。」我回答。
「是這樣嗎?」紅子微微地笑了起來。「我看到的是那樣。你對於自己的選擇好像很樂在其中。」
「嗯……這個嘛……也許吧!」
「不過,這玉有一點瑕庛。」紅子豎起一隻漂亮的手指。
「是什麼呢?」
「就是跟我說這件事呀!」紅子定定地凝視著我。「不能不說嗎?」
原來如此,我感到一陣疼痛,因為她說得沒錯。
那是事實,以前我就有自覺了。
是的……為什麼我會跟她說呢?像這樣,連寫下這故事也都是為了她。這不合理之處該怎麼解釋才好?
當然,我知道答案是什麼。
答案可以說是非常明確的。
但是……
我尊重她的忠告。
所以我想,在這裡……
就先別說了吧!
第一章 訪客
在每天的使用中,夜也漸漸地被切短了。
1保呂草潤平化名秋野秀和,造訪這座宅邸。
秋野的名片上所印的頭銜是「藝術品鑑定師」,這個跟保呂草原來的工作性質非常接近。藝術品的價值說到底幾乎都是一樣的,一個人如果不認同某件藝術品的價值,最後可能只是對著頂級的藝術品微笑,什麼都沒說就結束了。如果判定那件藝術品有價值,那麼之後的反應,也就是行動,就會依據那個人的職業是單純的藝術品鑑定師或是保呂草原來的職業而有若干的差異。換言之,對於那件藝術品的處置方式會分為軟性的或是硬性的。
若要詳細說明保呂草為什麼會以鑑定師的身分被招待至熊野御堂家的別墅,故事的篇幅應該會增加五倍左右吧!所以在這裡就不細述整個過程了。只是,至少這並不是偶然出現的結果,對於非常了解保呂草的人來說,應該很容易就可以想像得到。不過為了不了解他的人,也為了他的名譽,還是必須說明一下這並非偶然。一點點的時間和些微的投資還是必要的。這部(不?)全都和保呂草描繪的想像圖的結果相同。
保呂草這設想周全的性格好像是最近才開始的,小時候的他完全看不出有一絲一毫這樣的傾向,沒想到他會變成現在這樣,因為他是一個想到什麼就做什麼的人。有時候看著現在的自己,他會覺得很不可思議。是因為長大了、變成大人了,才變膽小了吧!他自己分析著。就像馬戲團的明星老了也只能演小丑,是一樣的道理。
保呂草策劃讓自己被招待到熊野御堂家的別墅作客的理由只有一個,只是為了實現一個願望──他想親自鑑賞某件藝術品。動機極為單純。他平常專門鑑賞或是蒐集畫作,而這件藝術品算是少數的一個例外。
「安潔拉•瑪奴伯(Angel Maneuver)」並不是一件畫作,它也被稱為「天空之閃電(Sky bolt)」或「飛翔之翼」,不過這件工藝品更適合被稱為「天使之演習(Angel Maneuver)」。如果將它實用化,它只能發揮短劍──也就是小刀的功能,若不論它的實用性,那麼它是一件藝術品,它的歷史比人的一生還要長一點,上面更點綴了可以說是禁欲性均整的精緻裝飾,特別是聽說上頭鑲了一顆名為「瑪絲嘉威之私語(mascovy murmur)」的巨大寶石。雖然看法因人而異,甚至也有人把安潔拉•瑪奴伯誤認為是那顆寶石的名字,然而像這樣物品本來就沒有可以還元它原有價值的替代品。保呂草相信,那是以人的雙手刻劃的時間的結晶。
在此將不特別敘述關於這件號稱市價數億日幣的藝術品的來歷,而關於它為什麼會在日本,也省略不作說明。
不管怎麼說,對保呂草潤平個人而言,那是一件讓他內心五味雜陳的物品,即使這件物品並非他專門收藏的東西,他對它仍十分執著。這對他來說是很少見的,他對於這樣的自己也覺得有趣。如果這件物品真的存在,他倒想要親眼看看它,就算是看一眼也好。
這個願望似乎終於能夠實現了。因此,自從上個禮拜下定決心之後,他的心情就非常好,一股些微的緊張感同時亦襲捲而來。辦大案子時的那股緊張氣氛對健康最有益了!至少,在這種狀態下死去的人應該不多。那就是所謂的生命力。工作帶來的緊張,對於人的生命來說就像毒品的效果一般。有好幾次,這種緊張氣氛都驅使他去做一些煩麻又消耗體力,甚至有危險的工作。如此看來,似乎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緊張的奴隷。
正在陽台抽菸的保呂草耳邊傳來了說話聲,他靜靜地靠到欄杆旁,偷偷看著樓下。他的房間在二樓,剛好有兩個人從他正下方的小徑穿越而過。他們大概是從森林裡散步回來的吧!其中一位戴著白色大帽子,帽子的直徑約六十公分左右。從服裝上很明顯可以看出那是一名女性。她察覺到保呂草的存在,抬頭往上看,宛然一笑,一個晴空萬里般的笑容。保呂草覺得那笑容好像似曾相識。另一個人則穿著白襯衫牛仔褲,一身和渡假勝地不太搭軋的普通穿著,臉上戴著一副眼鏡。說話的是戴著白色帽子的女性,從她漂亮的高亢嗓音中可以聽到「老師」這個的單字──也就是說,那位戴眼鏡的人是她的老師囉?
兩人走進磚牆裡便即刻消失了身影。時間是傍晚五點鐘。開車上來的時候山路還被濃霧包圍著,現在卻像夢一般變成晴天了。這該不會是在雲端上吧!空氣就像她剛才的笑容一樣的澄淨。
對了!他想起來了!
她的笑容跟瀨在丸紅子的笑容很相似。說那笑容充滿自信與博愛是有點誇張,不過那是個像人偶一樣柔順、完美的笑容。對一個陌生人抱持這樣的想法,對保呂草來說是很難得的。
山上氣溫相當低,保呂草原本擔心會下雪或是路面結冰,不過總算到達了。接下來就是要完美地完成工作,然後安全地下山。保呂草的腦袋裡只想著這個。
明明知道現在幾點,卻又看了一下時鐘。晚餐是六點半開始。這裡除了熊野御堂家的人還有數位訪客,剛剛那兩個人應該也是客人吧?用餐時也許又能見到她的笑容。保呂草享受著這意料之外的樂趣,慢慢地吐出一口煙。
2保呂草一下樓來到休息室,就看到可以眺望中庭的大玻璃窗附近擺放著可以容納七、八個人輕鬆休息的長沙發,而她就一個人坐在長沙發大約中間的位置。沙發椅的高度相當低,她那從柔軟的裙子下方露出的膝蓋彎曲成漂亮的銳角。保呂草莫名有股衝動想在胸前畫個十字。
「午安。」保呂草繞進馬蹄形的沙發內側,靠近她打了聲招呼。
「午安。」正在讀雜誌的她抬起頭來,看著保呂草微微一笑。「剛剛屋子裡的主人說,晚餐好像會晚點開始。」
「這樣子啊……」保呂草在離她約兩公尺的地方坐了下來。「那剛剛好。」
「為什麼呢?」她輕輕的側著頭問。
「沒有,只是想在這裡坐一下而已。」
「您該不會是開金龜車的那位吧?」
「咦?啊……嗯,是的!」保呂草被這突如期來的疑問嚇到,不過他馬上察覺到自己有點失態。她應該是在停車場看到他的車子了吧!
「那是很舊的車了。」
「是很有年代的東西呢!」她也點點頭。「雖然樣好像有點多事,不過……如果您覺得我說得不好,請您聽聽就算了。我是覺得車子引擎的狀況好像有點不好,如果有好好的保養的話應該輕而易舉就可以爬上那樣的坡道。」
「我是有保養,不過還是……」保呂草做出輕輕地點頭的樣子後開始思考。來這裡的路上,追過他的金龜車的只有法拉利,也就是說,她坐在那輛車上。這樣的話,開著那輛醒目的跑車的,應該就是被她稱為「老師」的那位花花公子了。保呂草再次觀察她的笑容,開始有點羨慕她那位有錢的男友。他已經很久沒有過這樣的感覺了,所以連他自己都覺得很驚訝。
「跟妳一起來的那位呢?」他問。
「啊!嗯……我想他馬上就會過來了。」她如此回答之後,調整了一下坐姿,身體稍微朝向保呂草這邊,雙手放在膝上重疊著。「承蒙熊野御堂先生邀請,我是西之園。」
「啊!不好意思,失禮了!初次見面,我叫做秋野。」
「秋野先生是吧!」她伸出一隻手的食指輕輕放在頭的一側。那裡大概是有錄音機的開關吧!
「我的工作是藝術品鑑定。不好意思,妳右手戴著的手錶如果是真品的話,沒有五百萬應該沒有辦法拿到手吧?」
「哎呀!」她微笑著,露出雪白的牙齒,完全沒看自己的手腕。「這是您的工作啊?感覺上這好像是您慣用的手法。」
「嗯,」保呂草聳聳肩。「這個嘛,證明它還是有效果的。」
「有什麼效果?」她噗嗤一笑。
「那個,是真品吧?」保呂草說。
「什麼?」她張著小巧又可愛的嘴。「為什麼?」
她眨了眨一雙大眼睛。她應該知道那個動作所造成的後果吧!
「如果那是膺品的話,妳不會不去注意別人是怎麼看它的。剛才我那樣說之後,妳完全沒有看自己的手錶一眼,光那份自信就足以證明它是真品。」
「哦,原來如此。」她用力地點頭,看起來更高興了。「這是你自創的方法嗎?」
「嗯,任何事物都適用於這種方法。」
「藝術品鑑定中哪一類是你的專長?」
「我經手任何東西,只要是美麗的東西。不過,算起來畫作還是比較多吧!」
「這麼說,這裡的『安潔拉•瑪奴伯』並不是你的專長囉?」
「不,美麗的東西是不分種類的,不論是藝術品或是有生命的東西。」
「有生命的東西?比如說熱帶魚之類的嗎?」
「我看起來像是這麼清心寡欲的人嗎?」
「你鑑定過嗎?」
「鑑定過什麼?」
「『安潔拉•瑪奴伯』。有人說它很美。」
「啊,沒有……」保呂草搖搖頭。「不過它確實是很美。」
「怎麼說?」
「名字很美。」
「好經典!」她又微微一笑,咬著嘴唇,只有一邊的嘴角出現酒窩。
「咦,妳說名字嗎?」
「不是,是你的答案好經典。」
「謝謝。不過,那個……西之園小姐,妳怎麼會到這裡來?」
「我是……嗯……為什麼呢?」她用天真的表情看著天花板。保呂草也不加思索地跟著她抬頭看著吊燈。「我跟熊野御堂先生是朋友。」
「這個簡潔的答案又出乎我預料之外了。哪位熊野御堂先生?」
「啊,當然是現在當家的熊野御堂讓先生。」
「熊野御堂讓先生,我記得他是……七十七歲?」
「是的,前陣子才剛過完大壽。」
「以朋友來說,那個……你們年紀不會差太多了嗎?」保呂草問。眼前的女性怎麼看都是個十幾二十歲的女性,和熊野御堂家主人的年齡至少差了半個世紀。
「不行嗎?」她側著頭瞇起雙眼,展現悠閒的神情。「而且,我覺得這樣的情勢很有趣。」
「情勢?」
「就像是河流遠方的對岸一樣,如果不下定決心用力跑是沒有辦法跳越過去的。」她的嘴角上揚。
「真是意義深遠的比喻啊!」
「是啊,我現在好像有點醉了呢!」
保呂草一直都沒有發現,窗邊的桌子上豎立著一瓶空的玻璃酒瓶。好像是免費的飲料。
「不過,秋野先生你也是個怪人。」
「嗯?哪裡怪?」
「一個藝術品鑑定家開著那樣的古董車來到這裡,這樣的事讓人覺得有點怪異。」
「怪異?為什麼?」
「一般來說,像你們這樣的人不都應該開著閃亮新穎的賓士車或BMW嗎?你們的工作不也算是一種聲譽的買賣嗎?不用亞曼尼、勞力士之類的行頭包裝自己,展示給別人看的話……」
「嗯……」保呂草點點頭。
「不是嗎?開金龜車不會對你的工作造成妨礙嗎?」
「嗯,的確是有那種需要讓自己稱頭點的場合。在那種場合上我會好好穿戴適當的服飾,不過我想這裡應該沒關係,所以就隨便弄個便宜的行頭來了。不過,說起車子,我還真的很喜歡那輛車。」
「嗯,很經典。」
「嗯?金龜車嗎?」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扭曲小屋的利鈍-瀨在丸紅子之v系列08的圖書 |
 |
$ 198 ~ 220 | 扭曲小屋的利鈍──瀨在丸紅子之V系列08
作者:森博嗣(MORI Hiroshi) / 譯者:陳慧如 出版社:尖端 出版日期:2008-04-17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08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扭曲小屋的利鈍-瀨在丸紅子之V系列08
【媒體推薦】 日本達文西雜誌連續數年獲選「最受歡迎的男作家」TOP3 西之園萌繪登場!達‧文西雜誌強力推薦。 【內容簡介】 在「梅比斯環帶」構造的扭轉之屋中,沉睡著一件祕寶「安潔拉.瑪奴伯」。保呂草潤平,還有西之園萌繪受邀前往觀賞。在呈密室狀態的建築物內部,發現一具屍體,而寶物也消失了──更驚人的是,在完美的密室中,出現了第二具屍體! 本集將用前所未聞的手法,指出犯人是誰── 沒有正反之分的無限循環,隱藏著森式推理的驚人伏筆! 【作者簡介】 森博嗣(Mori HIROSH
章節試閱
序章 要求車子攀爬在霧中的山路上。FM的電波如我所預料,已經接收不到了。沒辦法,我只好將頻道切換成AM,雖然得聽著那像油炸食物般混雜雜音的廣播新聞。不過新聞的尾音偶爾也會消失,消失在我身後愉悅地微響著的氣冷式引擎聲中。車裡只有我一個人,我眼睛盯著前方,手握方向盤。然而,當我想著這路途前方的某件事時,並不覺得不可思議,反而不知為何浮現一股懷念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會想起過去的事也是很自然的吧……我想,就算我已經可以駕輕就熟地單手解開女性背後的鈕扣,或者完全習慣了梳子掠過頭髮時那若有似無的抵抗感──也...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森博嗣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08-04-16 ISBN/ISSN:978957103819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8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日本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