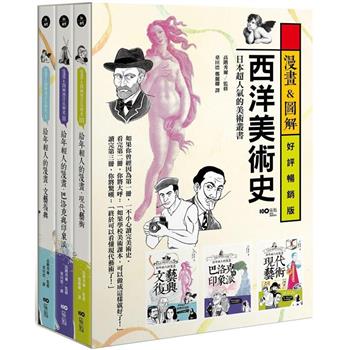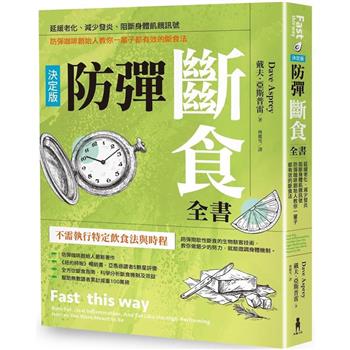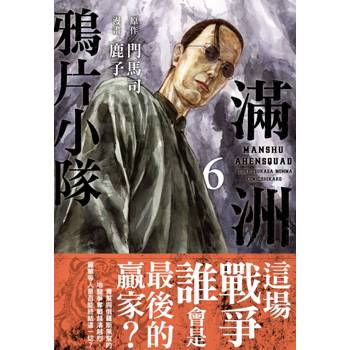序
文學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的東方論析
——序荒林的《文學的女性主義》
朱壽桐
女性主義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具有特定的歷史地位和文化地位。世界文明的每個階段,都可能敏感於並專注於性別差異、性別權力和女性解放之類的問題,特別是走出了宗教傳統的近代啟蒙主義之後,思想界、文化界都會格外重視女性和性別問題的思考,於是《太太學堂》之類的啟蒙主義文學作品產生了超越國界和超越時代的文化影響。
女性主義在社會學意義上往往包含著天然的革命性。人類文明進入到成熟階段以後,性別角色和性別地位就已經作為社會秩序的必然組成部分得到了較為穩固的定位,這樣的定位在東西方主流文明的語境下遙相吻合:從女性的家庭角色以及社會生活角色的角度看,東西方的文明秩序竟然如此相通,如此同步,實在匪夷所思。聯想到當初東西方先哲都曾從各種角度對女性發表較為相似的歧視性的文明觀念,如西方宗教界曾討論過女性有無靈魂的問題,中國的孔夫子發表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神論,這些在今天看來非常奇葩的觀念,確曾代表了東西方文明某些階段較為普遍或較為流行的女性觀。不必驚異於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在女性認知和女性評價方面曾經如此相似,倒是應該驚異於東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和文化進程中,何以對女性的態度是如此相像並如此同步。這種對女性的歧視性認知同樣成為腐朽觀念的代表在東西方世界遭到了批判與淘洗,不過因為這樣的批判和淘洗的徹底性往往需要藉助近代啟蒙主義和近代革命,而近代啟蒙主義和近代革命,東西方並不同步,其酷烈、徹底的程度也有較大的區域性差異、民族性差異和時代性差異,因而女性解放、性別平等之類的社會問題的關注與解決,在步驟與程度上,東西方文明拉開了距離。這距離又不是簡單同步的:女性解放在西方世界並未經過太多突變性的革命,而是處在近代文明的漸變過程之中發生的社會文化更新,因而它的歷史較為漫長,其徹底性也並不明顯。直至現在,西方女性出嫁以後仍然習慣於在自己的姓氏前冠以夫姓,這樣的情形在中國的主流社會則完全不必,可見女性解放、女性獨立的革命性程度在中國要進行得更為深切。
這實際上說明,在中國,女性解放的社會運作和文化運作更為猛烈,其結果也較為徹底。從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景幕上,女性解放、女性獨立等等社會話題,曾一度作為重大的時代命題和先鋒課題,被歸併到個性主義、民主自由的政治話題中展開,被賦予特別嚴重的時代感和使命感。這樣的社會運作伴隨著民主自由觀念的深入,被投入實際的社會革命實踐之中,於是同男性的剪辮子運作幾乎同步,女性世界則開始出現了放腳潮。經過歷次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和文化革命,中國女性的經濟權、人權、參政權等等已經得到了法律和政策的保障,甚至也得到了社會習慣的承認。魯迅當年所論述,婦女必須爭取到經濟權,才能夠真正解放自己,這往往比爭取到參政權需要付出更沉重的代價,道理非常清楚,論述也很深刻,但時代的局限也很明顯。事實上,女性的參政權固然已獲得,每個人有一張選票的時候,女性同樣可以獲得屬她的那一張,但這票有時不過是印製的時候加印的部分;女性的經濟權的確很難爭取,然後並不意味著很難獲得;一場革命完全可以賦予婦女相當的經濟權利,包括各種形式的經濟分配權。這樣的情形在魯迅活著的那個年代就已經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並且形成某種流行的態勢。但中國的婦女問題,中國社會的女性難題,是否真的就此解決了?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是在女性不僅參政,而且有可能當政的中國社會的各個區塊,女性作為輔助性別,作為第二性或作為弱勢性別的文化定位並沒有消除。深徹到包括女性自身在內的中國人心理世界的男權意識、男尊意識仍然處於支配地位。至今,相當高層次的人才的退休年齡還在執行不同的性別政策,女性的家庭角色、社會角色實際上都有一種習慣性的定位,這種定位在許多男性乃至女性的心目中都堅如磐石般地一如既往。參政權、經濟權解決以後,性別解放的路途依然漫長,只不過,這時候性別問題包括女性解放問題不再呈現在法權制度方面,而是深深地沉潛在社會文化的心理層面。
社會文化心理層面的性別話題似乎是永恆的。即便是在許多地方女子已經掌握了家庭的財政權力,男子已經爽快利落地成了名副其實的甩手掌櫃,他們除了暗自留一些私房錢而外,幾乎所有的收入都交給了家裏的“一把手”——老婆大人,可也還是有女子抱怨,其實這是讓家累和沉重瑣碎的生活壓力更加緊密地套在女性的頭上,男子獲得了解放與瀟灑;作為女子,也希望將自己其實是累贅的家務總管的差事交出去,讓自己獲得解放與瀟灑。即便是男子將操持家務的負擔全都承擔起來,如在經濟發達文明程度高的上海等地,男人繫上圍裙上鍋台的事情已經相當普遍,“上海男人”作為含義複雜的社會指稱和文化指稱已經成為專用名詞,可女子作為被保護、被呵護進而被弱勢地對待的地位反而更為突出,只不過是在一種當代文明的背景下被突出罷了。無論在事實層面上女子如何受到男子的尊重和愛護,但其作為“第二性”甚至作為弱勢性別的社會定性情形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只有到了社會主義文明階段,到了“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價值理念時期,女子作為弱勢性別群體的定位才可能被徹底改變。
由上可知,女子與男子在現代社會中的真實關係其實並未得到徹底改變,女子作為“第二性”的社會定位也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但另一方面,女子與男子在社會意義上的性別差異、性別矛盾和性別對立也沒有引起人們想像中的激化與極端化,一切的差異都在可識別的意義上存在,一切的矛盾都在可調和的意義上展開,一切的對立也都在可融合的意義上消解。女性的美麗的笑容在正常的社會生活中依然像美麗的鮮花一樣迎風綻放,正像男性的雄壯的身影在正常的社會中依然像雄壯的山石一樣昂然矗立,這樣的社會景象清晰地表明,性別差異、性別矛盾和性別對立的命題在現代文明社會其實都不可能真正成為時代發展的陰影。
但社會文明永遠需要一種批評的話題,社會文化的爭辯需要一種想像的對立,女性與性別差異的話題被歷史地選擇為這樣的批評話題與文明論辯的話題,於是,女性主義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成了一種文化的話語,甚至成了一種批評的話語,它反映著一定意義上的社會現實,但更確切地說是社會現實的文化反映而已。只要稍微關注一下就能發現,相當多的後現代話題都不過是社會現實問題的一種文化反映,而並不是社會現實本身。例如後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等等,都只是社會現實問題的某種文化反映,是一種文化的話語體現。與此相似,女性主義在當代的不斷發酵,其實不是社會現實問題的暴露甚至極端化,而是當代文化話語的一種呈現。女性主義話題在啟蒙主義時代、現代主義時代都曾經是核心話題,到了後現代主義時代依然是中心話題,但這時候它更多地體現為文化話語的特性,而不是迫切的社會現實話語的特性。
當女性主義作為文化話語出現在文化領域的時候,它就獲得了進入意識形態的某種資格,於是在西方的學術文化界,女性主義被一波又一波的文化運作催逼上了意識形態的軌道,在相當意義上被渲染成偏激的、敏感的話題,甚至被賦予某種革命性的素質,從而在遠離了社會現實、人生現實的意義上演繹成極端性的文化話語和文化命題。的確,在女性主義被推向極端化的現代社會,女性和男性的性別矛盾、性別對立其實體現得相當溫和、沉潛以及委婉,而這樣的溫和、沉潛與委婉卻在言論世界被渲染得非常尖銳,甚至通向某種觀念的危機。
這樣的危機在東方世界,在中華文化圈同樣存在,只不過更明顯地存在於文學描述之中,存在於被虛擬性地展現的文學世界,這就是荒林所刻畫的文學的女性主義。如果說女性主義在西方世界被置於文化的極端性、危機性的緊張話語層面,在東方世界特別是在中華文化語境下,它則更多地被納入文學文化的想像之中,呈現出文學的虛擬性和想像性的特徵。啟蒙主義話語時代,包括魯迅等偉大的啟蒙主義者都深深地涉入其中,女性主義話題被文學所包圍,所呈現,易卜生主義、“娜拉”現象,包括魯迅所刻畫的“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那個勇毅的女子子君,也包括那個可憐的祥林嫂,以及葉聖陶筆下的《這也是一個人》的那個女人,都是啟蒙意義上的文學形象。現代主義意義上的文學的女性主義,其代表人物當然是丁玲筆下的那個閃耀著時代光芒的莎菲,那個以反抗的意氣向男性世界堅決地然而又是變態地宣戰的現代女性的典型。後現代主義在中華文化語境下展現得較為委婉和沉潛,但女性主義的文學展示仍然是那麼鮮明而堅毅。這些都在荒林的學術描述中有著縝密而精細的展現,這樣的展現成就了荒林學術分析的特性和優勢,成為女性主義學術呈現熱潮中的富有獨特性的成就。
女性主義在西方世界是一種社會文化運動,雖然與大眾現實社會和現實人生依然相對脫節,但作為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的熱點話題,對知識生產產生重要影響,在意識形態意義上甚至釀成了革命性、顛覆性的時代話語,這就是弗吉尼亞·伍爾芙( Virginia Woolf)和西蒙娜·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出現的意義。她們提出的諸如“男性社會合謀論”和“人造女性論”等著名論點,都不再具有現實的社會針對性,而更多的是一種文化表述和文化深言的需要,也體現著理論闡述的快感和理論表述的深刻性和震撼力。當現實社會和現實人生早已經超越了奧蘭普·德·古熱( Olympe de Gouges)發表《女權宣言》時的那種男女政治上、法律上不平等的狀況之後,女性主義實際上在理論意義上的成就遠遠超過其實際生活的批判意義。中華文化語境下的女性主義從來沒有在理論意義上與西方女性主義爭奇鬥艶的意識,甚至也很難與之形成對話關係,但女性主義在東方世界和大中華語境下的文學展現,確是東方女性主義特別是中華女性主義話語的重要特徵,也是中華文化對於世界女性主義文明話語所做出的一個重要貢獻。
文學的女性主義作為學術概念和文化概念,無疑是一種創新,也是對大中華語境下的女性主義思潮和文化形態的一種準確的描述。這一概念的提出顯然受到郁達夫關於文學的無政府主義一說的影響,郁達夫在《自我狂者須的兒納》一文(發表於《創造周報》 1923 年第 6 號)指出,施蒂納的無政府主義是一種文學的無政府主義,有別於政治上的乃至思想文化上的無政府主義。其實,大中華語境下的文學的女性主義,也有別於政治理論和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女性主義,也有別於社會運動乃至文化運作意義上的女性主義,而是一種在想像和虛構意義上的女性主義,是一種典型的文化的審美判斷意義上的女性主義。文學女性主義往往在文學想像的意義上將女性話題推向極端,推向明顯的危機感和偏激的理念境界,進而通過文學表現的手段將女性主義命題引向深刻和強烈的文學展現。典型的例子莫如李昂《殺夫》等一系列的創作。這類文學的女性主義具有如此明顯的東方特性和中國特色:第一,文學的女性主義都是在理念意態上展開的,因而不應該理解為現實主義的女性文學;它與現實社會和現實人生展現的性別差異、性別矛盾和性別對立並無直接的對應與聯繫,因此,這是一種典型的文學文化意義上的女性主義。第二,文學的女性主義往往不會基於氾濫的、偏激的乃至極端的女性主義政治、社會和文化理念,而是基於女性問題的東方經驗和中國體驗,意味著中華文化語境中女性主義思想成果的集中體現,是漢語文學世界對世界女性主義文明做出的獨特的貢獻。
文學的女性主義體現出大中華文化語境中的女性主義思潮的特性,其實也是東方世界女性主義含蓄、曲折地進行文化呈現的基本形態。女性主義在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合謀中已經走向極端、偏激並充滿危機感,這樣的極端、偏激和危機感在西方的理論框架中得到了觀念的強化,而在東方語境和大中華語境中卻往往很難得到這樣的強化,甚至也不會得到相應的闡解,於是,女性主義理論在這樣的語境下顯得較為柔弱、陰晦。但在文學這一虛擬世界中,女性主義得到了補償性的表現,正如李昂等作家的創作所體現的那樣,在文學想像和虛構表現的意義上,女性主義也可以以極端、偏激和充滿危機感的性狀出現在大中華的文化語境中。
當然,由於道德和文化的制約,不同地區的文學的女性主義具有不同的表現形態和表現程度。大中華地區無疑以台灣、香港的文學創作在虛擬性地表現女性主義的極端、偏激和危機感方面較為強烈,而在內地和澳門體現得較為柔婉。這樣的差異凸現出文學女性主義的地區性的文化特性,但從總體上看,大中華語境下在文學想像的意義上展現女性主義的前衛性,應該是大中華文化的重要特徵。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荒林的研究必須在大中華文化語境的全貌觀照下展開,這也是這部論著必須體現這樣的空域廣度的重要原因:只有大中華語境的完整空域的廣度才能透視出文學女性主義的思想深度。荒林在這部論著中出色地完成了大中華地區文學女性主義的空域廣度的論析,同時也達到了其所指向的文學女性主義的思想的深刻性的揭示。因而,這是一部有思想創新和學術創新的論著,它的創新與相對世界性、地域性和時代性的女性主義的準確把握和獨到表述,其學術思維的開合度及其在學術方法上的啟示性遠遠超越於它所屬的女性主義研究和女性主義文學研究自身。

 共
共  現代標準漢語,亦稱現代漢語、標準漢語、華語,或逕稱為中文,是現代漢語之標準語與通用語。它以北京官話為基礎音、官話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與書面文體。其廣泛通行於華人地區,但在各地有不同標準與稱呼,依通行地區分為三套標準: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普通話」,中華民國為「國語」,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為「華語」。
現代標準漢語,亦稱現代漢語、標準漢語、華語,或逕稱為中文,是現代漢語之標準語與通用語。它以北京官話為基礎音、官話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與書面文體。其廣泛通行於華人地區,但在各地有不同標準與稱呼,依通行地區分為三套標準: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普通話」,中華民國為「國語」,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為「華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