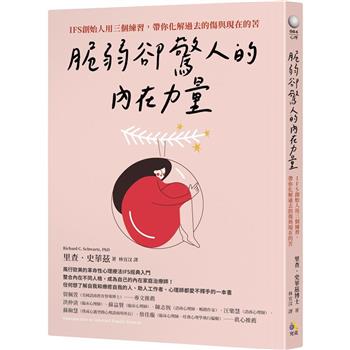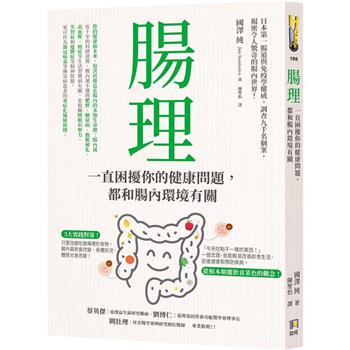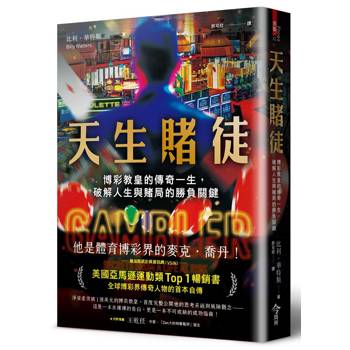王聰威、郝譽翔 知名小說家 聯合推薦
厄普代克(John Updike)專文導讀
納博科夫在美國名校講授歐洲文學,流傳逾半世紀講稿,精采也經典!
「在這門課中,我試圖揭示這些精采玩偶─文學名著─的構造。我試圖把你們造就成優秀的讀者。」 -------- 納博科夫
「納博科夫講稿的講解,讓作品中那些原來並未顯示出深長意味和特殊價值的文字,就像突然暴露在陽光之下的珍珠,驟然發出絢麗的光彩!」 (摘自譯序 /申慧輝)
*納博科夫:「擁抱全部細節吧,那些不平凡的細
作者簡介: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 , 1899-1977),俄裔美國小說家、文學批評家。1899年生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從小學習英、法、俄語。蘇維埃成立後,納博科夫一家被迫離開俄國,開始流亡生涯;先到倫敦,後移居柏林。1922年完成英國劍橋大學學業。1923至1940年間,納博科夫陸續發表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戲劇、新詩等創作,並將俄國文學翻譯成英文,被視為俄國流亡世代中最優秀的作家之一。
納博科夫1940年被希特勒趕出歐洲,偕妻兒繼續在美國流亡並開始用英
章節試閱
1
珍•奧斯汀(JANE AUSTEN, 1775-1817)
《曼斯費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 1814)
《曼斯費爾德莊園》寫於漢普郡的肖頓。寫作始於一八一一年二月,於一八一三年六月後完成;也就是說,珍•奧斯汀用了二十八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一部共四十八章,約十六萬字的小說。小說於一八一四年分三卷出版(與司各特的《威弗利》(Waverley)和拜倫的《海盜》(Corsair)同年出版)。作品分三部分出版是當時傳統的出版方式,但是實際上該書的三部分突出了小說的結構,即其類似戲劇的形式,這是一齣反映社會風俗人情、道德是非曲直、人物喜怒哀樂的三幕喜劇,各幕分別由十八、十三及十七個章節組成。
我很反對將內容與形式區分對待,把傳統的情節結構同主題傾向混為一談。在我們深入到作品內部盡情欣賞研究(而不是走馬看花地看上一遍)之前,我只需要說明一點,即《曼斯費爾德莊園》的表面情節是兩個鄉村紳士家庭之間的感情糾葛。一家是湯瑪斯•伯特倫爵士及其妻子,以及他們身材高大、體格健壯的子女湯姆、艾德蒙、瑪麗亞、朱麗亞,還有他們溫文爾雅的外甥女范妮•普賴斯。范妮是作者寵愛的人物,而且故事是通過她的眼光篩選組織的。范妮不僅是個一文不名的外甥女,也是個性格溫和的被監護人(注意,她母親婚前的姓是沃德)和養女。這種人物在十八、十九世紀小說裡是最常見的,小說家容易選擇這樣一個被監護人的角色來做文章是有種種原因的。作為生活在一個陌生且不冷不熱的家庭氛圍中的外姓人,她的地位賦予她一種常常牽動人們惻隱之心的特性,此其一;這個小小的外來人也很容易同主人家的兒子浪漫一番,明顯的衝突便由此產生,此其二;作為這個家庭日常生活的超然觀察者與參加者的雙重身分,又使她很方便成為作者的代言人,此其三。因此,這樣一個性格溫和的被監護人,不僅只出現在女作家的筆下,在狄更斯、杜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及許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同樣存在。這些文靜的少女們所具有的一種羞澀的美,在謙卑、自我隱沒的面紗下更顯出動人的光彩,它在美德方面的威力終於戰勝生活的機遇時越發光彩動人。這些文靜的少女的典型自然當屬灰姑娘。寄人籬下,無援無助,無親無友,受冷落,被遺忘,後來卻與男主角成婚。
《曼斯費爾德莊園》是一個神話故事,不過,所有的小說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神話。乍看之下,珍•奧斯汀的手法和題材也許會顯得過時、做作、不真實。但這是水準差的讀者不得不接受的錯覺,高水準的讀者知道,就書而言,從中尋求真實的生活、真實的人物,以及諸如此類的真實是毫無意義的。一本書中,或人或物或環境的真實,完全取決於該書自成一體的那個天地。一個善於創新的作者總是創造一個充滿新意的天地,如果某個人物或某個事件與那個天地的格局相吻合,我們就會驚喜地體驗到藝術真實的快感,不管這個人物或事件一旦被搬到書評作者、劣等文人筆下的「真實生活」中,會顯得多麼不真實。對於一個天才的作家來說,所謂的真實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須創造一個真實以及它的必然後果。我們只有接受了《曼斯費爾德莊園》的習俗、規則及其中經作者之手編造的種種有趣事件,才能充分欣賞領略到作品的魅力。曼斯費爾德莊園是根本不存在的,那兒的人們也是不曾存在的。
奧斯汀小姐的作品,並不像這一系列課程中討論的另外幾本小說那樣,稱得上極為生動的傑作。像《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這樣的小說,是作者的生花妙筆控制下,提供讀者快樂的炸彈。而《曼斯費爾德莊園》則出自於一位小姐的纖手,是一個孩子的遊戲。不過,從那個針線筐裡誕生的是一件精美的刺繡藝術品,而那個孩子身上煥發著一絲奇妙的才華。
「大約三十年前……」小說是這樣開始的。奧斯汀小姐寫書的時間是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三年間,所以小說開篇提到的「三十年前」就是指一七八一年了。那麼就是大約在一七八一年的時候,「亨廷頓的瑪麗亞•沃德小姐僅靠七千英鎊〔作嫁妝〕,就幸運地贏得了北安普敦郡曼斯費爾德莊園的湯瑪斯•伯特倫爵士的鍾情……」這裡,中產階級對此事所表現出的興奮與興趣(「幸運地贏得了」)非常輕鬆愉快地轉達給了讀者,同時也為下面幾頁所要敘述的事態發展,添加了一種適宜的氣氛,下面幾頁涉及了浪漫式愛情及宗教事件,而有關錢財方面的事情,則帶著忸怩的天真占居支配地位。在這開首的幾頁中,每一句話都簡潔明瞭,恰如其分。
2
查爾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荒涼山莊》(Bleak House, 1852-1853)
我們現在可以和狄更斯打交道了,我們現在可以擁抱狄更斯了,我們現在可以享受狄更斯的潤澤了。討論珍•奧斯汀的時候,我們不得不費點神,走到客廳中太太小姐們的身邊去。而談論狄更斯時,我們仍坐在桌邊,喝著褐色的葡萄酒。我們不得不找一條通向奧斯汀和《曼斯費爾德莊園》的小徑,我以為我們也確實找到了路,對她那些纖巧的花樣,對那些臥在棉花墊中的細瓷搜集品,我們的確感到有點意思。但那不是油然而生的興趣,我們必須進入某種情緒,必須用一定的方式凝神觀察。我個人並不喜歡瓷器和小玩藝兒,但我常常強迫自己用行家的眼光去審視一件小而晶瑩的瓷器珍品,從中倒也嘗到過內行人似的欣悅之情。不要忘記有些人終身研究奧斯汀,他們關在象牙塔中把一生奉獻給了奧斯汀。我深信有些讀者比我更懂得奧斯汀,然而,我力圖做到客觀。我的客觀方法尤指用稜鏡分析文化──從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的清洌泉源中流出、被奧斯汀筆下的紳士淑女們所汲取的文化。我們還追隨著奧斯汀那有點像蜘蛛結網似的造文:請回憶一下《曼斯費爾德莊園》那張網,排戲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功用。
到了狄更斯這裡,我們可以放開手腳,無羈無束。在我看來,珍•奧斯汀的小說
…………
我們說到一個故事的形式時,一、指的是什麼呢?指結構,亦即某個故事的發展,為什麼故事沿著這條線或那條線寫下去;二、也指人物的選擇,作者對他筆下人物的利用;三、指人物之間的互相作用,各種人物主題,主題線及諸線的交叉;四、指作者牽著故事變化多端地進展時所期望產生的這樣那樣的直接或間接的效果;五、也指製造效果和印象。簡言之,我們指經過精心設計的藝術作品的樣式,這就是結構。
形式的另一個方面是風格,風格指結構如何起作用;二指作者的手法,他的癖好,各種專用的技巧;三如果他的風格很生動,那麼他用了什麼樣的比喻,有哪些形象的描繪,又是如何著手的;四如果他用了比喻,那麼他又是如何使用隱喻、明喻這些修辭手法,加以變幻,並把它們結合起來的。風格的功效是通向文學的關鍵,是叩開狄更斯、果戈理、福樓拜、托爾斯泰和一切大師的作品之門的萬能鑰匙。
形式(結構+風格)=題材:為什麼寫+怎樣寫=寫了什麼。
在狄更斯的風格中,我們首先注意到他善於運用強烈訴諸官能感覺的比喻,有喚起逼真感覺的藝術功力。
一用修辭或非修辭手段喚起逼真的感覺
鮮明的比喻並非接連不斷使用的,它們的出現間歇有致,而其間又聚積了許多細膩詳盡的描繪。狄更斯想通過談話或思考把一些情況或消息告訴讀者的時候,往往並不使用顯眼的比喻。但書中有一些精采的段落,如描寫大法官庭的一段,就將濃霧主題寫神了:「話說在這樣的一個下午,大法官閣下應當高坐在此──如他此刻一樣── 頭上罩著霧濛濛的光圈,軟軟地圍在紅桌布和紅帷幔之間,邊聽大個子、大鬍子、細嗓子的律師沒完沒了地念案情摘要,邊把他的心思都集中到屋頂上去,他盯著那扇天窗,然而除了霧什麼也看不見。」
「曾得到許諾說在莊迪斯案了結時,會得到一匹新的搖木馬的年幼原告,或被告,已長大成人,獲得了一匹真馬,騎上了快步跑到另一個世界去了。」兩位受監護人由法庭指定與他們的親戚同住。第一章中自然界的霧和人世間的霧奇妙地混合,凝聚成團,所以這三言兩語的交代也像充了氣似的。主要人物(兩位受監護人和莊迪斯)被引進故事了,但此刻人們尚不知他們的姓名,也沒留下有血有肉的印象。他們彷彿從霧中冒出來,在又一次被霧淹沒之際,作者把他們拽了出來,這一章結束了。
3
居斯塔夫•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
《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1856)
現在我們來欣賞另一部名作,也是一個童話故事。我們賞析的這一組童話故事中,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是最富浪漫色彩的一篇。從文體上講,這部小說以散文擔當了詩歌的職責。
小孩子聽你讀故事的時候往往會問,這故事是真的嗎?如果不是真的,他會纏著要你講一個真故事。我們讀書的時候最好不要採取孩童般執拗的態度。當然,如果有人告訴你,史密斯先生看見一個綠臉人駕著藍色飛碟嗖地從空中掠過,你一定會問;那是真的嗎?因為這件事如果是真的,必會以某種方式對你的生活發生影響,必會產生一系列具體的後果。但是,對一首詩或是一部小說,請不要追究它是否真實,我們不要自欺欺人。請記住,文學沒有任何實用價值。只有一種情況例外,那就是:如果有人不想幹別的,偏偏要當開文學課的教授。世間從未有過愛瑪•包法利這個女人,小說《包法利夫人》卻將萬古流芳。一本書的生命遠遠超過一個女子的壽命。
這部小說涉及通姦,書中某些情節和話語,使庸俗淺陋卻又假充正經的拿破崙第三政府大感震驚。事實上,這部小說的確曾被當作淫書拿到法庭上受審。多麼離奇,好像一件藝術品也能誨淫似的。好在福樓拜打贏了官司,這件事發生在整整一百年以前。今天,在我們生活的時代……我還是不要扯得太遠了。
我們對《包法利夫人》的分析應當與福樓拜本人的創作意圖相符──從下面幾個方面進行討論:小說的結構(他本人稱作動作)、主題線索、風格、意境、人物。小說共有三十五章,每章長度約為十頁,全書分上中下三卷。三卷中故事發生的地點分別為盧昂、道特;永鎮;永鎮、盧昂、永鎮。除了盧昂,所有地名都是虛構的,盧昂是法國北部一座有大教堂的城市。
小說裡的故事主要發生在十九世紀三四○年代,路易•菲利普國王當政時期(一八三○─一八四八)。第一章始於一八二七年冬天。在小說的「尾聲」部分,某些人物的故事已經進展到一八五六年拿破崙第三統治時期,實際上福樓拜這部小說就是那時完成的。作者於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九日在盧昂附近的克瓦塞動手寫《包法利夫人》,一八五六年四月完稿,六月付梓,同年年底開始在《巴黎雜誌》上連載。在盧昂北邊一百英里處的布洛涅,查爾斯•狄更斯於一八五三年夏天寫完《荒涼山莊》,當時福樓拜剛寫到《包法利夫人》第二卷;此前一年,在俄國,果戈理去世了,托爾斯泰則已經發表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童年》(Childhood)。
三種因素造就一個人:遺傳因素、環境因素,還有未知因素X。這三種因素相比,環境因素的影響力遠遠弱於另兩種因素,而未知因素X的力量則大大超過其他因素。談到小說中的各種人物,當然是作者在控制、指揮和運用這三種因素。像包法利夫人這個人物一樣,包法利夫人所生活的社會環境也是福樓拜精心創造出來的。所以,說福樓拜式的社會影響了福樓拜式的人物,就是在作無意義的循環論證。小說中的每件事都發生在福樓拜的頭腦中,不管最初那微小的動因是什麼,也不管當時法國的社會環境或是福樓拜心目中的法國社會環境究竟如何。基於這一看法,我反對人們在女主角愛瑪•包法利受到客觀社會環境影響的論題上糾纏不休。福樓拜的小說表現的是人類命運的精妙的微積分,不是社會環境影響的加減乘除。
據說《包法利夫人》中多數人物都屬於布爾喬亞。但我們首先應當弄清楚的是,福樓拜本人使用的「布爾喬亞」這個詞具有什麼含義。除了在法文中常見的「城鎮居民」這個字面含義之外,福樓拜筆下的「布爾喬亞」這個詞指的是「庸人」,就是只關心物質生活,只相信傳統道德的那些人。福樓拜使用的「布爾喬亞」這個詞從來不具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上的內涵。福樓拜的「布爾喬亞」指的是人的心靈狀態,而不是經濟狀況。這部小說中有一個著名的場面:一個勤勞的老婦人由於像牛馬般賣力地為農場主幹活而獲得一枚獎章。評判委員會由一夥怡然自得的布爾喬亞組成,他們笑容可掬地望著老婦人。請注意,在這裡,笑容滿面的政客和迷信的老農婦都是「庸人」,也都是福樓拜所指的那種「布爾喬亞」。若要十分清楚地劃定這個詞的含義,我可以舉下面的例子。今天在俄國,蘇維埃文學、蘇維埃藝術、蘇維埃音樂、蘇維埃的理想抱負,都十足地帶著沾沾自喜的布爾喬亞的特徵,像是在鐵幕後邊襯著一道華麗而又俗氣的蕾絲紗幕。一個蘇維埃官員無論職位高低,在精神上都是典型的布爾喬亞和庸人。要想把握福樓拜賦予這個詞的真正含義,市井小人郝麥先生的行為就是最好的注腳……
4
羅伯特•路易士•史蒂文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
《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1885)
《化身博士》一書是作者患肺出血期間的臥榻之作,一八八五年寫於英吉利海峽的伯恩第斯,一八八六年一月出版。哲基爾是一個體態豐滿的仁慈的內科醫生,他並非不具備一般人的弱點。他不斷地服用一種藥液,集中了或者說是沉積了所有的邪惡,使自己突然變成了一個殘忍而野獸般凶惡的人,取名海德。在這種性格下,他開始了一種扭曲的犯罪式生活。曾經有一段時間,他完全能夠恢復他的哲基爾原形──既有變為海德的藥液,也有恢復成哲基爾的藥液──但是,他的善良本性愈來愈弱,終於,恢復哲基爾的藥液失效,當真相即將暴露時,他服毒自殺。這是該故事的簡單情節。
首先,假如你有我這樣一本袖珍版本的《化身博士》,你會憎惡那個荒謬、可惡、惡劣、殘忍、污穢而令人作嘔並使年輕人墮落的封面──或者確切地說是侷限了年輕人思維的封面。你將不去理會這個事實:在豬肉打包商導演下的笨拙演員,表演著歪曲了本書原意的劇作,後來這個改編拙劣的劇本又被搬上了銀幕,並且在被稱為劇院的地方上演。依我看來,把電影院叫做劇院,與稱呼那些辦喪事的人是承辦殯葬者或殯儀業者沒有什麼兩樣。
現在我要發布一項重要禁令:請完全徹底地忘卻這本書的內容,不要回憶什麼,要把原有的印象都去掉,要忘掉一切,使你的大腦對這部小說的任何見解呈現完全空白的狀態。只有這樣,你才能夠忘掉《化身博士》是一部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是一部偵探小說和一部電影。當然,史蒂文生一八八五年創作的這部篇幅不長的小說,是現代偵探小說的鼻祖之一,這一點的確是事實。但是,今天的偵探小說是對文體的徹底的否定,最多不過是因襲傳統的文學作品。坦率地說,我不是那些躲躲閃閃地誇耀自己欣賞偵探小說的大學教授們當中的一個──就我的口味來說,它們都寫得太糟,使我厭煩得要死。然而史蒂文生的作品──願上帝保佑他純潔的靈魂──作為偵探小說是有缺陷的。它也不是寓言或諷喻小說,不論作為寓言還是諷喻,它都索然無味。如果我們把這部小說看作一種文體學現象,無疑,它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不僅僅像史蒂文生從夢中醒來後宣稱的那樣,是一部很好的「鬼怪故事」。我想他的夢中所見,與神秘的思維帶給柯爾律治那個最著名的未完成詩作的想像,是很相似的。更為重要的是,這部小說是:「一個更接近於詩歌,而不是一般散文體小說的虛構故事。」因此,它與《包法利夫人》、《死魂靈》等屬於同一個藝術層次。
這本書具有一種令人愉快的葡萄酒的味道。事實上,故事中的人物喝掉了許多陳釀葡萄酒:可以回想一下厄特森愜意呷酒的樣子。愉快、安逸的飲酒享受,與變色藥液所引起的令人戰慄的痛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那種具有魔力的藥液是哲基爾在他那滿是灰塵的實驗室裡配製出來的。作者對所有情節的描寫都很吸引人、新穎。史蒂文生借用岡特大街的加布里埃爾•約翰•厄特森之口,對故事作了極為全面的描述。他描述了寒氣逼人的倫敦清晨有著迷人的氣息;甚至對哲基爾在變形的過程中所經歷的種種可怕的感覺,在描寫上也具有某種豐富的聲色。為了達到他的預期目的,史蒂文生必須十分依賴於文體,只有這樣才能解決他所面臨的兩個主要難題:⑴用藥劑師的配料製出具有魔力的、而且似乎有可能造出來的藥液;⑵使人認為哲基爾服藥前與服藥後邪惡的一面真實可信。「正像我曾經說過的,當我沉思默想的時候,實驗臺上得出的結果給我從側面提供了線索。我開始有了比以往對這個問題更加深刻的認識,即我們穿著服裝、四處行走的軀體表面上是那麼堅實,但實際上卻是那麼的虛弱、不實,像霧一樣短暫、無常。我發現了可以有某種力量能夠動搖和震撼那有形的肉體,甚至就像一陣風可以把樓閣的窗簾吹得飄蕩起來一樣……我不僅意識到了在我的天賦的軀體內存在著某種構成我的精神力量的光點,並且我設法配製出了一種藥劑,在這種藥力的作用下,這種力量會被迫從它的主宰地位上退下來,並且被第二種形體和相貌來代替。由於它們都表現了我的本性,並且帶著我靈魂中的較低級的素質,所以對於我來說仍然是自然的。
5
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
《在斯萬家那邊》(The Walk by Swann’s Place, 1913)
以下是普魯斯特的名著《追憶逝水年華》(In Search of Lost Time,此書被蒙克里夫譯為《往事的追思》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中的七個部分,後面括弧裡的是蒙克里夫的翻譯。
《在斯萬家那邊》
《在少女們身旁》
《蓋爾芒特家那邊》
《索多姆和戈摩勒》
《女囚》
《失蹤的阿爾貝蒂娜》
《重現的時光》
蒙克里夫譯書未竟就去世了,這一變故也並非事出突然。因而,這本書的最後一卷就由一位叫布勞瑟姆的人來譯出,他譯得相當不錯。這七部分的法文本共分十五卷,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七年相繼出版。它的英譯本有四千頁,約一百五十萬字。在規模上,這部著作的時間跨度有半個多世紀之長,從一八四○年直至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而且還一共有二百多個人物。整體來講,普魯斯特所虛構的,是一個十九世紀九○年代初的社會。
普魯斯特於一九○六年秋在巴黎開始寫這部小說,一九一二年完成初稿,隨後又重寫了其中的大部分,並一再地重寫和修改,直至他一九二二年去世。這整部作品是對寶貴事物的追尋和求索,這一寶貴事物就是時間,隱藏寶物的地方就是過去,這就是書名「追憶逝水年華」所包含的深層含義。那由感覺、知覺向情感方向的衍變,那如潮水般在心中湧來、退去的往事,那由渴望、嫉妒和富有詩意的欣喜之情等等的綿延起伏所構成的情感波瀾,所有這些加在一起,構織成了這部宏偉而又極其空靈,並透現出深邃意蘊的作品。
普魯斯特在青年時代曾研究過昂利•柏格森的哲學。普魯斯特關於時間流動的種種基本觀念,涉及就其持續性而言始終處於發展變化之中的特性,涉及唯有通過直覺、記憶和無意識聯想,才能獲得我們潛意識中的未知寶藏,還涉及純理性對天才的內心奇妙靈感的從屬地位,以及把藝術看作世界上唯一的真實存在的看法。這些觀點都是帶有普魯斯特色彩的柏格森思想。讓•科克托曾稱這部小說為「一幅巨型袖珍畫,其中盡是幻景,盡是浮置於景物之上的花園,盡是進行於時空之間的嬉戲、運動」。
有一點你們須牢記,這部著作不是一部自傳。書中的敘述者並不是普魯斯特本人,書中那些人物也只有在作者的心裡才存在。因此,我們就不要在此討論作者的生活了,他的生活對於我們目前談的問題來說,非但不重要,而且還會造成混淆,尤其在書中的敘述者與書的作者,的確顯現出種種相同之處,並處於幾乎同樣的環境之中時,就更是如此。
普魯斯特是一個透鏡,他的──或說是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將景物縮小,並通過縮小景物的方法重新創造出一個回顧中的世界來。這個世界自身以及這個世界中的人們都並不具有任何社會的和歷史的重要性。他們剛好就是報上所說的上流社會人士,也就是有閒的紳士、淑女們。他們富有,但無職業。我們從書中讀到,那些為人從事的唯一職業及其生產成果全都是藝術和學術方面的。在普魯斯特透鏡下的那些人物不操任何職業,他們的工作只是去娛悅作者。他們可以盡情地契闊談宴,盡情地娛樂,正像我們可以清楚地想像到的那些傳說中的古人,他們圍坐在堆滿水果的桌前,或是閒步在丹墀之上,高談闊論,這樣的人,我們在會計室裡,在船塢中,則是從來也見不到的。
恰如法國評論家阿爾諾•丹第歐(Arnaud Dandieu)所說,《追憶逝水年華》是對往日的召喚,而不是對往日的描繪。他接下來還說,小說作者是通過展現若干個經過精心選擇、並由一連串圖景和形象表現出來的時刻去完成這一召喚的。確實,整個這部鉅著就像這位評論家的結論所說的,完全是一個圍繞著「彷彿」ヾ二字擴展開來的比喻。對往日進行再造的結果也就成了藝術問題的關鍵。對寶物的搜尋最後終於在一個響徹音樂之聲的岩洞中,在一座鑲滿五彩玻璃的廟堂裡圓滿結束。這裡並沒有正規宗教中的那些神祇,或許我們應當這樣說才對,即這些神已經融入藝術之中了。
閱讀普魯斯特的著作對於一個粗淺的讀者來說──此話說來有些矛盾,因為一個粗淺的讀者在讀這部著作時會感到乏味,會呵欠連天,以致根本無法把它讀完──讓我們姑且這樣說吧,對於一個缺乏經驗的讀者來說,似乎書中敘述者所最感興趣的事情之一,就是幾家貴族間的宗族關係或者聯姻,似乎他莫名其妙地把發現某一位他原以為是個小商人的人,竟原來把經常出入上流社會ヾ當作一件樂事,把發現某一重要婚姻,以他原先做夢也想不到的方式,兩個家庭因此聯合起來當作一件樂事。那些就事論事的讀者似乎還會下結論說,這部小說中的主要事件就是由一連串的聚會組成的。比如說吧,書中寫一次晚餐就用去了一百五十頁的篇幅,寫一次晚會就占去了半卷書的長度。在小說的第一部分,讀者看到了韋爾杜蘭夫人家的那個格調低下的沙龍,當時斯萬經常出入這個沙龍。此外讀者還看到了在德•桑—歐韋爾特夫人家舉行的那次聚會,其間斯萬首次了解到他對奧黛特的愛情是徒勞無望的。小說後面的幾部分則又描寫了其他的客廳、其他的會見,還寫了德•蓋爾芒特夫人在家裡舉行的晚宴、韋爾杜蘭夫人在家裡舉行的音樂會,以及這位夫人在通過婚姻而搖身成為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之後,在同一住宅裡舉行的午後聚會──這是在小說末卷《重現的時光》中所描寫的最後一次聚會,在這次聚會上,書中敘述者發現了時間給他的朋友們帶來的變化,並猛然間得到了一個靈感──或者毋寧說是一連串的靈感,使他決計要立刻動手寫書,來重建往日的世界。
6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
《變形記》(The Metamorphosis, 1915)
當然,無論一個故事,一首樂曲,或者一幅畫喚起多麼激烈的、多麼熱心的討論和分析,仍然會有某些人思想一片空白,感情不為之所動。當初李爾王懷著多麼大的渴望為自己和考德麗婭的命運說出了「讓我們接受事物的神秘吧」這句話,而這正是我要給予每一位嚴肅地對待藝術的人的忠告。一位可憐的人,他的大衣被搶走了(見果戈理的《外套》);另一位可憐人被變成了甲蟲(見卡夫卡的《變形記》)──那又怎麼樣呢?對於這個「怎麼樣」沒有標準的答案。我們可以把故事拆開,找出各個部分如何銜接,結構中的一部分如何呼應另一部分;但是,在你身上必定得有某種細胞,某種基因,某種萌芽的東西因著某種既不可解釋又不能置之不理的感覺而振顫。美加上憐憫──這是我們可以得到的最接近藝術本身的定義。何處有美,何處就有憐憫。道理很簡單,美總要消失,形式隨著內容的消失而消失,世界隨著個體的死亡而消亡。如果你讀了卡夫卡的《變形記》後,並不認為它只是昆蟲學上的奇想,那麼我就要向你祝賀,你已加入了優秀而偉大的讀者行列。
我下面要談談幻想和現實,談談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如果我們把《化身博士》的故事看作一個關於人人身上皆有善惡之爭的寓言,那麼這個寓言便是幼稚的,枯燥無味的。對於那類能在這個故事中看出寓言的人,寓言的意義同樣要以具體實際的事件為基礎,而這些「事件」以常識來看則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實上,就故事的背景來說,普通人初看時覺得似乎並沒有違背一般生活經驗的地方。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仔細看一下就會發現故事的背景確與一般人的生活經驗相矛盾。出現在哲基爾周圍的厄特森以及其他的人,從某方面說,同海德先生一樣怪異。如果我們不從這一點來看他們,他們也就失去了魅力。一旦巫師離開了,只剩下講故事的人與說教者,他們就不會配合好。
哲基爾和海德的故事寫得相當漂亮,但卻是一個陳舊的故事。故事本身對善與惡都沒有真正描寫,因此其寓意很特別。從總體上看,小說中善與惡被視為眾所周知,因而未加描述,這樣一來,兩者之間的鬥爭就在兩個空架子間展開,史蒂文生小說藝術的迷人之處只在作品的結構。但是我要提醒的是:既然藝術和思想,形式與內容是不可分割的,那麼故事的結構也必然存在同樣的情形。不管怎樣,咱們還是謹慎些。如果我們把形式和內容分開來看,我仍然認為這個故事在藝術效果的實現上還存在著不足。而果戈理的《外套》和卡夫卡的《變形記》就沒有這方面的缺憾。史蒂文生的故事背景中怪誕的一面──厄特森、恩菲爾德、普爾、蘭尼昂以及他們所在的倫敦──與哲基爾變形的怪誕一面不屬同一性質。因而故事在描繪上存在某種斷裂,缺乏整體感。
《外套》、《化身博士》及《變形記》三篇小說通常都被稱為荒誕的幻想。在我看來,任何一部傑出的藝術作品都是幻想,因為它反映的是一個獨特個體眼中的獨特世界。然而當人們稱這三篇故事為荒誕的幻想作品時,他們僅僅是指故事在題材方面與我們通常稱為現實的東西不一致。為了搞清楚所謂的幻想是以何種方式、在何種程度上與所謂的現實相區別,還是先讓我們來看看現實到底是什麼。
那麼我們就拿三類不同的人,走過同一風景區作為例子吧。假定第一個人是位有相當不錯的職業的城市居民,第二位是職業植物學家,第三位是當地的農民。第一位城市居民是所謂現實的、有常識的、講求實際的人,在他眼裡樹就是樹。他從地圖上得知他走的那條路,是通往紐頓的一條相當不錯的新路,據他同一辦公室的朋友推薦,那裡還有一家不錯的飯館。那位植物學家向四周看看,以極其準確的植物學術語,精確的生物學的分類單位來把握他周圍的環境,例如某種特定花草樹木以及特定的蕨類植物。對他來說這就是客觀現實,而那位無知的旅遊者(他分不清哪棵是橡樹,哪棵是榆樹)的世界,在他眼裡,倒像是一個想像的、模糊的、夢一般的、並不存在的世界。最後,那個本地農民的世界與前兩者的世界又不同。他的世界與個人的經驗緊密相連,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因為他在那裡出生、成長,熟知每一棵樹,每一條小徑,熟知斜映在每條小徑上的每個樹影。所有這一切與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孩提時代,他的許許多多的瑣事和習慣緊密相關,而另外兩人(那個無聊的旅遊者和植物分類學家)在此時此地對這一切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們這位農民不會知道周圍的植物在植物學概念上的意義;同樣那位植物學家也不會知道這個穀倉或那個古老的田野,或者那個有著白楊屋頂的舊房子對這位農民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這些東西對於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農民來說,似乎總漂浮在他的記憶中。
7
詹姆士•喬依斯(JAMES JOYCE, 1882-1941)
《尤利西斯》(Ulysses, 1922)
詹姆士•喬依斯於一八八二年生於愛爾蘭,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裡離開愛爾蘭,大半生的時間寄居國外,生活在歐洲大陸上,直至一九四一年在瑞士逝世。《尤利西斯》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一年間在的里雅斯德港、蘇黎士和巴黎完成的。一九一八年,部分內容開始在所謂的《小評論》上刊登。《尤利西斯》是一本字數超過二十六萬的大部頭作品,它內容豐富,約用辭彙三千左右。都柏林的環境主要根據《湯氏都柏林詞典》中的資料,另一部分則由流放者的記憶所提供的資料構成。文學教授們在討論《尤利西斯》之前,都暗自拿這本詞典來武裝自己,這樣就可以用喬依斯本人用來裝備自己的知識去震懾學生。他還在全書中使用了都柏林的一家報紙:一九○四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四的《電訊晚報》,價格是每份半便士。這份報紙刊登了當天的各種新聞,其中有在阿斯科特舉行的金杯賽馬比賽(這場比賽的優勝馬匹是不大可能獲勝的思羅奧威)、震驚美國人的一場災難(斯洛克姆將軍號遊輪起火),以及在德國洪堡舉行的戈登•貝內特杯摩托車賽。
《尤利西斯》描寫了一九○四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四的一天,以及幾個都柏林人物的生活情形,他們在這一天當中以及第二天凌晨數小時之內的散步、坐車、談話、坐著、喝酒、做夢,以及一些次要的和主要的心理及哲學活動。為什麼喬依斯偏偏選擇了一九○四年六月十六日這一天?在《驚人的旅行家:詹姆士•喬依斯的〈尤利西斯〉》這本用心良好,但粗劣蹩腳的書中,理查•卡因告訴我們,喬依斯是在這一天與他未來的妻子諾拉•巴納克爾相識的。對作者的興趣到此為止。
《尤利西斯》由圍繞三個主要人物而展開的若干場景所構成,這三個主要人物當中,占統治地位的人物是利奧波爾德•布盧姆,一個廣告業的小商人,確切地說,是一個廣告推銷員。他一度在文具商威茲德姆•希利商行當吸墨水紙的旅行推銷員,但現在他已經自立門戶,做廣告宣傳,但生意不太好。喬依斯賦予他匈牙利|猶太人的出身,其中的原因我很快就會談到。另兩個主要人物是斯蒂芬•代達勒斯,喬依斯早在《年輕藝術家的畫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一九一六)中就已經描寫過他;還有布盧姆的妻子,馬里恩•布盧姆,即莫莉•布盧姆。如果說布盧姆是中心人物,斯蒂芬和馬里恩就是三張相連的圖畫中那兩張側面的圖畫:小說以斯蒂芬開始,以馬里恩結束。斯蒂芬•代達勒斯的姓氏出自神話中古代克里特島上那座皇城諾薩斯迷宮以及其他一些傳說中的新發明的製造者,這些發明包括給他自己和伊卡洛斯做的翅膀;伊卡洛斯是他的兒子,也就是斯蒂芬•代達勒斯。斯蒂芬二十二歲,是都柏林的年輕教師、學者和詩人,在他讀書時,他一直受到耶穌會教育的教規約束,現在則猛烈地反抗這種教規,但是從根本上講,他的本性仍是形而上學的。他是一個挺深奧的年輕人,甚至在喝醉酒時也還是個教條主義者,一個將自我束縛起來的自由思想家,一個聰慧絕頂、會出其不意說出許多格言或警句的人,他身體羸弱,和聖人一樣不洗澡(他最後一次洗澡是在十月,而現在已是六月了),一個好抱怨、愛生氣的年輕人──讀者從來都無法想像他的真正形象,他是作者精神的具象化,而不是由藝術家的想像力創造出來的活生生的新生命。批評家傾向於把斯蒂芬看作年輕時的喬依斯,但是這一點他們沒有說清楚,而我並不準備說明。不過哈里•萊文說過:「喬依斯失去了他的宗教信仰,但是卻保留了信仰的種種類別」,斯蒂芬也是如此。
1珍•奧斯汀(JANE AUSTEN, 1775-1817)《曼斯費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 1814) 《曼斯費爾德莊園》寫於漢普郡的肖頓。寫作始於一八一一年二月,於一八一三年六月後完成;也就是說,珍•奧斯汀用了二十八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一部共四十八章,約十六萬字的小說。小說於一八一四年分三卷出版(與司各特的《威弗利》(Waverley)和拜倫的《海盜》(Corsair)同年出版)。作品分三部分出版是當時傳統的出版方式,但是實際上該書的三部分突出了小說的結構,即其類似戲劇的形式,這是一齣反映社會風俗人情、道德是非曲直、人物喜怒哀樂的三幕喜劇,各幕分...
目錄
目次
中譯本序 申慧輝
前言 (美)約翰‧厄普代克
編者前言 (美)弗萊德森‧鮑爾斯
優秀讀者與優秀作家
珍‧奧斯汀(Jane Austen, 1775-1817)
《曼斯費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 1814)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荒涼山莊》(Bleak House, 1852-1853)
居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L, 1821-1880)
《包法利夫人》(Maddme Bovar
目次
中譯本序 申慧輝
前言 (美)約翰‧厄普代克
編者前言 (美)弗萊德森‧鮑爾斯
優秀讀者與優秀作家
珍‧奧斯汀(Jane Austen, 1775-1817)
《曼斯費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 1814)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荒涼山莊》(Bleak House, 1852-1853)
居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L, 1821-1880)
《包法利夫人》(Maddme Bovar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文學,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是任何單一的書面作品。更嚴格地說,文學寫作是一種藝術形式,或被認為具有藝術或智力價值的任何單一作品,通常是由於以不同於普通用途的方式部署語言。
文學,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是任何單一的書面作品。更嚴格地說,文學寫作是一種藝術形式,或被認為具有藝術或智力價值的任何單一作品,通常是由於以不同於普通用途的方式部署語言。 ![]()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