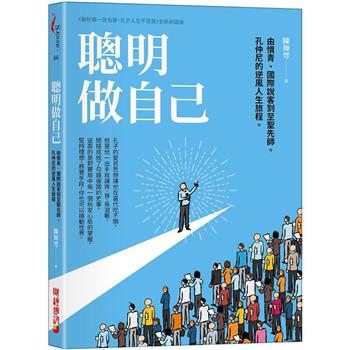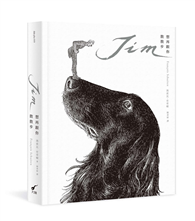啟程:轉捩中的事件
“印尼的海嘯奪去了20萬人的生命!”“狗仔隊偷拍到布蘭妮‧斯皮爾斯(Britney Spears)的私處”“我終於意識到應該拋下一切去幫助他!”“殘暴的軍事佔領摧毀了整個國家!”“這是人民的勝利!獨裁者逃走了!”“怎麼會有像貝多芬最後一首鋼琴奏鳴曲這樣美妙的音樂?”
所有這些陳述,都指涉着某些我們視為“事件”的東西──這是個有着《格雷的五十道色戒》般捉摸不定的概念。一個“事件”可以是淒慘嚴酷的自然災害,也可以是媒體熱議的明星緋聞;可以是底層人民的抗爭與勝利,也可以是殘酷的政權更迭;可以是藝術品帶給人的強烈感受,也可以是為愛與親情而作出的抉擇。鑒於事件的種類是如此紛繁多樣,除了懷揣着大抵不錯的理解,冒險登上這趟駛向概念探尋之旅的列車之外,我們幾乎想不出其他法子來給“事件”一個恰當的界說了。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Christie)的偵探小說《命案目睹記》(4.50 from Paddington)的故事在一趟由蘇格蘭駛往倫敦的列車上拉開序幕。埃爾斯佩思‧麥克基利科蒂要去看望老朋友簡‧馬普爾小姐,在車上目睹了迎面駛過的一列火車車廂裏發生的一樁命案。由於這一切來得過於迅速而突然,埃爾斯佩思視線也不太清晰,因此警方並沒有採信她的證詞;只有馬普爾小姐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展開了調查。這可算最簡單純粹意義上的事件了: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一件駭人而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發生,從而打破了慣常的生活節奏;這些突發的狀況既無徵兆,也不見得有可以察覺的起因,它們的出現似乎不以任何穩固的事物為基礎。
從定義上說,事件都帶有某種“奇跡”似的東西:它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意外,也可以是一些更宏大、甚至帶着神性的事情。基督升天的事件性(eventual nature),恰恰在於它要求人們對於一個特定事件(亦即基督復活)的信仰。在這方面,信念及其理由之間的循環關係或許更為根本:我並不認為自己之所以信仰基督,是由於我被信仰背後的理由所說服;因為只有當我相信自己能理解對此信念的理由之後,這種說服才成為可能。同樣的循環關係,也出現在對愛情的理解中:我並非出於某些具體的理由(例如她的嘴唇或笑容)才愛上她──相反,恰恰是因為我愛上了她,她的嘴唇和笑容才顯得如此打動我的心弦。這也正是愛情也具有事件性的原因。在循環結構中,若干事件互為因果。1 政治性事件也具有類似的循環結構:在其中,事件性的結果以回溯的方式決定了自身的原因或理由。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上的抗議示威推翻了穆巴拉克的威權統治:我們固然很容易將抗議活動的原因歸結為埃及社會發展的死結(例如受教育青年因大規模失業而導致的絕望情緒等),但在某種意義上,這些癥結又都無法解釋那場民眾運動為何會積聚起如此摧枯拉朽的力量。
在同樣的意義上,新藝術風格的興盛也可算是一類事件。在此不妨拿“黑色電影”(film noir)的出現作個例子。據文藝史家馬克‧維爾耐的考證2:黑色電影概念誕生之前,其所有主要特徵(如明暗交替的用光、傾斜的鏡頭角度、驚險跌宕的劇情、放蕩而有着致命吸引力的美女等)在荷里活作品中都早已有之。真正令人不解的是,“黑色”(noir)這個概念竟能帶來如此深入人心的神秘印象,事實上,維爾耐的研究所揭示的歷史事實愈是詳盡,我們便愈加感受到這個“虛幻”的黑色概念那種難以名狀的力度──以至數十年間,它始終在我們的想像中縈繞不去。
按照第一種界定事件的方法,我們可以將事件視作某種超出了原因的結果,而原因與結果之間的界限,便是事件所在的空間。循着這初步的定義上行,我們實際上已經踏入哲學的核心地帶──因果性正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之一:是否所有的事物都以因果鏈條相連?一切存在之物是否都受充足理由律的支配?真的有無緣無故憑空出現的事物嗎?如果事件的發生不以充足理由為基礎,我們又如何借助哲學給出對事件及其可能條件的界定?
自其誕生之日起, 哲學似乎就始終徘徊在先驗論(transcendental)與存在論(ontological/ontic)這兩個進路之間。先驗論旨在揭示現實以怎樣的普遍結構向我們呈現:它要回答的是實在物的感何可能的問題。主張先驗論的哲學家認為,我們的認知架構是“先驗”的(transcendental),它決定着現實的座標──例如,先驗論的進路往往讓我們意識到:對科學自然主義者而言,只有位於時空中且遵循物理定律的物質現象才是真實存在的;而在持前現代傳統觀念的人看來,在人類的籌劃之外,精神與意義也是實在的一部分。與此相反,存在論的進路關注的則是現實本身及其形成與發展過程,例如:宇宙是如何誕生的?它是否有起始和終結?我們在其中又處於怎樣的位置?到了二十世紀,這兩個哲學思考路徑之間的鴻溝已經空前巨大:先驗論思想在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那裏達到了巔峰;而存在論則轉變為自然科學的領地:量子力學、腦科學與進化論,成為我們尋求宇宙起源變化問題答案的依據。在其《大設計》(The Grand Design)一書的開篇,理論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勝利地宣稱“哲學已死”3:那關於世間萬物的形而上學問題,一度曾專屬哲學思辨的領域,如今不但被經驗科學所回答,而且還能通過實驗加以檢驗。
----------------------------------------
1 這也正是為甚麼在戀愛中,我們總是讓自身的弱點在所愛之人面前暴露無遺:當我們赤裸相對時,對方不經意間的嘲諷笑容與評論就可能讓魅力變成了笑柄。愛意味着絕對信任:當愛一個人時,我授予了他(她)能夠摧毀我自己的力量,我希望 / 相信對方不會使用它。
2 Marc Vernet, ‘Film Noir on the Edge of Doom,’ in Joan Copjec, ed., Shades of Noir, London: Verso Books, 1993.
3 Stephen Hawking and Leonard Mlodinow, The Grand Design, New York:Bantam, 2010, p.5.
令人驚訝的是,哲學的這兩個進路的發展與深化,又都與事件概念密切相關:在海德格爾那裏,存在的揭示(disclosure)正是一個事件,在其中,意義的視域得以敞開,我們對世界的感知以及和它的關係也由此確定下來。而當代量子宇宙論則認為,宇宙萬物都源於大爆炸(亦即“對稱破缺”)這個原初事件。
我們此前將事件界定為超過了原因的結果,在此,這個定義似乎面臨着模棱兩可的矛盾:事件究竟是世界向我們呈現方式的變化,還是世界自身的轉變?哲學究竟是減損了事件的自主性,還是使這種自主性得以澄清?面對這個難題,我們似乎可以通過一種顯而易見的方法理出頭緒,例如,我們可以將事件分為一系列的類別,每個類別下再分出子類:如物質事件、非物質事件、藝術事件、科學、政治與情感事件……然而,這個分類法忽視了事件的一個基本屬性,即:事件總是某種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發生的新東西,它的出現會破壞任何既有的穩定架構。因此筆者認為,唯一合適的研究方法,恰恰是以事件性的方式入手展開對事件的探索──我們將逐一討論關於事件的不同觀念,揭示出各個觀念的死結(deadlock),並分析此過程中普遍性自身的轉變。筆者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將趨近黑格爾意義上的“具體普遍性”,這普遍性“不僅是個別內容的容器,它更能通過對自身的對抗(antagonism)、死結與矛盾的部署,生成這些內容。”
這情形就如同坐在一列地鐵列車上,其運行線路有許多的停靠站與分岔,每一站都代表着對事件的一個假定定義。我們在第一站將討論世界向我們呈現的架構的變化與解體;第二站談的是宗教裏的“墮落”;接下來則依次是對稱破缺、佛教裏的“正等正覺”、破壞了日常生活的真相、具有純粹事件性的對自我的體驗、那些將真理本身事件化了的彷彿把握真理的幻覺、破壞了象徵性的秩序之穩定的創痛經歷、“主能指”(Master-Signifier)的出現(這種能指給出了整個意義之域的結構)、對純粹的感覺 / 非感覺之流的經驗……最後,我們還將提及取消事件性的成就(evental achievement)的問題。這旅途雖然不乏顛簸起伏,但將會是激動人心的,而隨着我們深入概念的腹地,許多問題也將得以澄清。那麼,閒言少敍,讓我們就此啟程!
第一站:架構、重構與建構
1944年9月7日,隨着盟軍開進法國境內,德國人將菲力浦‧貝當元帥及其名義領導下的維希政府遷到了德國南部的西格馬林根(Sigmaringen)。並在那裏建立了一個以費爾南‧德‧布里農(Fernand de Brinon)為首腦的,享有法國流亡政府治外法權的城市國家。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在西格馬林根開設了使館,這個城市擁有兩個廣播電台以及兩家出版社。生活在這塊飛地上的六千多名公民中,不但有像拉瓦爾(Laval)這樣的維希政府元老、賽琳(Céline)與雷巴特(Rebatet)等知名記者與作家,還有羅伯特‧勒‧維岡(Robert Le Vigan)這樣的電影明星,後者曾在杜維維耶(Duvivier)1935年執導的電影《髑髏地》(Golgotha)中飾演耶穌基督。此外,西格馬林根還駐紮着五百名士兵、七百名黨衛軍以及不少法國勞工。城中彌漫着近乎瘋狂的官僚作風:為了營造維希政府是代表法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幻象(雖然從法理上說,這在當時的確是事實),西格馬林根的國家機構繼續着它在法國時的工作:每天,政府都作出數不清的聲明、法案與行政決策,儘管所頒發的這些文件毫無實際效力──這就像一台失去了國家的國家機器,它自行運轉,漫無目的地實現着自身的職能。1
在倡導常識,反對哲學的人們看來,哲學這個行當無異於精神上的西格馬林根:哲學家不亦樂乎地虛構出天馬行空的理論,彷彿有了看穿人類命運的洞見,然而真實的生活卻與這些哲學巨擘的思想毫不相干。哲學真的只是一齣虛幻的影子戲嗎?它僅僅是些模仿着真實事件的虛假事件嗎?抑或它的真正力量,恰恰在於其不直接介入生活的超然態度?是否正由於這種與真實事件之間的“西格馬林根距離”,哲學才得以洞察這些事件中更深刻的緯度,並成為我們探索事件之多樣性的唯一方式?然而,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問的是:在其最基本的意義上,哲學究竟是甚麼?
----------------------------------------
1 儘管整個佈局顯得可笑,但其中也不乏悲劇式的淒美,例如在《從一個城堡到另一個城堡》(D’un château l’autre)中,賽琳就生動地描繪了西格馬林根悲催困惑的日常生活。
2002年2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曾在已知與未知的問題上,作了一番準專業的哲學思考,當時他說:“世上有已知的已知(known knowns),也就是我們知道自己已經知曉的東西;此外還有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就是我們知道自己並不了解的東西;然而除了二者之外,還有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亦即那些我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對其一無所知的東西。”當然,拉姆斯菲爾德這麼說的目的,是為美國即將對伊拉克展開的軍事行動辯護:我們知道某些事實(例如,薩達姆‧侯賽因是伊拉克總統);我們還知道自己對許多事並不知曉(例如,伊拉克到底擁有多少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還有許多事我們甚至不知道自己一無所知──薩達姆‧侯賽因是否還隱藏着其他秘密武器?不過,拉姆斯菲爾德似乎忘了加上第四種狀況:“未知的已知”,也就是那些我們不知道自己已然知曉的東西──這正是佛洛伊德意義上的無意識,也是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1901—81,拉康的著作是本書的主要參考2)所謂的“不自知的知識”。(在拉康看來,無意識並不存在於前邏輯或非理性的本能空間,相反,它是主體遺忘了的,由符號所表述的知識。)拉姆斯菲爾德認為,與伊拉克開戰的主要風險來自於“未知的未知”,也就是薩達姆可能掌握的秘密武器;相反,我們在此關於事件的討論,其困難則來自“未知的已知” ──亦即我們不願承認的下意識的信念與假設。事實上,這些“未知的已知”才是真正困擾着美軍在伊拉克軍事行動的關鍵因素,拉姆斯菲爾德對這個問題的忽略,也恰恰表明他不是真正的哲學家。“未知的已知”是專屬於哲學的話題—它們構成了我們日常經驗的先驗視域(或架構)。在詳述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看看在對於運動的理解上,近代早期的人們的認知架構發生了怎樣的轉變:
中世紀的物理學理論認為,推動力是物體運動的原因。靜止是物體的自然狀態,物體受到外力作用產生運動,當外力消失,物體便逐漸減速以致停止。為了維持物體的運動狀態,我們必須持續對其施加推力,而推力則是我們能夠感知到的東西。(這甚至被視作上帝存在的論據之一:既然萬物的運動都離不開持續施加的推力,因此上帝便是天堂的推動者。)這樣看來,如果地球在不斷轉動,為甚麼我們完全感覺不到它的運動?哥白尼無法給出這個問題的滿意回答……伽利略則認為:我們能感知的不是速度,而是加速度,因此地球的均速運動並不會被察覺。物體運動的速度只有在受到外力時才會發生改變,這種對於慣性的全新認識,取代了舊的推動力觀念。3
----------------------------------------
2 關於對拉康著作的導讀,參見Slavoj Žižek, How to Read Lacan, London: Granta Books, 2006。
3 摘自www.friesian.com/hist-2.htm。
運動觀從動力說到慣性說的變化,改變了我們看待現實的基本方式。這種轉變是一個事件:在其最基礎的意義上,並非任何在這個世界發生的事都能算是事件,相反,事件涉及的是我們藉以看待並介入世界的架構的變化。有時,這樣的架構直接以虛構作品的方式向我們呈現,這種虛構物恰恰使我們能夠間接地表達真相。最能體現“有着虛構作品結構的真相”的例子,當屬那些含有戲劇角色表演內容的小說(或電影),在這些作品中,演員在戲劇中的角色,正反映着他們在(作品裏的)真實生活中複雜糾結的戀愛關係。例如,在一部關於《奧賽羅》排演的電影中,排演奧賽羅的演員本人也深受嫉妒之苦,他在表演最後一幕時親手掐死了扮演苔絲狄蒙娜的女演員。簡‧奧斯丁的小說《曼斯費爾德莊園》給出了這類作品的一個早期例子。
范妮‧普萊斯是個出身貧寒的女子,由曼斯費爾德莊園的主人托馬斯‧貝特倫爵士撫養成人,與她一起長大的還有四個表兄姊:湯姆、埃德蒙、瑪利亞、朱麗亞。寄人籬下的范妮時常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只有表兄埃德蒙向來對她很好,隨着時光流逝,兩人之間漸漸生出愛慕之情。當曼斯費爾德莊園的孩子長大成人,托馬斯爵士須離開一段時間。在托馬斯爵士離開的兩年間,思想新潮、玩世不恭的克勞福特兄妹──亨利和瑪麗的到來,給平靜的曼斯費爾德莊園帶來了一系列情感波瀾。這羣年輕人一時興起,欲共演著名劇作《情人的誓言》(Lovers’ Vows)。范妮和埃德蒙持反對立場,認為這將敗壞托馬斯爵士的名聲,但最後還是同意參加演出。這場劇讓亨利和瑪利亞首次有機會公開調情,並讓埃德蒙和瑪利亞得以談論愛情與婚姻。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演出前幾天,托馬斯爵士突然返家,令整個計劃告吹。4但直到這一刻之前,展現在讀者眼前的排練過程,恰恰是劇中人物真實關係的反映,儘管他們自己不願承認這點。
在敍事中,故事的真正含義,往往只能通過類似的視角轉換來達成。前南斯拉夫電影導演杜尚‧馬卡維耶夫(Dušan Makavejev)雖以《有機體的秘密》(WR: Mysteries of the Organism)等影片名世,但他1968年的《不受保護的無辜者》(Innocence Without Protection)是更加傑出的作品。這部影片有着獨特的“戲中戲”結構。故事主人公德拉戈爾朱布‧阿萊斯克西奇是位年邁的塞爾維亞空中雜技演員,能懸掛在飛機上表演雜技。二戰中德軍佔領塞爾維亞的時候,阿萊斯克西奇在貝爾格勒拍攝了一部情節奇特而感人至深的音樂劇,該劇的名字也是《不受保護的無辜者》。馬卡維耶夫的電影完整包括了主人公阿萊斯克西奇的同名電影,還加上了對阿萊斯克西奇本人的採訪與其他一些紀錄影片。這部電影的關鍵,就在於這兩部電影之間的關係,它們向觀眾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誰才是不被保護的無辜者?在阿萊斯克西奇的電影中,無辜者顯然是那個受到壞繼母壓榨,並被強行嫁人的女孩。然而,馬卡維耶夫的整部影片中,這個不受保護的無辜者,恰恰是阿萊斯克西奇本人。阿萊斯克西奇到老都在表演危險的雜技,他在攝影機前身不由己地又跳又唱,擺弄姿勢。他既要取悅於納粹軍人,戰後又要討共產黨人的歡心,甚至還因其幼稚的表演而被片中的演員所嘲笑。隨着馬卡維耶夫這部影片情節的推進,我們會愈加感受到阿萊斯克西奇對於雜技表演的那種近乎無條件的忠誠態度。還有甚麼能比看到一個古稀老人,在地下室裏一邊用牙咬着吊索,一邊還在攝像機前擺弄各種姿勢更加令人笑中帶淚的呢?阿萊斯克西奇讓自己無辜地完全暴露在公眾眼前,毫無保護地承受着他們的嘲笑與揶揄。一旦我們意識到:片中主角阿萊斯克西奇才是真正不受保護的無辜者,這種視角的轉換便造就了影片的事件性時刻。這是對那些我們自己不願承認的現實的揭露,正是通過這種揭露,影片改變了整個表演的場域。
在荷里活,最流行的電影主題,當然要數情侶的破鏡重圓。在維基百科網站上,關於斯皮爾伯格的影片《超級8》(Super 8)的詞條有這樣一段描述:“在電影結尾,當星際飛船離開地球向着外星人的母星返航之際,喬和艾莉絲彼此雙手緊扣。”這對戀人終於走到了一起,他們愛情的障礙──那些神秘可怕的外星生物(也就是拉康所說的“帶來創傷的第三者”),如今終於要離開了。然而,片中外星生物這個障礙的角色是模糊不清的,因為儘管它極為殘忍兇惡,但這個生物恰恰是為了讓這對戀人走到一起而存在的;更確切的說法是,外星生物構成了喬與艾莉絲為了在一起而必須面對的困難與挑戰。5
----------------------------------------
4 同一個形式的更確切版本,出現在所謂“歌劇平行電影”中,這些電影讓當代故事與傳統歌劇(通常是意大利歌劇)的劇情平行發展,歌劇的佈景往往是電影情節的焦點所在。1939年的意大利電影Il Sogno di Butterfly(《蝴蝶之夢》)在此提供了有趣的例子:舞台上蝴蝶夫人的扮演者羅莎愛上了一個美國男高音並懷上了他的孩子,但這個歌唱家對懷孕並不知情,後來歌唱家回到了美國。四年之後,這個富有而家庭美滿的美國歌唱家又回到了意大利。與歌劇蝴蝶夫人不同的是,羅莎並沒有自殺,她後來全身心地與孩子生活在一起。
5 荷里活對破鏡重圓的青睞可謂持久──例如在2012年的影片《ARGO–救參任務》中,我們在開頭看到,身為CIA特工的男主角正與妻子分居,但他與小兒子的感情很深。而在影片結尾,他來到了妻子住處的門口,問妻子可否讓他進去,他的妻子默默地擁抱了他。這個場景的難解之處在於,因為與妻子的復合緊接着逃亡計劃的成功,我們不禁懷疑是否他妻子通過某種方式得知了這個特工的所作所為,但CIA的行動又是嚴格保密的。這意味着,這部影片的核心並不在於如何營救躲藏的美國人,而在於這對夫妻的破鏡重圓。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斯拉沃熱.齊澤克的圖書 |
 |
$ 290 ~ 360 | 事件
作者:斯拉沃熱.齊澤克 / 譯者:王師 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17-07-07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事件
乘坐哲學專車穿梭思想街巷
車廂裏閱讀齊澤克的哲學思想
「事件」究竟是甚麼?
事件可以是激進的政治革命(如「阿拉伯之春」),也可以是像墜入愛河那樣的強烈體驗。柏拉圖被理念迷住的瘋狂(就像墮入愛河般),笛卡兒心中「我思」的瘋狂和黑格爾絕對觀念的瘋狂,他們自身就是「事件」的哲學家﹗
從《ARGO──救參任務》到《江南style》,從大爆炸理論到佛教思想,齊澤克在書中以大量的電影、小說和社會文化現象為例,帶領我們登上這趟駛向概念探尋之旅的列車,了解每日所接觸的「事件」的真貌。
作者簡介:
斯拉沃熱•齊澤克 (Slavoj Žižek,1949年3月21日—),斯洛維尼亞社會學家、哲學家與文化批判家,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曯目的國際明星之一。他因1989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意識形態的祟高客體》(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而名聲大噪。
他長期致力於溝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將精神分析、主體性、意識形態和大眾文化熔於一爐,形成極為獨特的學術思想和政治立場,在歐美學界取得了巨大成功。
TOP
章節試閱
啟程:轉捩中的事件
“印尼的海嘯奪去了20萬人的生命!”“狗仔隊偷拍到布蘭妮‧斯皮爾斯(Britney Spears)的私處”“我終於意識到應該拋下一切去幫助他!”“殘暴的軍事佔領摧毀了整個國家!”“這是人民的勝利!獨裁者逃走了!”“怎麼會有像貝多芬最後一首鋼琴奏鳴曲這樣美妙的音樂?”
所有這些陳述,都指涉着某些我們視為“事件”的東西──這是個有着《格雷的五十道色戒》般捉摸不定的概念。一個“事件”可以是淒慘嚴酷的自然災害,也可以是媒體熱議的明星緋聞;可以是底層人民的抗爭與勝利,也可以是殘酷的政權更迭;可以是藝術品帶...
“印尼的海嘯奪去了20萬人的生命!”“狗仔隊偷拍到布蘭妮‧斯皮爾斯(Britney Spears)的私處”“我終於意識到應該拋下一切去幫助他!”“殘暴的軍事佔領摧毀了整個國家!”“這是人民的勝利!獨裁者逃走了!”“怎麼會有像貝多芬最後一首鋼琴奏鳴曲這樣美妙的音樂?”
所有這些陳述,都指涉着某些我們視為“事件”的東西──這是個有着《格雷的五十道色戒》般捉摸不定的概念。一個“事件”可以是淒慘嚴酷的自然災害,也可以是媒體熱議的明星緋聞;可以是底層人民的抗爭與勝利,也可以是殘酷的政權更迭;可以是藝術品帶...
»看全部
TOP
目錄
啟程:轉捩中的事件 / 001
第一站:架構、重構與建構 / 008
第二站:幸福之過 / 034
第三站:自然化的佛教 / 056
第四站:哲學三事件 / 076
轉乘站4.1──真理令人痛苦 / 078
轉乘站4.2──事件性的自我 / 089
轉乘站4.3──錯誤出真知 / 098
第五站:精神分析三事件 / 113
轉乘站5.1──實在:直面事物 / 119
轉乘站5.2──象徵:新的和諧 / 132
轉乘站5.3──想像:三聲響 / 149
第六站:事件的撤銷 / 157
終點站:“好好注意!” / 174
第一站:架構、重構與建構 / 008
第二站:幸福之過 / 034
第三站:自然化的佛教 / 056
第四站:哲學三事件 / 076
轉乘站4.1──真理令人痛苦 / 078
轉乘站4.2──事件性的自我 / 089
轉乘站4.3──錯誤出真知 / 098
第五站:精神分析三事件 / 113
轉乘站5.1──實在:直面事物 / 119
轉乘站5.2──象徵:新的和諧 / 132
轉乘站5.3──想像:三聲響 / 149
第六站:事件的撤銷 / 157
終點站:“好好注意!” / 174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斯拉沃熱.齊澤克
- 出版社: 香港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17-07-07 ISBN/ISSN:978962075712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86頁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西方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