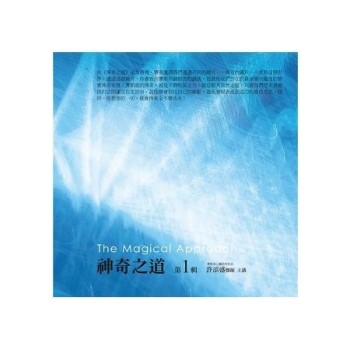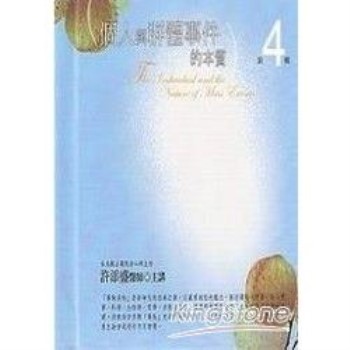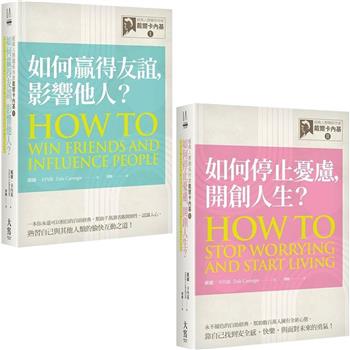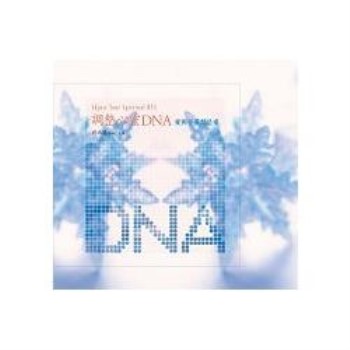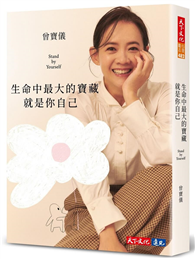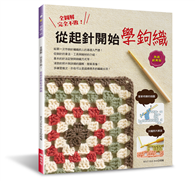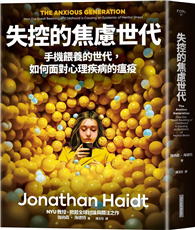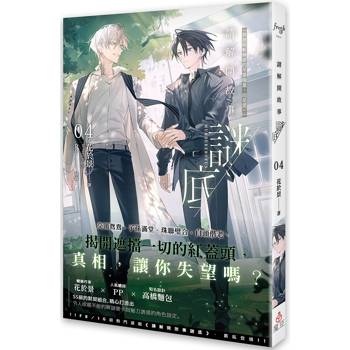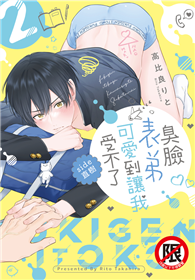導讀
一
《搜神記》是一部最有名的志怪小說。
「志怪」一詞出自《莊子‧逍遙遊》:「齊諧者,志怪者也。」齊諧應為人名。此句意謂: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到了魏晉時期,一些記載鬼神怪異的小說多以「志怪」為名,如祖台之、孔約、曹毗均著有《志怪》,殖氏有《志怪記》,尚有佚名所作《志怪集》、《志怪傳》、《志怪錄》等多種。「志怪」一詞終於從動詞性辭語一變而為書名的專稱。至唐末段成式才第一次在《酉陽雜俎‧序》中明確提出「志怪小說之書」,將「志怪」與「小說」聯繫在一起,以揭示出這類志怪書的小說性質。到了明代萬曆年間,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中,將小說分為六類,第一類即為「志怪」或「志怪小說」,進一步賦予「志怪」以小說分類學上的確切含義。清代以後編寫的文學史,大多立有「志怪小說」一目。「志怪小說」這一名稱,已為廣大研究者所公認。
志怪小說所反映的對象,多為神仙鬼魂、精怪妖異、凶祥卜夢,以及殊方異物之類,用以泛指社會上和自然界一切反常現象,包括非常之事、非常之物和非常之人。古人把它們記錄下來,一是出於獵奇。因為怪異之事,可以滿足人們的好奇心。而當時由於科學不發達,人們常用自己的幻想來解釋當時還不能解釋的各種奇特現象,具有超現實能力的鬼神就是這樣被創造出來。二是為了宣傳。即宣揚有神論,宣揚佛道等宗教。漢以前原始宗教的一個基本觀念就是萬物有靈論。漢以後道教開始形成,佛教隨之傳入中國。佛道思想及其神仙系統深入人們日常生活之中,鬼神觀念更成為人們的普遍認識。魏晉及南北朝的志怪小說,都包含有不少的宗教內容和宗教觀念。但是,我們也不能把凡是出現了鬼神怪異之類的文字,不加區別地一概斥之為宗教迷信;其中更多的應該是來自生活、來自歷史的東西,它還表現了人類的想像力,是在有神論或宗教觀念支配下的一種不自覺的藝術創造。古人常常在鬼神幻想中注入自己的美好願望,或者借助鬼神形式以表現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抨擊。而且,作為文學作品的志怪小說,是中國古小說的早期形式;它以大量的虛構、奇幻的境界、離奇的故事、簡潔的語言、優美的文筆,為中國小說奠定了發展的基礎。正因為如此,志怪小說才一直流傳下來,並獲得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喜愛,至今仍誦讀不衰。志怪小說的這一永恆的魅力就在於「波譎雲詭的豐富幻想和短小精悍的藝術描寫。豐富奇麗之幻想足使人置身玄虛之境而睹莫測之奧,優美雅潔的文筆亦令人含英咀華而口吻生香。」
志怪小說,萌芽於先秦,形成於兩漢,繁榮於魏晉南北朝。先秦志怪極少,且多已散失不存。僥倖保存的有「古今語怪之祖」《山海經》(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這是一部融合神話傳說及博物地理為一爐的「雜體小說」(《四庫總目提要》),形式雖與志怪有所不同,但亦具有志怪小說的某些性質,對後來的志怪影響甚大。兩漢志怪開始定型,作品數量漸多,藝術上也有所進步;但多神仙家言,題材不夠廣泛;體制仍保留著雜史雜傳或方經地志的成分,不夠精純。到了魏晉時期,志怪才大量湧現,今知者約三十種左右。著名的如曹丕《列異傳》、王浮《神異記》、張華《博物志》、郭璞《玄中記》、葛洪《神仙傳》、王嘉《拾遺記》、干寶《搜神記》、陶潛《搜神後記》,以及著者不詳的《西京雜記》等。此時的志怪小說,多為雜記體,體制上已完全定型;題材極為廣泛,舉凡世間奇怪之事,無所不記;篇幅也有所增加,一般都是多卷本;藝術想像力和表現力大為提高,描寫亦趨細致。魏晉志怪得到飛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它們的作者大多是當時著名的學者文人,如曹丕、張華、郭璞、葛洪、王嘉、干寶、陶潛等,都是有名的詩人、學者或歷史家。著名人物的參與必然極大地提高志怪小說的藝術品味和聲望。這一切都標誌著志怪小說已經從野史雜傳、方經地志中正式分流出來,而成為獨立的文學品類。
魏晉時期志怪小說之所以能夠空前繁榮,也有其深刻的時代原因。這個時期,社會動盪,戰亂不息,朝政黑暗,民不聊生,這正是鬼神傳說孳生的極好土壤。以《搜神記》為例,今存四百六十四篇中,至少有近二百篇與戰亂有關。其次是佛道流行,影響遍及於社會各階層;宗教思想中鬼神顯靈、肉體飛昇、靈魂不死、輪迴報應之類的觀念,成為普遍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宗教的盛行,造成了大批鬼神傳說的出現和流傳。侈談鬼神,稱道靈異,成為一時風氣。此外,談風的盛行,也有助於鬼神傳說的流傳。魏晉談風,包括清談和閒談兩類。清談用以品評人物或談論玄理,對軼事小說影響較大。而閒談多以「民間細事」、「淺俗委巷之語」為內容,包括「神鬼之情況、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抱朴子‧疾謬》)等屬於志怪小說的描寫對象。這些奇特之事借談風之助才得以廣泛流傳,並迅速集中到文人學者手中,使之匯聚成書。
在諸多的魏晉志怪小說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搜神記》。
二
《搜神記》的作者是東晉初著名史學家干寶。
干寶,字令升,新蔡(今屬河南省)人。祖父干統,仕吳為奮武將軍、都亭侯。父干瑩,仕晉為丹陽縣丞。干寶大約生於西晉太康、元康年間(即西元二八〇二九九年),唯具體生年則不可考。晉愍帝建興元年(西元三一三年),由於鎮東將軍諮祭酒華譚的推薦,出任佐著作郎,開始步入仕途。兩年之後,他參與平定江南杜弢之亂,「有功,賜爵關內侯」(《晉書‧干寶傳》)。東晉元帝初年,中書監王導推薦他升任著作郎,主修國史。此後數年,他由於「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本傳),大概擔任過一段時期的地方官。晉成帝咸和元年(西元三二六年),司徒王導請他擔任司徒府右長史。歷官至散騎侍郎。以後的事蹟,由於資料缺乏,已無從查考。他的卒年,一般認為在東晉穆帝永和末年前後(永和十二年為西元三五六年)。
干寶一生著作,除《搜神記》之外,還有編年體西晉史《晉紀》二十卷,所記從西晉宣帝(司馬懿)迄於愍帝,共五十三年,已佚;僅存〈總論〉一篇及散見於《三國志》裴注、《文選》注、《世說新語》注和《初學記》、《太平御覽》中的一些片段。另有《春秋左氏義外傳》十五卷、《周官禮注》十二卷、《周易注》十卷、《史議》及文集若干,都已散失不存。留存下來較為完整的著作,就是這一部《搜神記》。
《搜神記》的寫作時間,根據《文選集注》中江淹〈擬郭弘農游仙詩〉注引干寶《搜神記‧序》曰:「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發憤焉。」由此可以推定:干寶在東晉元帝建武年間(西元三一七三一八年)就開始醞釀和準備,當時他擔任著作郎,主修國史,能廣泛接觸圖書祕籍,他當然會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為此書搜集材料,進行創作。至於最後成書,一般認為在東晉穆帝永和初年(永和元年為西元三四五年)。因為,干寶在成書之後,曾將此書「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劉惔卒於永和二年(西元三四六年)到永和五年(西元三四九年)之間。故至遲當成書於永和初年。前後寫作,幾近三十年。可見,《搜神記》應該是干寶以畢生精力精心結撰的一部重要作品。
干寶撰寫《搜神記》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搜神記‧序》)。受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干寶也是個有神論者,他愛好陰陽術數,醉心於京房、夏侯勝之學。據《晉書》本傳記載:他家中還出現過兩件奇怪之事,一件是他父親有個寵婢,父死埋葬時,其母出於妒忌,將此婢推入墓中。十多年以後,母死合葬,掘開父墳,此婢尚在,一天後蘇醒。自言在墓中其父經常給她飲食,恩愛之情與生前一樣;還告訴她家中吉凶之事,這些事都與實際情況完全相符。另一件事是,干寶之兄曾因病氣絕,但軀體不冷,幾天之後才復甦,說曾看見天地間鬼神之事,好像做夢一樣,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這兩件事顯然不是事實,而是出於某種附會,但干寶卻深信鬼神是確實存在的。他搜神記異,目的正是為鬼神靈異提供大量的例證。雖然他也承認,他所記載的並非全都可信;傳聞失真之處,在所難免,但他確信多數是屬實的。所以,他並不僅僅由於未經核實而拒絕傳聞,他認為:正史尚且不排斥傳聞,就在於這樣做「所失者小,所存者大」,為此他「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故《晉書》本傳也說此書「博采異同,遂混虛實」。但無論是虛妄的還是真實的,他都是以史官的嚴肅態度,以「實錄」的筆法來記載這些神鬼之事。故與他同時代的清談家劉惔在讀過這部書後,稱他為「鬼之董狐」。當時人正是把此書當成一部鬼神的信史來看待;所以《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都把它列入史部雜傳類,直到《新唐書‧藝文志》,才改列入子部小說類,開始承認此書作為小說的虛構性質。
干寶撰寫《搜神記》,其材料來源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承於前載」,即從以往的一些記載中廣為蒐羅。今流行本的四百六十四則中,錄自干寶以前的志怪書及其他書籍的約二百則。二是廣收遺佚,即搜集在民間長期流傳,但尚未形成文字記載的故事和傳說。三是「採訪近世之事」,即訪問記錄產生於當時的一些傳聞。為此,干寶曾經「博訪知之者」,進行過廣泛的調查、采集。他說過:「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均見《搜神記‧序》)為了寫好這部書,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涉獵極為廣泛。這才使得此書成為漢晉以來鬼神傳聞的總匯,志怪的集大成之作。
三
據《晉書》說:干寶「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三十卷」。可見原書應為三十卷本。《隋書‧經籍志》與兩《唐書‧藝文志》亦著錄為三十卷。這說明直到北宋初年,這部三十卷本還一直完整地保存下來。此後便開始散失,故後來的《宋史‧藝文志》著錄「干寶《搜神總記》十卷」,又稱「不知作者」,前後矛盾。《崇文總目》著錄亦同,並注云:「不著撰人名氏,或題干寶撰,非也。」這個十卷本的《搜神總記》,也許是干寶書的殘本,也許是另外的一種,現已無法考定。到了明代,高儒《百川書志》著錄為二卷,稱干寶編。《趙定宇書目》著錄《搜神記》一本。這些大約是干寶原書的殘本。這說明干寶原書從北宋到明已經大量散失,留存下來的已經不多了。
但是到了明萬曆中,胡震亨刊刻《祕冊匯函》,其中搜集一部《搜神記》竟有二十卷之多。此後不久,毛晉又將這部二十卷的《搜神記》刻入《津逮祕書》之中。一般研究者認為,這已經不是干寶原書,而是明人胡應麟的一個輯錄本。據胡應麟《甲乙剩言》云:
姚叔祥見余家藏書目有干寶《搜神記》,大駭,曰:「果有是書耶?」余應之曰:「此不過從《法苑》、《御覽》、《藝文》、《初學》、《書鈔》諸書中錄出耳。豈從金函石匱、幽巖土窟中掘得耶?」大抵後出異書,皆此類也。
細味上文口氣,這個輯錄者很可能就是胡應麟自己。他輯錄的依據除了文中列舉了的五部古籍之外,還遺漏了一部比較重要的共五百卷的《太平廣記》。另外,他手邊可能還有幾種流傳到明代的《搜神記》殘本。由於輯錄者「多見古籍,頗明體制」(《四庫總目提要》),加以文筆流暢,態度嚴謹,因此,這個輯本雖非原書,但卻接近原書。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一八云:「余謂此書似出後人輯補,但十之八九出於干寶原書。」這一看法大體上是符合事實的。
這個二十卷本共收四百六十四則,其中見於上述諸書者共達三百零七則,接近三分之二。不見上述諸書徵引者,還有一百五十七則。這一百五十七則中,有的可能是輯錄者誤收,如卷三〈費孝先之卦〉(六五),費孝先是北宋時人,距干寶死後八百餘年,決不可能出自干書。實出宋人章炳文《搜神祕覽》,可能因書名相似而誤收。卷一〇〈夢入蟻穴〉(二五五),是後魏莊帝永安年間事,時代在干寶死後。《太平廣記》卷四七四引自《窮神祕覽》,應非干寶原書。但宋人《類說》、《紺珠集》均作引自《搜神記》,可見此則誤作《搜神記》中篇目,由來已久。又如卷二〈夏侯弘見鬼〉(四八),《太平廣記》卷三二二引自《志怪錄》。文中言「鎮西將軍謝尚」,謝封鎮西將軍在永和十一年(西元三五五年),應在《搜神記》成書之後。卷四〈河伯招婿〉(七六),《太平廣記》卷二九五引作《幽明錄》。這些都應該是誤收。但這類有可靠根據證明確係誤收者,最多不過二三十則。而其餘更多的部分很可能是收自流傳到明代的一些《搜神記》殘本。這說明了輯錄者是在殘本基礎上再從諸書輯錄而成。由於輯錄者本人就是個學者,態度嚴肅而認真,閱讀廣泛,蒐羅細致而又比較謹慎,這才使得這個二十卷本成為宋以後的一個最完備的刊本,也是我們目前能夠看到的最好的,甚至是唯一接近於原書的一個本子。這個二十卷本理所當然地成為本書所根據的底本。
儘管這個二十卷本是當前能夠找到的唯一善本,但它與干寶原書畢竟有許多不同。原書應該是以故事內容分類相從,類為一篇,篇有目,解題有序論。今知所分之篇及篇目者凡四:即〈變化篇〉、〈妖怪篇〉、〈感應篇〉及〈神化篇〉。今知留存之序論有二:一為卷一二〈五氣變化論〉(三〇〇),實為原書〈變化篇〉之序論。一為卷六〈論妖怪〉(一〇二)也許還應包括〈論山徙〉(一〇三),實為原書〈妖怪篇〉之序論。從目前已知的這四個篇目、兩篇序論中可以推知:干寶原書乃是一部有組織、有一定體系、規模宏大、結構嚴密之書,只是其本來面目已經無法恢復了。到了劉宋時期,臨川王劉義慶編撰《世說新語》時,也採用了這種按內容分類,以類相從為篇、篇有標目的體制,這很可能並非劉義慶的獨創,而是受干寶《搜神記》影響所致。僅從體制的獨創性這一點看,干寶《搜神記》對後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流傳至今以《搜神記》為書名的還有另外兩種:一為八卷本,最早見於明萬曆年間商濬所輯之《稗海》,後又收入《廣漢魏叢書》、《龍威祕書》等。這應是明人贗本,而不是干寶原書之殘卷。全書共四十則,僅有十二則見於二十卷本,且文字差別較大。還有不少屬東晉以後事件,並多用北朝及隋唐時地名。故此書另有作者,與干書關涉不大。另一種為西元一八九九年從敦煌石室中發現的《搜神記》殘本一卷,題為句道興撰。此書文字通俗,「包含著變文的原始材料」(王慶菽《敦煌變文集‧敘例》),書中避唐諱,則句道興至遲當為唐人。全書共三十五則,有二十二則不見於二十卷本。相同的一些條目文字出入也相當大,足以證明此書也不是干寶原書之殘卷。
這一切都說明:這個二十卷本雖非干寶原書,但卻是經明人輯補、整理過的比較接近原書的唯一本子。
四
本書所採用的二十卷本雖非原書,也未採用按內容分類、以類相從的體制,僅僅用分卷編寫的方法;但仔細閱讀收入各卷的一些故事,其內容還是比較接近的。全書卷與卷之間,大體上還是有個分工;內容相同或相近者總是被編輯在同卷或相鄰卷內。這也許是輯錄者獨出心裁的設計,但我認為更大可能是由於輯錄者受到手邊的一些原書殘卷的啟發。
按故事的內容性質劃分,二十卷本《搜神記》大致可以分成以下的六個部分:
甲、從卷一至卷五,多為神仙、術士及其神異事蹟。其中有神農、赤松子、王子喬、彭祖之類古代神仙,也有劉根、王喬、左慈、于吉、葛玄、吳猛之類漢魏時晚出的神仙或術士。還有海神、水神、廬山使君、蔣山神、黃公、丁姑、竈神、蠶神之類的民間神仙。所敘之事多為法術變化、神靈感應之類,偶亦有人神結合、仙凡溝通的愛情故事。如卷一〈董永和織女〉、〈杜蘭香與張傳〉、〈弦超與智瓊〉等,都能突破仙凡阻隔,達到人神相愛的結果。
乙、卷六到卷一〇,多為妖祥符命、卜筮夢兆之事,材料大多來源於前後《漢書》的〈五行志〉,簡陋破碎,大都缺乏故事性,價值不高。
丙、卷一一,主要是歷史傳說和故事。如熊渠子射石虎、養由基射白猿、古冶子殺黿、萇宏化碧、何敞消災、王祥剖冰、郭巨埋兒、樂羊子妻賢孝等等,其中不少宣揚了封建道德觀念,但也有不少內容精彩的篇章,如韓憑夫婦的傳說、東海孝婦的傳說和干將莫邪的傳說等,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很高。
丁、卷一二至卷一四,主要是各類精怪及靈奇之物、變異傳說。如卷一二中的賁羊、地狼、霹靂、貙虎、冶鳥、鮫人、短狐、鬼彈,卷一三中的澧泉、劫灰、餘腹、青蚨、火浣布等,卷一四則多為各類精怪神話,如盤瓠神話、蠶馬神話、嫦娥奔月神話,都較有意義。
戊、卷一五至卷一九,多記載鬼魂妖魅的故事;其中以鬼魂較多,也有不少花妖狐魅。如驢精度朔君、飯臿怪、杵精細腰、怒特祠梓樹精、司徒府蛇怪、樹神黃祖、羊精高山君、木精彭侯、田琰及來季德家之狗妖以及張華、劉伯祖、郅伯夷、胡博士諸篇中的狐精。這些鬼物和妖精,具有不同的稟性和行為;它們有善有惡,有損人害人者,也有愛人助人者。數量多,佳作也不少。如〈紫玉韓重〉、〈盧充幽婚〉、〈談生妻鬼〉、〈駙馬都尉〉等篇,都寫人鬼相戀;〈王道平妻〉、〈賈文合娶妻〉、〈李娥復生〉、〈戴洋復活〉諸篇,都寫死後復生;〈秦巨伯鬭鬼〉、〈西門亭鬼魅〉、〈安陽亭三怪〉、〈吳興老狸〉諸篇,都寫了鬼魅作祟;而〈宋定伯賣鬼〉、〈鍾繇殺女鬼〉、〈張華擒狐魅〉、〈宋大賢殺鬼〉、〈郅伯夷擊魅〉、〈謝鯤獲鹿怪〉、〈李寄斬蛇〉諸篇,內容都是寫古代人物憑藉自身機智和勇敢,與鬼魅相鬥,並將其擒獲殺滅的故事。以上各種內容,思想及藝術價值都較高,大多可歸入《搜神記》中比較優秀的篇章中。
己、即卷二〇,專載動物報恩報仇之類故事,以表現善惡均有報的主旨。因果報應,這乃是佛家觀念,《搜神記》中確實存在此類佛家思想。但是,本卷的一些故事主要表現的是普通民眾的善惡觀和是非觀。因為,像〈孫登治病龍〉、〈蘇易助虎產〉、〈鶴銜珠報恩〉、〈黃衣童子〉、〈隋侯珠〉、〈孔愉放龜〉、〈古巢老姥〉、〈蟻王報董昭之〉、〈義犬冢〉、〈華隆家犬〉、〈螻蛄神〉諸篇,寫動物報恩;〈猿母猿子〉、〈虞蕩獵麈〉、〈華亭大蛇〉以下諸篇,寫動物報仇。內容都是善惡得果報於生前,而沒有涉及六道輪迴之類的冥報。
以上各類神怪故事,無可否認地多少會滲透著某些宗教迷信的思想:或鼓吹丹鼎符籙、服藥求仙,或宣揚天堂地獄、靈魂不滅,或談論巫鬼妖魅,或誇飾殊方異物,目的都在於證明神仙及幽冥世界的實有和鬼神靈異的感應。但是,由於其中多數故事採自民間傳說或歷代逸事,不少出於民眾口頭創造,故而多少會反映出一定的時代的政治或文化狀況,必然具有某些現實感,蘊含著豐富的社會內容,具有積極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搜神記》之所以能夠傳誦不衰,其主要原因即在於此。
《搜神記》中的積極內容,主要表現在如下的幾個方面:
第一、《搜神記》中不少篇目,透過幻想形式,能對當時社會黑暗、民生疾苦,作出某些反映;從而揭露了王侯貴族的凶殘暴虐和荒淫墮落,並借助神異情節,以表現民眾的憤怒和反抗。如卷一一〈三王墓〉(二六六),寫善鑄寶劍的干將被楚王無理殺害,其子赤比用其父保存下來的一把雄劍自刎,並親手將自己的頭與劍交付與允諾為其報仇的山中俠客。俠客將其頭獻給楚王。楚王以湯鑊煮頭,三日不爛。楚王前往臨觀,俠客用劍殺楚王,並自刎其頭。三頭均墜湯中,頭爛不可辨識。只好一同埋葬,故名「三王墓」。這個故事,悲壯感人;不僅鞭撻了楚王的凶殘暴虐,而且頌揚了赤比至死不變的復仇精神,以及山中俠士不吝生命、見義勇為的英雄氣概。同卷〈相思樹〉(二九四),寫宋康王霸占韓憑妻何氏,韓憑含憤自殺。何氏趁與康王登臺觀景之時,也跳臺自盡。遺書要求與韓憑合葬。康王大怒,有意把他們分葬兩處,並說:「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結果:
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
這是一個纏綿悱惻的愛情悲劇故事。作品集中塑造了何氏這一「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偉大女性。她忠於愛情,堅定不屈,不惜以身殉情,但仍死而不改其初衷,表現了崇高的思想品德。此外,卷一〈左慈神通〉(二一)、〈于吉求雨〉(二二)兩篇,均以歷史人物為藍本,並與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相出入,但都寫出了這兩位術士非凡的法術變化,特別突出了他們對獨霸一方、剛愎自用的軍閥的冒犯和報復,從而表現了他們對那些掌握生殺大權的專制權威的蔑視和反抗。
在封建社會裡,不僅這些侯王軍閥殘暴成性,就是那些助紂為虐的貪官汙吏也無不腐敗已極。他們昏庸愚昧,妄作威福,草菅人命,無惡不作。如邛都縣令因所乘之馬為蛇所殺,尋蛇不見,乃憤而殺害曾餵養過此蛇的老姥,致令邛都城陷為湖(〈邛都陷湖〉四六三)。高要縣鵠奔亭亭長龔壽為奪取一百二十疋繒帛,竟殘忍地殺死了兩名弱女子,致令被害者的鬼魂出來訴冤(〈鵠奔亭女尸〉三八四)。(〈東海孝婦〉二九〇)中孝婦周青被昏庸太守屈打成招,判為死罪。負屈者臨刑時發下重誓:立十丈竹竿,以懸五幡,若為冤枉,血當順竿而上。後來果然如此,且當地從此大旱三年。這些故事都深刻揭露了封建吏治的黑暗腐敗,進而表達廣大民眾的怨憤和不平。
第二、由於人們對黑暗現實的厭惡,因而產生一種對於無暴政、無苛斂、無壓迫,人們自食其力、和睦相處的理想社會的嚮往。《搜神記》中不少篇目借助仙境或遠離人世的幻想世界,或異域殊方以表達對這種和平、寧靜、幸福的生活的羨慕。如卷末〈劉晨阮肇入天台〉的故事(又見《幽冥錄》),劉阮共入天台山,在溪邊遇見兩個仙女,結為夫妻,過著遠離人世、怡然自樂的生活,半年後返回,但「鄉邑零落,已十世矣」。而〈董永和織女〉(二八)、〈園客養蠶〉(二七)、〈楊伯雍種玉〉(二八五)等三篇的男主人公,都是善良而又貧困的農夫,都以誠實的工作態度,獲得了仙人的幫助,因而得以改善自己的處境,擺脫貧困,甚至得以飛昇成仙。這多少表現了當時處在困境中的人要求改變生活環境的理想。由於魏晉時期戰亂頻繁,社會動盪,人們嚮往太公望治理下灌壇的那種「風不鳴條」,即風調雨順的太平治世(見〈太公望為灌壇令〉七三)。由於科賦繁重,民不堪命;故而在〈盤瓠子孫〉(三四一)這則主要敘述蠻夷起源的神話中,也突出強調了他們的那種沒有租稅、沒有關隘阻隔,即「田作賈販,無關繻符傳租稅之賦」的「不常之律」。
第三、歌頌美好的愛情,表達了男女青年對婚姻自由的強烈追求和排除干擾、雖死不變的堅貞。這也是《搜神記》中一個十分突出的主題。如〈王道平妻〉(三五九)、〈紫玉韓重〉(三九四)、〈駙馬都尉〉(三九五)、〈談生妻鬼〉(三九六)、〈盧充幽婚〉(三九七)均寫人鬼相戀。前二篇敘封建家長的干預導致女兒的死亡;但由於受到情人的精誠所感,終於得以使其鬼魂從墳墓中走出來與之相會。紫玉邀韓重同入冢中,「與之飲讌,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文榆則還陽再生,與王道平終成眷屬,結為一對美滿夫妻。團圓的幸福加深了人們對紫玉之父吳王夫差不許婚姻、文榆的父母強迫改嫁的行徑的不滿。〈駙馬都尉〉以下三篇主要寫鬼魂主動求偶。三篇中的男主角:辛道度、談生、盧充都是門第不高的貧苦書生。而三篇中的女主角:秦文王女、睢陽王女和崔少府女溫休,則都是出身於高門的貴族女鬼。她們在陽世時未能獲得愛情的幸福,只有在作了鬼以後才能徹底地擺脫人間社會的種種約束和偏見,敢於主動地自由擇偶。她們不但要克服幽冥阻隔,還要突破門第懸殊。三篇作品都讚揚了這種不受傳統觀念約束的自由愛情。在〈杜蘭香與張傳〉(三〇)、〈弦超與智瓊〉(三一)、以及前面提到的〈園客養蠶〉、〈董永和織女〉等篇中都寫了人神相戀。天上的神女為了要擺脫生活的「孤苦」,而「下嫁從夫」,與凡人相戀。作品充分展現了這種愛情生活的幸福美滿。當「天上玉女」首先降臨弦超的夢境之中:
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美異,非常人之容。覺寤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
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之衣,姿顏容體,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壺、榼,青白瑠璃五具。飲啖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不謂君德,宿時感運,宜為夫婦。……」
這些神女都能給戀人以各種幫助,或使之改善體質,生活富裕;或使之脫離困境,得以贖身;或使之延年益壽,同登仙界。幸福的愛情自然能帶給人以更多的幸福。《搜神記》正是通過這些奇幻的描寫以表達對愛情的歌頌。
第四、對於各種理想品質的表彰和頌揚,這也是《搜神記》中一個比較常見的主題。這些理想品質,例如像忠誠、孝順、友愛、信用、廉潔、堅貞、勇敢、堅毅、慈愛、無私和無畏等等,都屬於傳統道德範疇,是塑造我們民族高尚情操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例如卷一〈焦山老君〉(一三):
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穿,當得道。」積四十年,石穿,遂得神仙丹訣。
短短四十餘字,表面上寫的是獲得「神仙丹訣」的途徑,實際上是歌頌焦山學道者那種堅忍不拔的毅力,木鑽穿石,四十年如一日的恆心。這正是中華民族可貴的品質之一。又如〈張璞二女〉(七八)寫張璞之女因戲耍而接受廬山使君的聘禮,其妻不忍割捨,乃投侄女於江以替代,張璞發現之後怒說:「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己女於江,因而感動了廬山使君將二女奉還。這充分表現了守信用、重然諾的高尚品質。此外如樂羊子妻的廉潔、堅貞,范式、張劭的感人至深的友誼,郭巨對兄弟的禮讓,庾衮不畏時疫、照顧其兄的情誼,叔先雄捨身投江以尋父屍的至孝,還有王祥、王延、楚僚等人為後母剖冰、臥冰求鯉所表現的孝心,以及徐栩之執法詳平、蝗不過境,諒輔之捨身祈雨、為民請命中所表現出的那種愛民如子的崇高品質(以上均見卷一一有關各篇),這些理想品質無論對於古今讀者來說,都是富有教育意義的。
這些優秀品質,不僅體現在人身上,也能體現在某些靈異的動物身上。《搜神記》中也有少數篇章寫到了動物與動物或動物與人交往之中所表現的某些值得肯定的品質。如卷一四〈蘭巖雙鶴〉(三五三)就著重表現雙鶴之間那種堅貞不渝的夫婦情誼。由於「一鶴為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其年歲也」,這種永恆不變的悼念之情令人感動。同卷〈竇氏蛇〉(三四七)寫竇奉之妻產一蛇,後來竇奉妻死將葬之時,此蛇徑來棺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狀若哀慟。有頃而去」。蛇對生母的孝心,因母死而悲痛至極,一如人間孝子。卷二〇還寫了很多動物報恩的故事,如楊寶救雀,銜環以報;隋侯醫蛇,報以徑寸之珠;噲參救鶴,亦報以明珠;蘇易為虎接生助產,虎乃「再三送野肉於門內」。知恩報恩,正體現了這些動物的正直和善良。其中,〈義犬冢〉(四五七)一則,尤為感人。李信純因飲酒大醉,臥於草中,時大火突發;其犬「黑龍」拽衣不動,乃往返於距主人臥處三五十步之溪水中,入水濕身,以身上之水灑主人四圍,才使主人免於大難。而此犬卻由於多次奔走,運水困乏,致斃於主人身側。這種捨身救人、義不顧己的犧牲精神,是可以愧煞世間人的。所以當地太守憐惜地說:「犬之報恩甚于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
第五、儘管作者撰寫此書的目的是「發明神道之不誣」,即宣傳有神論的需要;但是作者同時又是反對那種非其神而祀之的「淫祀」。他曾借仙人杜蘭香之口說:「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故在《搜神記》中,對於那些妖魔鬼魅有意冒充神靈,或民眾由於癡迷無知而妄加崇拜的那些生物,總是加以揭露和嘲笑,使之當場出醜。前者如袁術家走失之羊,冒充神道,自稱「高山君」,大能飲食,受人奉事,終因醉後現形出醜,並被殺滅(卷一八〈高山君〉四三一)。後者如卷五〈張助斫李樹〉(一〇〇),寫農民張助偶將一李核種於空桑之中,使桑中長出一株李樹。又因某一有目疾者在李下許願而目疾自癒。從此以後,「眾犬吠聲」,誇之為盲人復明。「李樹神」之名,喧傳遠近。一年後,張助遠出歸鄉,才指明「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並把它砍掉,才結束了這一幕庸人自擾的滑稽戲,從而表明「妖由人興,神由人崇」的道理。
《搜神記》作者不僅反對「淫祀」,還主張對那些作祟禍人、妄作威福的妖魔鬼魅給以揭露和打擊,以達到除惡務盡的目的。如王臣家的飯臿怪,張奮舊舍之金、銀、錢及杵等妖,安陽城南亭之老蝎、老雄雞、老母豬諸怪,南陽西郊亭、廬陵郡都亭及郅伯夷路過之某亭都有一老狐狸為患,裝神弄鬼,害人不淺,直到被人清除殺滅之後,「其怪遂絕」(以上見卷一八之四一三、四一四、四三八、四二六、四三九及四二七各則)。作者對於那些不畏鬼魅、敢於鬥爭、智勇兼備的人物則給以充分的肯定和讚揚。如〈宋定伯賣鬼〉(三九三)、〈鍾繇殺女鬼〉(三九九)、〈宋大賢殺鬼〉(四二六)、〈郅伯夷擊魅〉(四二七)、〈謝鯤獲鹿怪〉(四二九)、〈田琰殺狗魅〉(四三二)、〈湯應斫二怪〉(四三九)等篇,就表現了宋定伯、鍾繇、宋大賢、郅伯夷、謝鯤、田琰和湯應等人敢於破除迷信、不懼鬼魅的英勇精神。要勇鬥鬼魅,首先必須善於識別鬼魅,撕去它們身上的各種偽裝。如湯應止宿於「常有鬼魅」的廬陵郡都亭中,忽有府君及部郡從事吏夤夜造訪。湯應才起疑心說:「此夜非時,又部郡、府君,不應同行。」知道這是鬼魅。以刀逆擊,果然是老狶、老狸所變化。特別是宋定伯的那種沉著機智,遇鬼不驚而又善於應對並充滿詼諧的性格,終於抓獲了同行的鬼魅。「定伯賣鬼,得錢千五」,這正是當時人對他的讚譽。還值得一提的是〈李寄斬蛇〉(四四〇)篇,故事寫東越國有大蛇為害黎民,地方官聽信巫祝之言,每年送一貧家少女餵此蛇神。少女李寄挺身應募,終於殺死大蛇,為民除害。李寄之所以能取得勝利,正由於在她身上集中體現了我們民族敢於鬥爭的膽略和善於鬥爭的智慧。
五
魏晉志怪還處於中國古小說發展的初期,在形式體制、藝術表現等方面還比較簡單、粗率。一是沒有擺脫「短書」、「叢殘小語」(桓譚《新論》)的格局,篇幅短小,粗陳梗概,多敘事,少描寫,不注意人物形象的刻劃,以情節離奇取勝,但情節又往往極為簡略。二是沒有擺脫史傳文學格局,仍然遵循史家「實錄」體如實記載,僅僅滿足於「有聞必錄」,而排斥有意識的虛構;材料堆砌,以歷史的真實來取代藝術的真實。
《搜神記》是魏晉志怪中的佼佼者。在中國小說史上,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質的作品。它不僅在內容上成為當時志怪的總匯,而且在藝術水準方面,也是整個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成就最高的優秀之作。儘管它並沒有完全擺脫「叢殘小語」和史家「實錄」的格局,但卻能在故事的完整性、注意人物和細節描寫等方面有所增強和提高,從而體現出向唐人傳奇這一比較成熟的中國小說過渡的趨勢。特別是其中的一些優秀篇章,其表現形式、藝術水準,已與後代的志怪和傳奇相差無幾,完全可以列入中國古代比較優秀的文言短篇小說而無愧色。
《搜神記》中的一些優秀篇章初步擺脫了志怪體常見的那種細碎片段的模式,增強了故事的完整性和豐富性,前後連貫,首尾銜接,篇幅加長,情節曲折多變而又渾然一體:大大提高了古小說藝術的成就。例如〈弦超與智瓊〉(三一)、〈胡母班傳書〉(七四)、〈丁姑渡江〉(九七)、〈相思樹〉(二九四)、〈三王墓〉(二六六)、〈盤瓠子孫〉(三四一)、〈王道平妻〉(三五九)、〈李娥復生〉(三六二)、〈蔣濟亡兒〉(三八〇)、〈紫玉韓重〉(三九四)、〈盧充幽婚〉(三九七)、〈張華擒狐魅〉(四二一)、〈李寄斬蛇〉(四四〇)、〈劉晨阮肇入天台〉(卷末)都是此中代表。它們在情節結構上都開始擺脫了「叢殘小語」與粗陳梗概的寫法。例如〈三王墓〉就寫了干將藏劍別妻被害,赤比入山逢俠,俠客攜赤比頭入宮行刺作為開頭、發展和結尾三個部分。這三部分緊密相連,融為一體,完整圓合,一步步把衝突推向高潮。在〈李寄斬蛇〉中,作者先寫官吏的腐朽無能,九女的軟弱被吞嚙作為鋪墊。接著再通過李寄主動應募、智斬大蛇過程的細緻描寫,作為小說的重點,以刻劃李寄沉著機智的性格;最後再寫李寄斬蛇後「緩步而歸」及最後全家受封賞的圓滿結局。不僅故事委曲多姿,引人入勝;而且以九女的怯弱來反襯李寄的勇敢,以李誕家原先的貧困來烘托最後的榮耀,從而形成一篇結構完整、首尾連貫的作品。又如〈弦超與智瓊〉,乃是一篇人神之間的相當完整的戀愛故事。內容可分為成婚、離別、重逢三個部分。他們成婚是前世姻緣所定,只是人神之間,不能生子,但亦不妨礙弦超人世婚姻。後弦超因娶妻而洩露與神女的愛情,才引起神女離去。五年後,弦超離家去洛陽,途中重又相逢。前後往來共三十餘年。這篇小說描寫細緻,敘述宛轉,情節波瀾曲折,神異性大為減弱,人情味得到加強,充分表現了志怪向傳奇演進的軌跡。
《搜神記》中確有不少篇章並不滿足於情節的離奇曲折,進而追求更為廣泛的世俗性,並使世俗性與神異性緊密結合。作者在塑造鬼神狐魅形象常常以現實中的人作為參照,賦予被描述對象以人性的內容和可感的聲容笑貌,用寫人的方法來寫鬼神。如果我們去掉它們身上神異性的一面,剩下來的則完全是人的聲態、感情和靈魂。例如卷三〈顏超增壽〉(五四)一篇,內寫南斗、北斗二仙翁在刈麥地南大桑樹下圍棋,注定會短壽的顏超帶著一壺酒、一斤鹿肉奉上;二仙翁只顧飲酒吃肉,等吃完喝完之後,才發現顏超及其意圖,只好以「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的態度,把本來注定只能活十九歲的文書,「取筆挑上」,改成九十歲。此二人名為神仙,但貪杯好吃、善良豁達之狀,宛如世間和睦可親的老頭子。又如〈胡母班傳書〉(七四)中,胡母班之父的鬼魂,在服勞役時,哀苦百狀。在因賴子求情而得任社公之後,卻又貪戀酒食,忘乎所以,致諸孫死亡略盡,因此而丟官,才又「涕泣」悲哀。雖為鬼魂,但卻活畫出一個市井庸人形象。又如〈張華擒狐魅〉(四二一)中千年得道之斑狐,不僅「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外貌一似翩翩少年,而且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使得當時號稱「博物」的大學者張華也只得「應聲屈滯」。但此狐卻逞才使氣,誇飾炫耀,不納忠言,終遭殺身之禍。這一狐精,從外貌到性格,都更像一個涉世不深而又露才揚己的風流才子。以上三例足以說明:其形雖為神、鬼、妖之類而非人,但其質則為人;有人心、人格、人的感情,甚至人的弱點和缺陷。儘管此類描寫在《搜神記》中還不是多數,但卻標誌著古小說家的注意中心已開始從非人的世界向人的世界轉化。
《搜神記》中不少篇章已開始注意到對場面、動作、情態等方面進行細節性的描寫渲染,以襯托人物性格。如〈三王墓〉(二六六)不僅具體描述了赤比報仇的堅決,不惜以劍自刎。之後還能「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而且,還寫出他的頭被煮時「踔出湯中,躓目大怒」的細節,以突出渲染他的剛烈之氣和對楚王的刻骨仇恨。〈相思樹〉(二九四)寫何氏跳臺前「陰腐其衣」,以表現她的機智和視死如歸的殉情精神。〈趙公明府參佐〉(九八)寫充任參佐之某鬼魂率領眾士卒來到王祐家,「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為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這裡寫眾鬼魂之衣著舞蹈,情態宛然。又如〈千日酒〉(四四七)寫劉玄石因喝了狄希所釀造的千日酒一杯,醉死三年,家人已將他埋葬。狄希來到他家探問:
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爾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
寫墓中薰天之酒氣,彷彿如見;寫劉玄石酒醒後之情態語言,極為傳神。特別是「日高幾許」之問,顯示出他錯把三年當成一宿,錯把墓中當作床上。說明他雖已酒醒,但仍然醉態矇矓。
《搜神記》歷來都受到後人的推崇。唐劉知幾《史通》稱干寶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此書敘事簡潔而又曲盡其情,語言直樸而又雅致清峻。包括那些人物對話,不少地方也寫得生動傳神,如〈秦巨伯鬭鬼〉(三九〇)中,二鬼假冒其孫,責問巨伯說:「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汝。」口吻畢肖,情貌宛然。又如〈倪彥思家魅〉(四〇五),郡中典農認出彥思家魅當是狸物,此魅即到典農家對他說:「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為吏污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要挾恐嚇,目的在於令其箝口,活畫出一幅頑童聲口。此外,還有少數篇章,在散文敘事中,穿插韻文詩歌;開始採韻散結合以打破散文的單調。如紫玉、何氏賦四言詩,智瓊、杜蘭香、崔少府女賦五言詩,詩句皆錄於文中。這不僅增加了文學色彩,而且能進一步描摹主人公內心感情,加強形象塑造的深度。這種韻散結合的寫法,為中國古代敘事性作品提供了一種新的表現手段,並為後來的唐人傳奇,乃至明清章回小說所師承。
《搜神記》在魏晉志怪中獨占鼇頭,對後世影響尤大。它引起許多志怪愛好者和創作者的重視,後來的續作和仿作者如晉末陶潛的《搜神後記》,北魏曇永的《搜神論》,唐句道興的《搜神記》、焦璐的《搜神錄》,還有不著撰人的《搜神摭記》。這些書不僅模仿其內容,而且又襲用其書名。至於另取書名,而在內容體例上與《搜神記》一脈相承的志怪小說,僅六朝時就在六十部左右。可見此書影響之大。至於在題材方面承襲此書者,那就更多了。無論唐人傳奇、宋以後白話短篇小說和元明戲曲,都有不少從《搜神記》中汲取題材,以加工改寫。如卷四〈胡母班傳書〉(七四)演變為唐人李朝威〈柳毅傳〉和元雜劇尚仲賢的《柳毅傳書》,又進而改編成明人傳奇黃維楫《龍綃記》及許自昌《橘浦記》和清初李漁的《蜃中樓傳奇》。卷一二〈猳國馬化〉(三〇八)被改寫成唐人傳奇〈補江總白猿傳〉及宋代話本小說《陳從善梅嶺失渾家》。卷一一〈山陽死友傳〉(二九九)被改編成宋元話本《死生交范張雞黍》和元人雜劇宮大用的《范張雞黍》。卷末的〈焦湖廟玉枕〉演變為唐人沈既濟小說〈枕中記〉及明代湯顯祖傳奇《邯鄲記》。〈董永和織女〉被陸續改編為唐代的《董永變文》、宋話本《董永遇仙記》、明傳奇《織錦記》、《天緣配》,以及後來的黃梅戲《天仙配》。〈相思樹〉被改寫成唐變文《韓朋賦》和元代庾吉甫雜劇《青陵臺》。〈劉晨阮肇入天台〉被改編為明初王子一雜劇《誤入天台》。至於關漢卿雜劇《竇娥冤》取材於本書卷一一〈東海孝婦〉,那更為廣大讀者所熟知。這些都說明了《搜神記》中不少題材都具有較強的生命力。
六
這次校點注譯《搜神記》,主要以明末毛晉《津逮祕書》本為根據,校刊則以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汪紹楹校注本為主,並參考了清光緒年間崇文書局《百子全書》本。這些版本,文字出入均不大。倒是汪紹楹校注本考源鉤沉,對二十卷本本身文字及出處,作了很多有益的考訂,校正了不少錯誤。對此,本書採取擇善而從的態度。考慮到本書只是一部通俗性讀本,不宜作繁瑣引證。因此,凡屬正確的校訂,例如卷一〈雨師赤松子〉中「水玉散」,原文作「冰玉散」;但據《法苑珠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均作「水玉散」。又如卷一八〈郅伯夷擊魅〉中「郅伯夷」,原文作「到伯夷」;但據《後漢書》等,「到」應作「郅」等等。這都是有理有據的校正,本書都加以吸收,直接錄入正文,並在注釋中略作說明。也有一些可取的純文字方面的校正,為避免累贅,減輕讀者負擔,有時在注釋中亦不作說明。
正文中的有關人名,凡屬有史傳可考者,都在注釋中略加介紹。正文中所涉及的地名,一般也按大陸目前行政區劃在注釋中作古今對照。這樣做,目的在於使廣大讀者對書中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及有關人物,增加一些了解。
由於本人才識淺陋,加以注譯匆忙,錯誤之處一定不少,敬希讀者指正。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新譯搜神記(三版)的圖書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新譯搜神記(三版)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以大量虛構的故事、奇幻的境界、離奇的情節、簡潔的語言、優美的文筆,為中國小說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中由東晉著名史學家干寶所撰寫的《搜神記》,是諸多志怪小說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廣搜民間各種關於神異、奇蹟、鬼怪以及神仙方士的傳說,並旁採正史中有關祥瑞、異變的記載,內容豐富生動,異想奇思紛呈,對後世傳奇、小說和戲曲都有深刻啟發與影響,也是研究古代神話和民間傳說的寶庫。本書正文以各善本參校,導讀詳盡,注譯精當,人名、地名可考者皆有注釋,是讀者進入志怪小說瑰奇世界的最佳途徑。
作者序
導讀
一
《搜神記》是一部最有名的志怪小說。
「志怪」一詞出自《莊子‧逍遙遊》:「齊諧者,志怪者也。」齊諧應為人名。此句意謂: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到了魏晉時期,一些記載鬼神怪異的小說多以「志怪」為名,如祖台之、孔約、曹毗均著有《志怪》,殖氏有《志怪記》,尚有佚名所作《志怪集》、《志怪傳》、《志怪錄》等多種。「志怪」一詞終於從動詞性辭語一變而為書名的專稱。至唐末段成式才第一次在《酉陽雜俎‧序》中明確提出「志怪小說之書」,將「志怪」與「小說」聯繫在一起,以揭示出這類志怪書的小說性質。到了明代萬曆年...
一
《搜神記》是一部最有名的志怪小說。
「志怪」一詞出自《莊子‧逍遙遊》:「齊諧者,志怪者也。」齊諧應為人名。此句意謂: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到了魏晉時期,一些記載鬼神怪異的小說多以「志怪」為名,如祖台之、孔約、曹毗均著有《志怪》,殖氏有《志怪記》,尚有佚名所作《志怪集》、《志怪傳》、《志怪錄》等多種。「志怪」一詞終於從動詞性辭語一變而為書名的專稱。至唐末段成式才第一次在《酉陽雜俎‧序》中明確提出「志怪小說之書」,將「志怪」與「小說」聯繫在一起,以揭示出這類志怪書的小說性質。到了明代萬曆年...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導讀
卷一
一、神農鞭百草
二、雨師赤松子
三、赤將子轝
四、甯封子自焚
五、偓佺採藥
六、彭祖七百歲
七、師門使火
八、葛由乘木羊
九、崔文子學仙
一〇、冠先被殺
一一、琴高取龍子
一二、陶安公騎赤龍
一三、焦山老君
一四、魯少千應門
一五、淮南八公歌
一六、劉根召鬼
一七、王喬飛舄
一八、薊子訓飲啖公卿
一九、漢陰生行乞
二〇、卒常生復生
二一、左慈神通
二二、于吉求雨
二三、介琰隱形
二四、徐光種瓜
二五、葛玄法術
二六、吳猛止風
二七、園客養蠶
二八、董永和織女
二九、鉤弋夫人之死
三〇、杜蘭香...
導讀
卷一
一、神農鞭百草
二、雨師赤松子
三、赤將子轝
四、甯封子自焚
五、偓佺採藥
六、彭祖七百歲
七、師門使火
八、葛由乘木羊
九、崔文子學仙
一〇、冠先被殺
一一、琴高取龍子
一二、陶安公騎赤龍
一三、焦山老君
一四、魯少千應門
一五、淮南八公歌
一六、劉根召鬼
一七、王喬飛舄
一八、薊子訓飲啖公卿
一九、漢陰生行乞
二〇、卒常生復生
二一、左慈神通
二二、于吉求雨
二三、介琰隱形
二四、徐光種瓜
二五、葛玄法術
二六、吳猛止風
二七、園客養蠶
二八、董永和織女
二九、鉤弋夫人之死
三〇、杜蘭香...
顯示全部內容
|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