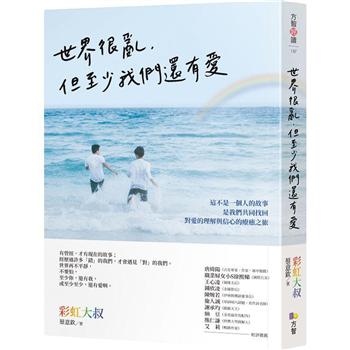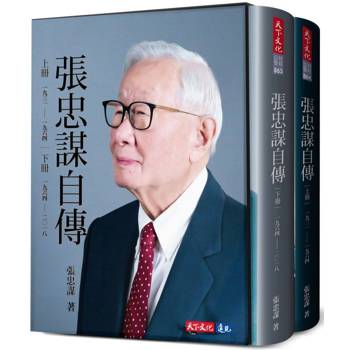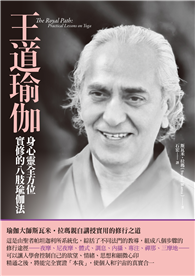自序
完成書稿交付書局後,接獲編輯先生發來的郵件,要求注譯者另寫一篇或長或短的文字,交代撰稿緣起、感想,或研究的心得等,俾使讀者認識,拉近距離。這較之於撰寫書的正文來說,自然是件最輕鬆愉悅的事了。如同讀一本學術著作,最有意思的事情莫過於看「序言」或「後記」—聽作者傾訴一本書背後的人情冷暖,如同冬夜坐在溫暖的壁爐旁,手捧一杯熱飲,與感興趣的人閒話平生。
最近一段時間,碌碌於教學、思考和寫作,對當下關注點之外的事情大多犯迷糊,其中尤其對日期、數字極不敏感,每每總是靠別人提醒。翻出過往的郵件,終於確定接受《新譯法句經》撰作任務的確切日期是一二年十月中旬,當時我還在南京大學讀博士學位。鑑於以往的學術興趣集中在中古這一段,且多年來也並未有所變化,所以我就決心在博士階段更進一步,想把這一時期佛教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做一番相對細緻的清理,當然選擇切入的角度一定是具體而微的。
我原先是做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常常陷入各種文論概念中難以通脫,後來轉入「兩古」專業(古典文學、文獻)學習,就想在文獻基礎上面多用用功。這其實意在遵循太老師程千帆先生留下的教諭,即文藝學與文獻學相結合、「兩條腿走路」。二○一二年的夏天,溽熱無比,我協助我的老師張伯偉教授將國內東亞研究最具實力的研究機構「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從南大鼓樓校區搬遷到仙林校區。大量的中日韓書籍文獻,被逐一下架、封裝、編號、運輸、上架。在這個過程中,我粗粗摸索一過所內的各種研究材料,逐漸開始對「東亞視野中的佛教」這一課題生發興趣,以為這可以成為東亞文明研究的一把鑰匙(日本學者西?定生似乎早也有這樣的提法)。
隨後到來的十月,太陽已然不再毒辣,在新布置完畢的研究所裡,微風吹過,帶來絲絲清涼。某一天,伯偉師大約是看見我在翻閱《大日本佛教全書》,就跟我說有人想請他推薦合適的人來注譯一本佛經,或許你可以試試,藉此也可以再鞏固一下佛教文獻的基礎。幾天之後,收到三民書局編輯先生的郵件,正式邀請參與這本佛經的注譯工作。這樣,一方面有業師的囑託,另一方面又有編輯先生的熱情誠邀,遂恭敬地接受了此項任務。可是坦白地說,當時自己心裡還多少有點猶豫,因為有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即當時我的博士論文計劃正在緊張推進,從時間和精力上說,無法騰出完整的時間專心從事此事。於是,藉編輯先生來南京出差相約見面的時機,我將心中的顧慮說出,孰料得到的回應竟然是莫大的寬容,慨允兩年之內完成即可。
有了這份信任,接下去便是一種見縫插針的工作狀態,伴隨著我的博士論文寫作、答辯、畢業和進入新研究機構工作,注譯的工作時做時輟。直到二○一五年底約定的交稿截止時間,我才完成了全部工作的三分之二。以我的秉性,自然是不願意為自己的拖延尋找借口,遂寫了一封郵件給書局請求再寬限兩個月時間,以便自己利用春節假期專心了結此事,得到的回復依然是理解和寬容。於是,在剛剛過去寒假的一個月時間裡,我全力將本書完成並前後校閱了至少兩遍。
總之,這本小書的撰作,前後歷時兩年多,得到了業師張伯偉教授和三民書局各位編輯的寬容和幫助,使我有精力盡量把它完成得更令人滿意,因此我除去感謝之外,也認為這是一種勝緣!
此外,還需要交代的是,對於《法句經》這樣一部廣受世界佛教信眾喜愛的經典,如何在前人的基礎之上把它注譯得更好?成了我這兩年一直思考的問題。雖然中國詩歌闡釋傳統有所謂「詩無達詁」一說,漢傳佛教也教人根據緣分的深淺自我領悟,不強求統一,但就這樣一部早期佛教經典來說,我以為還是不能將之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即便還有很多沒有被釐清)中抽離出來,淪為一種「自說自話」。正是基於這樣一點考慮,我在具體每章每句的注釋中,盡可能地在校勘文字的基礎上參合各家的意見,給出一種言之成理的注釋和翻譯,必要時還引用其他經典來加以疏解(詳見「導讀」部分說明)。可儘管如此,我同時也自覺,一方面限於自己佛學修養、學術功力和時間精力等方面的原因,本書有些地方的注譯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另一方面,為了照顧通俗性、可讀性和啟發性,本書捨棄了繁瑣的文本校勘記,以及「嚼飯予人」式的「賞析」,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會讓讀者產生困惑。但聊可自慰的是,自己已經盡了最大程度的努力,盡可能不要人為地將讀者引入歧途。知我罪我,其在於此乎。我非常希望得到來自讀者的指謬!
過去冬日的某個深夜,青燈枯坐,專心注譯佛經。一時萬籟俱寂,除了窗外簌簌雪落的聲音。信手在稿紙上寫下一句不甚合格律的詩句,或可表達彼時的心境,今錄於此,以備日後紀念—「雙目微茫經卷字,青燈搖曳如來心」。
劉學軍
二○一七年十月十八日於駑馬十駕齋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新譯法句經(二版)的圖書 |
 |
$ 314 | 新譯法句經(二版)
作者:劉學軍 出版社: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11-27 語言:繁體書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新譯法句經(二版)
《法句經》是早期佛典中輯錄出來的佛教格言偈頌集,是一部深受廣大佛教信眾喜愛的經典。《法句經》一度是佛法入門的必讀經典,因為其中有很多偈頌是佛陀所說,有的即使不是佛陀所說,也比較直接地反映出佛陀的思想智慧。而對於一般的讀者來說,由於早期佛教思想,比較切近人類本真的心理狀況和倫理需求,所以這部經典也能為現代人提供有益的道德啟發和人生智慧的滋養。此外,《法句經》的語言具有高度的濃縮性、鮮明的形象性,以及回環往復的語體化的文學特徵,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肯定能獲得極佳的閱讀體驗和審美享受。
作者簡介:
劉學軍,一九八二年生,安徽六安人,南京大學博士,現就職於江蘇第二師範學院文學院,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研究領域在中古佛教與文學、東亞漢文學等方面。在《文學遺產》、《中華文史論叢》等學術刊物發表有論文十餘篇。
作者序
自序
完成書稿交付書局後,接獲編輯先生發來的郵件,要求注譯者另寫一篇或長或短的文字,交代撰稿緣起、感想,或研究的心得等,俾使讀者認識,拉近距離。這較之於撰寫書的正文來說,自然是件最輕鬆愉悅的事了。如同讀一本學術著作,最有意思的事情莫過於看「序言」或「後記」—聽作者傾訴一本書背後的人情冷暖,如同冬夜坐在溫暖的壁爐旁,手捧一杯熱飲,與感興趣的人閒話平生。
最近一段時間,碌碌於教學、思考和寫作,對當下關注點之外的事情大多犯迷糊,其中尤其對日期、數字極不敏感,每每總是靠別人提醒。翻出過往的郵件,終於確定接...
完成書稿交付書局後,接獲編輯先生發來的郵件,要求注譯者另寫一篇或長或短的文字,交代撰稿緣起、感想,或研究的心得等,俾使讀者認識,拉近距離。這較之於撰寫書的正文來說,自然是件最輕鬆愉悅的事了。如同讀一本學術著作,最有意思的事情莫過於看「序言」或「後記」—聽作者傾訴一本書背後的人情冷暖,如同冬夜坐在溫暖的壁爐旁,手捧一杯熱飲,與感興趣的人閒話平生。
最近一段時間,碌碌於教學、思考和寫作,對當下關注點之外的事情大多犯迷糊,其中尤其對日期、數字極不敏感,每每總是靠別人提醒。翻出過往的郵件,終於確定接...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新譯法句經目次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自序
導讀
卷上
無常品 一
教學品 一二
多聞品 二五
篤信品 三四
戒慎品 四三
惟念品 五○
慈仁品 五五
言語品 六四
雙要品 六九
放逸品 八○
心意品 八八
華香品 九三
愚闇品 一○二
明哲品 一一○
羅漢品 一一九
述千品 一二四
惡行品 一三三
刀杖品 一四四
老耄品 一五二
愛身品 一五八
世俗品 一六三
卷下
述佛品 一六九
安寧品 一七八
好喜品 一八四
忿怒品 一八九
塵垢品 一九九
奉持品 二○六
道行品 二一○
廣衍品 二二二
地獄品 二二九
象喻品 二三七
愛欲品 二四五
利養品 二五七
沙門...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自序
導讀
卷上
無常品 一
教學品 一二
多聞品 二五
篤信品 三四
戒慎品 四三
惟念品 五○
慈仁品 五五
言語品 六四
雙要品 六九
放逸品 八○
心意品 八八
華香品 九三
愚闇品 一○二
明哲品 一一○
羅漢品 一一九
述千品 一二四
惡行品 一三三
刀杖品 一四四
老耄品 一五二
愛身品 一五八
世俗品 一六三
卷下
述佛品 一六九
安寧品 一七八
好喜品 一八四
忿怒品 一八九
塵垢品 一九九
奉持品 二○六
道行品 二一○
廣衍品 二二二
地獄品 二二九
象喻品 二三七
愛欲品 二四五
利養品 二五七
沙門...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