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合夥創立、獨資經營到災後重生,
一家走過一甲子歲月的咖啡館,承載著許多時光故事與重量。
一杯咖啡與一份甜點,是白俄羅斯股東們的辛酸與鄉愁,
二、三樓的雅座,是文學作家們耙梳文稿的書桌或編輯台。
這裡具備濃濃的人情味,許多精采的人生故事在此不斷上演。
回顧明星咖啡館的傳奇,有如享受著一杯香氣四溢的人文史咖啡。
這一切的背後,都有著創辦人的智慧與膽識,情義及精神。
全書收錄了明星咖啡館創辦人簡錦錐至第三代李柏毅的人生故事。並附有多款珍貴照片、明星咖啡館著名點心、以及藝術家第三代柏毅的優異畫作。
在咖啡飄香的同時,明星咖啡館裡的故事,依舊繼續發光發熱……
名人推薦
季季、黃春明 推薦
走進明星,坐在三樓的火車座,依著冰涼的、墨綠花紋的大理石桌面,慢慢的寫;那是我最放鬆,最愉悅的寫作時光。——季季
對作家來說,寫作就好像母雞要找窩下蛋,明星就是我寫作的窩。我可以很安心的在那裡寫作。——黃春明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明星咖啡館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3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 208 ~ 270 | 明星咖啡館
作者:簡錦錐/謝祝芬 出版社: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6-01  3 則評論 3 則評論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明星咖啡館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簡錦錐
1932年生於台北州新莊郡新莊街。畢業於台北一中(今建中)。八歲時隨兄長赴上海,與霞飛路上的ASTORIA咖啡廳有一面之緣。1949年,與俄羅斯皇族後裔艾斯尼先生結緣,並與六位白俄羅斯人於武昌街一段七號合夥開設ASTORIA明星西點咖啡廳。
1951年獨資經營ASTORIA,研發出台灣第一個巧克力蛋糕、戚風蛋糕、瑞士蛋糕與可頌麵包,並首創多層蛋糕製作。爾後,詩人周夢蝶先於咖啡館樓下擺攤,黃春明、林懷民、白先勇、季季、陳若曦、三毛等人先後在此伏案寫作,《文學季刊》創辦人尉天驄、陳映真等人亦曾在明星咖啡館三樓進行編輯。文人雅士及作家接受到簡錦錐的尊重與照顧。
1970年,明星西點咖啡中山北路分店開幕。
1987年,金錢遊戲席捲全台,明星咖啡廳武昌店湧入大批股票族,加上種種因素與壓力,於1989年12月宣告歇業,武昌店與中山北路店同時熄燈。2004年在各界人士的連署下,於2004年,重新點燈開業。
簡錦錐
1932年生於台北州新莊郡新莊街。畢業於台北一中(今建中)。八歲時隨兄長赴上海,與霞飛路上的ASTORIA咖啡廳有一面之緣。1949年,與俄羅斯皇族後裔艾斯尼先生結緣,並與六位白俄羅斯人於武昌街一段七號合夥開設ASTORIA明星西點咖啡廳。
1951年獨資經營ASTORIA,研發出台灣第一個巧克力蛋糕、戚風蛋糕、瑞士蛋糕與可頌麵包,並首創多層蛋糕製作。爾後,詩人周夢蝶先於咖啡館樓下擺攤,黃春明、林懷民、白先勇、季季、陳若曦、三毛等人先後在此伏案寫作,《文學季刊》創辦人尉天驄、陳映真等人亦曾在明星咖啡館三樓進行編輯。文人雅士及作家接受到簡錦錐的尊重與照顧。
1970年,明星西點咖啡中山北路分店開幕。
1987年,金錢遊戲席捲全台,明星咖啡廳武昌店湧入大批股票族,加上種種因素與壓力,於1989年12月宣告歇業,武昌店與中山北路店同時熄燈。2004年在各界人士的連署下,於2004年,重新點燈開業。
目錄
推薦序:
我們的明星歲月/季季
寫作的窩/黃春明
八歲,一個人飄洋過海
囝仔,你要去叨位?
阿公的預言 天頂的掃帚星
收留逃兵四百多天
沒錢,就向天公伯仔要!
俄羅斯奇緣,明星誕生
阿錐抹治ㄟ
飛虎隊運來的馬桶
Lucky Seven vs. 廟沖
六個白俄一個台灣人
俄羅斯股東的異國辛酸淚
落難的俄國皇族
俄國到了,安息吧!
歸化的俄羅斯軍官
回來吧!親愛的尼吉
俄羅斯女的台灣歲月
曾經熱情的蔣方良
一粒鹽巴,一趟霜雪之旅
四樓的太太——瑪蘭
台灣文學作家的窩
樓下擺攤的周夢蝶
《文學季刊》的基地 白色恐怖的陰影
黃春明的育兒桌
阮家的少爺在樓上嗎?
白先勇和ASTORIA的羅宋湯
和《晚安曲》比晚的三毛
明星的滋味,西點的感動
不能看的俄羅斯祕方
越洋連線,台灣首個巧克力蛋糕
蔣中正的最後一個生日蛋糕
保存二十年的蛋糕盒
幕落又起,明星重生
走味的咖啡,歇業的無奈
一場火災,三百人連署
運回老桌椅,重新開幕
影視明星,再聚明星
天才畫家誕生,愛在當下
爸爸,醫生說他是自閉兒
從重症到十大傑出青年
與羅馬教宗一抱
愛在當下,活在當下
附錄
明星咖啡與簡錦錐大事紀
享食明星 一口一故事
我們的明星歲月/季季
寫作的窩/黃春明
八歲,一個人飄洋過海
囝仔,你要去叨位?
阿公的預言 天頂的掃帚星
收留逃兵四百多天
沒錢,就向天公伯仔要!
俄羅斯奇緣,明星誕生
阿錐抹治ㄟ
飛虎隊運來的馬桶
Lucky Seven vs. 廟沖
六個白俄一個台灣人
俄羅斯股東的異國辛酸淚
落難的俄國皇族
俄國到了,安息吧!
歸化的俄羅斯軍官
回來吧!親愛的尼吉
俄羅斯女的台灣歲月
曾經熱情的蔣方良
一粒鹽巴,一趟霜雪之旅
四樓的太太——瑪蘭
台灣文學作家的窩
樓下擺攤的周夢蝶
《文學季刊》的基地 白色恐怖的陰影
黃春明的育兒桌
阮家的少爺在樓上嗎?
白先勇和ASTORIA的羅宋湯
和《晚安曲》比晚的三毛
明星的滋味,西點的感動
不能看的俄羅斯祕方
越洋連線,台灣首個巧克力蛋糕
蔣中正的最後一個生日蛋糕
保存二十年的蛋糕盒
幕落又起,明星重生
走味的咖啡,歇業的無奈
一場火災,三百人連署
運回老桌椅,重新開幕
影視明星,再聚明星
天才畫家誕生,愛在當下
爸爸,醫生說他是自閉兒
從重症到十大傑出青年
與羅馬教宗一抱
愛在當下,活在當下
附錄
明星咖啡與簡錦錐大事紀
享食明星 一口一故事
序
推薦序
我們的明星歲月/季季
一九六四年我到台北後的一年多,時常在明星咖啡館寫作。有些訪問者聽我說起這段往事,都會露出驚訝的表情:「哇,妳好浪漫啊,那時就在咖啡館寫作…。」
「不,不是浪漫,」我說,「是沒有書桌寫作。」
「真的嗎?」年輕記者不相信的說,「那時妳連一張書桌都沒有嗎?」
當然是真的。剛來台北時,沒錢買書桌,只能雙手俯在竹床上寫,沒多久就肩頸緊縮,筋骨痠痛。後來走進明星,坐在三樓的火車座,依著冰涼的、墨綠花紋的大理石桌面,慢慢的寫;那是我最放鬆,最愉悅的寫作時光。
.一九六四的明星因緣
作家與明星,或者明星與城隍廟,與流亡的白俄人,以及台灣人簡錦錐怎樣遇到了五個白俄人,與他們延續了上海的明星,合創了台北的明星⋯⋯。現在回首逐一翻閱,發黃的歷史冊頁裡還瀰漫著麵包與咖啡的甜香,而其間的生命起伏,故事轉折,卻是一本書也難以道盡的。
先說我自己與明星的因緣吧。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二日,我剛到台北兩個多月,在重慶南路書店街免費閱讀之後逛到了武昌街一段,看到一座很古樸的廟宇,走近一看,是台灣省城隍廟(現在已金光閃耀華麗貴氣了)。後來站在廟埕花園裡(那時尚未加蓋棚頂)瀏覽周遭,發現對面「明星西點麵包」騎樓下有個清癯的中年男子,頂著光頭手握書卷,坐在椅子上垂目閱讀。街邊坐讀,神色肅穆,這陌生的影像彷彿一塊吸鐵把我吸了過去。男子手上握著泛黃線裝書,看不到封面和書名,但他旁邊立個木頭書架,排列著一些我讀虎尾女中時沒看過的詩集和雜誌。我立即明白這是他的書攤,於是第一次買了一本《現代文學》,五塊五毛。不過我沒跟那個賣書人說話。
後來我把這個發現告訴文友隱地,他是老台北。「那就是詩人周夢蝶呀,」隱地很平常的說︰「那家明星麵包很有名,是白俄人開的,樓上還有明星咖啡館呢。」
周夢蝶書攤和明星咖啡館,於是在我的台北記憶裡留下了難忘的刻痕。六月初,皇冠通知我簽「基本作家」合約,我挑了一個星期天,請隱地、我的讀者阿碧,以及我的男友小寶去明星喝咖啡,一杯六塊錢。那時的稿費一千字五十元,四杯咖啡差不多喝掉五百字。但是就算喝掉一千字,我也很高興啊。
那天是六月七日,我第一次走進明星,並且在三樓看中一個靠窗的位子,後來在那裡寫了〈沒有感覺是什麼感覺〉、〈擁抱我們的草原〉、〈我的庇護神〉)等多篇小說。
.周夢蝶的愚人節故事
「我這是愚人節的故事啊,」二○○四年六月六日,諾曼地登陸六十周年的深夜,周夢蝶在電話的那一端這樣說。
「我第一天到明星門口賣書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最後一天是一九八○年四月一日;不都是愚人節嗎?」他哈哈大笑了起來。
「到明星之前呢?」
「逐水草而居啊,每天揹一箱書帶一塊布,找個警察比較不容易發現的地方,把布攤開來,書就放在上面⋯⋯。」
逐水草而居那兩年,因為沒執照,常被管區警察驅逐。有個警察是同鄉,勸他最好找個固定的地方,取得合法執照。他到明星第一天,仍是把書攤在布上,「簡太太看到了我,還拿了一塊蛋糕請我吃,對我非常友善。」
每天揹書來去很沉重,後來他徵得明星同意,在騎樓下靠牆釘了一個書架,也取得了合法執照;「如此二十一年,除了農曆年假,每天都去明星,在那裡認識了很多朋友…。」─二○一四年五月一日,周夢蝶以九十四高齡辭世。
.《文學季刊》與「明星之子」
二○○四年五月十八日,明星歇業十五年之後,重新開幕試賣,八十四歲的周夢蝶依舊穿著一襲布袍,頂著一頭光芒,仙風道骨走進明星咖啡館。七十四歲的明星老闆簡錦錐則穿著一身牛仔裝,英挺帥氣,兩人相互輝映。重新裝潢拓寬的明星更為寬敞,牆上掛的還是當年白俄畫家帕索維基(Nadejda Tpassoviky)的油畫,五十多年前在淡水訂做的紅木桌椅,刻意的沒有重新上漆,桌邊椅腳那些直的橫的痕跡,深深淺淺就像我們走過的滄桑。
《文學季刊》的尉天驄、陳映真、黃春明都帶太太同來;春明的大兒子國珍新婚兩天,也帶著新娘子趙容旋來了。天驄說,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文學季刊》創刊後,他們常在明星三樓看稿討論內容,那時只有春明已婚。第二年八月國珍出生,才二十多天,春明太太林美音就把他抱到明星,睡著了就放在靠牆的桌上安睡。國珍稍大一點,簡太太常請他吃蛋糕,吃得白白胖胖的;國珍不但是《文學季刊》之子,也是標準的「明星之子」。陳映真則說,那個年代大家都窮,辦文學雜誌靠的是理想和革命感情,有時候在明星肚子餓了,叫一盤蛋炒飯兩人分著吃,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特別香。一九七七年他和陳麗娜結婚,唐文標去明星訂了一個蛋糕送到耕莘文教院禮堂;「簡老闆還特別把那蛋糕做得像一本翻開的書呢。」
他們分別說著《文學季刊》同仁與明星的舊事時,坐在一旁的我有點遺憾,也有點孤單。曾與我在明星寫稿的林懷民,帶雲門出國巡演,而白先勇則去故鄉桂林參加書展,都沒能重返明星敘舊。白先勇大三與台大外文系同學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創辦《現代文學》,他們在明星聚會是一九六○到六一,畢業後女生出國;男生當兵兩年,一九六三年也出國了。我在明星寫稿是一九六四年五月至次年五月;婚後偶而還去,六六年十一月做了母親後就較少去,無緣見識一九六七年的「明星之子」,以及一群熱血男子聚精匯神為《文學季刊》選稿的「聖會」。但我婚後那年,他們籌畫《文學季刊》時曾來我家聊天討論,後來大夥也曾一起去阿肥家(他的姊夫蔣緯國當時赫赫有名),聽瓊拜雅、鮑伯狄倫的反戰歌曲,談越戰,談社會寫實,談彼岸正敲鑼打鼓的文革。遺憾的是,一九六八年陳映真、阿肥等人因「民主台灣聯盟」案被捕,《文學季刊》也在次年停刊。
.最珍貴的明星特質:「從來沒有人趕過我…」
我也常對訪問者說,我在明星寫作,一去就是大半天:「從來沒有人趕過我;這種包容與愛心,是明星最珍貴的特質…。」
我到明星寫稿比《現代文學》的人晚,比《文學季刊》的人早,一個人很安靜,也很孤單而沉默。除了點飲料,幾乎沒和誰說過話。當時我只認識馬各、隱地、門偉誠等文友,他們都要上班,偶而才來明星;最早認識的文友林懷民則還在台中讀衛道中學。明星的二樓很典雅,半捲的長窗簾,暈黃的燈輝,散發著古樸悠閑的光影;加上那些色彩沉鬱的白俄人油畫,濃郁的咖啡香,以及當時少有的冷氣,永遠瀰漫著一種慵懶浪漫的歐洲式氣氛,每次我去都看到一桌桌的人似乎無憂無慮,閑閑的坐在那裡談天抽菸。或許其中也有知名的作家吧?可惜我一個也不認識。而且剛從鄉下來還很怕羞,我總是快速穿過二樓,從來也不敢去問哪個是白俄老闆,當然也不認識簡先生。
爬上三樓,靠牆那個面窗的位子最亮,我喜歡坐那裡,寫不下去時還可以貼著窗玻璃看城隍廟的香爐,看久了身心漸漸沉靜,腦子彷彿空了,新的想像又幻化而出,於是坐下來繼續寫。三樓沒冷氣,但比二樓寬敞,左右兩排隔著紅木屏風的火車座,中間還有三個圓桌,但客人不多;常常一個下午只有我一個人,寫累了就趴在冰涼的大理石桌面小睡。明星咖啡雖然香醇,但我後來發現檸檬水更對我的胃口,一大玻璃杯也是六塊錢。午後走進明星叫一杯檸檬水,慢慢的喝慢慢的寫。傍晚又叫一杯檸檬水加一盤十二塊的火腿蛋炒飯,寫到快打烊才下樓。擴音器裡不時播放著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天鵝湖〉,〈胡桃鉗〉,或德弗乍克的〈新世界〉⋯⋯。對一個在台北沒書桌也沒收音機和音響的鄉下女孩來說,在明星寫稿的感覺真是奢侈而又幸福。一個人守著一張桌子,自由自在想像,無拘無束描摹,在紙上呢喃的無非是青春的感傷,對人世愛恨的質疑,或者一些年輕浪漫的夢想。每次寫完一篇小說走下三樓,心裡總是又快樂又滿足,而且依依不捨。
.林懷民:「嘿,我來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懷民考上政大,住在木柵,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也會到明星來。一走上三樓,他就興奮的說︰「嘿,我來了。」然後坐在我後排的火車座。隔著屏風,聽到他窸窸窣窣攤開稿紙,聽到二樓服務生送來檸檬水,然後又安靜了下來。他寫他所想所見,我寫我所見所想。寫得不滿意,他會大聲嘆口氣,窸窸窣窣把稿子揉掉。有時他會走過來,拿著他正寫著的那頁︰「這個字這樣寫對不對?」有時則會坐在圓桌邊,靠著綠皮圈椅,把腳擱在另一隻椅子上,悠閑點燃一支菸。「先休息一下,」他充滿期待的說︰「我唸一段剛才寫的,妳聽聽看!」
那一刻的明星三樓,像個小劇場;懷民是唯一的演員,我是唯一的觀眾。演員結束了演出,總要急切的問觀眾意見。但是觀眾口才不好,常常辭不達意。演員最後總是看著自己的稿子,慢慢的說︰「我感覺,這樣比較好。」
懷民後來帶著雲門演出,有了更大的舞台,更多的觀眾。有些老朋友問他:「什麼時候再寫小說?」我從沒這樣問過。我知道,他一直在寫,把他的小說用身體寫在舞台上;因為,「我感覺,這樣比較好。」他帶著雲門到世界各地演出時,也總會對當地的粉絲說:「嘿,我來了。」
林懷民所說的「這樣比較好」,是一種理想的追求;「我來了」,則是一種行動的實踐。簡錦錐先生與明星咖啡館,六十六年來所走的路,也正是堅持理想與實踐的過程。
恭喜簡先生。也誠摯的謝謝,明星對我的包容。
寫作的窩/黃春明
民國五十年初,台灣的農業開始解構,年輕人口外移到都市,台灣的社會結構、家庭結構也開始改變。我當時很年輕,也到了台北發展,我當時租的房子是木造的日式宿舍,分租的房間只有三坪多,浴廁共用。那時我已經很喜歡寫作,但在這麼小的空間裡,根本找不到地方可以書寫。
當時我在漢口街的國華廣告公司工作,有一次客戶說要去明星咖啡館開會,我一進去就很喜歡那個地方。咖啡館的生意很好,後來我常去,而且都據著二樓樓梯口旁邊的位置。也因為在樓梯口,一般人比較不喜歡,但因為我得坐很久,可以讓我一天見好幾組客戶,所以才特地挑了個一般人比較不會去坐的位置。因為我工作的關係,所以我可以到外面寫稿,不一定得要一直待在公司,我常一大早去,幾乎一待就到晚上打烊。有錢的時候,早上一杯咖啡,中午點一盤炒飯,下午再一杯咖啡;沒有錢的時候,就點一杯咖啡坐到底,餓了就到店外用餐,東西就放在桌上。而老闆簡先生對我這樣的狀況,從不干涉,也不趕人,這在現在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他還特別交代店裡員工阿昆、阿成不要打擾我。
那時我常常一早來到店裡,就會看到簡先生早已經在店裡頭,而且他都會自己打掃廁所,這讓我覺得他很特別。他也不是個愛講話的人,但就是在很多地方都盡量給了我方便。那個年代,在台北要租寫字間非常花錢,但在明星只要十五元一杯咖啡,就可以從早坐到晚,有人打電話到明星來找我,還會幫我接,在家裡哪有這麼好的事?就這樣,我跟他就慢慢地熟赧了。
簡先生知道我在寫作,許多出版社和讀者也都知道到明星來找我。那時差不多是民國五十五年到五十八年左右,是我創作的高峰期;當我靈感來了,我就會要到明星寫作,常常天一亮就出門,待在明星的時間比家裡還多。其實對作家來說,寫作就好像母雞要找窩下蛋,明星就是我寫作的窩。我可以很安心的在那裡寫作,當時〈看海的日子〉、〈我愛瑪莉〉、〈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莎喲娜拉再見〉,幾篇我的作品中比較出名的,和好幾本重要的小說都是在明星完成的,甚至連廣播劇、電視劇的稿子也是在那寫出。
後來,明星的客人愈來愈多,有股票族的會聚集在漢口街,許多藝文人士、畫家也會在那出沒,當時侯孝賢的電影公司就在附近,有時候碰到也是點個頭打招呼。而《文學季刊》也是在明星成立的,那時大家常常會在明星二樓聚會、寫稿;成員裡,尉天驄、陳映真和我最常待在那裡,分別交稿、收稿、催稿與寫稿,而王禎和是最規矩的一位。我的兒子國珍,是在那時期出生,剛出生一個月就被帶到明星去,我就讓他躺在旁邊的桌上,一直到他五、六歲,都常往那跑。
後來咖啡館的業務擴大,多了三樓,有一天簡先生跟我說,以後你們雜誌要開會可以到三樓去。我們非常開心,因為三樓不僅空間大、又有開會長桌(我可以把小孩子放上面),最好的是更加安靜。我記得後來明星歇業時,老闆還送了我會議桌、兩個咖啡圓桌、四張沙發,以及我很喜歡的杯盤(去年被我弄破了一個),這些東西讓我覺得很親切。在那裡的顧客可能沒有人跟老闆要過東西,我可能是老闆唯一有送東西的人。
後來去明星的人愈來愈多,我們在那邊開會有時也不是那麼方便。我也到過它位於中山北路的分店,我就是在那裡的廁所發現中風的俄國人艾斯尼。不過,雖然中山北路的店面空間更大,但我覺得氛圍不對,還是不習慣那裡,我依舊會去武昌街的明星。後來因為我搬了好幾次家,家裡多了可以寫作的空間,加上公司後來也搬到別的地方,所以走動沒有以前勤快,就比較少到明星。明星之後也歇業了好幾年,一直到後來重新開業,幾個老朋友才又陸陸續續在那裡碰頭。
說起來,相較之下,我真的是最常在明星的作家。因為我工作的地點離明星近,很方便,工作性質也很彈性,也不怕人干擾。或許這也跟我從事廣告有關,雖然是在國華廣告工作,但上班地點幾乎都跑到明星,那裡不僅是開會方便、寫作也方便,最主要的是簡先生人真的很好。
簡先生的女兒簡靜惠也很難得,從小受美式教育,小時候跟洋娃娃一樣,還到美國留學,後來當了媳婦,把患有自閉症的柏毅教導得那麼好,這很不簡單。而能教養出這樣的女兒,簡先生夫妻兩人也很不簡單。他們待人處事就像是台灣人所說的「有肚量」。我們當時從鄉下來到台北,通常都會覺得台北人很冷漠,但是簡先生不會給人這種感覺,而那時只是覺得他人很好,後來回憶起來,才真的感受到他的待人和善。
很多人說起明星,都能說出自己跟明星的一段故事。最主要的是,這個地方可以吸引這麼多藝術家、創作者,一定有它的基本價值。而那裡同時的有那麼多人在工作和理想中努力,之後也各自做出了成就,這是最重要的。其實明星對每個人的意義都不同,這些如果自己沒有講出來,明星那邊是不會知道它扮演著這麼重要的角色。這次再看到這些書稿時,讓我又開始想起一些緣分與回憶。我在明星認識了很多人,例如詩人周夢蝶,我除了常和他聊天,也常看到年輕人來找他聊天。透過這些機緣與溝通,改變了我的想法、靈感,我說不上具體的感觸,但卻知道這些是有意識形成的。
我們的明星歲月/季季
一九六四年我到台北後的一年多,時常在明星咖啡館寫作。有些訪問者聽我說起這段往事,都會露出驚訝的表情:「哇,妳好浪漫啊,那時就在咖啡館寫作…。」
「不,不是浪漫,」我說,「是沒有書桌寫作。」
「真的嗎?」年輕記者不相信的說,「那時妳連一張書桌都沒有嗎?」
當然是真的。剛來台北時,沒錢買書桌,只能雙手俯在竹床上寫,沒多久就肩頸緊縮,筋骨痠痛。後來走進明星,坐在三樓的火車座,依著冰涼的、墨綠花紋的大理石桌面,慢慢的寫;那是我最放鬆,最愉悅的寫作時光。
.一九六四的明星因緣
作家與明星,或者明星與城隍廟,與流亡的白俄人,以及台灣人簡錦錐怎樣遇到了五個白俄人,與他們延續了上海的明星,合創了台北的明星⋯⋯。現在回首逐一翻閱,發黃的歷史冊頁裡還瀰漫著麵包與咖啡的甜香,而其間的生命起伏,故事轉折,卻是一本書也難以道盡的。
先說我自己與明星的因緣吧。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二日,我剛到台北兩個多月,在重慶南路書店街免費閱讀之後逛到了武昌街一段,看到一座很古樸的廟宇,走近一看,是台灣省城隍廟(現在已金光閃耀華麗貴氣了)。後來站在廟埕花園裡(那時尚未加蓋棚頂)瀏覽周遭,發現對面「明星西點麵包」騎樓下有個清癯的中年男子,頂著光頭手握書卷,坐在椅子上垂目閱讀。街邊坐讀,神色肅穆,這陌生的影像彷彿一塊吸鐵把我吸了過去。男子手上握著泛黃線裝書,看不到封面和書名,但他旁邊立個木頭書架,排列著一些我讀虎尾女中時沒看過的詩集和雜誌。我立即明白這是他的書攤,於是第一次買了一本《現代文學》,五塊五毛。不過我沒跟那個賣書人說話。
後來我把這個發現告訴文友隱地,他是老台北。「那就是詩人周夢蝶呀,」隱地很平常的說︰「那家明星麵包很有名,是白俄人開的,樓上還有明星咖啡館呢。」
周夢蝶書攤和明星咖啡館,於是在我的台北記憶裡留下了難忘的刻痕。六月初,皇冠通知我簽「基本作家」合約,我挑了一個星期天,請隱地、我的讀者阿碧,以及我的男友小寶去明星喝咖啡,一杯六塊錢。那時的稿費一千字五十元,四杯咖啡差不多喝掉五百字。但是就算喝掉一千字,我也很高興啊。
那天是六月七日,我第一次走進明星,並且在三樓看中一個靠窗的位子,後來在那裡寫了〈沒有感覺是什麼感覺〉、〈擁抱我們的草原〉、〈我的庇護神〉)等多篇小說。
.周夢蝶的愚人節故事
「我這是愚人節的故事啊,」二○○四年六月六日,諾曼地登陸六十周年的深夜,周夢蝶在電話的那一端這樣說。
「我第一天到明星門口賣書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最後一天是一九八○年四月一日;不都是愚人節嗎?」他哈哈大笑了起來。
「到明星之前呢?」
「逐水草而居啊,每天揹一箱書帶一塊布,找個警察比較不容易發現的地方,把布攤開來,書就放在上面⋯⋯。」
逐水草而居那兩年,因為沒執照,常被管區警察驅逐。有個警察是同鄉,勸他最好找個固定的地方,取得合法執照。他到明星第一天,仍是把書攤在布上,「簡太太看到了我,還拿了一塊蛋糕請我吃,對我非常友善。」
每天揹書來去很沉重,後來他徵得明星同意,在騎樓下靠牆釘了一個書架,也取得了合法執照;「如此二十一年,除了農曆年假,每天都去明星,在那裡認識了很多朋友…。」─二○一四年五月一日,周夢蝶以九十四高齡辭世。
.《文學季刊》與「明星之子」
二○○四年五月十八日,明星歇業十五年之後,重新開幕試賣,八十四歲的周夢蝶依舊穿著一襲布袍,頂著一頭光芒,仙風道骨走進明星咖啡館。七十四歲的明星老闆簡錦錐則穿著一身牛仔裝,英挺帥氣,兩人相互輝映。重新裝潢拓寬的明星更為寬敞,牆上掛的還是當年白俄畫家帕索維基(Nadejda Tpassoviky)的油畫,五十多年前在淡水訂做的紅木桌椅,刻意的沒有重新上漆,桌邊椅腳那些直的橫的痕跡,深深淺淺就像我們走過的滄桑。
《文學季刊》的尉天驄、陳映真、黃春明都帶太太同來;春明的大兒子國珍新婚兩天,也帶著新娘子趙容旋來了。天驄說,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文學季刊》創刊後,他們常在明星三樓看稿討論內容,那時只有春明已婚。第二年八月國珍出生,才二十多天,春明太太林美音就把他抱到明星,睡著了就放在靠牆的桌上安睡。國珍稍大一點,簡太太常請他吃蛋糕,吃得白白胖胖的;國珍不但是《文學季刊》之子,也是標準的「明星之子」。陳映真則說,那個年代大家都窮,辦文學雜誌靠的是理想和革命感情,有時候在明星肚子餓了,叫一盤蛋炒飯兩人分著吃,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特別香。一九七七年他和陳麗娜結婚,唐文標去明星訂了一個蛋糕送到耕莘文教院禮堂;「簡老闆還特別把那蛋糕做得像一本翻開的書呢。」
他們分別說著《文學季刊》同仁與明星的舊事時,坐在一旁的我有點遺憾,也有點孤單。曾與我在明星寫稿的林懷民,帶雲門出國巡演,而白先勇則去故鄉桂林參加書展,都沒能重返明星敘舊。白先勇大三與台大外文系同學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創辦《現代文學》,他們在明星聚會是一九六○到六一,畢業後女生出國;男生當兵兩年,一九六三年也出國了。我在明星寫稿是一九六四年五月至次年五月;婚後偶而還去,六六年十一月做了母親後就較少去,無緣見識一九六七年的「明星之子」,以及一群熱血男子聚精匯神為《文學季刊》選稿的「聖會」。但我婚後那年,他們籌畫《文學季刊》時曾來我家聊天討論,後來大夥也曾一起去阿肥家(他的姊夫蔣緯國當時赫赫有名),聽瓊拜雅、鮑伯狄倫的反戰歌曲,談越戰,談社會寫實,談彼岸正敲鑼打鼓的文革。遺憾的是,一九六八年陳映真、阿肥等人因「民主台灣聯盟」案被捕,《文學季刊》也在次年停刊。
.最珍貴的明星特質:「從來沒有人趕過我…」
我也常對訪問者說,我在明星寫作,一去就是大半天:「從來沒有人趕過我;這種包容與愛心,是明星最珍貴的特質…。」
我到明星寫稿比《現代文學》的人晚,比《文學季刊》的人早,一個人很安靜,也很孤單而沉默。除了點飲料,幾乎沒和誰說過話。當時我只認識馬各、隱地、門偉誠等文友,他們都要上班,偶而才來明星;最早認識的文友林懷民則還在台中讀衛道中學。明星的二樓很典雅,半捲的長窗簾,暈黃的燈輝,散發著古樸悠閑的光影;加上那些色彩沉鬱的白俄人油畫,濃郁的咖啡香,以及當時少有的冷氣,永遠瀰漫著一種慵懶浪漫的歐洲式氣氛,每次我去都看到一桌桌的人似乎無憂無慮,閑閑的坐在那裡談天抽菸。或許其中也有知名的作家吧?可惜我一個也不認識。而且剛從鄉下來還很怕羞,我總是快速穿過二樓,從來也不敢去問哪個是白俄老闆,當然也不認識簡先生。
爬上三樓,靠牆那個面窗的位子最亮,我喜歡坐那裡,寫不下去時還可以貼著窗玻璃看城隍廟的香爐,看久了身心漸漸沉靜,腦子彷彿空了,新的想像又幻化而出,於是坐下來繼續寫。三樓沒冷氣,但比二樓寬敞,左右兩排隔著紅木屏風的火車座,中間還有三個圓桌,但客人不多;常常一個下午只有我一個人,寫累了就趴在冰涼的大理石桌面小睡。明星咖啡雖然香醇,但我後來發現檸檬水更對我的胃口,一大玻璃杯也是六塊錢。午後走進明星叫一杯檸檬水,慢慢的喝慢慢的寫。傍晚又叫一杯檸檬水加一盤十二塊的火腿蛋炒飯,寫到快打烊才下樓。擴音器裡不時播放著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天鵝湖〉,〈胡桃鉗〉,或德弗乍克的〈新世界〉⋯⋯。對一個在台北沒書桌也沒收音機和音響的鄉下女孩來說,在明星寫稿的感覺真是奢侈而又幸福。一個人守著一張桌子,自由自在想像,無拘無束描摹,在紙上呢喃的無非是青春的感傷,對人世愛恨的質疑,或者一些年輕浪漫的夢想。每次寫完一篇小說走下三樓,心裡總是又快樂又滿足,而且依依不捨。
.林懷民:「嘿,我來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懷民考上政大,住在木柵,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也會到明星來。一走上三樓,他就興奮的說︰「嘿,我來了。」然後坐在我後排的火車座。隔著屏風,聽到他窸窸窣窣攤開稿紙,聽到二樓服務生送來檸檬水,然後又安靜了下來。他寫他所想所見,我寫我所見所想。寫得不滿意,他會大聲嘆口氣,窸窸窣窣把稿子揉掉。有時他會走過來,拿著他正寫著的那頁︰「這個字這樣寫對不對?」有時則會坐在圓桌邊,靠著綠皮圈椅,把腳擱在另一隻椅子上,悠閑點燃一支菸。「先休息一下,」他充滿期待的說︰「我唸一段剛才寫的,妳聽聽看!」
那一刻的明星三樓,像個小劇場;懷民是唯一的演員,我是唯一的觀眾。演員結束了演出,總要急切的問觀眾意見。但是觀眾口才不好,常常辭不達意。演員最後總是看著自己的稿子,慢慢的說︰「我感覺,這樣比較好。」
懷民後來帶著雲門演出,有了更大的舞台,更多的觀眾。有些老朋友問他:「什麼時候再寫小說?」我從沒這樣問過。我知道,他一直在寫,把他的小說用身體寫在舞台上;因為,「我感覺,這樣比較好。」他帶著雲門到世界各地演出時,也總會對當地的粉絲說:「嘿,我來了。」
林懷民所說的「這樣比較好」,是一種理想的追求;「我來了」,則是一種行動的實踐。簡錦錐先生與明星咖啡館,六十六年來所走的路,也正是堅持理想與實踐的過程。
恭喜簡先生。也誠摯的謝謝,明星對我的包容。
二○一五年五月四日於台北
寫作的窩/黃春明
民國五十年初,台灣的農業開始解構,年輕人口外移到都市,台灣的社會結構、家庭結構也開始改變。我當時很年輕,也到了台北發展,我當時租的房子是木造的日式宿舍,分租的房間只有三坪多,浴廁共用。那時我已經很喜歡寫作,但在這麼小的空間裡,根本找不到地方可以書寫。
當時我在漢口街的國華廣告公司工作,有一次客戶說要去明星咖啡館開會,我一進去就很喜歡那個地方。咖啡館的生意很好,後來我常去,而且都據著二樓樓梯口旁邊的位置。也因為在樓梯口,一般人比較不喜歡,但因為我得坐很久,可以讓我一天見好幾組客戶,所以才特地挑了個一般人比較不會去坐的位置。因為我工作的關係,所以我可以到外面寫稿,不一定得要一直待在公司,我常一大早去,幾乎一待就到晚上打烊。有錢的時候,早上一杯咖啡,中午點一盤炒飯,下午再一杯咖啡;沒有錢的時候,就點一杯咖啡坐到底,餓了就到店外用餐,東西就放在桌上。而老闆簡先生對我這樣的狀況,從不干涉,也不趕人,這在現在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他還特別交代店裡員工阿昆、阿成不要打擾我。
那時我常常一早來到店裡,就會看到簡先生早已經在店裡頭,而且他都會自己打掃廁所,這讓我覺得他很特別。他也不是個愛講話的人,但就是在很多地方都盡量給了我方便。那個年代,在台北要租寫字間非常花錢,但在明星只要十五元一杯咖啡,就可以從早坐到晚,有人打電話到明星來找我,還會幫我接,在家裡哪有這麼好的事?就這樣,我跟他就慢慢地熟赧了。
簡先生知道我在寫作,許多出版社和讀者也都知道到明星來找我。那時差不多是民國五十五年到五十八年左右,是我創作的高峰期;當我靈感來了,我就會要到明星寫作,常常天一亮就出門,待在明星的時間比家裡還多。其實對作家來說,寫作就好像母雞要找窩下蛋,明星就是我寫作的窩。我可以很安心的在那裡寫作,當時〈看海的日子〉、〈我愛瑪莉〉、〈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莎喲娜拉再見〉,幾篇我的作品中比較出名的,和好幾本重要的小說都是在明星完成的,甚至連廣播劇、電視劇的稿子也是在那寫出。
後來,明星的客人愈來愈多,有股票族的會聚集在漢口街,許多藝文人士、畫家也會在那出沒,當時侯孝賢的電影公司就在附近,有時候碰到也是點個頭打招呼。而《文學季刊》也是在明星成立的,那時大家常常會在明星二樓聚會、寫稿;成員裡,尉天驄、陳映真和我最常待在那裡,分別交稿、收稿、催稿與寫稿,而王禎和是最規矩的一位。我的兒子國珍,是在那時期出生,剛出生一個月就被帶到明星去,我就讓他躺在旁邊的桌上,一直到他五、六歲,都常往那跑。
後來咖啡館的業務擴大,多了三樓,有一天簡先生跟我說,以後你們雜誌要開會可以到三樓去。我們非常開心,因為三樓不僅空間大、又有開會長桌(我可以把小孩子放上面),最好的是更加安靜。我記得後來明星歇業時,老闆還送了我會議桌、兩個咖啡圓桌、四張沙發,以及我很喜歡的杯盤(去年被我弄破了一個),這些東西讓我覺得很親切。在那裡的顧客可能沒有人跟老闆要過東西,我可能是老闆唯一有送東西的人。
後來去明星的人愈來愈多,我們在那邊開會有時也不是那麼方便。我也到過它位於中山北路的分店,我就是在那裡的廁所發現中風的俄國人艾斯尼。不過,雖然中山北路的店面空間更大,但我覺得氛圍不對,還是不習慣那裡,我依舊會去武昌街的明星。後來因為我搬了好幾次家,家裡多了可以寫作的空間,加上公司後來也搬到別的地方,所以走動沒有以前勤快,就比較少到明星。明星之後也歇業了好幾年,一直到後來重新開業,幾個老朋友才又陸陸續續在那裡碰頭。
說起來,相較之下,我真的是最常在明星的作家。因為我工作的地點離明星近,很方便,工作性質也很彈性,也不怕人干擾。或許這也跟我從事廣告有關,雖然是在國華廣告工作,但上班地點幾乎都跑到明星,那裡不僅是開會方便、寫作也方便,最主要的是簡先生人真的很好。
簡先生的女兒簡靜惠也很難得,從小受美式教育,小時候跟洋娃娃一樣,還到美國留學,後來當了媳婦,把患有自閉症的柏毅教導得那麼好,這很不簡單。而能教養出這樣的女兒,簡先生夫妻兩人也很不簡單。他們待人處事就像是台灣人所說的「有肚量」。我們當時從鄉下來到台北,通常都會覺得台北人很冷漠,但是簡先生不會給人這種感覺,而那時只是覺得他人很好,後來回憶起來,才真的感受到他的待人和善。
很多人說起明星,都能說出自己跟明星的一段故事。最主要的是,這個地方可以吸引這麼多藝術家、創作者,一定有它的基本價值。而那裡同時的有那麼多人在工作和理想中努力,之後也各自做出了成就,這是最重要的。其實明星對每個人的意義都不同,這些如果自己沒有講出來,明星那邊是不會知道它扮演著這麼重要的角色。這次再看到這些書稿時,讓我又開始想起一些緣分與回憶。我在明星認識了很多人,例如詩人周夢蝶,我除了常和他聊天,也常看到年輕人來找他聊天。透過這些機緣與溝通,改變了我的想法、靈感,我說不上具體的感觸,但卻知道這些是有意識形成的。
圖書評論 - 評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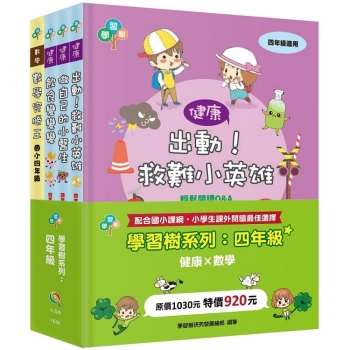










「明星咖啡館」由簡錦錐口述,謝祝芬撰文,全書文字流暢自然,一讀便不忍釋手,直到闔上最後一頁。我讀著咖啡館,才知道背後竟藏著如許動人的故事。全書分八大章節,原本我以為主要在說咖啡館與台灣文學作家的軼事,例如在門口擺攤的詩人周夢蝶,或是在二樓寫作的許多知名作家的書寫經歷。然而一開始,便被簡先生不平凡的童年生活給吸引住了。 從「八歲,一個人飄洋過海」,到「天才畫家誕生,愛在當下」,有如自傳,將簡先生如何與俄羅斯的落難皇族結下奇緣,開了咖啡館,描述了中間經歷的各種困境,卻因不怕挑戰的個性,即使在絕處,也不放棄,終能讓咖啡館在在一九六一年成立。也述說當時在台的俄羅斯股東們的異國辛酸淚,政商界的軼事,之後明星如何落幕,如何又重生。當然也有文學家們在明星時的年輕身影。有了明星的包容,讓他們對文學的熱情有了發揮的空間,足以讓咖啡館閃耀在時局動盪的年代裡。 讀「明星咖啡館」的種種,時而讓人歎息,時而讓人垂淚,時而讓人感到溫馨,時而被注入了幸福的感覺。 最讓我感動的是簡先生及家人在二戰期間曾經收留台灣逃兵;在二二八事件中曾經收留處境堪危的外省人;在反共抗俄時間,幫助在台灣的俄羅斯人……簡先生說:「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大樹讓鳥築巢,鳥幫大樹吃蟲,人與人之間自然也需要互相幫忙。」這個幫忙,跨越種族與政治,純然呈現的是人性中最單純,最寶貴的善與愛,有了這個成份,讓明星的咖啡更香醇了。 「明星咖啡館」雖然已大名鼎鼎,但是藉由這本書,不僅能知道更多那個時代的故事,看著歷史一路走過,伴著明星的咖啡與蛋糕,有完全不一樣感觸。 原來,「明星咖啡館」不只是一間喝咖啡的地方,還是一間愛與善良流動的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