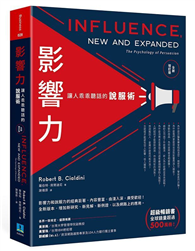第一章
這是一樁令人疲憊的婚事,程家三口在馬車上一路相對無言,不知從何說起──程老爹臉色迷茫,緊緊攥著袖口,好似剛被麻婆吃了豆腐。蕭主任神色肅穆,充滿了主持追悼會般的儀式感。少商則像隻小老鼠般窸窸窣窣的啃著手中的糕點。
蕭主任忍無可忍:「才兩塊糕點,妳怎麼還沒吃完?」
少商嚥下嘴裡的點心,「阿苧給的早吃完了,這是出長秋宮時凌不疑塞給我的。」
程始長嘆口氣,看著女兒彷彿她吃的是巴拉松。
回到程府已是月懸當中,老的小的都歇下了,唯有程家三兄弟和程姎領了一群引燈的僕從,拉長了脖子在門口等著。蕭夫人懶得廢話,長袖一揮,把幾個小兒女都喚去了九騅堂開家庭研討會順帶宵夜。程始大馬金刀的高坐上首,言簡意賅的將今日宮中訂親之事跟大家說了。
程家三兄弟都呆了,交換了幾個不敢置信的眼神後,都去看對面正熱情款待宵夜的幼妹,只有為程始夫婦布置食案的程姎和青蓯夫人十分淡定,前者根本沒見過也沒怎麼聽說過凌不疑,後者見多識廣,老成穩重。
九騅堂內一陣安靜,只聞少商歡快的咀嚼聲,過了良久,程詠才試探著問道:「……阿父,阿母,我們是否該去拜訪一下親家?」這也是一樁詭異的親事,當今皇帝為心愛的養子代行長輩之職,可問題是凌不疑究竟不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人家親爹娘還好好活著呢!
程老爹一臉茫然,「說起來……」他看看妻子,「我還不認識凌侯呢。」大朝會時遠遠見過幾次,依稀記得那是個長相俊秀舉止溫和的中年男子。
蕭夫人咬了下顎骨,不發一言。
程始見妻子不理自己,轉頭去看女兒,「妳妳妳、妳還吃得下去!」
這時,少商對於食物的熱情終於告了一個段落,捧起食案旁的陶樽,舀了一勺清水漱口後,才道:「為何吃不下去?又不是我答應親事的。」
程老爹的嘴皮子也不是吹出來的,瞪眼罵回去:「那也不是為父私底下結識凌不疑的!」
少商放下陶樽,語重心長道:「阿父,此時追究誰的責任為時已晚,不如想想對策吧。」
感覺自己無法跟上節奏的程姎猶豫了半晌,才怯怯道:「……大伯父,嫋嫋,既然那位凌大人是個大大了不得的人物,那這婚事不是、不是好事麼?你們為何……」
此言一出,除她以外的程家眾人俱是齊齊嘆氣,不知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少商嘆完氣,問道:「阿母,您跟我說說凌不疑家裡的事吧……我是說,他的生身父母。」
蕭夫人沒好氣的橫了她一眼,「我就看不慣現下的小女娘小郎君,鎮日在一起卿卿我我膩膩歪歪,什麼風花雪月詩詞歌賦都談遍,就是不說到正事上!連人家家裡水深水淺都不知道就談婚論嫁,活該婚後吃苦受罪!」
程始連忙幫腔:「那是,妳阿母和為父見面三次,就連妳大父遠在他鄉的祖墳在哪裡和兩家的存糧都問得一清二楚了!」
程少宮側眼去看次兄,低聲道:「大父老家的祖墳不是被人拔了麼?哪裡還有……」
「你閉嘴。」程頌也低聲道。
少商覺得自己的人品和智商都受到了攻擊,趕緊申訴:「阿母此言差矣!第一,我什麼時候和凌不疑卿卿我我膩膩歪歪了,我們幾番見面都有旁人在場的,我們再守禮也不過了!第二,您和阿父是奔著成婚去的,自要凡事問清楚了,可我和凌不疑都是碰巧遇上的!人家一點也沒露出那意思,我就追著問東問西的豈不可笑?!再說了,我和凌不疑也沒見幾回……也就三四五六七八回……吧……」她越說聲音越低。見面次數似乎是多了點……不過每次見面,她都以為以後不會再見,何必問人家祖宗八代?
程詠看著幼妹,柔聲道:「嫋嫋,妳是不是不喜歡凌大人?」
「是呀……」程姎也溫柔道,「當初說到樓家親事時,嫋嫋十分高興呢。」全不是眼下心煩意亂的模樣。
「所以,嫋嫋妳心中所愛的是阿垚?可、可他已經……」程頌十分為難。
程少宮撇嘴道:「我覺得嫋嫋也沒多喜歡那個樓垚,愣頭愣腦的,嫋嫋說什麼就是什麼,白比我們大兩歲了,還沒我有主見有氣概!」
少商聽不得這個,飛去一記眼刀,「行,回頭我就給你找個全都城最有主見的妹婿,叫你見了他連坐都不敢坐大氣也不敢喘,比看見祖先牌位都老實恭敬,到時你就舒服了!」
程少宮笑道:「妳那位凌大人可比祖先牌位有氣勢多啦,我上回……」
「夠了!」蕭主任忍不住整肅紀律了,低聲喝斥道:「你們倆渾說什麼!再有對祖先不敬之言,看我請不請家法!」
雙胞胎都是受過棍棒招待的,立刻縮起嘴巴,不敢繼續牌位話題了。
蕭夫人深吸一口氣,平鋪直敘道:「凌不疑生父凌侯,素以性情溫和為人稱道,雖無顯績,但也是最早從龍的重臣之一。其母霍氏,乃是陛下過世的義兄霍公之妹。那年陛下最艱難之時,腹背皆受強敵夾擊,全虧霍侯拚死相助,以一座孤城拖住二十萬敵軍足有半年,這才給了陛下周旋之力,分別擊殺敵酋,至此方才定鼎新朝基業。可惜,霍侯闔家死於圍城屠戮,兒孫盡沒。」
少商張大了嘴巴,「全死了?難道老家也沒一個旁系子姪嗎?」
程詠補充道:「與霍侯最近的一支也出了五服的,連聚居地都隔著老遠。何況,當年霍侯是舉家襄助陛下的,沒有隨他從龍的族人也談不上有什麼情分了。」
蕭夫人繼續道:「其後戰亂時凌侯與家眷們失散了,後來好不容易找回幾個,皆道霍夫人母子已死。隔了一年凌侯就續弦了。誰知數月後霍夫人攜子找了回來,而那時新夫人已懷有身孕了……」
「那就讓凌侯休了新夫人和霍夫人破鏡重圓唄,人家是功臣遺族呢!」少商說得輕巧。
程頌猶豫道:「我彷彿聽說,凌侯夫人……哦,就是現在這位凌侯夫人,她和汝陽老王妃交情匪淺……」
「正是。」蕭夫人道,「當年兵荒馬亂之際,陛下的叔母汝陽老王妃受了重傷,那會兒又缺醫少藥的,眼看非死即殘,全靠這位新夫人悉心照顧,大半年裡日夜不休,不敢懈怠半分,這才叫老王妃掙回性命,肢體周全。」
「原來如此,那老王妃必是要給她撐腰的。」少商撇嘴道,「那就前後兩位夫人姐妹相稱唄,便宜凌侯了。」
蕭夫人搖頭道:「我家是後來歸順的,許多事都不得而知。不過我聽說這位新夫人倒願意為妾,可霍夫人自小就異常暴烈驕悍,對那新夫人喊打喊殺。彷彿休了還不夠,非要殺了她才甘休,更別說共事一夫了。」
少商若有所思:「……這麼記仇,兩位夫人恐怕是舊識吧,這是新仇舊怨都趕上來了。」
程始讚賞的看了女兒一眼,乾脆道:「妳阿母好不容易才打聽到的,原來那新夫人本是凌侯的姨家外妹,霍夫人失散前她就寡居在凌家多年了。」
少商呵呵笑了幾聲,毫不掩飾鄙夷神色。堂內眾人發出不同的咿呀之音,俱是同樣心思。
「後來,兩邊調和不下,霍夫人就和凌侯絕婚了,如今不知住在哪裡靜養。」蕭夫人結束故事。「為此,陛下更覺愧對已故的霍侯。沒過多久,陛下就從霍夫人身邊將凌不疑帶入宮中,親自教養。」
少商笑道:「這位『續弦』的凌侯夫人當年守寡後不回娘家,卻依附凌氏而居,想來沒什麼家世。如此看來,凌侯倒是深情之人,那麼多高門世族的女子不要,卻娶了無勢寡居的外妹。」
「休得胡言。」蕭夫人沉聲道,「他們都是凌不疑的長輩。」
少商嘟嘟嘴,不說話了。
程始深覺妻子文韜武略,可在收拾女兒這小冤家上就不如自己了,他板著臉道:「好啦,凌家就這麼點事,嫋嫋如今也知道了,妳對這樁婚事有看法就趕緊說出來,皇帝金口玉言發了話,妳若沒什麼異議,咱們就各自睡了吧,也別折騰了!」
「不不不,阿父,我有看法的!」少商立刻咬餌,趕緊往前膝行數步。
「那妳倒是說呀。」程頌看幼妹慌頭慌腦的樣子,笑罵道。
少商小大人般嘆氣,半刻才道:「這麼說吧,不算凌家那些亂七八糟的,樓家也不見得清淨。可是,在我心中阿垚乾淨剔透,他想什麼要做什麼,我都能摸個七八成。他又願意聽我的話,將來我們會過什麼樣的日子,走什麼樣的路,我大概全都有數。可凌不疑則不然……」她斟酌了一下語氣,傷感道:「他就如巫山雲霧,我看不清也摸不著……」
「摸還是摸過的吧。」程少宮酸溜溜道,「我聽老程順說,前日還是他拉扯妳下車輿的呢。」
少商立刻一點也不傷感了,直著脖子向蕭夫人告狀:「阿母我告訴您,少宮他可風流了!您去搜他的箱籠看看,包管能找出許多粉巾、絹帕、香囊、花葉簡什麼的,都是外面的小女娘給他的,說不得還有示愛書函呢!」
「少商妳……」程少宮立刻急了,面孔漲成豬肝色,「阿母您別聽她的,那都是別人硬塞給我的!嫋嫋她上回去探望凌不疑,他們……」
「你們倆都閉嘴!」蕭主任大喝一聲,然後悶悶的側身坐下──本來三兒就算嘴碎了點,還在可控制範圍內,但自從這對雙生子相逢,也不知怎的,就跟揭了貼在千年老妖身上的封印般,一天三頓的來氣她,果然當初應該把么女帶上一同管教才是!
程始揉著額頭,下結論道:「所以,阿垚聽妳的話,妳就高興樓家的親事;凌大人妳拿捏不住,妳就不大高興這樁婚事了,對吧?」
程姎終於聽懂了,神奇的望著堂妹,「妳竟是為了這個緣故……」她實在不能理解,讓有能耐的人給自己做靠山,聽話信任不是一樁福氣麼?
少商囁嚅道:「阿父您怎麼說得這麼直白。不過……」她扭扭身子,不好意思的低聲道:「阿母將阿父您拿捏得牢牢的,您看阿母過得多舒心。要是隨了凌大人,女兒哪有這樣的好日子。」這簡直是血淋淋活生生的案例呀!
「嫋嫋!」青蓯夫人忍無可忍,暴起大聲喝斥,「父母親長妳也敢議論?!」
這次程始夫婦連氣都懶得生了,相對嘆氣。程頌和程少宮互看一眼,偷偷笑著。
程詠嘆道:「凌大人……他究竟看上嫋嫋什麼了?」他沒有貶低自家妹妹的意思,但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論相貌,這些年送到凌不疑身邊的美姬爭奇鬥豔,自家幼妹也不知能否排入前十;論才學,至今幼妹還認不全字,更遑論吟詩作賦了;論性情,那更是一言難盡。
少商聞言,惡狠狠向他道:「我也不懂姁娥阿姐究竟看上兄長你什麼了,現在日日窩在家中學著溫良賢淑,得體持家呢!」
程詠搖搖頭,看向兩個弟弟,眼中神情明白寫著「看我說得沒錯吧」。
程頌倒有不同意見:「話不是這麼說的。萋萋說得好,少商有情有義、聰敏伶俐,大事來臨能扛得住,生可託付榮辱前程,死可託付家小墳塚,天下有幾個這麼有擔當的?」
少商眉開眼笑,「我也覺得萋萋阿姐是世上頂頂好的女子!大氣豪邁、心胸寬闊,將來誰娶了她,真是天大的福氣!以後一定兒孫滿堂、白頭偕老、團圓和美、萬事如意、事事順心、天下大同!」自從來到這裡,她發現自己的國學涵養簡直一日千里。
「我們嫋嫋真會說話!」程頌笑得見牙不見眼。
「你們也閉嘴!」蕭夫人用力拍著食案,然後轉頭對丈夫道:「我們明日求見陛下,推辭了這樁婚事吧。」
「啊?」程始吃驚,「這、這能成麼?」
「成成成,怎麼不成?!」少商趕緊插嘴,「那什麼,上古的皇帝禪讓時不還得推辭個三五次的麼?凡事不都講個客氣嘛。」
「戾帝篡位時也推辭了三五次,人家也很客氣……」程少宮涼涼的潑冷水。
「你能不說話嗎!」少商怒目相對。
蕭夫人當作沒聽見,繼續對丈夫道:「看看嫋嫋這樣子,你覺得陛下願意看見這樣的新婦?別說陛下了,就是凌不疑,恐怕也不甚清楚嫋嫋的真性情。」
程始遲疑的看向女兒。哪怕不帶偏見的看,女兒做人新婦,也是被一天三頓打的料。
程詠拱手道:「阿母說得是,我們不妨推辭一下,面聖時將妹妹的性情脾氣如實相告。陛下若不願,那就當這事沒有過,若陛下還要這婚事,那以後嫋嫋若與凌大人有爭執,我們也算有個說法。」
程頌聽懂了這言下之意,失笑道:「陛下和凌大人不會見了嫋嫋的樣貌,就以為她溫順柔弱、楚楚可憐吧。」可幼妹的長相和性情簡直南轅北轍,反差極大。
少商看向眾人,扭著手指嘟囔著,「我是在家裡才這麼言談無忌的,在外面我說話當心著呢!不過……也對,我可扮不了一輩子。」仔細想想,她的確在凌不疑面前表現得特別懂事乖巧識大體。她抬頭望向程始,大聲道:「阿父,您想想啊,我若和阿垚爭吵打架,樓家頂多休了我。可我若是惹翻了凌不疑,皇帝說不定就賜我白綾一條或毒酒一杯,沒準還會連累阿父阿母,說你們教導不嚴呢!」
「危言聳聽!」程始用力揮了揮袖子,然後搔搔髮髻,沉聲道:「不過,你們說得也有理。明日一早我們就進宮求見陛下,推辭了這樁婚事。成與不成,聽天由命!」
家主都發話了,青蓯和眾兒女都躬身應喏。
尤其是少商,莫名覺得一陣輕鬆,輕快的甩著袖子就回自己居處了──雖然覺得對不住凌不疑,但自己舒服最要緊。凌不疑比較適合做靠山,做老公她會心肌梗塞的!
當夜,程氏夫婦就寢時,蕭夫人伏在被褥間睡得半昏半醒,忽聞丈夫胸腔震動,長長一聲嘆息,低聲道:「……元漪啊,我此時才明白妳當日所說,『我放心將姎姎嫁到任何人家』。這回若凌不疑想娶的是姎姎,妳我絕不會如此患得患失。」
蕭夫人都沒睜眼,低聲道:「可世事往往就是如此,想來的盼不到,不想來的偏要送上門。我知道你捨不得這門親事,往好處想,嫋嫋聰慧狡黠,風趣討喜,聞一知十,沒準凌不疑就愛這樣的。可往壞處想,嫋嫋性情驕烈,將來若像霍夫人與凌侯似的夫妻反目成仇,我們可沒霍家那樣深厚的底氣給她撐腰。醜話說在前頭,總是不壞的。」
◎
次日上午既無大朝會也無小朝會,程始夫婦穿戴整齊後,正要為愁死人的么女進宮辭婚,誰知宣旨的小黃門又顛顛的來了,表示皇帝又叫他們一家三口進宮去。
「……不知陛下宣臣等所為何事?」程老爹表示這麼頻繁的聖恩他有些吃不大消。
「程校尉喜得貴婿,難道不用見親家的麼?」小黃門滿臉堆笑,全不復昨日中規中矩的模樣,「陛下仁厚體貼,今日也將凌侯宣進宮去了,好叫你們兩家親長見上一見,當著陛下的面把事情說清楚,後面的事就好辦啦。」
程始和蕭夫人心中俱想:皇帝是有多怕婚事生變,竟連兩家自行見面都不許。事已至此,他們只能將還賴在被窩裡的女兒挖出來,洗洗涮涮後拉出來給小黃門過目。
被糊里糊塗塞進馬車的少商猶自夢囈般的叨叨:「阿父阿母去就好了……為何叫我呀?阿母不是說沒學好禮儀之前不要再進宮了麼?不然又惹人笑……」
程始一本正經道:「為父改主意了,今日推辭婚事還是應當由汝自行張嘴,父母在旁幫襯一二就是。」
少商立刻清醒了,「我自己去說?這、這合適麼?這種大事不是該由長輩出面嗎?」
「怎麼不合適?」程始道,「又不是為父要退婚的。」
少商賭氣道:「我就知道阿父捨不得這門親事,索性阿父自己去嫁凌不疑好了!」
「若為父是女兒身,凌不疑這樣好的郎婿,我一口氣嫁上二十回連個頓都不打妳信不信!」
「阿父是糊塗蟲,只看見眼前好處!」
「妳是不孝女,根本不長眼!」
──這段沒營養的互懟,照例終結於蕭主任的低聲喝止。
沒等三人開始新的話題,就聽見車外宮門開啟交接符牌的聲音。這次路程如此短暫讓程家三口俱是一愣,詢問過後才知道,這回並未如昨日一般從南正門進入後再穿整座宮城而過,而是從上西門進入北宮,直達皇后所居的長秋宮。
既走了近路,少商這回沒走幾步就再度回到了昨日面聖的長秋宮後殿,跪拜之際她看見帝后俱身著常服端坐上首,殿內除了或站或跪的黃門宮婢外,當中還跽坐著一名樣貌風度俱佳的中年士大夫。
那中年士大夫側頭朝程始夫婦微笑頷首,又不著痕跡的細細打量少商,見她行止天真,禮數疏漏,目中不免露出訝異疑慮之色。這種神色少商見過,上回在塗高山御帳之內,皇帝頭回見到自己時也是這麼一副神氣──她立刻就明白這人是誰了。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星漢燦爛,幸甚至哉 三的圖書 |
 |
$ 180 ~ 270 | 星漢燦爛,幸甚至哉三【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關心則亂 出版社:知翎文化(欣燦連) 出版日期:2022-05-05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星漢燦爛,幸甚至哉(三)
上午剛讓出樓家婚事,下午就與凌不疑訂親,
讓程少商頓時成為全城未婚女子嫉妒羨慕的對象。
但這等「福氣」,少商只覺實是消受不起。
凌不疑就如巫山雲霧,她既看不清也摸不透,
當男神、當靠山雖是上上之選,
可要讓這美麗強勢,誰也拿捏不住的男人當夫婿,
自己先前對未來生活的美好盤算豈不全打了水漂?
程少商本想藉著自貶,辭了與凌不疑的婚事,
不料在凌不疑的見招拆招下,她全然不是對手,
反被送到皇后身邊,好好學習、提升自我一番。
深宮可畏,又因凌不疑,少商早成忌恨的目標,
幸而她向來就不是束手待斃的溫順性子,
又有凌不疑滴水不漏的全面監……守護,
再多難題也能迎刃而解──
咦?如何待凌不疑好,對他以情相待?
這、這……這題她不會啊!
商品特色
我與妳一處時,最有人味。
他容貌昳麗,風姿卓然,位高權重,卻活得彷彿一縷遊魂。
遇上她,終教他動了心思,懂了萬般滋味,有了鮮活氣息。
作者簡介:
關心則亂,晉江文學城簽約作者,代表作《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我喜歡繁華迤邐如蜀錦的文字,然而我能寫出來嗎,我寫不出;我喜歡跌宕起伏如深淵高嶺般的情節,然而我能編出來嗎,我編不出;我喜歡妖氣繚繞重彩斑駁的氤氳,然而我能營造出這樣的文字氣氛嗎,我還是不能。
我能寫的,不過是家長裡短和兒女情長,用最簡單輕快的語氣勾勒出古今永恆的主題,婚喪嫁娶,手足親眷;在平凡的故事中,感受一點人情溫暖。
章節試閱
第一章
這是一樁令人疲憊的婚事,程家三口在馬車上一路相對無言,不知從何說起──程老爹臉色迷茫,緊緊攥著袖口,好似剛被麻婆吃了豆腐。蕭主任神色肅穆,充滿了主持追悼會般的儀式感。少商則像隻小老鼠般窸窸窣窣的啃著手中的糕點。
蕭主任忍無可忍:「才兩塊糕點,妳怎麼還沒吃完?」
少商嚥下嘴裡的點心,「阿苧給的早吃完了,這是出長秋宮時凌不疑塞給我的。」
程始長嘆口氣,看著女兒彷彿她吃的是巴拉松。
回到程府已是月懸當中,老的小的都歇下了,唯有程家三兄弟和程姎領了一群引燈的僕從,拉長了脖子在門口等著。蕭夫人懶...
這是一樁令人疲憊的婚事,程家三口在馬車上一路相對無言,不知從何說起──程老爹臉色迷茫,緊緊攥著袖口,好似剛被麻婆吃了豆腐。蕭主任神色肅穆,充滿了主持追悼會般的儀式感。少商則像隻小老鼠般窸窸窣窣的啃著手中的糕點。
蕭主任忍無可忍:「才兩塊糕點,妳怎麼還沒吃完?」
少商嚥下嘴裡的點心,「阿苧給的早吃完了,這是出長秋宮時凌不疑塞給我的。」
程始長嘆口氣,看著女兒彷彿她吃的是巴拉松。
回到程府已是月懸當中,老的小的都歇下了,唯有程家三兄弟和程姎領了一群引燈的僕從,拉長了脖子在門口等著。蕭夫人懶...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