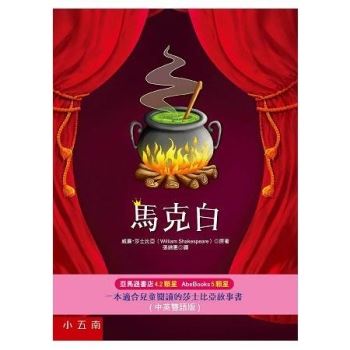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晚清史要》為著名歷史學家楊天石先生“近代史研究六種”之一,蒐集了楊先生有關晚清歷史的重要論著,分為鴉片戰爭前後、戊戌變法前後與辛亥革命前後三個部分。這些文章或為報章上的精簡論述,或為學術刊物上的扎實大作,共同展現出楊先生除了在大家所熟知的民國史研究之外,對於晚清史事與人物也下過很深的功夫。各篇著作都從一個關鍵問題著手,再引證新史料層層解析,引人入勝,生動再現了晚清風雲變幻之際的歷史圖景。
作者簡介:
楊天石,1936年出生於江蘇興化。1955年畢業於無錫市第一中學。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現為中央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浙江大學客座教授。國家圖書館民國文獻保護工程專家委員會顧問、中華詩詞研究院顧問、《中華書畫家》雜誌顧問、上海《世紀》雜誌顧問、廣東《同舟共進》雜誌編委。中央文史研究館34卷本叢書《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副主編之一。曾任中國文化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為《中國文化詞典》副主編之一。
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中國近代史、民國史、國民黨史。合著有《中國通史》第12冊,《中華民國史》第1卷、第6卷等。個人著作有《楊天石近代史文存》( 5卷本)、《揭開民國史真相》(7卷本)、《楊天石文集》、《尋求歷史的謎底: 近代中國的政治與人物》、《近代中國史事鉤沉:海外訪史錄》、《從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後史事發微》、《朱熹及其哲學》、《朱熹》、《朱熹: 孔子之後第一儒》、《王陽明》、《泰州學派》、《南社史三種》、《半新半舊齋詩選》、《橫生斜長集》等。主編有《〈百年潮〉精品系列》(12卷)、《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4卷)等。
楊天石參與寫作的多卷本《中華民國史》獲國家圖書獎榮譽獎。個人著作《尋求歷史的謎底》獲國家教委所屬高校出版社及北京市優秀學術著作獎。《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蔣介石日記解讀》第1輯獲全國31家媒體及圖書評論家協會十大圖書獎以及香港十大好書獎,第2輯獲南方讀書節最受讀者關注的歷史著作獎,第3輯及第4輯獲《亞洲週刊》十大好書獎。楊天石著作所獲的獎勵還有孫中山學術著作一等獎、二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學術著作獎等。《帝制的終結》獲《新京報》 2011年度好書獎,是當年該報獎勵的唯一歷史圖書。
作者序
楊天石先生著《晚清史要》序
楊天石先生來信告知香港三聯書店將出版他有關晚清研究的論文集《晚清史要》,希望我撰一序言,“以紀念你我多年之友誼”。我不敢推辭,只得應命。楊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前輩學者,以民國政治史研究聞名於世。他也是我的老師張朋園先生、汪榮祖先生和墨子刻先生的好友。楊先生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博聞強記、思慮敏捷、口才辨給,聽他在席間縱論民國掌故乃是人間一大快事。
1990 年代中後期,我多次受邀於張海鵬與耿雲志教授,陪同張朋園先生與墨子刻先生去位於北京王府井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每次去訪,楊先生與夫人均熱情招待。我也多次去他在書海中的研究室暢談。他告訴我有關《百年潮》與“烏有之鄉”等等的各種學術動態。後來我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任內( 2009—2015),與呂芳上教授、黃自進教授共同推動蔣介石日記的出版與蔣介石研究,楊先生在這方面用力甚勤,他以“突破內戰思維”的研究角度,對蔣氏功過有十分中肯的評論。我們也多次邀請楊先生來台交流講學。有關楊先生與台灣學者之間深厚的友誼,請參考他所寫的〈最重要的是面對史實、忠於史實:回顧我的民國史研究以及和台灣同行的交流〉,載呂芳上主編,《春江水暖:三十年來兩岸近代史學交流的回顧與展望(1980s—2010s),台北:世界大同, 2017 年。
我也有幸在香港、法國與美國等地與楊先生見面,或是開會、或是論學。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 1995 年 12 月巴斯蒂教授(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在法國中部羅亞爾河畔的加爾希(Garchy) 召開“歐洲思想與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精英文化研討會”,我們共同應邀出席。我發表嚴復翻譯的《群己權界論》,楊先生撰寫蘇曼殊、陳獨秀翻譯的雨果的《悲慘世界》。兩者分別代表清末民初英國的自由主義改良思潮與法國社會主義革命思想進入中國的重要文本。會後還去巴黎羅浮宮博物館等地遊覽。蔣介石日記開放之後,楊先生多次去我的母校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看日記。我也去過幾次。墨子刻先生當時仍擔任胡佛研究院的高級研究員,曾邀請大家一起餐敘。我被楊先生以七十高齡還認真抄寫檔案的精神所感動。楊先生的大量著作都是奠基於這種非常扎實的史料工夫。
英國學者柏林在分析托爾斯泰時曾分辨出兩種類型的學術性格,一種是刺猬型,他們喜歡把所有的事情都貫穿在一個明確的系統之內,一切細節都必須通過單一的系統才有意義。另外一種是狐狸型,他們從事多方面的追逐而不必有一個一貫的中心系統。狐狸型的作者對各種經驗採取一種嚴肅的就事論事的認真態度,而不企圖把零散的史實納入一個無所不包的統一論點。用這種分析概念來看,楊先生應該屬於“狐狸型”學者,與我的老師墨子刻教授的風格截
然不同。
我常想這可能與楊先生所處的大環境有關,在他所寫作文章的時期,要做一個剌猬型的學者,可能必須得呼應主流的立場(官方觀點),而少有批評討論的空間。相反地,作為狐狸型的學者,則可以游擊戰的方式對主流想法提出反省。
楊先生的做法是從史料開始。他在國內外,致力於訪求各種未刊的檔案、日記、函電、筆談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考辨探微,鉤沉索引,揭示鮮為人知的歷史奧秘”,一方面揭露虛假,一方面彰顯事實,反映出歷史的複雜面貌。這是使歷史學能不斷地推陳出新的重要方法,楊先生在這個方面無疑是數一數二的高手。
本書蒐集了楊先生有關晚清歷史的重要論著,分為鴉片戰爭前後、戊戌變法前後與辛亥革命前後三個部分。這些文章或為報章上的精簡論述,或為學術刊物上的扎實大作,共同展現出楊先生除了在大家所熟知的民國史研究之外,對於晚清史事與人物也下過很深的功夫,展現出高度的狐狸式的技巧。各篇著作都從一個關鍵問題著手,再引證新史料層層解析,引人入勝。我相信讀者一定和我一樣, 讀時會感到津津有味而手不釋卷。謹以此序恭祝先生健康長壽。
黃克武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楊天石先生著《晚清史要》序
楊天石先生來信告知香港三聯書店將出版他有關晚清研究的論文集《晚清史要》,希望我撰一序言,“以紀念你我多年之友誼”。我不敢推辭,只得應命。楊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前輩學者,以民國政治史研究聞名於世。他也是我的老師張朋園先生、汪榮祖先生和墨子刻先生的好友。楊先生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博聞強記、思慮敏捷、口才辨給,聽他在席間縱論民國掌故乃是人間一大快事。
1990 年代中後期,我多次受邀於張海鵬與耿雲志教授,陪同張朋園先生與墨子刻先生去位於北京王府井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每次去訪...
目錄
目錄
楊天石先生著《晚清史要》序黃克武
第一部分 —
鴉片戰爭前後 001
林清起義攻入皇宮之後的思考—龔自珍的《明良》四論002
鴉片戰爭期間的龔自珍007
馬桶陣、面具兵與“五虎”制敵009
《天朝田畝制度》與“割尾巴”011
太平天國的“太陽”013
附:《馮婉貞》的真相與史學家的困惑015
何如璋、黃遵憲初到日本時的筆談019
黃遵憲的《朝鮮策略》及其風波—韓國漢城大學奎章閣讀書記025
黃遵憲與宮島誠一郎—宮島吉亮先生家藏資料研究之一043
黃遵憲與蘇州開埠交涉060
第二部分 —
戊戌變法前後 077
梁啟超為康有為弭禍—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078
翁同龢罷官問題考察084
光緒皇帝的新聞思想099
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后確證102
康有為“戊戌密謀”補證108
天津“廢弒密謀”是維新派的虛構111
附:圍園殺后—康有為的武力奪權密謀116
袁世凱《戊戌紀略》的真實性及其相關問題134
慈禧太后其人148
戊戌變法與近代中國162
唐才常佚札與維新黨人的湖南起義計劃188
沒有不可變的“祖宗之法”—戊戌維新運動一百週年感言192
《戊戌六君子遺集》再版序195
保皇會的“妙語妙事”204
康有為致日、英各國領袖函—讀日本外務省檔案之一206
梁啟超遊美國而夢俄羅斯209
須磨村密札與改良派請殺袁世凱的謀劃212
犬養毅紀念館所見王照、康有為等人手跡—日本岡山訪問所得之一222
第三部分 —
辛亥革命前後 231
畢永年生平事蹟鉤沉232
章太炎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啟》—讀日本外務省檔案244
鄒容自貶《革命軍》247
章士釗與辛亥革命前的理論鼓吹249
1901年至1905年的拒俄運動252
反對取締規則與楊度避難274
陳天華的《要求救亡意見書》及其被否定經過277
托爾斯泰《致一個中國人的信》的遭遇282
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運動285
從“排滿革命”到“聯滿革命”304
為有炮聲動地來—清末報紙對武昌起義的反應306
湯化龍密電辨訛317
康有為的聯滿倒袁計劃—讀台灣所藏梁啟超未刊函稿332
清末,中國的改良道路為何沒有走通341
目錄
楊天石先生著《晚清史要》序黃克武
第一部分 —
鴉片戰爭前後 001
林清起義攻入皇宮之後的思考—龔自珍的《明良》四論002
鴉片戰爭期間的龔自珍007
馬桶陣、面具兵與“五虎”制敵009
《天朝田畝制度》與“割尾巴”011
太平天國的“太陽”013
附:《馮婉貞》的真相與史學家的困惑015
何如璋、黃遵憲初到日本時的筆談019
黃遵憲的《朝鮮策略》及其風波—韓國漢城大學奎章閣讀書記025
黃遵憲與宮島誠一郎—宮島吉亮先生家藏資料研究之一043
黃遵憲與蘇州開埠交涉060
第二部分 —
戊戌變法前後 077
梁啟超為康有為弭禍—近世名人未刊函電...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