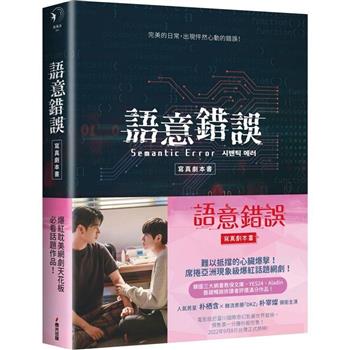序
平埔研究與台灣許多流行事物一樣,從默默無聞,到突然爆紅,最後又歸於平靜。在1980年代以前,甚少有人進行平埔研究,當時的平埔研究者甚至慨嘆平埔研究為「學術雞肋」。然而從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這段期間,平埔研究就像是爆紅的蛋塔或海角七號電影一樣,在跨領域的學術界甚至民間的文史工作者之間掀起了一股熱潮,各式各樣的平埔研究或尋根探源的工作,在這一段期間有豐富的發展。而筆者也像一般的市場大眾一樣,在1998年這段平埔研究市場進入高峰時投入關注,開始注意平埔族的相關事務。如果將學術研究比擬為股票市場,平埔研究這檔熱門股已經在2000年達到最高點(詳見第一章),這也意味著筆者進場的時間已經太晚了。而事實證明,筆者在2004年才完成第一本平埔研究論文,那時平埔研究已經處於下跌的階段了。當下平埔研究已非熱門股,但是很慶幸地它還沒有到達下市的境地,還是有許多同好持續進場關注。不過,無可否認地,今日的平埔研究已不復昔日的榮景,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為低迷的平埔研究市場,注入一點活水。
話說回來,雖然學術研究有其市場取向,但是研究興趣的支撐也同樣重要。雖然已經不記得在什麼時候什麼情境下首次接觸到平埔議題,但我還記得深入對平埔議題產生興趣是在1998年,那時為了協助家兄製作家鄉網站而多方閱讀文史書籍,當時在楊碧川所著的《簡明台灣史》讀到一段關於「平埔族大流亡」的敘述,其內容提到:「新頭家大清來了以後,原住民更被迫退到山邊僻地,新港社番退入新化的左鎮、岡仔林、高雄的旗山、木柵、溝坪……」。當初讀到這段內容時,內心的激動可以說是無法言語的,因為文中所提到的地名都是我相當熟悉的地方,尤其是旗山、木柵、溝坪等地。當時我心想,我生長在這個區域已經十幾二十年,但卻完全不知道故鄉有所謂的「番仔」的存在,印象中的「番仔」不都是住在深山地區嗎?
就這樣抱著尋根探源的情懷,我開始閱讀相關的平埔研究文獻,並回溯以前的生活經驗,試圖將自己的生活經驗與故鄉有「番仔」的事實進行連結,這樣的探索工作其實是相當令人振奮的。記得國中時學校有許多同學膚色較為黝黑,五官輪廓深邃鮮明,而且有相當奇特的姓氏。當時雖然有覺得這些同學很特別,但是從語言以及文化習慣來看,並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族群差異,我也相信些同學們也應該不認為他們是有別於漢人的「番仔」。當時有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案例,有一個姓黃的男同學,他長得相當好看,皮膚也不算黝黑,但其深邃的眼眶輪廓有一次引起一位老師的好奇詢問。老師問他是不是原住民,他神色堅定地回答說不是。當時我只覺得老師是不是想太多了,因為這學區根本就沒有「原住民」。以現在的角度來看,我那位同學應該就是平埔族裔,而其他具有濃厚平埔特徵的同學應該也是平埔族裔。但在1980年代的當時,他們知不知道自己就是平埔族裔呢?
我看別人像原住民,那別人又怎麼看待我自己呢?既然自己的家鄉有許多平埔族裔的存在,因此在平埔研究的過程中,我也懷著自我尋根的心情探詢自己是否有平埔淵源。在我的生活經驗裡,並沒有被視為原住民的體驗,也沒有任何能自我察覺的原住民的文化習俗。但關注台灣史的人應該都知道「有唐山公,沒有唐山嬤」的道理。當我知道可以查詢日本時代的戶籍資料來探查族群背景時,藉著研究的便利,我曾經逐一檢視了家鄉村落所屬的日本時代戶籍資料簿,從那古老殘破但珍貴的戶籍簿當中,我發現我的祖母、曾祖母、外曾祖母都有濃厚的平埔淵源,尤其外曾祖母更被明確登記為「熟」。
曾經有人估計,全台灣像我這樣具有平埔淵源的人超過八成。這個數字可以被作許多不同的政治解讀,筆者無意涉入其中的糾葛。在擁有多重族群選擇空間時,要進行單選題的族群認同選擇並不是當務之急。我最關心的是,從這樣的自我探索過程中,至少我知道自己是誰,也可以避免陷入單純以父系認同來透視世界的迷思,畢竟母系祖先也有很高的機率提供我們同樣比例的血緣。然而可惜的是,在父系漢族沙文主義的影響下,這廣大的埔漢混血者當中,許多人可能不知母系是平埔族,甚至因無知而有蔑稱平埔族為「番仔」的可悲情形,無形中不但傷害了原住民∕平埔族,也傷害了自己。混血者的無知所造成的傷害固然悲哀,但身為血統較為純正的平埔族裔若也處於無知狀態,其悲哀恐怕更甚於混血者。
基於自我探索,嘗試更進一步瞭解自己是「誰」的動力,族群認同的研究成為我進行平埔研究的重點。在過去平埔族被污名化為「番仔」的情境下,要去挖掘自己祖宗八代的歷史,要平埔族裔「番」回歷史,其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這也是為何過去平埔認同研究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誠如早期的美國社會學者Marcus L. Hansen所提的「第三代返回」理論所言:「兒子所亟欲忘記的,是孫子所亟欲記住的」(what the son wishes to forget the grandson wishes to remember)。以前被污名化的平埔族裔或許想極力擺脫「番」的污名,而試圖隱藏或忘卻其平埔淵源,但時至今日已經歷經了不只第三代,平埔認同的尋根探源已經廣泛為平埔族裔或者一般民眾所接受了。可惜的是,當下的平埔認同研究還是太少,而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平埔族的瞭解也還是嚴重不足。因此筆者鄭重呼籲,平埔研究(尤其是認同研究)還是有持續進行的必要。
以西拉雅族而言,其族裔之平埔認同復振運動事實上已經有一定的規模,而台南縣政府更已認定西拉雅族為縣定的原住民族。縱使西拉雅族要得到中央政府正式認定為原住民族仍有一段艱辛的路要走,但地方政府與族裔的努力仍值得肯定。然而,比較可惜的是,或許是受到過去以傳統祀壺∕公廨信仰為主流之平埔研究典範所影響,今日的西拉雅復振運動似乎也以傳統宗教文化的承襲者為主流,而已經改宗基督教或其他信仰的族裔則往往被忽略。即使有像新化口埤教會這樣致力於以語言作為認同復振的一群,但他們的努力仍未能與主流的認同復振者有效結合,殊為可惜。除了台南縣以外,高雄縣也是西拉雅族裔群聚之處,但迄今除了少數傳統宗教文化較為顯著的聚落較受關注外(例如甲仙小林),其餘改宗基督教或其他信仰的族裔也處於被邊緣化的狀態。
平埔研究曾經一度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但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平埔族的認識還是相當有限。在今日平埔研究已經趨緩,有清楚的平埔淵源意識的族裔仍是少數,而承襲傳統宗教文化且有平埔認同之族裔更是少數的情境下,有志復振平埔認同者著實有必要更加團結,並將關注的範圍擴大到所有可能的族裔。筆者基於這樣的信念,於本書的內容安排上也與主流的平埔研究典範有所差異。本書以西拉雅平埔族為研究範圍,除了有探究傳統平埔宗教依然活絡的熱門聚落之外,也嘗試對改宗其他宗教之聚落與族裔進行探究。
本書雖然大多數之章節內容都已曾經發表過,但將全文之邏輯彙整,文辭之潤飾、增刪等工作,也必須耗費許多時間。將文章集結成書的想法事實上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卻一直無法付諸實行。本書的完成,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妻子,若非她的支持與督促,本書之完成恐怕不知還要延宕至何時。此外,我也要謝謝娃娃與佳佳這兩個可愛孩子的體諒,我必須犧牲陪伴他們的時光,閉關在電腦桌前敲敲打打。當然,若非岳父岳母多所犧牲,特別南北兩地奔波幫忙照顧小孩,本書也無法完成。再者,我要感謝所有協助我進行研究的人,特別是提供我研究靈感的我敬愛的父親母親與兄長們,接受我訪談的平埔族裔、漢族裔,以及協助田野訪談的研究助理們,沒有你們的幫忙不可能有具體的研究內容出現。我也要感謝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的出版,尤其是院長施正鋒教授的敦促與協助,讓本書能在緊湊的期限內順利付梓。最後,感謝翰蘆出版社編輯部的校稿與編輯,有你們專業且有效率的協助,讓本書更具可看性。
謝國斌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東華原住民族叢書(8):平埔認同的消失與再現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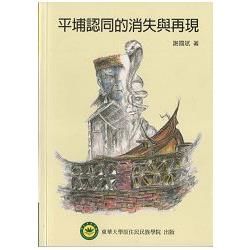 |
$ 237 ~ 250 | 東華原住民族叢書(8):平埔認同的消失與再現
作者:謝國斌 出版社: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2-01 語言:繁體書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東華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東華原住民族叢書(8):平埔認同的消失與再現
台灣具有平埔淵源之人,據估計超過八成,因此,對於平埔族的認同與理解,感情層面上也有尋根的意義。
九○年代「平埔學」曾蔚為風潮,惟後來漸趨消寂,本書出版,在本土研究上意義深遠,作者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社會學博士,對於平埔研究懷抱高度熱情,受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支持和施正峰教授鼓勵,卓然成書。這是研究平埔漢人極重要的著作,更是有意研究原住民文化或參加相關認證與研究所考試必讀之作。
作者序
序
平埔研究與台灣許多流行事物一樣,從默默無聞,到突然爆紅,最後又歸於平靜。在1980年代以前,甚少有人進行平埔研究,當時的平埔研究者甚至慨嘆平埔研究為「學術雞肋」。然而從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這段期間,平埔研究就像是爆紅的蛋塔或海角七號電影一樣,在跨領域的學術界甚至民間的文史工作者之間掀起了一股熱潮,各式各樣的平埔研究或尋根探源的工作,在這一段期間有豐富的發展。而筆者也像一般的市場大眾一樣,在1998年這段平埔研究市場進入高峰時投入關注,開始注意平埔族的相關事務。如果將學術研究比擬為股票市場,平埔研究這...
平埔研究與台灣許多流行事物一樣,從默默無聞,到突然爆紅,最後又歸於平靜。在1980年代以前,甚少有人進行平埔研究,當時的平埔研究者甚至慨嘆平埔研究為「學術雞肋」。然而從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這段期間,平埔研究就像是爆紅的蛋塔或海角七號電影一樣,在跨領域的學術界甚至民間的文史工作者之間掀起了一股熱潮,各式各樣的平埔研究或尋根探源的工作,在這一段期間有豐富的發展。而筆者也像一般的市場大眾一樣,在1998年這段平埔研究市場進入高峰時投入關注,開始注意平埔族的相關事務。如果將學術研究比擬為股票市場,平埔研究這...
»看全部
目錄
第1章 導論:平埔認同研究之發展
1. 平埔研究與政治發展的連動:沈潛、興盛、消退
2. 平埔研究的途徑:歷史途徑的興盛與田野途徑的弱勢
3. 認同研究的重要性:釐清「誰」是平埔族?
4. 平埔族認同的消失與再現?
5. 研究範圍界定與論文架構
第2章 族群認同理論文獻回顧與評述
1. 族群的定義與區別族群的指標
2. 族群的形成與維繫
3. 族群關係
4. 族群同化的層面
5. 影響族群存續程度的情境因素
6. 族群同化理論對平埔研究的啟示
第3章 西拉雅平埔族的過去
1. 早期他者眼中的西拉雅平埔族
2. 19世紀末的西拉雅平埔...
1. 平埔研究與政治發展的連動:沈潛、興盛、消退
2. 平埔研究的途徑:歷史途徑的興盛與田野途徑的弱勢
3. 認同研究的重要性:釐清「誰」是平埔族?
4. 平埔族認同的消失與再現?
5. 研究範圍界定與論文架構
第2章 族群認同理論文獻回顧與評述
1. 族群的定義與區別族群的指標
2. 族群的形成與維繫
3. 族群關係
4. 族群同化的層面
5. 影響族群存續程度的情境因素
6. 族群同化理論對平埔研究的啟示
第3章 西拉雅平埔族的過去
1. 早期他者眼中的西拉雅平埔族
2. 19世紀末的西拉雅平埔...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謝國斌
- 出版社: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2-01 ISBN/ISSN:978986017652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9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文化研究
|
 東華是香港中西區區議會下轄的選區,代號A13,於1994年設立,現任區議員為民主黨成員伍凱欣。
東華是香港中西區區議會下轄的選區,代號A13,於1994年設立,現任區議員為民主黨成員伍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