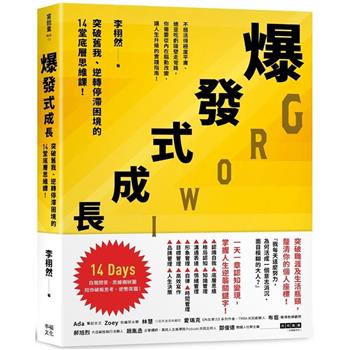朱增祥醫師,被傳媒稱為「出入港督府的中醫」,皆因在彭定康時代,中醫當中就只有他一位在港督府出入,為前港督夫人治愈其痛症。朱醫師也是風靡台灣的拍打拉筋法始創人,名人政要、演藝明星向他求診的多不勝數,包括︰周梁淑怡、杜琪峰、鍾楚紅、汪明荃、袁詠儀、金城武等……
<<棒敲擊療法>>是朱醫師累積五十年經驗創造的一種實用新療法。眾多的奇難雜症︰五十肩、椎間盤突出、類風濕關節炎、肩周炎、股骨壞死、筋縮、駝背……在朱醫師的妙手和創新的療法之下得以治癒。
這本書讓你更清楚了解這種療法的根據和技巧,帶你進入嶄新的中醫傷科療法世界!
此書詳盡介紹了棒敲擊療法的來源和發展、操作手法與技巧和朱醫師多年使用此法治病的心得,還有講解了製棒物料和技巧,讓讀者對這個較罕見的中醫療法有更具體的認識。
朱醫師行醫五十年,遇到過的奇難雜症多如繁星,此書收錄了很多病患故事,記錄了這些病人如何在病痛的折磨中得到朱醫師的拯救,體現了朱醫師斷症的準確,不墨守成規的求真態度,和他對醫學研究的熱誠。書中多少難治之症經朱醫師的獨創療法醫治下都有立竿見影的療效,例如︰類風濕關節炎、肩周炎、痛風、椎間盤突出……
書中有個部分,記錄了一些朱醫師行醫生涯中遇到過的不能治好的病例,這是作者希望讓大家了解得更多、更真實、更全面,不想讀者以為他是神醫──什麼病都能治,而身患這些症狀的讀者,也就不必花費精力與財力千里迢迢到香港找他。此外,也給作者本人一種鞭策力,更努力研究。體現了這位仁醫的責任心和謙虛的態度。
末章怪醫心語是作者的個人隨筆,讀者們可在這些文章中窺探這位怪醫做人處事和行醫的態度。
本書特色
棒敲擊療法作為一種創新的中醫傷科療法,作者在這本書中詳記其由來、使用技巧、作用、要注意的事項和心得等,讓大家更了解這個療法的來龍去脈。此外,朱醫師行醫五十年來,利用此療法治癒無數奇難雜症,書中有林林種種不同病患的故事,有長期眼臉抽搐的、有只能半屈膝走路的、有走路只能腳尖觸地的, 有終日頭暈頭痛的、有手不能動的、有頭不能動的……娓娓道來他們經朱醫師妙棒一揮之下的康復過程,更令人驚嘆這種療法神奇兼快速的療效!
從怪醫心語中,讀者更可一窺這位仁醫的處世和行醫之道,更深入認識這位治癒過多位名人政要和演藝明星的杏林奇葩之內心世界!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棒敲擊療法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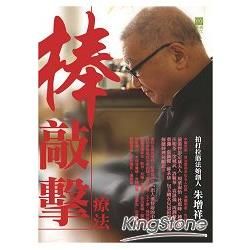 |
$ 237 ~ 238 | 棒敲擊療法
作者:朱增祥 出版社:青森文化 出版日期:2013-06-14 語言:繁體書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棒敲擊療法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朱增祥
著名的中醫傷科醫師,出身於世代中醫名家。他總結五十年行醫、研究之經驗,發明和創造了治療脊柱及關節錯位的頸、胸、腰、四肢關節復位技巧和三種針對筋緊、筋硬、筋縮等引起的肌肉僵硬症治療方法和醫療器械︰拉筋櫈、棍針和敲擊。經無數臨床案例証明,以上療法具有快速、省錢和治本的奇妙療效。
朱增祥
著名的中醫傷科醫師,出身於世代中醫名家。他總結五十年行醫、研究之經驗,發明和創造了治療脊柱及關節錯位的頸、胸、腰、四肢關節復位技巧和三種針對筋緊、筋硬、筋縮等引起的肌肉僵硬症治療方法和醫療器械︰拉筋櫈、棍針和敲擊。經無數臨床案例証明,以上療法具有快速、省錢和治本的奇妙療效。
目錄
第一章 來龍去脈
什麼叫棒敲擊治病法
敲擊棒的來源與發展
敲擊棒的分類
敲擊棒的操作手法
棒敲擊時的持棒方法
敲擊棒治病時的動作要點
敲擊棒治病時的手法
棒敲和棒擊的區別
敲擊棒的作用
棒敲擊治療法的適應證和禁忌證
手拍打與棒敲擊有何不同
棒敲擊治療後的注意事項
第二章 棒敲擊神效
股票經紀人的苦惱
不知道的反應
百變的冷氣病
半屈膝進來的男士
前衛的髮型師
擺明要來挨打的
通則不痛
患有筋縮症的年輕人
她到底是什麼病
玩槍後的肩痛
腳踝扭傷的老爺子
產後風
身體側彎的女士
他的膝痛二十年
頭暈頭痛,活動受限
走路只能腳尖點地的女士
西醫患者的信任
遍尋名醫的她
半邊臉、眼抽搐的男子
二百公斤的他,拄著拐來
慢性病容的年輕男子
物理治療師的苦惱
患肩周炎的女士
類風濕關節炎意外的收穫
理解萬歲
重症監護室的護士
加拿大來的女士
地鐵修理工
太極拳愛好者的背痛
瑜伽愛好者的膝痛
她真的是S彎,長短腿嗎?
用土方法對付洋學生
脖子突然不能動了
不能彎腰的背
吹冷氣的律師
肌無力患者的哈哈大笑
頸椎退化的女喇嘛
救生員的手,不能動了
淚流滿面的美容師
樓梯滑倒後的全身痛
馬先生的背不駝了
全身不適的空姐
痛則不通
做完治療才知道病因的男子
頭不能動的音樂家
第三章 口傳心授
致病因素篇
製棒技巧
用棒技巧
棍棒心得
吹噓的包治百病
第四章 看不了的病
骨結核的病人
壓縮性骨折患者的腰痛
陝西來的老夫妻
吃標靶藥物的人
十幾年前做過手術的脊椎側彎
裝了心臟起搏器的老人
他到底要幹嘛
不能醫的彈弓手
這一次我也無能為力
請不要再來找我
坐輪椅來的女孩
不能看的「O」型腿
為什麼我的病不能看
醫不了的側彎
冷氣吹出來的疼痛
幫助不大的筋縮
四歲的小男孩
未能醫好的腿疼
無從下手治療的打嗝
第五章 患者心聲
神醫治病,「神棒」強身
打走的病痛
朱醫師讓我老有所健
我得到的不僅是健康
不能不寫的經歷
神奇的療法
從懷疑到相信,感謝朱醫師
誠心感謝
感謝信
第六章 怪醫心語
說話
談事
做人
治病
我如浮萍
做個有心人
捨得
練功
車輪
路
低調
金子,銀子,鐵
角度
觀人於細微處
廣闊的思路
看書
明白 通透
什麼叫棒敲擊治病法
敲擊棒的來源與發展
敲擊棒的分類
敲擊棒的操作手法
棒敲擊時的持棒方法
敲擊棒治病時的動作要點
敲擊棒治病時的手法
棒敲和棒擊的區別
敲擊棒的作用
棒敲擊治療法的適應證和禁忌證
手拍打與棒敲擊有何不同
棒敲擊治療後的注意事項
第二章 棒敲擊神效
股票經紀人的苦惱
不知道的反應
百變的冷氣病
半屈膝進來的男士
前衛的髮型師
擺明要來挨打的
通則不痛
患有筋縮症的年輕人
她到底是什麼病
玩槍後的肩痛
腳踝扭傷的老爺子
產後風
身體側彎的女士
他的膝痛二十年
頭暈頭痛,活動受限
走路只能腳尖點地的女士
西醫患者的信任
遍尋名醫的她
半邊臉、眼抽搐的男子
二百公斤的他,拄著拐來
慢性病容的年輕男子
物理治療師的苦惱
患肩周炎的女士
類風濕關節炎意外的收穫
理解萬歲
重症監護室的護士
加拿大來的女士
地鐵修理工
太極拳愛好者的背痛
瑜伽愛好者的膝痛
她真的是S彎,長短腿嗎?
用土方法對付洋學生
脖子突然不能動了
不能彎腰的背
吹冷氣的律師
肌無力患者的哈哈大笑
頸椎退化的女喇嘛
救生員的手,不能動了
淚流滿面的美容師
樓梯滑倒後的全身痛
馬先生的背不駝了
全身不適的空姐
痛則不通
做完治療才知道病因的男子
頭不能動的音樂家
第三章 口傳心授
致病因素篇
製棒技巧
用棒技巧
棍棒心得
吹噓的包治百病
第四章 看不了的病
骨結核的病人
壓縮性骨折患者的腰痛
陝西來的老夫妻
吃標靶藥物的人
十幾年前做過手術的脊椎側彎
裝了心臟起搏器的老人
他到底要幹嘛
不能醫的彈弓手
這一次我也無能為力
請不要再來找我
坐輪椅來的女孩
不能看的「O」型腿
為什麼我的病不能看
醫不了的側彎
冷氣吹出來的疼痛
幫助不大的筋縮
四歲的小男孩
未能醫好的腿疼
無從下手治療的打嗝
第五章 患者心聲
神醫治病,「神棒」強身
打走的病痛
朱醫師讓我老有所健
我得到的不僅是健康
不能不寫的經歷
神奇的療法
從懷疑到相信,感謝朱醫師
誠心感謝
感謝信
第六章 怪醫心語
說話
談事
做人
治病
我如浮萍
做個有心人
捨得
練功
車輪
路
低調
金子,銀子,鐵
角度
觀人於細微處
廣闊的思路
看書
明白 通透
序
自序
我的醫家和我的醫術
我出生在一個中醫世家,太祖父朱南山由南通學醫,年輕時到上海行醫,擅長醫治婦科疾病,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被稱為十大名醫。祖父朱鶴皋除了精通婦科、內科、兒科外,對傷科復位也很拿手。我在十歲時曾親眼見到一位下頷脫臼的病人,看了幾位師傅也無法復位,祖父用雙手大拇指一按一托就復位了,非常容易,也許這是我喜歡傷科的原因。父親朱南蓀繼承祖訓,集家傳內、婦、兒科於一身。
我朱增祥二門傳授,除家傳外,外太公沈篆如是蘇州名醫,官職本為府台三品,但棄官從醫,薄良相,為良醫,外公沈衡甫亦專長婦科。
最初我學醫拜在嚴陵老師門下,學習中醫內科,在前輩身上學到醫德、醫術、醫理,然而我卻喜歡傷科,因能即時看見療效。另外李錫九老師的手法,黃恤民老師的醫術理論,李春陽老師樸素實用的治法、治則,對我都有較大影響,我今天有一點經驗,全賴三位前輩的啟蒙。
嚴老師有兩句話我永遠銘記在心,一是輕可取賓,重病也不一定要用重藥;二是忙而不亂,即使病人再多、病情再急也要鎮定,千萬不可慌張。李春陽老師訓導我,凡脫臼復位要用巧力,不可用蠻力,最主要是用拔伸手法;錯位的復位方法主要是拔伸、按壓、旋轉、抖動,不能用死力,一定要用巧力;遇到疑難痛症一定要多想通了才可落手診治,不可魯莽。祖父常說:「醫不好病人不要緊」,只要是盡心盡力去醫,對病人負責任便問心無愧;另外又常說:「不要醫壞人」,不會的千萬不要亂開藥,治不了的病應該跟病人或其家屬交代清楚,絕不能為了錢而胡亂醫人!
外公沈衡甫嘴邊常有一句話:「天下無棄物」—「宇宙皆萬物,萬物皆有用,不是物無用,是你不知用。」幾千年來中醫留下了無數的寶藏,又有多少識貨之人將它發揚光大?炎黃子孫又有多少是熱衷於保留、發掘這些?中藥雖有毒藥,卻可以毒攻毒,現今的中醫又有誰敢去使用?社會是否同意你這樣做?難矣!十年或數百年後,人們可能又會再找出毒藥去醫治頑疾,哈哈,那時候這些棄物就可以翻身了!真的希望有人能繼續真誠發掘中國醫學的寶藏,並將之發揚光大,推廣至全世界!
家父與我經常閒談,父曰:「晉代名醫王叔和,專長脈理,然想做好中醫單靠脈象不夠全面,古有『熟讀王叔和,不及臨症多』,想做一個好中醫,除脈理外,還要多臨床、多醫症,方可成為一個全面的中醫。」
王叔和有一順口溜:「家有不賢妻,砒霜當藥醫,乘我一年運,快快來求醫。」大意是某日王叔和外出診病,夫人在家,突然眾人抬了一個面青、呼叫肚痛的病人前來求醫,因吃生冷所起,出冷汗,情況很急。叔和不在,王妻走到平時放著很多小瓶的藥架邊,隨手拿了一個小瓶,倒了少少紅粉交給其家人,病者立即服下,不多時病者不叫痛,面色轉為微紅,平靜得很,一會兒後病者家人抬著患者回家,患者道:「吾可自行,不必再抬。」家人扶著下地,慢步離去。叔和到家,妻笑曰剛才一切經過,叔和急問:「拿的是何藥?你怎可亂拿呢?」妻曰:
「每每見你急診都在此架上拿藥,我有何不可?」叔和曰:「此乃砒霜,有毒,怎能亂服?」妻曰: 「不是好好的步離我家? 我錯在何處? 」叔和曰: 「今你好運, 下次切記不可亂來。」
其實萬物均有用,天下無棄物,雖謂毒藥,也可醫病,這就要看醫師本身的修養多高。
能者不難,難者不能。古人有上山學藝,學成下山,然後才創一番事業。
兒時聽家人講上海冬季下大雪,馬路上的乞丐們是怎樣穿單薄的衣服渡過嚴寒呢?他們在中藥店買少少紅砒,用酒送下,這樣全身滾熱。他們是靠砒霜逃過嚴冬的。
《七俠五義》中蔣平寒潭盜印,下寒潭前先飲紅砒酒,方能潛入寒潭取回大印,所以古人早就懂得利用毒藥的另類作用,幫助解決生活中的困難。
可惜現在,中醫的醫治範圍愈來愈小,急診病人大部分都被送往急診室,輪不到中醫開單煎藥,中藥以往的急救法到哪裡去了?
以上所述是長輩日常口頭傳,只要有心人便可從中汲取養料,我對以上各老師長輩們的教誨,至今仍謹守遵從,亦以此教導我的晚輩。
薑是老的辣,人是老的精,經驗亦是老的豐富,辦法當然又是老的多,年輕人雖然敢闖,但沒有經驗,又往往遇到急症不夠冷靜,也缺乏一整套的辦法,面對千變萬化的病症時便束手無策,正如我的祖父常說:「行醫者初學三年天下通行,再做三年寸步難行。」
我寫這本書是因為自己感覺到,現在有必要把我的治病方法流傳下去,這本書主要是給我的病人、了解我的醫術及相信我的讀者閱讀的。因為事實上療效太神奇、太不可思議了,不熟悉我的人一定會打上很多問號:「真有這種事?是不是真的?有這種可能性嗎?你是否碰運氣?你真的太好運了,我做這麼多年醫務工作,怎麼遇不到這種事?」以上是客氣的想法。有的則會想:「一派胡言!吹牛!」
我寫這本書是因為自己得了肝癌,做了三次射頻手術,現在跟正常人一樣過活,行動自如,生活的質量很高,與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但癌症這種病,說變就變,昨天還一切正常,一星期後也許情況就惡化了,因此在我還可以說、可以寫的時候,把這本書寫下來。
我希望我的讀者、我的病人,或是他們的家屬、親戚、朋友、總之是曾看見病人所受的病痛,了解他曾找過無數醫生治療,痛不欲生,最後抱著姑且一試的心念來找我,看到幾分鐘或十幾分鐘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讓世人知道很多病症其實並不是那麼可怕,而且沒有那些醫生說得那麼嚴重;也可能會看見有些病症我不懂醫治,因為有很多病症我既不認識亦不會醫治,但我會坦白告訴病人我不懂,希望他另請高明,我不會診治不代表這病不能醫治,有些病的症狀雖多,痛苦亦不少,但病況卻不複雜,只是沒有找到病因,但若知道病症的起因在何處,就容易解決了。所以,這本書是我寫給我的病人和朋友們的,若由我的病人手上推介出去,患者就信心大增了。
最後我必須衷心感謝兩位教授—查良鎰教授及陳敏華教授。當我被發現患了肝癌,家人非常緊張,四方八面通訊聯絡(因為家族中有很多中、西醫的專業人才。各方回音:「最多生存三個月到半年」,可做的是換肝)。就在這緊急關頭,查良鎰教授為我聯絡陳敏華教授,在北京用射頻替我燒掉肝瘤,連續三次都使我在病情復發時轉危為安。一直以來,一切大小病症皆由兩位教授保我過關斬將,衝出死亡重圍。二零零一年後我的病人們,你們能夠得以治愈,解除多年來的苦痛,不要感謝我,應該感恩於兩位救我性命的仁醫!
我的醫家和我的醫術
我出生在一個中醫世家,太祖父朱南山由南通學醫,年輕時到上海行醫,擅長醫治婦科疾病,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被稱為十大名醫。祖父朱鶴皋除了精通婦科、內科、兒科外,對傷科復位也很拿手。我在十歲時曾親眼見到一位下頷脫臼的病人,看了幾位師傅也無法復位,祖父用雙手大拇指一按一托就復位了,非常容易,也許這是我喜歡傷科的原因。父親朱南蓀繼承祖訓,集家傳內、婦、兒科於一身。
我朱增祥二門傳授,除家傳外,外太公沈篆如是蘇州名醫,官職本為府台三品,但棄官從醫,薄良相,為良醫,外公沈衡甫亦專長婦科。
最初我學醫拜在嚴陵老師門下,學習中醫內科,在前輩身上學到醫德、醫術、醫理,然而我卻喜歡傷科,因能即時看見療效。另外李錫九老師的手法,黃恤民老師的醫術理論,李春陽老師樸素實用的治法、治則,對我都有較大影響,我今天有一點經驗,全賴三位前輩的啟蒙。
嚴老師有兩句話我永遠銘記在心,一是輕可取賓,重病也不一定要用重藥;二是忙而不亂,即使病人再多、病情再急也要鎮定,千萬不可慌張。李春陽老師訓導我,凡脫臼復位要用巧力,不可用蠻力,最主要是用拔伸手法;錯位的復位方法主要是拔伸、按壓、旋轉、抖動,不能用死力,一定要用巧力;遇到疑難痛症一定要多想通了才可落手診治,不可魯莽。祖父常說:「醫不好病人不要緊」,只要是盡心盡力去醫,對病人負責任便問心無愧;另外又常說:「不要醫壞人」,不會的千萬不要亂開藥,治不了的病應該跟病人或其家屬交代清楚,絕不能為了錢而胡亂醫人!
外公沈衡甫嘴邊常有一句話:「天下無棄物」—「宇宙皆萬物,萬物皆有用,不是物無用,是你不知用。」幾千年來中醫留下了無數的寶藏,又有多少識貨之人將它發揚光大?炎黃子孫又有多少是熱衷於保留、發掘這些?中藥雖有毒藥,卻可以毒攻毒,現今的中醫又有誰敢去使用?社會是否同意你這樣做?難矣!十年或數百年後,人們可能又會再找出毒藥去醫治頑疾,哈哈,那時候這些棄物就可以翻身了!真的希望有人能繼續真誠發掘中國醫學的寶藏,並將之發揚光大,推廣至全世界!
家父與我經常閒談,父曰:「晉代名醫王叔和,專長脈理,然想做好中醫單靠脈象不夠全面,古有『熟讀王叔和,不及臨症多』,想做一個好中醫,除脈理外,還要多臨床、多醫症,方可成為一個全面的中醫。」
王叔和有一順口溜:「家有不賢妻,砒霜當藥醫,乘我一年運,快快來求醫。」大意是某日王叔和外出診病,夫人在家,突然眾人抬了一個面青、呼叫肚痛的病人前來求醫,因吃生冷所起,出冷汗,情況很急。叔和不在,王妻走到平時放著很多小瓶的藥架邊,隨手拿了一個小瓶,倒了少少紅粉交給其家人,病者立即服下,不多時病者不叫痛,面色轉為微紅,平靜得很,一會兒後病者家人抬著患者回家,患者道:「吾可自行,不必再抬。」家人扶著下地,慢步離去。叔和到家,妻笑曰剛才一切經過,叔和急問:「拿的是何藥?你怎可亂拿呢?」妻曰:
「每每見你急診都在此架上拿藥,我有何不可?」叔和曰:「此乃砒霜,有毒,怎能亂服?」妻曰: 「不是好好的步離我家? 我錯在何處? 」叔和曰: 「今你好運, 下次切記不可亂來。」
其實萬物均有用,天下無棄物,雖謂毒藥,也可醫病,這就要看醫師本身的修養多高。
能者不難,難者不能。古人有上山學藝,學成下山,然後才創一番事業。
兒時聽家人講上海冬季下大雪,馬路上的乞丐們是怎樣穿單薄的衣服渡過嚴寒呢?他們在中藥店買少少紅砒,用酒送下,這樣全身滾熱。他們是靠砒霜逃過嚴冬的。
《七俠五義》中蔣平寒潭盜印,下寒潭前先飲紅砒酒,方能潛入寒潭取回大印,所以古人早就懂得利用毒藥的另類作用,幫助解決生活中的困難。
可惜現在,中醫的醫治範圍愈來愈小,急診病人大部分都被送往急診室,輪不到中醫開單煎藥,中藥以往的急救法到哪裡去了?
以上所述是長輩日常口頭傳,只要有心人便可從中汲取養料,我對以上各老師長輩們的教誨,至今仍謹守遵從,亦以此教導我的晚輩。
薑是老的辣,人是老的精,經驗亦是老的豐富,辦法當然又是老的多,年輕人雖然敢闖,但沒有經驗,又往往遇到急症不夠冷靜,也缺乏一整套的辦法,面對千變萬化的病症時便束手無策,正如我的祖父常說:「行醫者初學三年天下通行,再做三年寸步難行。」
我寫這本書是因為自己感覺到,現在有必要把我的治病方法流傳下去,這本書主要是給我的病人、了解我的醫術及相信我的讀者閱讀的。因為事實上療效太神奇、太不可思議了,不熟悉我的人一定會打上很多問號:「真有這種事?是不是真的?有這種可能性嗎?你是否碰運氣?你真的太好運了,我做這麼多年醫務工作,怎麼遇不到這種事?」以上是客氣的想法。有的則會想:「一派胡言!吹牛!」
我寫這本書是因為自己得了肝癌,做了三次射頻手術,現在跟正常人一樣過活,行動自如,生活的質量很高,與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但癌症這種病,說變就變,昨天還一切正常,一星期後也許情況就惡化了,因此在我還可以說、可以寫的時候,把這本書寫下來。
我希望我的讀者、我的病人,或是他們的家屬、親戚、朋友、總之是曾看見病人所受的病痛,了解他曾找過無數醫生治療,痛不欲生,最後抱著姑且一試的心念來找我,看到幾分鐘或十幾分鐘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讓世人知道很多病症其實並不是那麼可怕,而且沒有那些醫生說得那麼嚴重;也可能會看見有些病症我不懂醫治,因為有很多病症我既不認識亦不會醫治,但我會坦白告訴病人我不懂,希望他另請高明,我不會診治不代表這病不能醫治,有些病的症狀雖多,痛苦亦不少,但病況卻不複雜,只是沒有找到病因,但若知道病症的起因在何處,就容易解決了。所以,這本書是我寫給我的病人和朋友們的,若由我的病人手上推介出去,患者就信心大增了。
最後我必須衷心感謝兩位教授—查良鎰教授及陳敏華教授。當我被發現患了肝癌,家人非常緊張,四方八面通訊聯絡(因為家族中有很多中、西醫的專業人才。各方回音:「最多生存三個月到半年」,可做的是換肝)。就在這緊急關頭,查良鎰教授為我聯絡陳敏華教授,在北京用射頻替我燒掉肝瘤,連續三次都使我在病情復發時轉危為安。一直以來,一切大小病症皆由兩位教授保我過關斬將,衝出死亡重圍。二零零一年後我的病人們,你們能夠得以治愈,解除多年來的苦痛,不要感謝我,應該感恩於兩位救我性命的仁醫!
朱增祥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於香港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於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