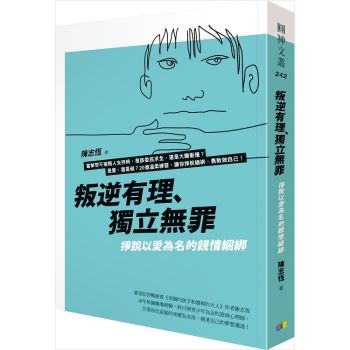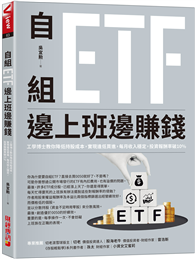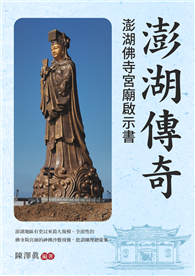前言:亞力的問題
地球上各大洲的族群,有不同的歷史發展軌跡。自從冰期(Ice Age)結束以來,在這1萬3000年間,世界上有些地區發展出有文字的工業社會,發明了各種金屬工具,有些區域仍舊是沒有文字的農業社會,還有一些則停滯於使用石器的狩獵-採集社會。那些歷史的不平等,在現代世界史的面貌上留下了深刻的陰影,因為使用金屬工具的文明社會,征服了或滅絕了其他類型的社會。雖然這些歷史與社會類型的差異是世界史中最基本的事實,原因卻不明,且有爭議。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困惑人的問題,是在25年前。那時這個問題是以比較簡單的形式提出的,發問的人也是從他個人的經歷提問的。
1972年 7 月,我在新幾內亞(New Guinea)沙灘上漫步。那時,我在那裡研究鳥類的演化。我已聽說當地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亞力(Yali)也在這兒活動。一天,我們碰巧在同一條路上,一前一後地走著,後來他追上了我。我們同行了一個小時左右,而且有說不完的話。
亞力散發著領袖的氣質與活力,眼睛閃爍著迷人的神采。談起自己,他滿懷信心,同時向我提出許多深刻的問題,也很專注地聽我訴說。我們的談話從當時每個新幾內亞人都關心的問題開始,就是當時政治局勢的快速變化。今天,亞力的國家正式的國名是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einea),當時仍是聯合國的託管地,由澳大利亞治理,但獨立的呼聲甚囂塵上。亞力說,他的角色就在為自治政府鋪路。
談著談著,亞力話鋒一轉,開始考較起我來。這人從未離開過新幾內亞,教育程度也僅止於中學,卻有一顆永遠無法滿足的好奇心。首先,他想知道我在新幾內亞的鳥類研究(包括可以得到多少酬勞)。我向他解釋,過去幾百萬年來,不同種類的鳥移居至新幾內亞的情況。他問道,在過去的幾萬年中,他的祖先如何在新幾內亞落地生根?又,近兩百年來,歐洲白人如何使新幾內亞淪為他們的殖民地?
雖然我和亞力所代表的兩種社會一直處於緊張關係,我們還是相談甚歡。兩個世紀前,新幾內亞人還活在「石器時代」,歐洲人早在幾千年前就以金屬工具取代了原始的石器。此外,新幾內亞人仍在村落中生活,沒有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白人來到後,設立集權政府,輸入貨品。新幾內亞人立刻發現這些物品的價值,舉凡鐵鑄的斧頭、火柴、藥品,乃至衣服、飲料和雨傘……應有盡有。在新幾內亞,那些一概名之為「貨物」。
許多來此殖民的白人公然鄙視新幾內亞人,說他們「原始」、「落後」。即使是最平庸的白人「主子」(1972年他們仍享有這個尊稱),生活水準都遠超過新幾內亞人,連亞力那樣有魅力的政治人物也不能企及。在亞力考較我之前,他已經考較過許多白人了,而我也考較過許多當地的原住民。我們倆都很清楚,新幾內亞人和歐洲人一樣聰明。那種種情事想必在亞力內心盤旋已久。這時,他那閃爍的雙眼流露出敏銳的心思,問我:「為什麼是白人製造出這麼多貨物,再運來這裡?為什麼我們黑人沒搞出過什麼名堂?」
這個問題雖簡單,但一針見血--在亞力的生活經驗中,那是最基本的事實。是的,就生活方式而言,一般新幾內亞人和一般的歐洲人或美國人仍有很大的差距。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有同樣的差異。這種天壤之別必然有重大原因--你可能會認為顯而易見。
然而,亞力的問題看來簡單,卻難以回答。那時,我還沒有答案。歷史學者仍莫衷一是;大多數人也不再討論這個問題了。與亞力一席話後,這些年來,我一直在研究人類演化、歷史與語言的其他面相。經過25年,本書是為了回答亞力的問題而作。
雖然亞力的問題只涉及新幾內亞人和歐洲白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異,但他的問題可以擴展到現代世界中其他更大現象的對比。歐亞大陸的族群,特別是今天仍然住在歐洲和東亞的人,加上移民到北美洲的人,掌控了現代世界的財富和權力。其他族群,包括大多數的非洲人,雖已推翻歐洲殖民政權,就財富和權力而言,仍遠遠落後。還有一些民族,比方說澳洲、美洲和非洲南端的土著,甚至連自己的土地都丟了,慘遭歐洲殖民者的殺戮、征服,甚至滅族。
因此,對於現代世界中的不平等,套用亞力的問題,我們可以問:為何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是以今天這種面貌呈現,而非其他形式?例如,為什麼越過大洋進行殺戮、征服和滅絕的,不是美洲、非洲或澳洲的土著,而是歐洲人和亞洲人?
即使不從世界的現況出發,回到古代世界,我們仍然可以問同樣的問題:公元1500年,歐洲的殖民擴張才剛開始,各大洲的族群在科技和政治組織的發展上已有相當大的差異。分布於歐、亞與北非的,是使用金屬工具的國家或帝國,有些已逼近工業化的門檻。而美洲土著建立的阿茲特克(Aztecs)和印加帝國(Incas),仍以石器作為主要工具。非洲亞撒哈拉(sub-Saharan)一些小國和酋邦已使用鐵器。其他大多數的族群,包括澳洲和新幾內亞所有的土著、多數太平洋上的島民、大部分的美洲土著和少部分的非洲亞撒哈拉土著,都是農耕部落,或者是使用石器狩獵-採集的遊群(bands)。當然,公元1500年世界各地區在科技和政治發展的差異是現代世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以鋼鐵打造武器的帝國征服或族滅還在利用石器或木器的部落。然而,這個世界是如何發展成公元1500年的模樣的?
同樣地,我們可根據歷史記載和考古學的發現,更進一步地回溯歷史,直到上一次冰期結束時。那是在公元前1萬1000年,當時各大洲上的各個族群皆以狩獵-採集維生。從公元前1萬1000年到公元1500年之間,各大洲的發展速率各不相同,導致1500年世界上科技和政治不平等的現象。澳洲土著和許多美洲土著一直停留在狩獵-採集階段,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美洲和非洲的亞撒哈拉的許多地區逐漸發展出農業、牧業、冶金技術和複雜的政治組織。歐亞大陸的一些地區和美洲的一個區域,也各自發展出文字。然而,這些新發展都在歐亞大陸最早出現。例如,南美西部的安地斯山區(Andes)直到公元1500年的前幾個世紀,才開始大量生產青銅器,比歐亞大陸足足晚了4000年。公元1642年歐洲的探險家首次接觸到塔斯馬尼亞人(Tasmanians),發現他們的石器技術比起好幾萬年前歐洲的舊石器時代晚期製作的石器,要來得簡陋。
總之,關於當今世界不平等的問題,我們可以重述如下:為何各大洲上人文發展的速率迥異?那些不同速率構成的人類歷史基本模式,也是本書的主題。
雖然,本書討論的是歷史與史前史,但主題不僅有學術意義,在經世上與政治上更重要。人類各族群透過征服、傳染病與滅族行動而互動的歷史,就是塑造現代世界的力量。族群衝突在歷史上的回響,經過幾個世紀,至今未嘗稍歇,仍在今日世界上某些最動盪不安的區域發酵。
舉例來說,非洲許多地方仍在現代殖民主義的灰燼中掙扎。其他地區,包括大部分的中美洲、墨西哥、秘魯、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 位於南太平洋、澳洲東部,紐西蘭北部)、前蘇聯和印度尼西亞的部分地區,仍擾攘不安;各地在人口中佔多數的原住民,以街頭暴動或游擊戰,對抗由外來征服者後裔掌控的政府。其他許多地方的原住民--如夏威夷土著、澳洲土著、西伯利亞土著和美國、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印第安人,由於種族屠殺和傳染病,人數銳減,而侵略者後裔卻後來居上,成為絕對的多數。這些族群雖無法發動內戰,卻越來越堅決地爭取自己的權利。
過去的族群衝突除了繼續在今天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中迴盪,對人類的語言世界也造成重大衝擊。今日世上尚存6000種語言,大多數都面臨消失的命運。英語、漢語與俄語,還有其他幾個語言已成為地球上的主流語言。使用這些語言的人口,在最近幾個世紀大幅增加。現代世界中的這些問題,全肇因於各大洲族群不同的歷史發展軌跡。亞力的問題就是這麼來的。
在解答亞力的問題之前,我們應先考慮幾個反對討論這個問題的理由。有些人一看到這個問題就怒不可抑,有幾個原因。
其中一個反對的理由是:若我們解釋某一族群支配另一個族群的緣由,不正是為這樣的奴役支配張目?似乎是振振有辭地說,這種結果是無可避免的,因此改變現況的努力註定徒勞無功?這個反對理由混淆了解釋與辯護,是常見的謬誤。運用歷史解釋和解釋歷史是兩回事。了解往往是為了改變,而不是為了重複或延續。心理學家努力了解謀殺犯或強暴犯、社會史家了解「滅族」事件、醫生了解造成疾病的原因,都抱著同樣的目的。他們並不是為謀殺、強暴、種族滅絕和疾病辯護而研究,釐清了導致這些慘劇與悲劇的因果鎖鏈之後,才能設法打斷那條鎖鏈。
其次,認真對待亞力的問題必然要採用以歐洲為本位的歷史觀,結果當然是吹捧西歐人的業績,執迷於西歐與歐化美國在今日世界的卓越地位。然而,那種卓越地位不過是過去幾個世紀打造出來的。世事如棋,白雲蒼狗,日本和東南亞不是異軍突起,後來居上了嗎?其實,本書主要討論的是歐洲人以外的族群。除了歐洲人和非歐洲人的互動,我們還要討論歐洲以外的不同族群之間的相互關係,尤其是非洲亞撒哈拉、東南亞、印度尼西亞和新幾內亞等地的族群互動。我們不會吹捧源於西歐的族裔,本書將顯示西歐文明最基本的要素,其實是由其他地區的族裔發展出來的。西歐當年是文化入超地區,而不是輸出地區。
第三,「文明」和「文明的興起」這種詞彙會誤導讀者,以為文明是好的,狩獵-採集部落的生活是悲慘的,而過去1萬3000年的歷史見證了「進步」--逼近真善美境界的發展!其實,我並不認為工業化的國家比狩獵-採集部落「高明」到哪裡。也不認為從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換成使用鐵器的國度,就代表「進步」。至於增進人類福祉云云,更是無稽之談。我在美國和新幾內亞村落的生活體驗,讓我明白:文明是福是禍實在難說。例如,比起狩獵-採集部落,現代工業國家的公民享有較佳的醫療照顧、遭到謀殺的風險低、壽命較長,但朋友和親族的社會支持卻少得多。我研究人類社會的地理差異,動機不在鼓吹某一種社會型態的好處,而只是單純地想了解:歷史上,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亞力的問題真需要用一本書來回答嗎?我們不是已經知道答案了嗎?那麼,答案是什麼呢?
或許,最常見的解釋,就是假定族群間有生物差異。公元1500年之後的幾百年間,歐洲探險家注意到世上各個族群之間在科技和政治組織上有相當大的差異。他們認為那是因為各族群的天賦有差異。達爾文理論(Darwinian theory)興起後,天擇與演化系譜成為解釋的工具。既然人是從類似猿猴的祖先演化而來的,技術原始的族群就代表人類演化史上的「過渡階段」。出身工業社會的殖民者之所以能取而代之,不過演示了適者生存的道理。後來,遺傳學的興起,又產生另一套說法。這次套用的是遺傳學:現在歐洲人在遺傳天賦上比非洲人聰明,比起澳洲土著那更不用說了。
今天,西方社會中的一些角落裡可以聽到公然譴責種族主義的聲音,然而許多(也許絕大多數)西方人私底下或潛意識裡仍繼續擁抱種族主義。在日本和其他許多國家,公開支持種族主義的解釋,更是不必抱歉的。甚至連受過教育的白種美國人、歐洲人和澳洲人,一討論到澳洲土著,也不免認為他們比較原始。他們看起來與白種人不同,不是嗎?許多澳洲土著,雖然熬過了歐洲殖民期,他們的子孫在白澳社會中仍然難以致富發家。一個看來讓人信服的論證,是這麼說的:白種人到澳洲殖民,只花了100年就建立了一個民主國家--使用金屬工具、有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文字、工業、農業等一應俱全,而澳洲土著在澳洲至少住了4萬年,一直在部落中過著狩獵-採集的生活,連金屬工具都沒有發展出來。這是人類史上的兩個實驗,一前一後。實驗在同一環境中進行,唯一的變項是居住在這環境中的人種。就澳洲土著和歐洲白人的業績而言,他們的差距若不是由他們本身的差異造成的,是什麼?
我們反對此一種族主義的解釋,不僅因為這種解釋令人作嘔,更重要的是,這麼說根本大錯特錯。各族群間是有技術發展程度的差異,但是並沒有可靠的證據可以證明各族群間有智力的差異。其實,那些仍在「石器時代」生活的族群,智力非但不比工業社會裡的人遜色,或許反倒更勝一籌。這聽來有點弔詭,我們會在第15章討論,澳洲今日的文明工業社會,以及前面談過的各種現代特色,實在不是白人殖民者的功勞。此外,澳洲土著和新幾內亞土著的技術,雖然在接觸白人之前仍非常原始,但若給他們機會,駕馭工業科技並非難事。
有些國家,人口包括不同地理族群的後裔。認知心理學家花費了極大的力氣,想找出族群間在智商方面的差異。特別是,美國白人心理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想證明:非洲裔美國人天賦智力比不上歐洲裔白人。然而大家都知道,這兩個族群的社會環境和教育機會差別很大。這個事實使驗證「技術水準反映智力高下」這個假設,遭遇雙重困難。首先,認知能力的發展,受社會環境的強烈影響。因此成人認知能力的差異,難以分辨先天遺傳因素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再者,認知能力的測驗(如智力測驗),測量的是文化學習,而不是先天智力(暫時不談所謂「先天智力」究竟是什麼玩意)。成長環境和學得的知識,勢必影響智力測驗的結果,因此心理學家至今還未能提出強有力的證據,證明非白人族群有先天的智力缺陷。
對於這個引起爭議的課題,我的觀點源自與新幾內亞人工作了33年的經驗。他們的社會還維持著傳統的形態。打從一開始,我就發現,這些新幾內亞人比起歐洲人或美國人,一般而言更聰明、機警,更有表達能力,對周遭的人事物也更感興趣。有些任務他們執行起來,比西方人俐落多了。例如在陌生環境中,掌握四周動靜、判斷進退趨避的本領。那種能力應能反映出大腦功能的許多面向。當然,有些任務西方人從小就受過訓練,新幾內亞人根本沒有學習的機會,表現得很差。所以,沒上過學的新幾內亞人從偏遠的村落進得城來,西方人會覺得他們看來蠢得很。反之,換了我跟著新幾內亞人到叢林中蹓躂的話,在他們眼中我是多麼的蠢,我心知肚明。像是在森林中找出路、搭建蓬屋,我一點也幫不上忙,因為我從來沒有學過。那些可是新幾內亞人從小練就的本事。我對新幾內亞人的印象是:他們比西方人聰明。我有兩個理由支持這個印象,一說你就明白。第一,幾千年來,歐洲人生活在人口稠密的社會中,中央政府、警察系統和司法制度一應俱全。在這種社會中,傳染病(例如天花)長久以來一直是主要的死因,謀殺反倒比較不尋常,而戰亂是變態而非常態。大多數歐洲人,只要熬過傳染病的侵襲,就不再受死神的威脅。他們就可以把基因傳給下一代。今天,西方人嬰兒,不管他們智力或基因的品質,大都不受致命傳染病侵襲,順利傳宗接代。相形之下,新幾內亞人的社會,人口稀疏,只能在稠密的人口中演化的傳染病,根本無從生根。新幾內亞人的死亡原因,向來以謀殺、部落間的長期戰爭、意外、食物不足為大宗。
在傳統新幾內亞社會中,聰明的人比較有機會逃出鬼門關,傳遞基因。然而,在傳統歐洲社會中,傳染病篩檢出的不是智力,而是與基因有關的身體化學。例如,血型為B或O者,對於天花的抵抗力就比A型的人來得強。也就是說,針對智力的天擇壓力,或許在新幾內亞社會中表現得更為赤裸裸。相較之下,人口稠密、政治組織複雜的社會,天擇鑑別的是身體化學。
新幾內亞人也許比較聰明,除了前面談的遺傳因素,還有一個原因。現代歐洲和美國的兒童,花了太多時間在不必動用大腦的娛樂上,如電視、收音機和電影。一般美國家庭,每天電視開機的時間長達七小時。相對的,新幾內亞的孩子在傳統社會中,根本沒有機會接觸那種「被動娛樂」。他們只要不睡覺,就會主動的做一些事,像是與人說話或玩耍。
幾乎所有的兒童發展研究都強調:童年的刺激和活動有助於心智發展;不可逆的心智障礙,與童年的刺激不足有關。新幾內亞人比較聰明,這個非遺傳因素當然扮演了一個角色。也就是說,就智力而言,新幾內亞人先天上或許要比西方人強;可是就後天條件而言,新幾內亞人不受文明之害,不像工業社會大多數的孩子,都在不利於心智發展的環境中成長。因此,亞力的問題,答案不在新幾內亞人的智力不如人。先天的遺傳與後天的兒童心智發展,這兩個因素也許不只區別了新幾內亞人與西方人,也區別了技術原始的狩獵-採集社會和技術先進的社會。
因此,種族主義者的一貫論調應該顛倒過來。換言之,我們應該問:為什麼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歐洲人能生產出那麼多的貨物?儘管我認為新幾內亞人比較聰明,他們沒搞出什麼名堂是事實,為什麼?
回答亞力的問題,不依賴遺傳因素,也可以有幾個不同的方案。有一種解釋,是北歐人的最愛,他們相信北歐的寒冷氣候有激發創意、精力的效果,而炎熱、潮溼的熱帶氣候使人遲鈍。也許高緯度地區四季分明的氣候,提供了複雜多樣的挑戰。終年溼熱、四季長青的熱帶氣候是單調了些。也許寒冷的氣候讓人不得不絞盡腦汁、發明創造,建溫暖的房舍、縫暖和的衣物,不然就活不下去。在熱帶只需要簡單的房舍,衣服不穿也成。不過氣候的故事可以顛倒過來說,仍然得到同樣的結論:高緯度地區由於冬季長,大家閒居家中百無聊賴,以發明消磨時間。
雖然這種解釋以前很流行,後來證明不堪一擊。因為直到1000年前,北歐人對歐亞文明的發展,可說毫無貢獻。他們只是運氣好,住在一個方便輸入先進發明的地點。農業、車輪、文字、冶金術,都是歐亞大陸比較暖和地區的產品。
在新大陸,高緯的嚴寒地帶更是落後。美洲土著社會唯一的書寫系統,是在北回歸線之南的墨西哥發展出來的;新世界最古老的陶器,是在南美熱帶靠近赤道之處發現的;新世界在藝術、天文學和其他方面最為先進的,是古典馬雅社會,位於熱帶的尤卡坦(Yucatan)、瓜地馬拉(Guatemala),則在公元第一個千年內興起。
解答亞力的問題,第三種答案和氣候乾燥的河谷低地有關。那兒高產量的農業仰賴大規模的灌溉系統,得有中央集權的政府才能興修水利。
這種解釋源自一個確定的事實:人類最早的帝國和文字,興起於肥沃月彎的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發拉底河(Euphrates)河谷、埃及的尼羅河河谷。在世界其他地區,控制灌溉系統也和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有關,如印度次大陸上的印度河河谷、中國的黃河與長江河谷、中美洲的馬雅低地還有秘魯的海岸沙漠。
然而,詳細的考古研究發現,複雜的灌溉系統並不是隨著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出現的,而是隔了一段時間之後才出現。換言之,國家機器是為了別的原因打造的,有了國家機器,才有可能興修大規模的水利事業。在那些文明的搖籃中,國家機器興起之前的歷史發展關鍵,和河谷或灌溉系統毫無關係。例如肥沃月彎的糧食生產和農村,發源於丘陵、山區,而非低地河谷;此後三千年,尼羅河河谷仍是一片文化邊鄙。美國西南部的河谷,最後出現了灌溉農業、複雜社會,但是灌溉農業和複雜社會的要素,都是在墨西哥發展出來,再輸入這裡的。澳洲東南部的河谷,一直由沒有農業的部落佔居。
針對亞力的問題,另一種解釋路數,是研究近代歐洲的殖民歷史,列舉那些有助於歐洲人征服、殺戮其他族群的因素。其中犖犖大者,有槍炮、傳染病、鋼鐵工具和工藝產品。
這個路數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史料俱在、鐵案如山,那些因素的確直接協助歐洲人完成征服大業。然而,這個假設並不完整,因為直接因素,最多不過是解釋歷史事件的「近因」。找出近因後,自然引出「遠因」(終極因)的問題:為什麼槍炮、病菌、鋼鐵站在歐洲人這一邊,為什麼不是非洲土著或美洲土著?
歐洲人征服新世界的終極因,目前已有眉目。至於歐洲人征服非洲,仍是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謎。非洲大陸是猿人的演化搖籃,現代人可能也是在這裡演化出來的。這裡的風土病像是瘧疾、黃熱病,當年不知奪去了多少歐洲探險者的性命。要是先發制人、先馳得點這類成語符合世情,非洲為何不能「制人」反而「受制於人」呢?為什麼槍炮、鋼鐵不是在非洲最先發展出來的?有了槍炮、鋼鐵,再加上這兒的病菌,非洲人應能征服歐洲。澳洲也是塊「萬古如長夜」的大陸,土著始終過者狩獵-採集生活,為什麼?
放眼世界,作人類社會的比較研究,過去吸引過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最有名的現代例子,是湯恩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的12卷《歷史研究》。湯恩比特別感興趣的,是23個先進文明的內在發展動力--其中22個有文字,19個都在歐亞大陸。他對史前史和簡單的、沒有文字的社會,較不感興趣。然而現代世界的不平等,根源可以追溯到史前史。因此湯恩比並沒有提出亞力的問題,也沒有認真討論我所謂的大歷史模式。其他世界史的著作也一樣,重點都在近五千年歐亞大陸上的先進文明,對哥倫布之前的美洲文明,只有簡短的介紹。至於其他地方的文明,就別提了,只約略討論了它們近代和歐亞文明的互動。湯恩比之後,「世界大歷史」被當成無法處理的問題,不再受歷史學者的青睞。
幾個不同學科的專家在他們的專長領域中,將全球各地的資料綜合分析過,產生了許多對我們特別有用的見解。尤其是生態地理學家、文化人類學家、研究馴化植物與動物的生物學家、研究傳染病的歷史衝擊的學者,他們的研究讓我們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線索。但是他們的研究成果不能解釋「世界大歷史」模式。必須綜覈百家,才能提綱挈領。
因此,如何解答亞力的問題,目前尚無共識。我們對近因已有腹案:有些族群著了先鞭,發展出槍炮、病菌、鋼鐵,以及其他增進政治、經濟力量的條件;有些族群什麼名堂都沒搞出來。仍不明確的是遠因。例如青銅器很早就在歐亞大陸上的某些地區出現;新世界青銅工藝發展得很晚,只局限於某些地區,從未流行;澳洲土著從未發展出金屬器具,為什麼?
我們對遠因無法掌握,這是個知識上的挑戰:世界大歷史模式是怎麼形成的?總該有個道理吧!更嚴重的是,這還影響到道德層次的考量。大家都很清楚,不同族群在歷史上遭到不同的命運,這是個教人無可推諉的事實,管你是不是種族主義者。今天的美國,社會是以歐洲為模型打造出來的;土地是從美洲土著掠奪過來的;人口中又有從非洲亞撒哈拉劫持來的黑奴的後裔--當年輸入的黑奴共有數百萬。要是現代歐洲是個非洲亞撒哈拉黑人的殖民地,社會是非洲式的,人口中還有黑人從美洲劫持來的印地安人,你會怎麼想?
我們觀察到的結果,是一面倒的-歐亞大陸上的族群征服了美洲、澳洲、非洲。現代世界是這種一面倒現象的結果。這裡必然有個「非戰之罪」的解釋。也就是說,幾千年前某人贏得一場戰役,或某人發明了某樣東西之類的細節,不是我們所要找尋的歷史遠因。
我們可能會認為,只要假定族群間有天賦差異,就足以解釋我們正在討論的歷史模式。當然,我們的教養不容許我們公開這麼主張,那太不禮貌了。許多專家發表研究報告,宣佈他們證實了人種的先天差異。然後有另一批專家出面反駁,指出那些研究的技術瑕疵。科技發展的研究宣稱可以表示這種差異,但這些研究卻有其技術上的缺失。我們親眼目睹某些給征服了的族群成員,今天仍居於弱勢階層,距離他們的祖先遭到征服或奴役的命運已經好幾個世紀了!這個事實有人主張是社會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先天稟賦,例如弱勢族群能享受到的社會資源不足,他們上進的機會有限。
然而,我們不禁疑惑起來。族群之間地位並不平等,顯而易見,難以推諉。公元1500年的世界已表現出今天的不平等,以生物稟賦來解釋,肯定那是錯的。然而正確的解釋是什麼?我們必須提出一個可信、詳盡的解釋作為共識的基礎,不然大多數人還是會繼續疑惑:說不定種族主義者的主張是正確的!所以我才起意寫作本書。
媒體記者最喜歡請作者用一句話來交代一本厚書。本書可以這麼交代:「各族群的歷史,循著不同的軌跡開展。那是環境差異造成的,而非生物差異。」
環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響社會的發展,這當然不是新觀念。然而今天的歷史學家卻嗤之以鼻:它不是錯了,就是簡化了實況;或是給嘲笑為「環境決定論」,不予採信;或者乾脆把「解釋全球族群差異」當成無解的難題,束之高閣。但是,地理的確會影響歷史,問題是:影響的程度?地理是否可以解釋大歷史模式?
以新的觀點解答這些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因為好幾門科學生產了新的資料,可供我們利用。那幾門科學與人類歷史似乎不怎麼有關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農作物的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生物地理學,以及它們的野生祖先;人類病菌和相關動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學;人類疾病的流行病學;人類遺傳學;語言學;各大洲及主要島嶼上的考古研究;技術、文字、政治組織的歷史研究。
任何人寫一本書回答亞力的問題,都得研究、評估許多不同學科的論證與證據。他必須學識淵博,前面談到的各個學科都能悠游自得、取精用宏,這才能自出機杼、成一家言。地球各大洲的史前史與歷史也得納入。那本書的主題是個歷史問題,但是解答的門路是科學,特別是演化生物學、地質學等歷史科學。從狩獵-採集社會,到邁入太空時代的文明社會,他對各種類型的人類社會,都必須親身體驗過。
從以上條件看來,這本書似乎該由幾個人合作才應付得了。這種規劃註定失敗,因為解答亞力的問題,講究匠心獨運、脈絡貫通;幾個學究各說各話、莫衷一是,反倒治絲益紊、徒亂人意。因此這書非得找個自拉自唱、自作自受的作者不可,他的功力也許達不到學究天人的境界,但是自助人助,不必妄自菲薄。作者得上窮碧落下黃泉,出入百家、探賾索引。這麼浩大的知識工程,當然少不了同事的指引。
湊巧得很,在遇見亞力之前(1972),我的家庭背景已經引導我涉足過那些學科。我母親當老師,她也是個語言學家;我父親是兒童遺傳疾病專科醫師。因為父親的緣故,我小學起就立志當醫生。還不到17歲,我又瘋狂愛上了賞鳥。所以大四那年我放棄醫學,改念生物,跨出這一步我並不感到困難。不過,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我的訓練主要是語言、歷史與寫作。甚至決心攻讀生理學博士之後,也就是進研究所的第一年,我還差點放棄科學去唸語言學。
1961年我拿到博士學位後,我的研究在兩個領域中進行:分子生理學,以及演化生物學和生物地理學。演化生物學是歷史科學,不能使用實驗科學的方法。因此我涉足演化生物學的經驗,對我研究亞力的問題,幫助很大,那是當初沒料到的。利用科學研究人類歷史,必然會遭遇的困難,我早已熟悉。1958年到1962年,我住在歐洲,看到朋友的生活讓 20 世紀的歐洲史重創了,我開始對歷史作嚴肅的反思,想解開歷史中的因果鎖鏈。
過去33年中,我到各地作演化生物學田野研究,和許多類型的人類社會有過親近的接觸。我的專長是鳥類演化,停駐之地包括南美、南非、印尼、澳洲,特別是新幾內亞。在各地我與土著一起生活,逐漸對許多工技原始的社會有親切的知識,例如直到近代之前仍生活在石器時代的社群--狩獵-採集社會、農民部落、漁獵社群。因此,遙遠的史前時代的生活方式,文明人覺得怪異,卻是我生命中最鮮活的成份。新幾內亞面積在地球上算不了什麼,卻表現出高度的人類歧異--現在世界上的語言約六千種,其中一千種在新幾內亞。我在新幾內亞研究鳥類時,對語言的興趣死灰復燃了,因為我必須搞清楚各種鳥在一百種當地語言中的俗名。
最近,我從前面談到的各種研究興趣理出了頭緒,寫成了《人類:第三種黑猩猩》(The Third Chimpanzee, 1992),是一部通俗的人類演化史。書中第14章〈意外的征服者〉,討論的是歐洲人和美洲土著接觸的後果。那本書出版了之後,我才恍然大悟:無論史前時代或現代,族群接觸引發的是同樣的問題。我發現:我在那一章全力周旋的問題,根本就是1972年亞力提出的問題,只不過換了場景罷了。現在的這本書就是答案--我終於回答了亞力的問題,許多朋友都出過力。希望本書能滿足他的好奇心,也滿足我的。
本書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有3章。第一章帶領讀者回到人類自然史作一趟旋風之旅;起點是七百萬年前,那時人類與黑猩猩剛剛分化,直到冰期結束,約當1萬3000年前。人類先祖發源於非洲,擴散到全球,為了了解「文明興起」之前的世界,我們得追溯這個過程。結果發現:各大陸上的族群,「起步」的時間不同。
本書探討各大洲的自然環境對人類歷史的影響,第2章是出發前的暖身活動:把島嶼當作實驗室,看看環境在一個比較小的時空中,對歷史有什麼影響。3200年前,玻里尼西亞人的祖先開始散居大洋洲。南太平洋中的島嶼各有特色,環境迥異。短短幾千年之內,同出一源的族群,發展出形態迥異的社會,從狩獵-採集部落到頗具帝國雛形的社會,琳琅滿目。這種「趨異演化」現象,可以當作基本模型。從冰期結束至今,各大洲的人類族群發展出的社會形態,差異更巨大,無論狩獵-採集部落還是帝國,都有不同類型。南太平洋中的趨異演化,能提供睿見,協助我們探討較大尺度的洲際趨異演化。
第3章是洲際族群衝突的一個例子。地點在秘魯的卡哈馬卡城,印加帝國末代皇帝阿塔花普拉(Atahuappla 1502-1533),與從西班牙來的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 1475-1571)會面。皮薩羅只有一小撮人跟著。結果大軍簇擁著的阿塔花普拉,卻在眾目睽睽之下給皮薩羅擒住。我們將透過當時人的眼光,來看這段人類歷史上最戲劇化的一幕。皮薩羅擒住阿塔花普拉這個事件,我們可以分析出一串環環相扣的「近因」,而歐洲人征服美洲其他社會,也循著同樣的因果鎖鏈進行。那些近因包括西班牙病菌、馬匹、文字、政治組織和工藝技術(特別是船隻與武器)。分析近因是本書比較容易的部分;困難的是找出遠因(終極因)。那些遠因導致了近因?歷史是遠因的後果嗎?為什麼不是阿塔花普拉率大軍到馬德里擄獲查理一世(AD1500-1558,西班牙國王,1516-1556在位)呢?
第二部「生產食物生業的興起與傳播」,共有7章(第4章至第10章)。這裡討論的是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一組遠因。第4章討論促成皮薩羅勝利的直接原因,指出生產食物的生業(指農、牧業,相對於狩獵-採集而言)是終極因。但農牧業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發展模式。第5章討論發展食物生產業的地理差異。地球上有些地方的族群獨立發展出生產食物的生業;有些族群在史前時代已經從那些獨立發展中心,採借了生產食物的生業;更有些族群既沒有發展生產食物的生業,也沒有採借,直到現代仍維持狩獵-採集生業。第6章探討為何有只有某些地方發生了生業變遷--從狩獵-採集演進至農業?而其他地方就沒有。第7章至第九章敘述史前時代發展農牧業的過程。最初的農夫、牧民馴化野生植物、動物,其實並沒有透視歷史的眼界。適合馴化的野生動植物,有不同的地理分布。這一個事實,足以解釋何以只有幾個地方獨立發展出生產食物的生業?何以各地發展生產食物生業,有遲速之別?生產食物生業從少數幾個中心向外傳播,有些地方很快就採借了,其他地方卻很慢。影響各地採借速率的主因,和大陸的軸線有關:歐亞大陸的主要軸線是東西向,而美洲、非洲則是南北向(第10章)。
本書第3章勾勒了歐洲人征服美洲土著的直接原因,第4章追溯遠因,那就是生產食物生業。在第三部分「從糧食到槍炮、病菌與鋼鐵」(11至14章),詳細討論了遠因與近因之間的因果關連,從病菌談起。主要的人類病菌是在稠密的人口中演化出來的。歐亞的病菌,殺死了更多美洲土著和其他有色人種;歐亞的槍炮或鋼鐵武器瞠乎其後。反過來說,歐洲人到了新世界幾乎沒遇上過什麼致命病菌。為什麼病菌的交流這麼不對等?最近分子生物學研究的結果,讓我們看清了病菌與農牧業的關連,而且與病菌的演化、傳播大有關連的,是歐亞的農牧業,而不是美洲的。
另外一條因果鎖鏈是從農業到文字;文字可說是最近幾千年中最重要的發明。人類歷史上,文字獨立發明過幾次而已,而且是在最早發展出農牧業的地區。其他的社會,或者從那幾個中心直接採借,或受到那些書寫系統的啟發,發展出自己的文字。因此對研究世界史的學者來說,書寫系統的分布資料特別有用,可以用來探討另一組因果關係:在思想與發明的傳播方面,地理有何影響?
工藝技術的發展、流傳,受到的限制和文字一樣(見第13章)。關鍵的問題在:工藝技術的發明、改進,依賴的是少數的天才以及許多獨特的文化因素呢?還是怎地?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們就不可能了解世界技術史了。說來,弔詭的是,數不清的文化因素使得技術發展的世界模式,更容易理解,而不是更難理解。農業讓農民生產更多的糧食盈餘,因此農業社會可以供養全職的技術專家,他們不親自耕作,專注於發展技術。
農業除了支持書寫系統、技術專才,還供養了政治人。狩獵-採集游動群的成員相當平等,他們的政治領域限於游群的領地,以及與鄰近游群合縱連橫的關係。而人口稠密、定居的農牧社會中,出現了首領、國王和官僚。這種層級體制不但治理廣土眾民是必要的,維持常備軍隊、派遣探險艦隊和發動征服戰爭,沒有層級體制就辦不到。第四部「環遊世界」(第15章到19章),把從第二、三部歸納出的道理,應用到各大洲和幾個重要的島嶼上。第15章討論了澳洲的歷史,以及原來和澳洲相連的新幾內亞。技術最原始的人類社會就在澳洲,澳洲還是唯一沒有獨立發展出農牧業的大洲。因此澳洲可以作為本書理論的決斷試驗(critical test)。我們要討論:為什麼澳洲土著一直維持狩獵-採集生業,而新幾內亞的土著大多數都成了農人?
第16、17章把澳洲、新幾內亞和東亞大陸與大洋洲聯繫起來,擴張我們的視野。農業在中國興起後,促成了好幾次史前人口或文化特質的大遷徙,也許兩者皆有。其中的一次發生在中國本土上,創造了今日我們所知的中國。另一次在熱帶東南亞,源自華南的農民顛覆了東南亞狩獵-採集土著。再來就是南島民族的擴張,他們顛覆了菲律賓、印尼群島的土著,深入南太平洋,散布到玻里尼西亞各島嶼,但是沒能在澳洲與新幾內亞殖民。對世界史的學者而言,東亞族群與太平洋族群的鬥爭,重要性有兩重:一,因為他們的國家總人口佔世界的三分之一,經濟力量更有日益集中的傾向。二、他們提供了非常清楚的模型,讓我們了解世界其他地區的族群歷史。
第18章則回到第3章的問題,就是歐洲人和美洲土著的衝突。回顧過去1萬3000年這兩大洲的歷史,可以幫助我們看清楚:歐洲人征服美洲,不過是兩條漫長的歷史軌跡,毫無交集的發展結果。這兩條軌跡的差異,反映在這兩大洲各方面的比較上:馴化動植物、病菌、定居的年代、軸線的走向和生態障礙等。
最後,亞撒哈拉非洲的歷史(第19章),和新世界的既神似、又相異。歐洲人與非洲土著的接觸,可說是歐洲人與美洲土著接觸的翻版。但是即使同樣的近因,非洲和美洲的情況也有差異。結果是,歐洲人沒有在非洲亞撒哈拉建立大片的或長久的殖民地,只有南非是例外。比較有長遠影響的,是非洲境內大規模的族群代換--班圖族擴張(Bantu expansion)。其實,這個戲碼一再在各地上演,卡哈馬卡、東亞、太平洋諸島嶼、澳洲和新幾內亞。班圖族擴張也是同樣的因素促成的。本書成功的解釋了過去1萬3000年來的世界史嗎?我並沒有幻想。即使我們真的了解所有的答案,也不可能只用一本書完整的鋪陳出來。何況我們還不了解。本書鋪陳了幾組環境因素,為亞力的問題提供了大部分答案。然而,找出那些因素,是為了彰顯我們沒有把握的部分,若要釐清,還有待未來的努力。
結語「未來的人類史是一門科學」,從那些尚無解答的部分,舉出幾點提醒讀者。例如歐亞大陸的內部差異、與環境無關的文化因素,以及個人的角色。或許尚未解決的問題中最困難的,是把人類史建構成一門歷史科學,和其他的歷史科學比肩,如演化生物學、地質學和氣候學。研究人類歷史的確會遭遇困難,但是已經成立的歷史科學也會遭逢同樣的挑戰。因此,那些領域發展出來的方法,或許在人類史研究裡可以派上用場。
無論如何,我希望能說服讀者:歷史絕對不只是一個又一個的事實。人類歷史的確有普遍的模式,解釋那些模式的努力,不僅能生產慧見,也是個令人著迷的事業。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的圖書 |
 |
$ 139 ~ 343 | 槍炮.病菌與鋼鐵-next 49
作者: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 / 譯者:王道還,廖月娟編者:柯淑芬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1998-10-2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80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 1998年美國普立茲獎、英國科普書獎。
為什麼現代社會中的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是以今天這種面貌呈現,而非其他形式?為何越過大洋進行殺戮、征服和滅絕的,不是美洲、非洲的土著,而是歐洲人和亞洲人?各族群間的生活差異為何如此之大?對於現代人類、國家間的種種不平等現象,連史學家都存而不論。許多大家熟悉以及想當然耳的答案,在作者的論述中都產生截然不同的意義。本書提出的結論必然會引起爭議,但這只是個開端,引領我們用全新的角度來看世界。
作者抽絲剝繭,解開種種歷史發展之謎,其巧心慧思與博學多聞,使本書讀來生動有趣,逐步帶領我們深思人類社會未來的命運。
這是一本極其重要的著作,書中主旨是現代人不可忽略並應從小開始教育給下一代。
作者簡介:
戴蒙(Jared Diamond)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醫學院生理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他不只是個實驗室的科學家,還是田野生物學家(鳥類演化)、人類學家。
本書源自生物學田野調查中觸及的人類學問題。
作者前一本書《人類:第三種猩猩》(洛杉磯時報書獎),是一部人類的「自然史」;本書則是人類的「文明史」,以生物地理的人文後果,重新回答盧梭的問題:《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作者展望全球、獨具隻眼,居然視野壯闊、引人入勝。
譯者簡介:
王道還
台北市出生,台大人類學碩士。曾赴哈佛大學受生物人類學訓練,目前任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生物人類學實驗室。
廖月娟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譯作有《旁觀者:管理大師杜拉克回憶錄》等多部作品。現專事翻譯研究。
章節試閱
前言:亞力的問題
地球上各大洲的族群,有不同的歷史發展軌跡。自從冰期(Ice Age)結束以來,在這1萬3000年間,世界上有些地區發展出有文字的工業社會,發明了各種金屬工具,有些區域仍舊是沒有文字的農業社會,還有一些則停滯於使用石器的狩獵-採集社會。那些歷史的不平等,在現代世界史的面貌上留下了深刻的陰影,因為使用金屬工具的文明社會,征服了或滅絕了其他類型的社會。雖然這些歷史與社會類型的差異是世界史中最基本的事實,原因卻不明,且有爭議。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困惑人的問題,是在25年前。那時這個問題是以比較簡單的形...
地球上各大洲的族群,有不同的歷史發展軌跡。自從冰期(Ice Age)結束以來,在這1萬3000年間,世界上有些地區發展出有文字的工業社會,發明了各種金屬工具,有些區域仍舊是沒有文字的農業社會,還有一些則停滯於使用石器的狩獵-採集社會。那些歷史的不平等,在現代世界史的面貌上留下了深刻的陰影,因為使用金屬工具的文明社會,征服了或滅絕了其他類型的社會。雖然這些歷史與社會類型的差異是世界史中最基本的事實,原因卻不明,且有爭議。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困惑人的問題,是在25年前。那時這個問題是以比較簡單的形...
»看全部
推薦序
導讀: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沈?
文/ 王道還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討論的人類社會,遍佈於三大洋、五大洲。不平等則是常識,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的議題,媒體上三不五時冒出「南北對抗」、「南北會談」的名目,實質的內容,就是「人類社會不平等」的現實。本書應該會讓那些「南方國家」(貧國、弱國、以及受過富國剝削壓迫的國家),稍稍釋懷,甚至在談判桌上更為振振有辭。因為作者強調:今天的世界現況,早在一萬三千年前就決定了,各大洲上的祖先族群披荊斬棘,歷盡滄桑,誰也沒閒著,他們的子孫今天或貧或富,莫非天定。...
文/ 王道還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討論的人類社會,遍佈於三大洋、五大洲。不平等則是常識,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的議題,媒體上三不五時冒出「南北對抗」、「南北會談」的名目,實質的內容,就是「人類社會不平等」的現實。本書應該會讓那些「南方國家」(貧國、弱國、以及受過富國剝削壓迫的國家),稍稍釋懷,甚至在談判桌上更為振振有辭。因為作者強調:今天的世界現況,早在一萬三千年前就決定了,各大洲上的祖先族群披荊斬棘,歷盡滄桑,誰也沒閒著,他們的子孫今天或貧或富,莫非天定。...
»看全部
目錄
導讀: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沈?
前言:亞力的問題
各大洲族群不同的歷史發展軌跡
第一部 從伊甸園到印加帝國
第1章:人類社會的起跑線
公元前1萬1000年各大洲到底發生了哪些事?
第2章 歷史的自然實驗
地理因素對玻里尼西亞社群的影響
第3章 卡哈馬卡的衝突
為什麼不是印加帝國滅了西班牙?
第二部 農業的起源與傳播
第4章 農業與征服
槍炮、病菌與鋼鐵的根源
第5章 如何在歷史上領先群倫
農業發展的地理因素
第6章 下田好,還是打獵好?
農業起源之謎
第7章 杏仁的前世今生
原始作物的發展...
前言:亞力的問題
各大洲族群不同的歷史發展軌跡
第一部 從伊甸園到印加帝國
第1章:人類社會的起跑線
公元前1萬1000年各大洲到底發生了哪些事?
第2章 歷史的自然實驗
地理因素對玻里尼西亞社群的影響
第3章 卡哈馬卡的衝突
為什麼不是印加帝國滅了西班牙?
第二部 農業的起源與傳播
第4章 農業與征服
槍炮、病菌與鋼鐵的根源
第5章 如何在歷史上領先群倫
農業發展的地理因素
第6章 下田好,還是打獵好?
農業起源之謎
第7章 杏仁的前世今生
原始作物的發展...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賈德.戴蒙 譯者: 王道還、廖月娟
-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8-10-20 ISBN/ISSN:957132730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西方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