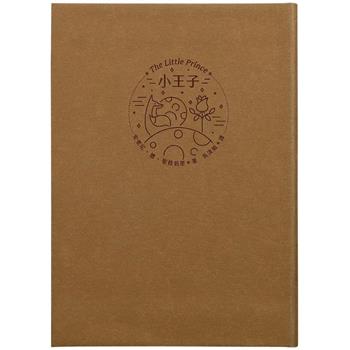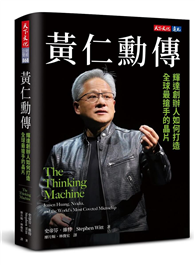序
民主教育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奮鬥
Carlos Alberto Torres
民主、教育、公民職權與全球化的概念,對不同的人而言具有不同的意義。這些概念早已成為一種「滑動的」指涉符徵(signifier)。因此,在多重全球化過程的脈絡裡,什麼形成了民主教育這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儘管這是被由上而下的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所宰制 。
儘管在這本書,我並未特別關注於民主在教育裡的正式過程,但是,我的目的,尤其在本書的結論裡,是想要尋求某些公民的美德,這些美德正是我們必須在教育的世界裡加以注入跟呈現的。我要談論諸如希望、誠實、高尚、勇氣、友誼、信任、自尊、自重等關鍵的美德,這些美德是身處在民主興盛下的個別公民如我們所需要的,以便促進在和平的環境裡(包括區域與全球的層級)的繁榮。
追隨著巴西教育家與政治哲學家Paulo Freire的啟發 ,我引用了古典的與當代的哲學作品,探究這些公民的美德如何在多元文化、多元語言以及衝突傾向的社會裡,貢獻於公民職權的社會化。
正如傑出的美國學者James Bank所主張的,有效的公民教育可能有助於學生習得在他們的文化社群、國家、區域與全球社群裡有效運作所需的知識、技能與價值。它同時也可能有助於學生習得,那些維持全世界人們的公平與社會正義所需的世界主義的觀點與價值。
社會正義的教育 是一種社會的建構,這種社會建構指的是那些批判的與激進的教育人員中大規模的中堅幹部,他們對資本主義國家對教育與學校教育所採用的方式,亦即把教育與學校教育作為一種社會控制的形式,而非一種在政治、社會與認知上增權賦能的模式,提出質疑。更有甚者,我們正在使用這種社會建構於UCLA師資訓練的方案裡,並且它也開始強烈的影響我們在洛杉磯與其他各地所提出的關於認知與道德教育的方式。
我也應該表達我自己對於翻譯重要性的看法。我們透過語言溝通,也就是,我們透過不同的認同進行溝通,因為語言組成了認同。把任何智性的作品翻譯成另一種語言例如中文的可能性,讓我感到十分高興。本書的情形是,把用英文寫成的作品翻譯成中文,而英文甚至也不是我的母語。這本書能在臺灣被翻譯甚至出版,讓我感到格外的榮幸。
我跟臺灣學術界的接觸已經超過十年,諸如課堂上的講演以及臺灣研討會的參與。此外,我特別高興這些年來,能接待到訪UCLA的臺灣學生與學者。並且我也跟一些來自臺灣的學生一起工作,我學會欣賞他們的思考品質、他們工作的強度、他們無可匹敵的勤奮、他們絕佳的責任感以及他們對社會改變的允諾。我真的覺得很幸運能夠擁有幾位真摯的臺灣友人與同事以及我的臺灣學生的友誼。並且,我把那些將我的作品翻成中文所付出的努力,當作是一種真正的榮耀與友情的象徵。
學識上的智性合作不是也不應該被簡單地縮減成只是一種觀點、立場、意見、理論、方法或資料的交換,而是上述的全部甚至更多。透過同僚的力量(colleageability)來連結人們也是一種很重要的方式,它創造出一種友誼的情感連結,而這種友誼是長存的。正是這些友誼與連結,使得我每次到訪臺灣都是一種學習的經驗,同時也是一種真正的學院式同僚合作的(collegial)喜悅。
一想到這本書將會在說中文的學生、學者或一般大眾的手上,讓我感到更加的欣喜。臺灣社會、中國大陸以及散佈在世界各地的中國人,一直非常關心地想要發展一種跟經濟成長相連結的新的民主意義。儘管臺灣、中國大陸、澳門與香港易於被西方人士視為同質性相當高的社會,但是差異與多樣性的界限也大大地跨越他們。因此,關於民主、多元文化與公民職權之間的關係、人權或是社會正義的教育困境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開始被視為是亞洲的民主的首要關心議題。
在1980年代,我是那些首先創立所謂教育政治社會學的理論架構的學者之一。1995年我跟加拿大的批判理論學者Raymond Morrow所寫的書《社會理論與教育:社會與文化再製理論的批判》(Social Theory and Education: A Critique of Theorie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對教育社會學的貢獻而言,被認為是最具廣泛分析與標準批判的書籍之一。這本書已經有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加泰倫語(Catalan )、英文的版本,而中文版也即將問世。然而,《民主、教育與多元文化主義:全球社會公民職權的困境》(Democracy, Educ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Dilemmas of Citizenship in a Global World)這本書則是我在教育政治社會學領域最重要的書。此書自1998年英文版問世以來,已經譯成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加泰倫語、亞美尼亞語(Armenian),以及現在的中譯本。亞美尼亞語的譯版一直免費分派給亞美尼亞境內所有的社會運動與社區組織,以便作為在前蘇維埃共和國建立民主架構的一種努力。韓文與義大利文的翻譯也刻正進行中。
歷經三十多年在此一領域的智性工作之後,我覺得必須清查(take stock)我對教育社會學、拉丁美洲研究,以及比較與國際教育等這些領域的貢獻。
我覺得我應該以適合我的方式(at my fit)握住球,然後看著它環繞著我轉。這樣的思考是很合適的,因為觀看與踢足球是我最大的興趣熱情之一。在我成人生命的好一大部分,我曾經踢過非常競爭的足球,並且當我還是青少年時,我曾試著想要在阿根廷踢職業足球,但是我停掉了沒有繼續,而去念大學。一直到現在,我仍然不斷地在思考我的選擇是否正確。
每一個了解足球邏輯的人都知道,在比賽中場時,有那麼一刻,主控球員(playmaker)應該放慢球速,握著它久一點,看看同隊的其他球員在哪裡,並且準備移轉球賽的節奏、強度以及韻律,在得分與贏球的目標下,那一刻不僅在策略上是困難的,同時在運動競賽上也是複雜的。
儘管這個隱喻用來描述在學術界裡的教授,可能有點超過,並且也許用來了解在我們生命裡的某一特殊時刻關於我們是誰,以及我們準備做什麼以便達成我們的夢想,可能更為合適。但是,我相信這個隱喻用來審視我們的學術軌道(academic trajectory),依然具有某些價值。
2003年是我大學教授生涯的第25週年,我的一些作品,以巴西式的葡萄牙文在巴西出版選集《批判理論與教育政治社會學》(Teoria Critica e Sociologia Polotica da Educanco)。一位卓越的巴西教育社會學教授──Pedro Demo博士,是Brasilia大學的榮譽退休教授,他在該書中寫了一篇很長的導論,以下是他撰文的一部分:
Carlos Alberto Torres的批判視野,不僅受到公共的政治約定(engagement)的滋養,同時也同等份量地受到他學術創造力的滋養,而這總是受到批判理論的影響。類似於法蘭克福學派,他基於批判的論證,助長了一種知識論的態勢,因為他知道思考就是質問。這就是為什麼他的批判視野並不虧欠忠誠給任何作者,因為他知道自主同時是批判能力的產物與重要過程。有趣的是,在實用(pragmatic)如北美以及跟實證傾向(positivist tendencies)連結的園地裡,這位教授為他自己掙得了一個位置,他不虧欠任何人任何事物,甚至也不虧欠批判理論,因為他以合宜的投球方式練習它,而那就是批判性的方式。同樣地,他也不受惠於美國的學術界,他知道如何正確地運用方法,他並不把政治的涉入跟行動主義(activisim)、軟弱無力的理論,或一知半解的論辯相混淆。相反地,他製造出具有最好品質的科學,所以他的批判主義才得以享有聲譽。
一直以來,我總是想要榮耀Demo教授對我作品的善意分析,我希望這些現今已翻譯成中文的書頁,將助益於有關教育社會正義的對話,並且在面臨著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危機之下,也能助益於對民主、公民職權、多元文化主義與教育之間的連結,獲得一種較佳的瞭解。
黃純敏 譯
中文版導論
變動世界中的教育、民主與公民職權
Carlos Alberto Torres
本書中文版得以問世,非常感謝張建成教授的協助。本書是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可以去問:自從六年前本書英文版付梓至今,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變化。全球經濟發生什麼變化?全球文化發生什麼變化?全球政治體系發生什麼變化?這些變化如何影響教育?以下是關於英文第一版出版之後,一些最重要變化的敘述。
最明顯的變化,是2001年911的恐怖攻擊以及它對全球經濟、政治、文化與教育的意義,它削弱了美國的無敵,在此之前,美國本土從未被攻擊過。在這些轉變之中,最顯著的是全世界對於自由的定義、享受與實施產生變化,自由主義對自由的看法受到挑戰。在前蘇聯解體之後,新聞報導那些未被承認的鈾彈,甚至核彈,我們似乎越來越受到具大規模毀滅性的生物、化學武器的威脅。
人們持續爭辯恐怖攻擊如何正中美國共和黨政府下懷,使其遂行狹隘的國際政治觀,完全的政治不讓步,對人權不尊重,決然地把狹隘的美國利益強加在全球範疇,包括忽視墨西哥對移民協定的要求。許多觀察家,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Jimmy Carter警告美國在國際事務的一意孤行的潛在危險。美國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就是政策愈受能源安全影響的表現。布希政府與美國能源公司關係密切,譬如安隆,能源政策被視為布希政府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最主要理由,伊拉克是全世界第四大產油國,擁有第二大原油儲藏量。
然而,我們尚未看到這些改變在美國或其他地方引來對學校愛國主義新的理解。就像世界上許多衝突表現出來的一樣,特別是波士尼亞內戰的悲慘例子,新的國家主義立場確實阻撓(如非徹底破壞)自由民主政府帶來的進步。唉,攻擊的遺緒,以及後續全球對恐怖主義的戰爭,對於前所未有相互關連的全球世界將有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在教育方面,這一點將在下個部分討論。
美國與聯軍對於911攻擊的立即回應,是阿富汗的戰爭,該戰顯示出對抗全球恐怖主義的困境。雖然有大規模轟炸與人員部署,並且戰前宣稱戰爭聯軍傷亡人數低、軍事效應高,但大部分的目標未能完全達成。賓拉登與塔利班領袖歐馬還沒被找到,他們大部分的副官跟數百名驍勇善戰的蓋達戰士仍然逍遙法外,阿富汗政府依然風雨飄搖,領導人物飽受政治暗殺威脅,並且遭受強大壓力:不同族群部落團體以及軍閥重複主張要從中央政府獨立,甚至主張保護前政權代表。
恐怖自有其邏輯。一般民眾只有在特別驚人的攻擊發生,或新發展促進對個人安全的注意時,才會發現這個邏輯的一些面向。在美國新政(New Deal)之後最重要的聯邦政府重組,亦即國土安全部,包含22個政府機構的建立,就是美國優先事物重新安排的指標。這些行政轉變發生在上台時財政剩餘,卻在執政不到兩年時財政赤字六兆元的政府。隨著2003年實施減稅,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繼續大幅增加。減稅與財政赤字會嚴重影響某些州的預算,這些州原本便因雷根政府將責任下放,而同時稅收減少,而接近破產。
反恐戰爭最明顯的損失之一,就是航空旅行的自由與便利。航空業的不安感漸升,包含飛機可能遭受可攜式飛彈攻擊、愈趨擔心飛機與航運安全。
從區域來看,拉丁美洲以一種三年前完全無法想像的方式改變。阿根廷是該區域落實國際貨幣組織(IMF)與世界銀行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模範國家,它嚴重的經濟失敗使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受到強烈質疑。猶有甚者,阿根廷有一個更灰暗的、人類悲慘的紀錄:它是歷史上有名的食物生產國,卻發生赤貧與孩童餓死的悲劇。諾貝爾經濟獎得主George Stiglitz曾寫下關於這些問題挑動人心的想法,開啟了相關爭辯,並對不同方面產生強有力的影響,包含對新自由主義雙邊組織及其對發展(特別是對教育)蘊含的重新、嚴厲的批判。對新自由主義的回應也到達其他方面,在這區域興起了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新關注。委內瑞拉的查維茲(Hugo Chavez)執政就是這麼一個反新自由主義的回應。在民粹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混合外衣下,查維茲總統這個前傘兵與民選總統對舊民主體系的拆解,以及他搖擺的政策與行為,引起許多不同地方的諸多抗拒,使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國之一陷入不安定。
毫無疑問,盧拉(Ignacio “Lula” da Silva,治金工會領導人與工黨【或稱PT】主席)當選巴西總統是拉丁美洲的政治奇譚。盧拉的心靈導師Frei Betto的一番話,強調了盧拉之所以成功,教育的重要性:「多虧過去四十年來串連的社會運動,盧拉才得以當選巴西總統,在這些運動中,Paulo Freire的教學論比馬克斯理論更有力量。事實是,PT因為大多數巴西人的支持,因為站在這個國家許多社會運動的政治行動主義肩膀上,贏得總統大選,特別重要的是農業改革運動,亦即無地農民運動。人道攝影師Sebastian Salgado的作品把這運動刻劃得很清楚。」
亞洲經濟體,不久前才被視為世界體系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還在日本持續的經濟不景氣中打轉與掙扎。然而,中國不斷成長的經濟與政治力量,繼續展現出令人驚嘆的經濟成長率,強化其為區域與世界主要國家的地位。中國的力量明顯展現在近來與北韓的核武計畫對峙、技術轉移,包括其核武科技或許已經與伊拉克齊步(雖然美國從未完整紀錄)。
確實,美國與伊拉克之間的戰爭是因為美國政府批評伊拉克明顯藏匿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但是,戰後證明,並沒有發現什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無論如何,布希政府的尖酸批評讓衝突變得較像是由海珊主事的伊拉克革命委員會與布希集團的世仇。
印度跟巴基斯坦這兩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之持續對立,或許是世界上最不穩定的衝突之一。與喀什米爾獨立運動有關連的回教狂熱分子對印度國會的攻擊,以及兩個政府之間升高的仇恨,導致喀什米爾地區短暫但危險的交火,促使聯合國還有一些調停的國家介入,以避免國家之間可能的全面開戰。除了回教與印度教激進分子之間的宗教仇恨,印度在喀什米爾的政權是棘手的議題,雙方邊界漸增的軍事與宗教運動導致原子彈的發展。兩個國家都擁有核武以及他們在1971年十二月已發動一場血腥戰爭的事實,使得情勢更危險。1971年,印度在戰爭中贏得勝利導致東巴基斯坦從西巴基斯坦獨立,並創造了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之一──孟加拉。不幸地是,正如某些科學家所宣稱,印度次大陸是世界上最有可能發生核子戰爭的地方。
美國與歐洲各國政府做出各種政治姿態,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仍持續向下沉淪,幾個國家(辛巴威、象牙海岸、奈及利亞,晚近則是賴比瑞亞)升高的政治不安顯現出該地區的政治不安與經濟危機繼續並行。安哥拉與獅子山之間的戰爭的可望終止開啟了希望之窗,然而,對於後種族隔離的南非所代表的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希望,卻可能被其人口的愛滋病傳染所粉碎。
反全球化運動從1999年的西雅圖開始,已成功建構了一個更有前瞻性的另類全球化議題,雖然主流的大眾媒體並未充分報導,卻影響了經濟高峰會議。甚至「揭露」了多邊與雙邊經濟組織研議如何啟動世界經濟引擎與╱或如何搶救經濟衰退的國家的過程。
過去幾年來,歐洲共同體與歐元的建立看似全球化的成功典範,新會員加入以及在2003年初歐元升值與美金等值或更高。在這過程中,歐洲高等教育的同質化將對該區域產生長遠影響,並且,在許多共同市場一直被審思著。
這些改變如何影響教育的優先順序?
在教育的領域,美國常被視為私立高等教育的典範。然而,美國學生在四年制公立大專院校的支出,在過去十年來增加了約20%左右,而加拿大與其他國家卻降低了約20%。這些支持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顧問中,有許多人受教於美國大學,而即使美國在研發上之所以有卓著成就,即是立基於公共教育系統(越來越多諾貝爾獎得主任教於美國公立大學即是明證),卻建議減少對公立大學的支持,這真是很奇怪的。
為推動高等教育全球化而對網路的擴大使用,促成了一些研究聚焦在全球化的政治經濟與語言的新角色下大學體系的轉化。這裡我所謂的「全球化」,是指在科技、勞工與資本間相互依賴且複雜的關係,使得千里之外的事件成為決定在地進程的因素,反之亦然。
美國911事件的負面影響之一,預計也會影響其他工業化國家,就是簽證條件與手續的改變,限制了外國學生接受國際教育的機會──而這些收入不是入學國家的次級收入。
如同de Souza Santos所說,這世上正在發生的是典範轉型(paradigmatic transition)。因此,探索社會變遷與理論分析之間的連結是很重要的。哪些難解的理論關係仍然未解?哪些難解的分析面向仍缺乏理解?哪些理論的連結被遺漏?當然,在我概述改變與挑戰所採用的典範視角中,有限的篇幅使我對重要爭辯的分析不得不以主觀的、選擇性的、有特定方向的方式呈現。
政治與教育之間的連結仍然是民主教育中未解的理論難題。在這個論戰中,各種體制(Establishment)(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分析的與規範的位置相近,卻與新左派有驚人的對比。
各體制的觀點是政治與教育是兩套截然劃分的實踐,不會也不該相互關連。教育維持理論上的「客觀性」(因真理可以被客觀陳述),政治上的「中立性」(因為教育人員不選邊站),最重要的是,規範上與政治選擇上的「非政治性」(政治通常體現的是抗爭意識形態位置,以維護社會的與╱或特定利益的作為,而教育是一個追求對眾人都好的公共善的崇高實踐。)。
各體制觀點認為,學者、實踐者與政策制定者應該將政治外衣留在教室外,或與他們的研究或政策陣營保持距離,不管是其所隸屬的政治團體、教義,或意識形態。否則,政治與教育合一必定導致對一些特定科目與主題的操弄與意識形態化。好的教育者在其教學、政策制定與研究中所實踐的是價值中立的教育。因此,教育是一個沒有意識形態與政治利益的實踐。雖然各體制的規範觀點肯定這世上有不公平與差異,但如何評估差異及界定受害者與評估問題的重要性,端賴分析者的意識形態。此外,各體制的觀點指出,很多的例子,即使是理性-法制的社會,都有差異歧視的歷程發生,必須經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與法律的落實才能避免。
因此,一個科學地理解與實踐,並且有嚴謹的實徵研究驗證的優質教育(透過測驗與績效的檢證),是建造一個更有效率與平等社會的社會工程最重要的資產。
對於新左派而言,故事是非常不同且更為複雜的。政治與權力關係密切,且與控制生產工具、分配、消費、再製,以及累積物質與符號資源息息相關。政治與政治性不限於政黨、政府的活動及其評論家或是投票。政治活動在私人與公共領域發生,並與人類各種與權力相關的經驗有關。從政治是一個社會中各種勢力的關係的組合來看,教育與政治的關係需要更多檢視。
Paulo Freire教導我們:宰制、侵略與暴力內在於人類與社會生活。他論到幾乎沒有人類的邂逅得以免除所有形式的壓迫,因為人們往往會成為階級、種族或性別壓迫的受害者與∕或施為者。他強調種族主義、性別主義與階級剝削是最明顯的宰制與壓迫形式,但他也指出,壓迫可能深植在宗教信仰、政治隸屬,以及對國家起源、體型、年齡與心理及肢體障礙的態度中。Freire受到心理治療家(如Freud、Jung、Adler、Fanon、Memmi與Fromm)的影響,開始鑽研壓迫心理學,並進一步發展出「受壓迫者的教育學」。他針對政治與教育之間關係的分析,以階級分析的語言指出政治、權力與教育是不可分解地結合。
雖然Freire有非常多的分析與洞見,並且用英文提出「教育的政治性」一詞並廣為推廣,政治與教育關係的本質卻還是非常不清楚。Freire所持的立場在其祖國巴西與其他地方也是重要論戰的主題。
如果我們檢視Freire的分析,許多問題仍然與政治與教育在理論層次的關係有關。除了被批評流於大型論述、壓迫觀點流於理想主義,或是關於如何具體建構壓迫指標的問題,其他急迫的議題也須被指出。如果在主體與結構的辯證脈絡中,教育與政治各有其相對自主性,那麼,兩者是只在某個時刻有交互作用?或如Freire所說的完全重疊?如Illich在「修道院式」研究氛圍中的名言:「知識生產有外於政治的自主性嗎?」
政治與教育之間是依賴還是獨立的問題,帶出另一個問題:此二人類領域真正的本質、目標與意圖,與實踐的異同。簡而言之,問題的全貌需要在Freire的深刻分析之外,有更完備、精細、整全的理論解答。
在尋求更完善的理論解答時,我們不能忘記政治與教育作為公共與私人利益衝突的場域,也受到國家行動、工具、規範、符碼、控制與資源的中介影響。
另一個尚未解決的主要理論挑戰,是對教育的後現代主義進行後現代分析。從理論來看,極端的後現代主義已失去動力、某些後現代主義者轉向革命觀點的馬克斯主義及結構主義傳統或許就是徵兆。我們應可從「後現代主義在教育研究中的實用性」角度討論這些改變。
這些理論的挑戰應該是最重要的理論議題,可以啟發實徵研究。然而,自本書第一版迄今,教育研究界的三個巨人相繼辭世(Bernstein, Bourdieu, Illich),他們值得在此提論一番。繼Freire在1997年過世,或離比較教育領域遠一些的政治哲學家John Rawls(1921-2002)的去世,我們見證了教育領域一些主要理論家的逝去。他們是難以取代的一代。站在這些巨人的肩膀上比扮演他們的角色要容易多了。
Bernard Basil Bernstein(1924-2000)在久病後棄世。自1979年至1991年退休,他是全世界教育社會學最有名望的第一把交椅,在倫敦大學教育學院擔任卡爾孟漢講座教授。
Bernstein身後留下的,是逾四十年的嚴謹研究,以及對階級、符碼與控制之間關連的新理解。他的著作,特別是《階級、符碼與控制》五冊著作,是教育領域的經典。Bernstein的理論顯示,人們在日常對話中如何使用語言,反映並型塑對某些特定社會團體的假設,因此,私人與公共的符碼很重要,在公共教育的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隨著Pierre Bourdieu(1930-2002)辭世,他在法蘭西學院擔任社會學教授,並兼任在巴黎的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多才多藝且多產,我們無疑損失了本領域有史以來最重要的社會學家之一。與Basil Bernstein同為國際教育學學會教育社會學研究委員會的創立者與前主席,Pierre Bourdieu激勵我們在教育(其「再製」是影響整個世代知識分子的重大概念)、美學、社會理論、流行文化、大眾傳播媒體、法國智識思想與文學的研究。
在Pierre Bourdieu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將自己型塑為一個對全球化最嚴厲、最不妥協的歐洲評論者之一,並且是對於全球社會美國化(Americanization)最不妥協的評論者之一。他對智識與文化領域全球化的批評,以及他對學術界的去政治化與身為知識分子角色的質疑是並行的。他最後的著作之一《防火牆》有說服力地證明了他的分析能力及對個人的與政治的投入。
晚近,Ivan Illich(1926-2002)離世。Eric Fromm在Illich的名著Celebration of Awareness前言中,將Illich描繪成一個激進的人文主義者。Illich身後留下的是一個如Freire所描述的和藹學者的形象,他身為時代先驅,卻自述為一個「陷在拜占庭與威尼斯對抗之間」的「迷途清教徒」(Errant Pilgrim)。
或許,對Ivan Illich的和藹表達敬意最好的方式,就是記得他視自己為二十世紀修道士Hugh of St. Victor的門徒。他修道士似的生活說明了他為何總是認為修道士的苦行生活、嚴謹的紀律訓練、愉快的友誼,是讓有意義的學術成果得以蓬勃發展的環境所不可缺少的前提。
在人類歷史非常危險的時期,Freire、Bernstein、Bourdieu以及Illich的過世,使教育理論失去了有力知識分子的發聲。他們的逝世,雖無助於解決比較教育的理論論戰,但他們所開創的理論途徑激勵我們繼續這個旅程。
教育領域的教學挑戰是巨大的。關於誰是教學主體有深切的理解危機。教育體系的危機反映在老師與學生的論述之間有真實的與符號的錯位(dislocation),也同樣反映在新世代(被稱為任天堂世代)與成人世代論述之間的錯位。這些學校環境中的文化錯位,使教育的平等與相關議題,以及學校課程中的平等、公平、社會流動與歧視議題雪上加霜。此外,我們現在面對教育體系有效性的正當性危機,即教育主體(包括老師、家長以及私人與公立教育機構)的有效性。然而,加上世代之間公共連結的斷裂,或許會引起比教育系統不足更大的危機。大眾傳播系統與新科技的出現以新形式結合了流行傳統文化、流行跨國文化,與由國家機構所發展出的政治文化,有時會面臨公民社會、社會運動與工會等機構激烈的對抗。
總之,過時的學校傳統、對立的論述、學校的文化資本定義問題、多元族群融入的問題、公民職權與民主概念遭遇的危機,以及教育模式與工作市場之間漸增的不對等(以上被強調是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對比較教育提出了各種挑戰。無須驚訝,在理解教育、權力、政治與現代性的文化之間的關連性時,上述許多的挑戰需要被討論。
無庸置疑,為了理解政治與教育之間難解的連結、分析公共教育的正當性危機,或評估後現代主義在比較教育中的角色,未來幾年教育領域將需要更清楚、更令人信服的理論建構。教育理論仍未產出一個對於區域研究與族群研究之角色與理論的決定性理解。同樣地,關於美國弱勢教育及多元文化主義議題的討論,或是關於歐洲跨文化主義的討論,將持續在今後數年引領本領域,燃起學者們的理論想像。我希望本書中文版將會對本領域尚未思考及值得再次思考的部分有所貢獻,並且有助於解決當代教育的難題,如Freire所述的:「創造一個更容易去愛的世界」。
林郡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張珍瑋 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助理研究員
原著誌謝
寫作是一趟智慧上的發現及對話之旅。撰寫本書時,作者深受許多同仁友好之惠。過去三年間,他們耐著性子,聽我著魔般地談論國家、教育、公民職權、民主,以及多元文化主義之間的關係,有時甚至因此攪壞了一餐美食或一場歡談的興致。
感謝Michael W. Apple、Robert Arnove、Atilio Alberto Boron、Sol Cohen、已故之Paulo Reglus Neves Freire、Moacir Gadotti、Walter Garcia、Zelda Groener、John Hawkins、Pat McDonough、Ted Mitchell、Marcela Mollis、Pilar O’Cadiz、Raj Pannu、Raymund Paredes、David Plank、Thomas S. Popkewitz、Adriana Puiggres、Jose Eustaquio Romeo、Daniel Schugurensky以及Welford (Buzz) Wilms。
有幾位同仁友好,曾就本書大部分或全部之初稿,提出極具洞見之建議與評論,謹此特向Nick Burbules、Ray Rocco、Doug Kellner、Todd Gitlin及Gloria Ladson-Billings致意。還有Raymond Allen Morrow,我倆在過去十年裡,一起研討、撰述有關社會學理論與教育的課題,他一直提出許多針砭之見,供我參考。
不少研究生也曾參與本書初稿的討論,並提供了極為有用的意見,讓我再三明瞭教學相長的道理。我在回應他們的問題、質疑及批評時,或許未能公正對待他們的才識,但我願在此承認,他們的建議確有見地。謝謝Maria Beatriz Santana、Octavio Pescador、Sail Duarte、Aly Juma、Carmen Laura Torres、Peter Kipp、Jeniffer Jafnosky、Xochitl Perez、Gabino Aguirre、David Victorin、Karen McClafferty、Julie Thompson以及Analee Haro。我的老友,Rowman & Littlefield書局的執行編輯Dean Birkenkamp,他的專業、熱心、支持,以及他對出版業能為民主公共領域的開創有所貢獻的胸懷,於此一併致意。
本書的初稿,是作者穿梭於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地的旅途上完成的。這三地友人的率真與親切,以及他們對人的熱愛與關懷,讓我不時想起一則拉丁箴言ad fontes,意指我們必須長存人性、慈悲及愛心——這些都是智慧靈感的真正泉源。
謹以此書,獻給家慈。她的為人,不時曉示於我:慈悲無界,行止有愛,民主生活就在平凡無奇處。
作者也願將此書與小女Laura Silvina同享之。她常跟我說,好學之心,以及渴盼與人交流的博愛之性,足以改變這個世界,或至少可以改變有緣與其相聚者的世界。她在當代社會學理論,特別是有關族群與性別議題的廣泛涉獵,助我關注並對這個領域有所認識。小犬Pablo Sebastiin

 共
共  公民身份或公民權是一種認同或身份的形式,使個人在政治社群中取得相關的社會權利和義務,和國籍概念不同,擁有國籍如未成年的國民可能沒有行使公民權的權利及義務,在憲法學及政治學則指由法律規範及政治社群中的個人和群體的權利及義務關係。
公民身份或公民權是一種認同或身份的形式,使個人在政治社群中取得相關的社會權利和義務,和國籍概念不同,擁有國籍如未成年的國民可能沒有行使公民權的權利及義務,在憲法學及政治學則指由法律規範及政治社群中的個人和群體的權利及義務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