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1
改變台灣命運的戰爭∕陳秋坤
台灣是打出來的。如果沒有外力入侵,台灣內部再怎麼亂,最多是部落、村莊、各大姓氏豪族、區域性祖籍分類械鬥,乃至官逼民反的小刀會揭旗反亂等類形的武裝鬥爭,從來沒有因內亂導致主權變遷。然而,在短短三百多年內(一六二○至一九四五年間),卻有三場戰爭,改變台灣政體;將台灣從孤立的島嶼提升為國際貿易要站,統一到中國,乃至獨立建省,回到孤島情境。
最早是一六六一年鄭成功海上艦隊向荷蘭人宣戰,從外海入侵,包圍熱蘭遮城長達九個月,逼迫荷蘭交出主權。一六八三年從鄭家軍投奔清朝的施琅,率領戰船打敗東寧王朝部隊,統一台灣。一八七四年日本派兵征服南恆春半島的土著牡丹社人,促成清廷「認領」整個台灣島嶼,「化番為民」,最後則脫離福建,獨立建省。至於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日本,以及一九四五年二次戰後台灣回歸中國,雖然影響台灣主權,不過,它們是在台灣以外,國與國之間戰爭下的談判結果。按照軍事革命理論,外來戰爭確實是改變台灣歷史面貌的最大基因。據說,大陸近年極力建造海上艦隊,並將其中最大的一艘航空母艦命名為「施琅號」,是否作為改變台灣命運的利器,仍待觀察。
在三場影響台灣面貌的戰役中,要屬第一場戰爭最具有世界史的意義。這是一場台灣海峽海盜和海商集團所集合的船舶戰艦,對抗十七世紀全世界最強大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的戰爭;它也是近代史上,中國人軍隊第一次打敗西方勢力的故事。直到今天,許多歐洲歷史學家仍然不能相信,為何當時船艦配備精良,駕駛技術優秀,能夠繪製海圖,逆風行駛,且船側裝置大炮,海軍士兵訓練嚴格的荷蘭艦隊,會敗給一群駕駛傳統中式船舶,沒有海圖知識的東亞海盜集團。他們認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歷經歐洲戰場的歷練,先後打垮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歐洲海上霸權,絕對可以打敗世界上任何勢力。荷蘭人之所以被鄭成功打敗,一定是有戰備以外,不能克服的因素。例如;運氣欠佳,天氣太壞,或領導人一時判斷錯誤等原因。
本書作者歐陽泰先前發表多篇學術論文,秉持軍事革命論調,認為歐洲國家從十六世紀開始,利用精良武器和講究組織的軍隊,尤其是大炮、火藥和善於在四季各種海流航行的船艦,早已橫征歐亞,變成全球政治經濟核心。不過,有一位編輯獨具慧眼,看到他一篇討論荷蘭東印度公司被鄭成功打敗,退出台灣的文章,覺得甚具世界史的涵意;他建議作者,將文章擴大,運用荷蘭文、中文和世界各地文獻,描寫一六六一年到一六六八年鄭成功軍隊如何入侵,包圍稜堡,利用戰術,誘使荷蘭人承認戰敗,交出台灣主權。
作者接受編輯的建議,大幅改寫論文,希望寫出一本比較通俗,易懂的中外戰爭史。結果不但沒有令人失望,而且讓所謂學界中人感到興奮,開創一個中西軍事史的新領域。本書體裁活潑而豐富,敘述嚴謹而不失風趣。例如,講到鄭成功父子,說他們長相英俊貌美,熟讀中國傳統戰書,善於謀略,知敵善變。尤其是鄭成功,皮膚白晰,在武士道世界長大,精於刀、箭,無可匹敵,對屬下具有絕對的權威,隨時可砍人腦袋。不過,他也說鄭成功身上到處是疤痕,最後罹患梅毒第三期,挖眼發瘋而死。相對的,他形容荷蘭在台灣最高、也是最後一任長官揆一,則是暴躁易怒,睚眥必報,性格怪異的領導。後來揆一被逐出台灣,被判刑幽禁在無人小島期間,撰寫《被遺誤的台灣》(’t Verwaerloosde Formosa),努力替自己辯護。
歐陽泰相當同情揆一的遭遇,因為丟掉台灣這塊荷蘭帝國「冠上最美的一顆珍珠」,畢竟不只是炮彈、鋼鐵、火藥和細菌的因素。十七世紀中葉全球天氣變遷,導致風暴,水災和海嘯頻繁出現,也觸使歐亞國家的征戰更為動盪不安。歐陽泰在分析荷蘭人敗戰的多種因素之外,不禁慨嘆,或許「天意」,才是人類事物的最高決定因素。例如,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十數萬軍艦為何能夠在天霧彌漫的短時間內,闖入狹窄多沙的鹿耳門河道?一六六二年揆一曾經想盡各種辦法阻擋,他還一度爭取到巴達維亞總部派遣救援台灣的艦隊,誰知當天天氣晴朗,看不出有任何「戰爭氣息」,領航司令乃率隊開拔台灣。揆一眼睜睜看著最後的救援機會就這樣溜走,也只能終日垂頭喪氣,感嘆自己被上帝丟棄。
歐陽泰先前已出版過一本有關早期台灣歷史的專書,《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二○○七);當時,他以敘述體寫法,描述十七世紀初期,荷蘭人、西班牙人和漢人,從不同時期,採用槍炮、鋼鐵和農耕方式,陸續征服台灣土著,將獵場闢成水田,使台灣變成南中國米糧供應中心。現在這本書,則以荷蘭人和鄭成功的海戰和包圍戰為中心,訴說中國人打敗荷蘭人,其實包含更深刻的歷史意義。他引用最新的中西戰爭研究報告,指出十七世紀歐洲普遍使用大炮和火藥等武器,其實源自中國元、明以來的持續發明;歐洲人從絲路獲得火炮知識,經過頻繁戰爭的試驗,逐步改良,變成稱霸世界的精良武器。相對的,明朝政府向來重視西洋的火炮技術,經常打撈廢船武器,重新複製。鄭成功很早就從出身海盜的父親鄭芝龍手上,獲得葡萄牙船艦的造船技術、新式武器和火藥炮彈等配備。為此,在一六六一年攻台前夕,鄭成功便不斷派遣船艦,試探荷蘭人的守備和攻擊要點。荷蘭人記錄台灣事物的官方文書──《熱蘭遮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登錄荷鄭兩方頻繁往來信函;當時,鄭成功雖然讚美荷蘭人的船艦和大炮,其實始終未將荷軍看在眼裡,好像隨時都可跟他們打一仗。這不是吹牛,也不是不自量力。鄭成功的龐大船艦隊伍和幾十萬的兵馬,對付荷蘭人兩千名守軍,當然有勝戰把握。更要命的問題是天候、海潮、暴風雨和運氣,都不在荷蘭長官揆一這邊。
想知道鄭成功為何看出機會,趁機而入,一舉擊敗荷蘭人。而揆一為了甚麼理由,會在被送上斷頭台前,懊惱地問上帝﹕時也?命也?
這本書將提供你所有想得到的答案。
本文作者為台灣史專家,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退休。
推薦序2
這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蕭瓊瑞
作為一個大半生在台南府城度過的文化工作者,我極樂意也極榮幸能為本書的出版,說幾句推薦的話,也分享我和這個城市,乃至這個島嶼歷史的深刻感情。
二○○○年元月,千禧年的第一個月,也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正式成立的第一個月,我們為《熱蘭遮城日誌》中文翻譯版的首冊,舉行新書發表會,地點刻意選在熱蘭遮城遺址的城牆殘跡前。在樂團音樂的背景下,我選擇了日誌中幾則記載,高聲地朗讀給所有出席的貴賓、朋友們聽:
一六二九年十月一日:那艘快艇Slooten號從北方抵達此地。該船於七月偕同快艇Domburch號、Diemen號及公司的戎克船駛離此地。帶來的消息,跟上述快艇Diemen號帶來的相同,別無其他消息。
十月四日:快艇Domburch號從北方來停泊在港道前面,於同月五日入港。她為要進行通商交易,曾於北緯三十二度,沿中國海岸漂航,但毫無收穫。上個月十三日正漂航於眾多島嶼之間時,遭遇強風;因此猜想:跟她一起自大員出現的那艘戎克船,可能已在上述島嶼擱淺遇難了。
十月九日:有一個新港居民,奉新港議會的命令來此地通報,有目加溜灣人和麻豆人共約五百人,已經來到他們地區南邊附近,計劃要在夜裡攻擊上述新開始建造的房屋,他們不願意我們在那裡又開始砌磚造屋,而且還計劃要偷襲這城堡。
十一月十日:無特別的事,天氣跟昨夜一樣,濛濛細雨,有風。……
相距三百七十餘年,同樣的地點,朗讀著這些古老的記載,「東印度公司」對我們而言,似乎不再是一個歐洲殖民帝國的組織,而是成了我們歷史的一部分。那樣的時代,有船、有貨物、有漂流、有抗爭、有風、有雨……。
歷史的建構,文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是我第一次深切地體驗到。
二○一二年,適逢荷、鄭決戰熱蘭遮三百五十周年的紀念,由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任教於埃默里大學的歐陽泰教授所撰寫的《決戰熱蘭遮》,中譯本由時報出版社出版,讓我再次領略文獻如何化為具體歷史故事的巨大震撼與迷人魅力。
序幕由一場象徵性的斬首行刑展開,受刑者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在熱蘭遮擔任東印度公司大員地區末任長官的瑞典人揆一。這位背負著「喪失福爾摩沙」罪名的官員,日後遭到長期的監禁,卻也以《被遺誤的台灣》一書,來澄清非戰之罪的委曲。
作為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歐陽泰教授以史詩般的筆法,重現了國姓爺謎一般的傳奇生平,和這場海陸大戰勝負的關鍵;尤其從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政治動亂,乃至國姓爺傳承中國豐富軍事智慧的角度,為全書置入了嶄新的學術觀點,讓人生發和以往絕然迥異的歷史認知與感動。
作為這場台灣最大海陸戰爭的歷史現場,台南迄今仍然保有許多相關的歷史古蹟;《決戰熱蘭遮》一書,優美的文筆和傑出的敘事手法,透過成功的翻譯,讓原本生硬的古蹟和冷僻的文獻資料,散發迷人的故事魅力與知識強度。
福爾摩沙海面的浪濤依舊拍岸、熱蘭遮的城牆殘蹟依然矗立、風仍輕輕吹拂……,熱愛歷史文化的你,漫步古蹟,手中不能沒有這本《決戰熱蘭遮》。
本文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所教授,國內知名美術史學者,曾任台南市政府首任文化局長,主持《熱蘭遮城日誌》(江樹生中譯)的首冊出版。
導讀
鹿死誰手未可知──軍事史研究的再起∕翁佳音
一六六二年,國姓爺鄭成功戰勝商業帝國的荷蘭而進占台灣,是世界史大事件,津津樂道與稱頌者,不乏其人。但像我一樣苦惱者,可能也不在少數。根據紀錄,鄭荷之戰,鄭方的兵數兩、三萬,船隻兩三百艘以上;荷方兵員、民眾前後加起來,不足兩三千人,船艘亦未逾數十隻。荷人兵寡力薄,卻在孤城中堅持九個多月。戰爭結束,鄭方至少損失九千人以上,荷方則在六百至一千六百人之間。梅花鹿雖落入國姓爺之手,不用一代時間,江山又易手滿清異族。如此,鄭家軍戰功彪炳之外,總是有些令人難以啟齒的陰翳。
另一方面的苦惱,是有些歷史讀物,有意與無意中將荷蘭東印度公司領有台灣的三十餘年間,描繪成西方近代理性殖民經營的代理人,原住民與漢人則為陪襯、被近代化的角色。這些苦惱,其實是歷史學界的老問題。近代的歷史觀,深受十九世紀西方崛起完遂稱霸之影響,形成一種「正統」觀念,認為十六世紀的近代初期以來,西方在思想、制度與科技,已凌駕東方。因此,不少人會用十九世紀的船堅炮利、帝國主義圖像,去想像十七世紀的東西會遇與衝突。哇,鄭成功以傳統武力擊潰西洋近代船堅炮利!然而,這是時代錯置(anachronistic)的歷史思考,往往看不到歷史精彩與意義層面。
美國歷史學者歐陽泰長期以來便相當關注上述議題,並且對這個問題作了不少研究上的回應。他上一本大作《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即敘述台灣海域已有華人勢力與網絡,新闖入的荷蘭、西班牙殖民者,終究力量有限,到頭來,台灣還是華人的(社會)。套句歐陽泰於這本新書所用的術語,十七世紀,依然是東西世界「勢均力敵」(The age of parity)的時代。這本新書,是承上一本書旨趣,繼續進行他對上述「正統」西洋優越史觀的「修正主義」主張,以及再自我修正的敘述與分析。
他廣泛運用中外文獻,以及近現代研究者的成果,以編年序列方式分析從鄭芝龍開始,到鄭成功、鄭經海上勢力與荷蘭人之間的數次戰爭。考察結果,他認為,就武器、軍紀與兵法上,荷蘭不見得占上風,這方面,他依然維持十七世紀東方中國優越的主論。不過,歐陽泰也提出一些對修正主義的修正。他認為荷鄭的圍城之戰能持久,甚至是荷船以寡敵眾,關鍵在西方軍事科技在十六、七世紀時已發展文藝復興式、外圍有稜形堡(bastion)的城堡,以及船舷炮。從軍事史角度而言,我相當同意歐陽泰的主張。新軍事科技的演進,確實讓火網密集,更具威力,難怪鄭軍傷亡慘重,連當時人都諷刺:鄭成功「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於火輪、宿將碎肢體於沙磧」。本書已透露我一開始所說的苦惱。
歐陽泰這本原名副題為中國首次打敗西方的書,對喜愛軍事史的讀者而言,當然不用我再介紹。上個世紀九○年代,我即聽說現代歷史學界比較不注意的軍事史,有鹹魚翻身的傾向。軍事史不僅只研究武器、軍團組成與戰術,連氣候、疾病,甚至是性,都可圍繞著戰爭來講;甚至能構成雄壯史詩,與日常生活細末的歷史影像,端看作者組織與敘述技巧如何。這方面,我不得不佩服作者處理相當成功。史料充足,故事性強,全書少有冷場。譬如,他連鄭成功在台灣戰場指揮之餘,還努力與妻妾敦倫,而有數名遺腹子的細節,都寫入書中。
然而,好書總是要勉強挑剔一番,如此才會引誘讀者延續有意義的話題。本書可能主要是以英語讀者為主,所以從台灣的立場來看,若干地方倒是可再斟酌。例如,書中講鄭氏海戰大捷,固然鄭家軍的紀律與孫子兵法奏效,但人海戰術也不能忽略。中方勝利,往往慘勝居多。料羅灣海戰,中方舊損失兩百多艘大小船隻,代價不可謂不大。作者多次提到荷蘭船可逆風行駛,中國船不行,但書中用《經國雄略》之「沙船」附圖,圖中文字卻明說沙船可「能調戧使逆風」。顯然,雙方船隻性能,還是可以繼續討論。
同樣也許因為原書以英語世界讀者為主,所以儘管經名家之手翻譯,書中讀起來有時不免異國風味濃郁。例如講無辜農民Sait,如果仔細核對檔案,應該是「蘇」(Sou),他是台南仁德崗港(Kankon)人。又,他提到一位探訪傳道士Hendricksz在海外一座小島被原住民所殺。冤枉啊,他因會講閩南話,才被派去小琉球。當時小琉球的居民,是漢人。
本書還有很多地方可以討論,我不能講太多,讓讀者自己開採。我順著歐陽泰注意疾病的故事作最後結語。書中提到西班牙神父李科羅說鄭成功死於劇烈的「日射病」。日射病西班牙語為tabardillo,照十七、八世紀的觀點,是屬斑疹熱之流,與其他歐語typhus、typhoid fever(傷寒)相同。長達半年以上的圍城之戰,雙方文獻充斥著兵民罹患地方病(landsiekte),或高燒熱病(heete koortse, coorsen);「驚聞海東水土惡,征人疾疫十而九」、「死者甚多」等等記載,讀來怵目驚心。文獻所載之地方病,通常是指流行病、瘟疫。此時疫病,是瘧疾、霍亂,或斑疹傷寒?我非專家,不能妄斷。鄭成功死因,歷來說法不一。但當時大清中國獲取的情報,一致說他「發狂身死」,與李科羅神父聽聞大抵相同。中國統帥發狂,是人格偏差之精神症狀,還是戰爭和瘟疫下的犧牲品?我想,後者的可能性也不低。清代文獻說「南淡水之瘴,作寒熱,號跳發狂」,斑疹傷寒亦有這般譫妄症狀,鄭成功死前狂走、嚙指與抓破面目,或許敗在身負摧毀不理性人間重任的病菌與病毒。
寫到這裡,不免令人想到一句名言:「是社會主義戰勝,還是虱子嬴了?」
台灣梅花鹿鹿死誰手,十七世紀是否中國首次「大敗」西方,看來今後還是有得爭。我期待歐陽泰教授的這本新書,為我們開啟討論的序幕。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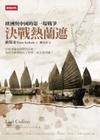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