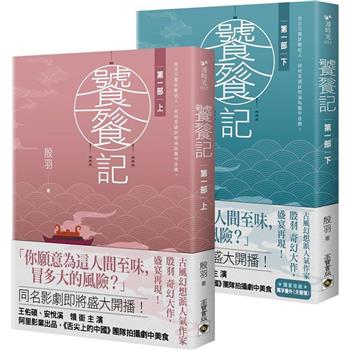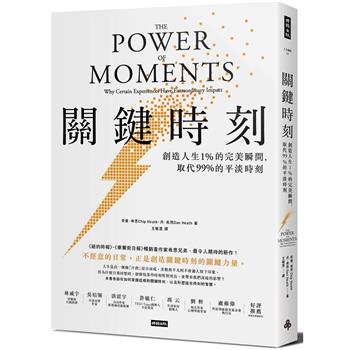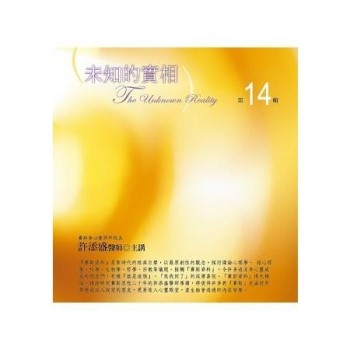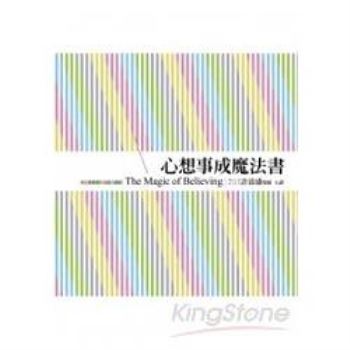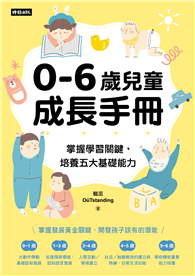延安一代,上承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下啟解放一代、紅衛兵一代,對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歷程深具影響。
本書以延安一代悲劇人生證示赤潮禍華巨大創傷,具體展現赤說如何領歪延安一代,以鮮活細節還原歷史實貌,剔選經典史料全方位駁斥馬列之謬。
本書特色
1.一本無法在大陸出版的「禁書」,深觸中共神經,受到「特別關注」!
2.深挖赤說謬根,具體列示赤潮禍華,全方位論證「中國,你走錯了路!」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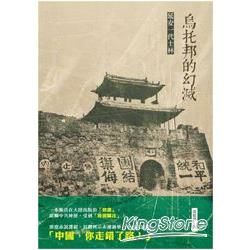 |
$ 637 ~ 819 | 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
作者:裴毅然 出版社: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14-04-15 語言:繁體書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
內容簡介
目錄
序 一本逼人深思的書─裴毅然《延安一代士林》/錢理群
引 言
第一章 代際作用
壹、黃金一代
貳、自養坐大的既定方針
參、最重要的組織基礎
肆、代際作用
第二章 學歷構成
壹、誰搶到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天下
貳、地方師範為中共儲才
參、學歷構成
肆、粗淺單一的知識結構
第三章 一時氣象
壹、赤潮入華
貳、紅色的1930年代
參、中國的耶路撒冷
肆、延安生活
伍、延安婚戀
陸、外客眼中的延安
柒、陽光下的陰影
第四章 思想框架
壹、隔著紗窗看曉霧
貳、呼喊跟從的一代
參、政治第一
肆、真理執行者
第五章 拐點整風
壹、短暫自由
貳、事情在悄悄起變化
參、初露崢嶸的紅色恐怖
肆、標準化與功利主義
伍、意味深長的拐點
第六章 撤守五四
壹、無遠弗屆的階級論
貳、撤守個性
參、思想改造
肆、遺禍子孫
第七章 組織崇拜
壹、革命宗教化
貳、自身局限
參、信仰代替思考
第八章 延安共性
壹、不識馬列
貳、概念人
參、工農化方向
肆、暴力文化
第九章 尷尬一代
壹、高調進城
貳、難說真話
參、尷尬人生
肆、打倒序列
伍、無有後來人
第十章 艱難反思
壹、起步維艱
貳、發現常識
參、反右~文革之棒喝
肆、突破毛崇拜
伍、面對現實
陸、撩看黨史
柒、反思難度
第十一章 分裂分化
壹、最初裂紋
貳、「六•四」之裂
參、反省漸深
第十二章 最後歸宿
壹、走錯了路
貳、實踐而後知
參、認清赤謬
肆、最後歸宿
結語
跋
附錄 深春訪銳老―馬列理論本身就全錯了
引 言
第一章 代際作用
壹、黃金一代
貳、自養坐大的既定方針
參、最重要的組織基礎
肆、代際作用
第二章 學歷構成
壹、誰搶到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天下
貳、地方師範為中共儲才
參、學歷構成
肆、粗淺單一的知識結構
第三章 一時氣象
壹、赤潮入華
貳、紅色的1930年代
參、中國的耶路撒冷
肆、延安生活
伍、延安婚戀
陸、外客眼中的延安
柒、陽光下的陰影
第四章 思想框架
壹、隔著紗窗看曉霧
貳、呼喊跟從的一代
參、政治第一
肆、真理執行者
第五章 拐點整風
壹、短暫自由
貳、事情在悄悄起變化
參、初露崢嶸的紅色恐怖
肆、標準化與功利主義
伍、意味深長的拐點
第六章 撤守五四
壹、無遠弗屆的階級論
貳、撤守個性
參、思想改造
肆、遺禍子孫
第七章 組織崇拜
壹、革命宗教化
貳、自身局限
參、信仰代替思考
第八章 延安共性
壹、不識馬列
貳、概念人
參、工農化方向
肆、暴力文化
第九章 尷尬一代
壹、高調進城
貳、難說真話
參、尷尬人生
肆、打倒序列
伍、無有後來人
第十章 艱難反思
壹、起步維艱
貳、發現常識
參、反右~文革之棒喝
肆、突破毛崇拜
伍、面對現實
陸、撩看黨史
柒、反思難度
第十一章 分裂分化
壹、最初裂紋
貳、「六•四」之裂
參、反省漸深
第十二章 最後歸宿
壹、走錯了路
貳、實踐而後知
參、認清赤謬
肆、最後歸宿
結語
跋
附錄 深春訪銳老―馬列理論本身就全錯了
序
序
一本逼人深思的書─裴毅然《延安一代士林》/錢理群
(一)
酷暑中讀完裴毅然先生這本好沉重的書─不僅是書的篇幅「重」,更是其內容之「沉」,我長長吐了一口氣:此書的出版,正當其時!
我這麼說,基於我對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問題的一項判斷。約於2010年初,郭小川(他正屬於本書所研究的「延安一代」)誕辰九十周年紀念座談會上,我有一篇發言,談到如何認識「革命時代」和當下「我們的時代」,這兩個有著內在聯繫的時代,「實際上是當下中國知識界、思想文化界、學術界所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也是爭論的焦點」;並且有這樣的分析:「據我的觀察,存在著四種傾向。一是對革命時代和當下中國現實的全面肯定和讚揚,將革命理想化、現實盛世化;二是對革命和現實都持尖銳的批判態度,以至全盤否定;三是肯定革命年代而否定現實社會;四是肯定現實而否定革命時代。」事實上,這些不同傾向,已經有了理論上的表述,一方面是黨內毛派呼籲「回歸毛澤東時代」,一部分知識分子提出「集權為民」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北京共識」;另一方面,黨內民主派高揚「民主社會主義」,另一部分知識分子提出以「憲政民主」為中心的零八憲章等等,其背後都隱含著對革命時代與當下時代的不同評價與態度。在發言中,我還談到自己的困惑:
這四種傾向,在我看來,都有兩個特點,一是觀點明快,態度鮮明,立場堅定;二是立場、觀點在先,缺乏具體的分析、研究。談歷史,實際上對歷史瞭解甚少,根本沒有進入具體的歷史情境;講現實,多從感情、道德、義憤出發,缺乏具體實際的調查研究,更不用說理論的辨析和批判。我的困惑在於,儘管我自有必須堅守的基本信念和基本判斷,但我更願意把問題看得複雜一些,對所有過於明快的判斷,我都有些懷疑,總覺得在明快因而痛快的背後,遮蔽了一些東西。因此,在對歷史與現實作出判斷時,我常常猶豫不決,即使作出了一些判斷,也有些心虛,自己就先懷疑起來。這樣的立場就顯得不夠堅定,在這處處要求站隊的時代,就不免把自己置於尷尬的境地。
在發言的最後,我還表達了這樣的期待:作為一個學者,一個知識分子,我們要做的,所能做的,不是急急忙忙地表態,而是要坐下來,踏踏實實地進行研究,創造對歷史與現實都具有闡釋力的新的批判理論。而這樣的探討,又應當從個案研究入手。
我正是以這樣的期待來看裴毅然先生的這本新著,論定它的出版「正當其時」,不僅是因為本書對當下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問題,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對時代所提出的重大問題作出了自己的回應,表現了在當下中國學術界特別難能可貴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更因為本書是作者坐下來踏踏實實地研究的成果,其用功之力、思考之深,表明這是一個學者的回應,它的鮮明的觀點,是建立在學術研究基礎上的,讀者盡可以不完全同意研究的結論,但確實能夠從中得到許多啟示。
我尤其欣賞的,是作者採用的「個案研究」的方法,而且選擇「延安一代知識分子」作為研究對象,這是顯示了一種銳利的學術眼光的:延安一代人,如作者所說,是上承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下啟解放一代及紅衛兵一代的,因此拎起這一代,可以把握與揭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道路的全景。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延安這一代還在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現實,前文提到的黨內毛澤東派與黨內民主派的主要骨幹都是延安一代人,意味著延安一代在當代的分化。因此,以延安一代人作為個案進行研究,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能夠有助於人們認清當下這些爭論的歷史淵源及其深厚的歷史內容:這是一個極好的歷史與現實的結合點。
(二)
我更看重本書的,是作者的研究對當下爭論的啟示。
本書的最大特點是史料的詳實,這也是作者的自覺追求:「儘量還原史實,以據立論,重在對具體歷史情境的剖析」。這本來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但在當下的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界卻成了問題。這也是本書所揭示的歷史的積弊:「為實現自己頭腦中的紅色概念,無視具體現實,尤其無視革命造成的悲慘現實」;立場在先,觀念在先,判斷在先,而且不需要事實的支撐,甚至不顧及基本歷史事實,睜了眼睛說瞎話。比如說,一位毛澤東派的帶頭人宣稱「文革前三年天下大亂,後七年天下大治─億萬人民意氣風發,各行各業碩果累累,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層出不窮,新型革命秩序初步確立」─作者自可以為毛澤東時代辯護,但用這樣歪曲事實的作法來唱讚歌,就有些離譜。還有一位鼓吹「中國模式」的學者,則揚言「人類在解決收入貧困、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生態貧困四類貧困中沒有什麼太大成功的案例,只有中國在其特定的國情條件和體制下,才取得了初步的成功」─這樣的描述和判斷,與真實地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普通人的實際感受大相徑庭。這位學者盡可以採取支援中國現行「體制」的立場,但如此不顧事實,在我看來,無異於在幫倒忙。
這當然不是一個單純的學風問題,它其實正是這些年當局推行「強迫遺忘」的思想、文化政策的產物。而且不能低估這樣的遮蔽、否認歷史事實的「強迫遺忘」國策的有效性。比如說,今天一些青年已經不知道,進而不相信1959~1961 年中國曾經發生過大饑荒引發的大規模死人的事實─人們對死人的具體數字與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原因盡可以有不同的認定和分析,但討論的前提,是必須承認歷史上確實發生過大規模非正常死亡這一基本事實。如果把論斷建立在不承認基本事實的基礎上,那是無法討論問題的。理論與觀點的力量正在於,能面對所有的事實,並作出有說服力的解釋與分析。也就是說,揭示與面對所有的事實,這應該是我們討論中國革命時代和當下時代問題的前提與基礎。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得出結論:不管人們在認識上存在怎樣的分歧,但在這一基本方法論或基本討論規則上應該取得共識,不然是越爭論越糊塗的。
我讀本書,最為感佩的,就是作者敢於面對事實的膽識。本書所揭示的事實,在今天的某些年輕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而是可疑的;對歷史的當事人而言,這些事實又是不堪回首的,對年輕時候深受延安這一代人影響的作者來說,面對這些事實,也會引發痛苦的記憶;而應該對這段歷史負責的執政者,不僅不願正視這些事實,更因為對事實的揭示、分析與批判,會觸動他們的統治利益,而運用權力對揭示者進行打壓。這就意味著,作者要面對歷史事實,必須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不僅是體制的,權力掌握者的外在壓力,更來自研究對象,接受對象,以至作者自身的內心恐懼。這是需要勇氣、良知和學術與歷史責任感的。
真正面對全部事實也不容易,除了主觀有意無意的遮蔽外,也還有材料不足的困難,事實上歷史也不可能完全復原;由此決定了任何對已掌握的事實作出的判斷,都具有相對性,隨著新的史料不斷發現,就可能對已有結論作出補充修正,以至局部或全部否定。而要面對不利於自己分析的材料,並作出合理解釋,則更不容易。比如本書多次談到一些延安人至今也還局部或全面地堅持自己當年的選擇和觀念,作者沒有回避這樣的事實,但卻歸之於這些歷史當事人缺乏反省和覺悟,迷途而不知返的局限,這就有點簡單化,是應該作更複雜的分析的。其實這是反而有助於對問題的深入認識和討論的,作者錯過了這樣的機會,有點可惜。
我一直記著恩格斯的一句話:道德的義憤,代替不了科學的研究。學術研究不能局限在對歷史或肯定或否定的價值判斷上,而應該對所發生的一切,作出學理的追問和解釋,並從中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這樣才能做到「將歷史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這正是本書的著力點,在這方面是顯示了作者思考的深度和功力的,也同樣給今天的爭論以啟發。比如,延安這一代人的最大悲劇,是所謂「從這道門進入,卻走到了另一個房間」。
用作者的話來說,就是「尋找中失去了尋找的東西,在努力中失去了努力的價值」。本書特地引述了原毛澤東秘書李銳先生的反思:
「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從根本上就錯了。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徵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麼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和私有制,無論遭到多大誤解,無論怎樣被妖魔化,最終都會被人類認同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是不能消滅的,消滅了還得請回來。這是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留給後世的最根本的教訓。
這其實也是所有面對這段歷史的人們,包括研究者,都必須認真思考的。於是,就注意到這樣的現象:延安這一代所獻身的中國革命事業除了它的現實性以外,還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每一個命題在邏輯與歷史的起點上,都充滿純粹、崇高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烏托邦主義精神,而其邏輯的展開,歷史的實現的結果,卻顯示出專制主義的血腥味。如作者所說,「一切非理性的所謂『抒情詩』都有導向專制與恐怖的可能」。而且終點的專制主義並非對起點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烏托邦主義的反叛,而恰恰是其邏輯與歷史展開的必然結果。這也就是說,專制主義的後果正孕育於起點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烏托邦主義之中。
本書的探討,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對上述起點的追問,作者用大量的史實,銳利的分析,真實而具體地揭示了這些真誠的革命者,是在什麼地方、通過怎樣的思想、邏輯而落入陷阱的。例如,以建立「至善至美」的「地上天堂」為目標,將彼岸理想此岸化,必然導向現實地獄化的後果;追求思想的至善至美性,絕對真理性,必然導致馬克思主義的絕對化與宗教化,同時也使自身發生了異化,「以信仰代替思考」,放棄探索真理的權利,而成為「真理的執行者」、「專橫的啟蒙者」;追求至善至美的人性,鼓吹「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聖徒道德,強調對人性的「改造」,必然導致人的異化,成了「馴服工具」和「用響亮的口號包裝自私的目標」的「偽君子」;將「人民」理想化神聖化,製造民粹主義的「人民崇拜」,其現實落實,必然變成對自稱「人民代表」的黨和領袖的「組織崇拜」與「領袖崇拜」;將鬥爭、矛盾、反抗、運動絕對化,鼓吹「階級鬥爭」、「鬥爭哲學」,也必然誘發人的嗜殺性,導致災難性後果,同時也將自身變成「終身生活在鬥爭思維和仇恨之中」的「政治動物」,等等。這樣一些追根溯源的分析,都是以大量的事實為依據,是從事實出發的,但又不是對事實的簡單描述,是高於事實,更具有理論的高度與深度的,這樣的建立在科學理性的分析基礎上的批判,才是真正有力的,由此總結出的歷史經驗教訓,就具有了某種普遍的啟示意義,足以警戒後人。─這正是我們的研究、討論、爭論的目的所在。
本書自然也有可能引起爭論的方面。前文已經談到,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批判立場是十分鮮明的,在行文中就常常忍不住跳出來發表許多含有主觀感情的尖銳議論,這固然可以取得「振聾發聵」之效,但也很容易遭到批評。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就有學者批評本書「感情色彩強烈,太重褒貶,文學筆調,缺乏學術性」。儘管我也認為作者對自己的主觀情感如有所抑制,或許更好;但卻願意為作者作一點辯護。其實,本書的寫作,某種程度上,是「當代人寫當代史」,也就是說,作者所要研究的這段歷史,是和自己的生命攸關的,是直接影響了自己人生道路與命運的,有著太多的刻骨銘心的記憶和種種身歷其中者才有的生命體驗。因此,在研究與描述這段歷史時,就很難做到「純客觀」,有必要把自己的生命投擲其中。這樣的主體投入式的研究,或許有它的局限,但同時又獲得了完全根據文獻資料來進行客觀研究與冷靜描述的學術研究所不具有的特殊價值。它不僅對遠溢於文字、文獻之外的歷史情境有深切的把握,對文字、文獻內在的言外之意有精微的體驗,這都是僅憑文獻來把握歷史的後世研究者所難以達到的;而且它自身就構成一種價值,讀者讀到的不僅是研究對象的歷史,也包括研究者自身的歷史,連同它的局限也都是一種歷史現象,可以作歷史的解釋,可以折射出歷史的某一側面。
這一點,作者也是高度自覺的。他一再強調自己「紅衛兵一代,知青一代」的身份,強調:「紅衛兵無論價值理念,文化構成,思維方式,行為範式,都出自延安一代的母體」。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本書寫的是「紅衛兵一代眼裡的延安一代」,更準確地說,是一位幡然醒悟的紅衛兵對曾經是自己「精神之父」延安一代的反思和反叛,所展現的是處於精神糾纏中的兩代人的精神史。這大概是本書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所在。
它自有不可取代的特殊價值,但同時,也就有了對其進行再反思的餘地。比如說,作者對精神之父的反思與反叛的背後,是一種刻骨銘心的「弒父情結」;而這又恰恰是延安一代覺醒的起點。如作者所說,延安一代對於五四一代也同樣存有「弒父情結」,而且不止於弒父,幾乎對所有的老祖宗都持尖銳的批判、否定的態度。而如作者所分析,這樣的和前輩、傳統的徹底決裂的決絕態度,發展到極端,就成為延安一代人後來走向迷誤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角度看,對各代人都難免的弒父情結,包括延安一代的弒父,都要有同情的理解,因為不對前輩進行反思和反叛,就永遠被傳統所籠罩,無法走出自己的路,但同時更要看到將必要的反思反叛,推向極端,就會成為一個陷阱。因此,我讀完本書,就不免產生一個疑惑:難道延安一代除了慘烈的教訓,就沒有給後代人留下任何精神財富嗎?他們的精神價值,僅存在於他們晚年的反思、懺悔顯示的「真」嗎?他們早年的「真」,難道僅僅是一種需要反思的幼稚與天真?作者也承認,延安一代人的特點是:「正直天真、嫉私如仇、浪漫激越、憎恨自由、害怕個性、思維偏狹」。不可否認,這樣的精神氣質,是他們後來走向精神迷誤的內在原因,這裡確實包含了慘痛的歷史教訓;但它難道就沒有正面的價值和意義?在我看來,今天大陸理想喪失激情不再是非不明,整個社會彌漫著遊惰、虛假、世故、市儈之氣,延安一代人精神氣質在經過反思以後,是可以轉化為新的精神資源的。─這裡有兩條界限:一是不能不加反思,批判,也就是絕不能把那一代人和那個時代理想化,那就會重犯歷史的錯誤;二是又不能因為反思和批判而將其全盤否定,那我們就會犯「把孩子和髒水一起倒掉」的新的歷史錯誤。
(三)
本書的敘述,給我的一個強烈印象,是處處充滿了「大徹大悟,回頭是岸」的氣息。而這恰恰是我最為擔憂的。因為這恰恰是延安一代曾經落入的一個陷阱。本書引述了當年丁玲在批判王實味會議上的發言,其中心意思就是大談她的「大徹大悟,回頭是岸」。客觀地說,當年丁玲的「徹悟」:從個人主義皈依集體主義,從自由、民主的理想到皈依追求平等、正義的社會主義理想,從追求個性解放到皈依爭取工農解放的革命,是自有邏輯,有局部的合理性的,並非完全的盲從,而且在丁玲看來,她所皈依的是「真理」,因此,她說自己「回頭是岸」,是有相當的真誠性的,當然也不排斥有屈服於外在壓力的成分。對這兩方面都不可忽視,這正是顯示了歷史和人的思想的複雜性。丁玲的真正迷誤在於,她將自以為找到的「真理」絕對化,把「回頭」看到的那個「岸」(革命,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終極化,其結果就是本書所總結的:走到了當初追求的反面,從理想主義、烏托邦主義走向了專制主義。我們不能一面總結這樣的歷史教訓,一面又自覺、不自覺地以另一種形式,從另一個極端,重複歷史的錯誤。也就是說,前文所概括的本書對延安一代的精神迷誤的批判、經驗教訓的總結,不僅要警示世人,也應該警示作者自己。其實,作者對此也並非沒有警覺:他在本書的《跋》裡就談到了「自己也難以避免像空氣一樣進入體內的紅色思維,難以避免『以赤反赤』」,反思、批判者與被反思、批判者之間,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存在著思維方式的類似或相同,正是深刻地反映了我們在前面一再強調的兩代人之間「生命的糾纏」,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作者所要批判的「從理想主義到專制主義」的思維毒害與危害之深重,並且反映了這段革命歷史的複雜性與豐富性。
本書作者曾引述了一位著名學者的一個觀點:應該在「保守」與「激進」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在我看來,這一命題具有普遍意義。我們應該在一切方面─民主、自由與平等之間,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都保持一定的張力。當然,就個人的具體選擇而言,總是有「偏至」的,所以魯迅有《文化偏至論》之說。也就是說,在現實政治思想文化的選擇中,有的人偏向於民主、自由,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有的偏向社會平等,集體主義,社會主義,這都是正常的。問題是,一不能把自己的選擇絕對化,終極化,二不能把不同於己的選擇妖魔化,而且還要善於從中吸取合理的資源。做到後者就自會有一種博大、寬容的胸襟,這是保證自身思想的健全發展和民族與世界文化的多元化的一個前提;做到前者,就會和自己信奉的思想、社會制度之間,保持一個距離,形成一種張力,這是保證自身思想、學術和精神上的獨立性、批判性與創造性的前提,而在我看來,這樣的獨立性、批判性和創造性,是一切真正的知識分子的生命之根本。在這方面,魯迅對民主、科學、自由、平等等工業文明的基本價值觀所採取的「既堅持又質疑」的態度,有極大的啟示意義。
寫到這裡,我突然想起了捷克著名改革家、思想家、前總統哈威爾的一個警告。我們知道,哈威爾也有過從理想主義的共產黨人到批判自己參與建構的體制、推動民主改革的經歷,和本書所討論的老延安人的思想發展有類似之處。他在談到自己這一代的「歷史經驗」時,就提醒說,時刻不要忘記我們曾被「一種透明的烏托邦所捕獲」,因此,我們必須「懷疑所有的烏托邦」,懷疑所有「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產物」,要永遠保持「對任何不能自審的東西的反感」和本能的警惕與抵制。應該說,缺乏這樣的懷疑和警惕,正是延安一代發生精神迷誤的重要原因,後來人應該永遠引以為戒。
當然,我對自己對本書的疑惑也有一個自我警戒:說不定我的疑惑正是本文一開始就提到的我在當前這場論爭中的「猶豫不決」,「不鮮明不堅定」,因而常「陷入尷尬」狀態的表現,因此,我的疑惑也只能「僅供參考」,說說而已。而我確實從本書中受到很大啟示和教益,包括引發的某些疑惑,也是能逼人深思的。我想,這或許也是作者對我們讀者的期待。
引言
延安澀重,史頁難翻。延安一代演出結束,即將整體隱入歷史帷幕的皺褶之中。但曾經大紅大紫的「延安一頁」,還未徹底翻過去,赤色烏托邦雖然幻滅,意識形態強大的滯後性使延安理念還在彌漫播遷─控制現實、影響未來。
拙著以延安一代紅色士林為研究對象,以個體行跡為依據,以集體整合為旨歸,以微觀細節支撐宏觀概括,具體展示赤潮禍華過程中對延安一代的實際影響。拙著力求還原歷史過程中的整體性,化抽象為感性,匯個例證整體。這一研究方法,庶可避免此前史學研究之兩難─或過於宏觀、缺乏具體實證;或過於微觀,失之宏觀整合。
拙著旨在剖析延安一代悲劇的過程中,全面檢討赤潮禍華的各項致因:激烈動盪的時代背景、日寇入侵的歷史機緣、老舊孱弱的傳統文化、辨別赤說的致命時差、中共「鬧紅」的真實過程、拖垂至今的現實影響。同時,剖駁馬列謬說、刨挖赤學歪根,為史立說,為後立警。惟願宏力拙,一士之力耳。
資料來源上,除依託綜合史、思想史、政治史、社會史、黨派史等,儘量參照各種傳記─自傳、評傳、回憶錄,以個人具體感受辨析各種史料史評,力避紅色史著「以論帶史」之惡弊。儘量還原史實,以據立論,重在對具體歷史情境的剖析,以史實、資料、言行等客觀材料佐證各種歸納。如延安一代的學歷、知識結構、五四方向何以被逆轉、延安與反右與文革與當下的聯繫、馬列赤說何以被廣泛接受……因研討中共奉為神靈的意識形態,為避「惡攻」,也必須握有結實可靠的論據。
如果延安之航大方向正確,怎會一步步走向暴烈土改、恐怖鎮反、三反五反、「擴大」肅反、反右反右傾、「人禍」大饉、十年文革、六四坦克?大批中共元勳怎麼成了反革命?聲名赫赫的林總竟成「叛國林賊」?一場「最偉大最徹底」的革命,怎麼還是演成那麼熟悉的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變革還是一場昔日舊戲?
後人當然有權轉動今日陽光去照射昔日陰霾,用今天的人文標準檢剔昨日的斑斑汙點。社會進化與時代進步,精髓當然是人文評判標準的提高。「革命人民」今天多少有點覺醒了:歷史不能任由統治者按需解釋;用哪一種理念闡釋歷史等於選用哪一根規尺裁量今天,即選用哪一種價值標準安排未來,茲事體大呵!對中共歷史的闡釋與判認自然不能任憑中共自評自擺,對延安一代的評議也不能由延安人自裁自量。
延安一代紅色士林,時代特徵烈然鮮明,價值取向渾然整一。無法複製的一段歷史使他們裹帶上濃密的紅色資訊,身後倚托著百年國史,腳下也就埋有史家最感興趣的史料,成為共產革命的重要標本。
「東風」「西風」,誰的「主義」真,是騾是馬還不得看政經效績?取決為社會帶來什麼。如今,俄中東歐越柬等赤國東風落篷,「風向」大致已定。雖然馬列旗幟尚在大陸飄揚,誰都明白:紅旗打不久了。事實上,文革後中共改革轉向,第一站就必須摘除毛澤東思想,必須與馬列主義有所剝離。雖然至今仍閃左燈,經濟實體畢竟早已右拐,資本主義早已復辟,「西風」已經壓倒「東風」。大陸今天的「言」「行」不一(打左燈向右行),當然是特殊的歷史產物,「言」「行」終將合一。
延安一代與馬列主義相始終,一輩子高舉赤色大旗,由延安人自己去降旗,雖然只是少數「兩頭真」,其間史蘊已夠史家啜吸。僅僅這一大轉折,就值得後人循階上山,嚼延安橄欖,覽紅色風景。延安一代,風景獨異呵!研析延安一代,釐清這代赤士何以整體走歪走斜,等於解剖赤色時代的骨骼,刨挖赤潮根鬚。
太陽明天還會重新升起,中國已從極左深巷折返,二十世紀一路滴淌的鮮血都將在二十一世紀模糊褪色,但對於那些註定在黎明前走進歷史褶皺的數代紅色士林,卻是真正的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如果後人不從他們那兒提煉經驗教訓,不從他們巨大的價值背反中找到悲劇成因,不從他們的腳步中總結出「千萬不要忘記」,認清「奪權大於原則」的延安之痛,那才叫最大的悲劇─還會在原地再摔第二跤。
延安一代的悲劇也許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無法規避的「俄狄浦斯命運」,但存在並非必然合理,今人有權要求終止這一「必然」。擴大每一代人的選擇權,而非限制甚至褫奪後人的選擇權,乃是歷史發展的前提,也是人類必須持守的基本人文價值。否則,自由的內涵還剩下什麼?
延安一代演出結束了,大幕即將合閉,惟少數耄耋延安老者「人還在,心未死」,憑藉歷史形成的高度發揮餘熱,對當下仍有重大影響,個別重要人物(如李銳、萬里、杜潤生、杜導正)餘熱尚熾。京中流諺:「老年燃燒,青年取暖。」觀之前人、驗之當世、參之後人,研析延安一代似有歷史、現實與未來三重意義。
黑格爾(1770~1831):「密納發的貓頭鷹要等黃昏到來,才會起飛。」對某一大型社會現象的理性認識,須待其形成過程結束才會開始。延安一代,變數幾盡,「密納發的貓頭鷹」庶可起飛矣。
一本逼人深思的書─裴毅然《延安一代士林》/錢理群
(一)
酷暑中讀完裴毅然先生這本好沉重的書─不僅是書的篇幅「重」,更是其內容之「沉」,我長長吐了一口氣:此書的出版,正當其時!
我這麼說,基於我對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問題的一項判斷。約於2010年初,郭小川(他正屬於本書所研究的「延安一代」)誕辰九十周年紀念座談會上,我有一篇發言,談到如何認識「革命時代」和當下「我們的時代」,這兩個有著內在聯繫的時代,「實際上是當下中國知識界、思想文化界、學術界所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也是爭論的焦點」;並且有這樣的分析:「據我的觀察,存在著四種傾向。一是對革命時代和當下中國現實的全面肯定和讚揚,將革命理想化、現實盛世化;二是對革命和現實都持尖銳的批判態度,以至全盤否定;三是肯定革命年代而否定現實社會;四是肯定現實而否定革命時代。」事實上,這些不同傾向,已經有了理論上的表述,一方面是黨內毛派呼籲「回歸毛澤東時代」,一部分知識分子提出「集權為民」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北京共識」;另一方面,黨內民主派高揚「民主社會主義」,另一部分知識分子提出以「憲政民主」為中心的零八憲章等等,其背後都隱含著對革命時代與當下時代的不同評價與態度。在發言中,我還談到自己的困惑:
這四種傾向,在我看來,都有兩個特點,一是觀點明快,態度鮮明,立場堅定;二是立場、觀點在先,缺乏具體的分析、研究。談歷史,實際上對歷史瞭解甚少,根本沒有進入具體的歷史情境;講現實,多從感情、道德、義憤出發,缺乏具體實際的調查研究,更不用說理論的辨析和批判。我的困惑在於,儘管我自有必須堅守的基本信念和基本判斷,但我更願意把問題看得複雜一些,對所有過於明快的判斷,我都有些懷疑,總覺得在明快因而痛快的背後,遮蔽了一些東西。因此,在對歷史與現實作出判斷時,我常常猶豫不決,即使作出了一些判斷,也有些心虛,自己就先懷疑起來。這樣的立場就顯得不夠堅定,在這處處要求站隊的時代,就不免把自己置於尷尬的境地。
在發言的最後,我還表達了這樣的期待:作為一個學者,一個知識分子,我們要做的,所能做的,不是急急忙忙地表態,而是要坐下來,踏踏實實地進行研究,創造對歷史與現實都具有闡釋力的新的批判理論。而這樣的探討,又應當從個案研究入手。
我正是以這樣的期待來看裴毅然先生的這本新著,論定它的出版「正當其時」,不僅是因為本書對當下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問題,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對時代所提出的重大問題作出了自己的回應,表現了在當下中國學術界特別難能可貴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更因為本書是作者坐下來踏踏實實地研究的成果,其用功之力、思考之深,表明這是一個學者的回應,它的鮮明的觀點,是建立在學術研究基礎上的,讀者盡可以不完全同意研究的結論,但確實能夠從中得到許多啟示。
我尤其欣賞的,是作者採用的「個案研究」的方法,而且選擇「延安一代知識分子」作為研究對象,這是顯示了一種銳利的學術眼光的:延安一代人,如作者所說,是上承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下啟解放一代及紅衛兵一代的,因此拎起這一代,可以把握與揭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道路的全景。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延安這一代還在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現實,前文提到的黨內毛澤東派與黨內民主派的主要骨幹都是延安一代人,意味著延安一代在當代的分化。因此,以延安一代人作為個案進行研究,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能夠有助於人們認清當下這些爭論的歷史淵源及其深厚的歷史內容:這是一個極好的歷史與現實的結合點。
(二)
我更看重本書的,是作者的研究對當下爭論的啟示。
本書的最大特點是史料的詳實,這也是作者的自覺追求:「儘量還原史實,以據立論,重在對具體歷史情境的剖析」。這本來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但在當下的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界卻成了問題。這也是本書所揭示的歷史的積弊:「為實現自己頭腦中的紅色概念,無視具體現實,尤其無視革命造成的悲慘現實」;立場在先,觀念在先,判斷在先,而且不需要事實的支撐,甚至不顧及基本歷史事實,睜了眼睛說瞎話。比如說,一位毛澤東派的帶頭人宣稱「文革前三年天下大亂,後七年天下大治─億萬人民意氣風發,各行各業碩果累累,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層出不窮,新型革命秩序初步確立」─作者自可以為毛澤東時代辯護,但用這樣歪曲事實的作法來唱讚歌,就有些離譜。還有一位鼓吹「中國模式」的學者,則揚言「人類在解決收入貧困、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生態貧困四類貧困中沒有什麼太大成功的案例,只有中國在其特定的國情條件和體制下,才取得了初步的成功」─這樣的描述和判斷,與真實地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普通人的實際感受大相徑庭。這位學者盡可以採取支援中國現行「體制」的立場,但如此不顧事實,在我看來,無異於在幫倒忙。
這當然不是一個單純的學風問題,它其實正是這些年當局推行「強迫遺忘」的思想、文化政策的產物。而且不能低估這樣的遮蔽、否認歷史事實的「強迫遺忘」國策的有效性。比如說,今天一些青年已經不知道,進而不相信1959~1961 年中國曾經發生過大饑荒引發的大規模死人的事實─人們對死人的具體數字與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原因盡可以有不同的認定和分析,但討論的前提,是必須承認歷史上確實發生過大規模非正常死亡這一基本事實。如果把論斷建立在不承認基本事實的基礎上,那是無法討論問題的。理論與觀點的力量正在於,能面對所有的事實,並作出有說服力的解釋與分析。也就是說,揭示與面對所有的事實,這應該是我們討論中國革命時代和當下時代問題的前提與基礎。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得出結論:不管人們在認識上存在怎樣的分歧,但在這一基本方法論或基本討論規則上應該取得共識,不然是越爭論越糊塗的。
我讀本書,最為感佩的,就是作者敢於面對事實的膽識。本書所揭示的事實,在今天的某些年輕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而是可疑的;對歷史的當事人而言,這些事實又是不堪回首的,對年輕時候深受延安這一代人影響的作者來說,面對這些事實,也會引發痛苦的記憶;而應該對這段歷史負責的執政者,不僅不願正視這些事實,更因為對事實的揭示、分析與批判,會觸動他們的統治利益,而運用權力對揭示者進行打壓。這就意味著,作者要面對歷史事實,必須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不僅是體制的,權力掌握者的外在壓力,更來自研究對象,接受對象,以至作者自身的內心恐懼。這是需要勇氣、良知和學術與歷史責任感的。
真正面對全部事實也不容易,除了主觀有意無意的遮蔽外,也還有材料不足的困難,事實上歷史也不可能完全復原;由此決定了任何對已掌握的事實作出的判斷,都具有相對性,隨著新的史料不斷發現,就可能對已有結論作出補充修正,以至局部或全部否定。而要面對不利於自己分析的材料,並作出合理解釋,則更不容易。比如本書多次談到一些延安人至今也還局部或全面地堅持自己當年的選擇和觀念,作者沒有回避這樣的事實,但卻歸之於這些歷史當事人缺乏反省和覺悟,迷途而不知返的局限,這就有點簡單化,是應該作更複雜的分析的。其實這是反而有助於對問題的深入認識和討論的,作者錯過了這樣的機會,有點可惜。
我一直記著恩格斯的一句話:道德的義憤,代替不了科學的研究。學術研究不能局限在對歷史或肯定或否定的價值判斷上,而應該對所發生的一切,作出學理的追問和解釋,並從中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這樣才能做到「將歷史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這正是本書的著力點,在這方面是顯示了作者思考的深度和功力的,也同樣給今天的爭論以啟發。比如,延安這一代人的最大悲劇,是所謂「從這道門進入,卻走到了另一個房間」。
用作者的話來說,就是「尋找中失去了尋找的東西,在努力中失去了努力的價值」。本書特地引述了原毛澤東秘書李銳先生的反思:
「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從根本上就錯了。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徵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麼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和私有制,無論遭到多大誤解,無論怎樣被妖魔化,最終都會被人類認同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是不能消滅的,消滅了還得請回來。這是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留給後世的最根本的教訓。
這其實也是所有面對這段歷史的人們,包括研究者,都必須認真思考的。於是,就注意到這樣的現象:延安這一代所獻身的中國革命事業除了它的現實性以外,還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每一個命題在邏輯與歷史的起點上,都充滿純粹、崇高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烏托邦主義精神,而其邏輯的展開,歷史的實現的結果,卻顯示出專制主義的血腥味。如作者所說,「一切非理性的所謂『抒情詩』都有導向專制與恐怖的可能」。而且終點的專制主義並非對起點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烏托邦主義的反叛,而恰恰是其邏輯與歷史展開的必然結果。這也就是說,專制主義的後果正孕育於起點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烏托邦主義之中。
本書的探討,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對上述起點的追問,作者用大量的史實,銳利的分析,真實而具體地揭示了這些真誠的革命者,是在什麼地方、通過怎樣的思想、邏輯而落入陷阱的。例如,以建立「至善至美」的「地上天堂」為目標,將彼岸理想此岸化,必然導向現實地獄化的後果;追求思想的至善至美性,絕對真理性,必然導致馬克思主義的絕對化與宗教化,同時也使自身發生了異化,「以信仰代替思考」,放棄探索真理的權利,而成為「真理的執行者」、「專橫的啟蒙者」;追求至善至美的人性,鼓吹「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聖徒道德,強調對人性的「改造」,必然導致人的異化,成了「馴服工具」和「用響亮的口號包裝自私的目標」的「偽君子」;將「人民」理想化神聖化,製造民粹主義的「人民崇拜」,其現實落實,必然變成對自稱「人民代表」的黨和領袖的「組織崇拜」與「領袖崇拜」;將鬥爭、矛盾、反抗、運動絕對化,鼓吹「階級鬥爭」、「鬥爭哲學」,也必然誘發人的嗜殺性,導致災難性後果,同時也將自身變成「終身生活在鬥爭思維和仇恨之中」的「政治動物」,等等。這樣一些追根溯源的分析,都是以大量的事實為依據,是從事實出發的,但又不是對事實的簡單描述,是高於事實,更具有理論的高度與深度的,這樣的建立在科學理性的分析基礎上的批判,才是真正有力的,由此總結出的歷史經驗教訓,就具有了某種普遍的啟示意義,足以警戒後人。─這正是我們的研究、討論、爭論的目的所在。
本書自然也有可能引起爭論的方面。前文已經談到,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批判立場是十分鮮明的,在行文中就常常忍不住跳出來發表許多含有主觀感情的尖銳議論,這固然可以取得「振聾發聵」之效,但也很容易遭到批評。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就有學者批評本書「感情色彩強烈,太重褒貶,文學筆調,缺乏學術性」。儘管我也認為作者對自己的主觀情感如有所抑制,或許更好;但卻願意為作者作一點辯護。其實,本書的寫作,某種程度上,是「當代人寫當代史」,也就是說,作者所要研究的這段歷史,是和自己的生命攸關的,是直接影響了自己人生道路與命運的,有著太多的刻骨銘心的記憶和種種身歷其中者才有的生命體驗。因此,在研究與描述這段歷史時,就很難做到「純客觀」,有必要把自己的生命投擲其中。這樣的主體投入式的研究,或許有它的局限,但同時又獲得了完全根據文獻資料來進行客觀研究與冷靜描述的學術研究所不具有的特殊價值。它不僅對遠溢於文字、文獻之外的歷史情境有深切的把握,對文字、文獻內在的言外之意有精微的體驗,這都是僅憑文獻來把握歷史的後世研究者所難以達到的;而且它自身就構成一種價值,讀者讀到的不僅是研究對象的歷史,也包括研究者自身的歷史,連同它的局限也都是一種歷史現象,可以作歷史的解釋,可以折射出歷史的某一側面。
這一點,作者也是高度自覺的。他一再強調自己「紅衛兵一代,知青一代」的身份,強調:「紅衛兵無論價值理念,文化構成,思維方式,行為範式,都出自延安一代的母體」。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本書寫的是「紅衛兵一代眼裡的延安一代」,更準確地說,是一位幡然醒悟的紅衛兵對曾經是自己「精神之父」延安一代的反思和反叛,所展現的是處於精神糾纏中的兩代人的精神史。這大概是本書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所在。
它自有不可取代的特殊價值,但同時,也就有了對其進行再反思的餘地。比如說,作者對精神之父的反思與反叛的背後,是一種刻骨銘心的「弒父情結」;而這又恰恰是延安一代覺醒的起點。如作者所說,延安一代對於五四一代也同樣存有「弒父情結」,而且不止於弒父,幾乎對所有的老祖宗都持尖銳的批判、否定的態度。而如作者所分析,這樣的和前輩、傳統的徹底決裂的決絕態度,發展到極端,就成為延安一代人後來走向迷誤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角度看,對各代人都難免的弒父情結,包括延安一代的弒父,都要有同情的理解,因為不對前輩進行反思和反叛,就永遠被傳統所籠罩,無法走出自己的路,但同時更要看到將必要的反思反叛,推向極端,就會成為一個陷阱。因此,我讀完本書,就不免產生一個疑惑:難道延安一代除了慘烈的教訓,就沒有給後代人留下任何精神財富嗎?他們的精神價值,僅存在於他們晚年的反思、懺悔顯示的「真」嗎?他們早年的「真」,難道僅僅是一種需要反思的幼稚與天真?作者也承認,延安一代人的特點是:「正直天真、嫉私如仇、浪漫激越、憎恨自由、害怕個性、思維偏狹」。不可否認,這樣的精神氣質,是他們後來走向精神迷誤的內在原因,這裡確實包含了慘痛的歷史教訓;但它難道就沒有正面的價值和意義?在我看來,今天大陸理想喪失激情不再是非不明,整個社會彌漫著遊惰、虛假、世故、市儈之氣,延安一代人精神氣質在經過反思以後,是可以轉化為新的精神資源的。─這裡有兩條界限:一是不能不加反思,批判,也就是絕不能把那一代人和那個時代理想化,那就會重犯歷史的錯誤;二是又不能因為反思和批判而將其全盤否定,那我們就會犯「把孩子和髒水一起倒掉」的新的歷史錯誤。
(三)
本書的敘述,給我的一個強烈印象,是處處充滿了「大徹大悟,回頭是岸」的氣息。而這恰恰是我最為擔憂的。因為這恰恰是延安一代曾經落入的一個陷阱。本書引述了當年丁玲在批判王實味會議上的發言,其中心意思就是大談她的「大徹大悟,回頭是岸」。客觀地說,當年丁玲的「徹悟」:從個人主義皈依集體主義,從自由、民主的理想到皈依追求平等、正義的社會主義理想,從追求個性解放到皈依爭取工農解放的革命,是自有邏輯,有局部的合理性的,並非完全的盲從,而且在丁玲看來,她所皈依的是「真理」,因此,她說自己「回頭是岸」,是有相當的真誠性的,當然也不排斥有屈服於外在壓力的成分。對這兩方面都不可忽視,這正是顯示了歷史和人的思想的複雜性。丁玲的真正迷誤在於,她將自以為找到的「真理」絕對化,把「回頭」看到的那個「岸」(革命,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終極化,其結果就是本書所總結的:走到了當初追求的反面,從理想主義、烏托邦主義走向了專制主義。我們不能一面總結這樣的歷史教訓,一面又自覺、不自覺地以另一種形式,從另一個極端,重複歷史的錯誤。也就是說,前文所概括的本書對延安一代的精神迷誤的批判、經驗教訓的總結,不僅要警示世人,也應該警示作者自己。其實,作者對此也並非沒有警覺:他在本書的《跋》裡就談到了「自己也難以避免像空氣一樣進入體內的紅色思維,難以避免『以赤反赤』」,反思、批判者與被反思、批判者之間,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存在著思維方式的類似或相同,正是深刻地反映了我們在前面一再強調的兩代人之間「生命的糾纏」,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作者所要批判的「從理想主義到專制主義」的思維毒害與危害之深重,並且反映了這段革命歷史的複雜性與豐富性。
本書作者曾引述了一位著名學者的一個觀點:應該在「保守」與「激進」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在我看來,這一命題具有普遍意義。我們應該在一切方面─民主、自由與平等之間,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都保持一定的張力。當然,就個人的具體選擇而言,總是有「偏至」的,所以魯迅有《文化偏至論》之說。也就是說,在現實政治思想文化的選擇中,有的人偏向於民主、自由,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有的偏向社會平等,集體主義,社會主義,這都是正常的。問題是,一不能把自己的選擇絕對化,終極化,二不能把不同於己的選擇妖魔化,而且還要善於從中吸取合理的資源。做到後者就自會有一種博大、寬容的胸襟,這是保證自身思想的健全發展和民族與世界文化的多元化的一個前提;做到前者,就會和自己信奉的思想、社會制度之間,保持一個距離,形成一種張力,這是保證自身思想、學術和精神上的獨立性、批判性與創造性的前提,而在我看來,這樣的獨立性、批判性和創造性,是一切真正的知識分子的生命之根本。在這方面,魯迅對民主、科學、自由、平等等工業文明的基本價值觀所採取的「既堅持又質疑」的態度,有極大的啟示意義。
寫到這裡,我突然想起了捷克著名改革家、思想家、前總統哈威爾的一個警告。我們知道,哈威爾也有過從理想主義的共產黨人到批判自己參與建構的體制、推動民主改革的經歷,和本書所討論的老延安人的思想發展有類似之處。他在談到自己這一代的「歷史經驗」時,就提醒說,時刻不要忘記我們曾被「一種透明的烏托邦所捕獲」,因此,我們必須「懷疑所有的烏托邦」,懷疑所有「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產物」,要永遠保持「對任何不能自審的東西的反感」和本能的警惕與抵制。應該說,缺乏這樣的懷疑和警惕,正是延安一代發生精神迷誤的重要原因,後來人應該永遠引以為戒。
當然,我對自己對本書的疑惑也有一個自我警戒:說不定我的疑惑正是本文一開始就提到的我在當前這場論爭中的「猶豫不決」,「不鮮明不堅定」,因而常「陷入尷尬」狀態的表現,因此,我的疑惑也只能「僅供參考」,說說而已。而我確實從本書中受到很大啟示和教益,包括引發的某些疑惑,也是能逼人深思的。我想,這或許也是作者對我們讀者的期待。
2010 年8 月14~18 日
引言
延安澀重,史頁難翻。延安一代演出結束,即將整體隱入歷史帷幕的皺褶之中。但曾經大紅大紫的「延安一頁」,還未徹底翻過去,赤色烏托邦雖然幻滅,意識形態強大的滯後性使延安理念還在彌漫播遷─控制現實、影響未來。
拙著以延安一代紅色士林為研究對象,以個體行跡為依據,以集體整合為旨歸,以微觀細節支撐宏觀概括,具體展示赤潮禍華過程中對延安一代的實際影響。拙著力求還原歷史過程中的整體性,化抽象為感性,匯個例證整體。這一研究方法,庶可避免此前史學研究之兩難─或過於宏觀、缺乏具體實證;或過於微觀,失之宏觀整合。
拙著旨在剖析延安一代悲劇的過程中,全面檢討赤潮禍華的各項致因:激烈動盪的時代背景、日寇入侵的歷史機緣、老舊孱弱的傳統文化、辨別赤說的致命時差、中共「鬧紅」的真實過程、拖垂至今的現實影響。同時,剖駁馬列謬說、刨挖赤學歪根,為史立說,為後立警。惟願宏力拙,一士之力耳。
資料來源上,除依託綜合史、思想史、政治史、社會史、黨派史等,儘量參照各種傳記─自傳、評傳、回憶錄,以個人具體感受辨析各種史料史評,力避紅色史著「以論帶史」之惡弊。儘量還原史實,以據立論,重在對具體歷史情境的剖析,以史實、資料、言行等客觀材料佐證各種歸納。如延安一代的學歷、知識結構、五四方向何以被逆轉、延安與反右與文革與當下的聯繫、馬列赤說何以被廣泛接受……因研討中共奉為神靈的意識形態,為避「惡攻」,也必須握有結實可靠的論據。
如果延安之航大方向正確,怎會一步步走向暴烈土改、恐怖鎮反、三反五反、「擴大」肅反、反右反右傾、「人禍」大饉、十年文革、六四坦克?大批中共元勳怎麼成了反革命?聲名赫赫的林總竟成「叛國林賊」?一場「最偉大最徹底」的革命,怎麼還是演成那麼熟悉的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變革還是一場昔日舊戲?
後人當然有權轉動今日陽光去照射昔日陰霾,用今天的人文標準檢剔昨日的斑斑汙點。社會進化與時代進步,精髓當然是人文評判標準的提高。「革命人民」今天多少有點覺醒了:歷史不能任由統治者按需解釋;用哪一種理念闡釋歷史等於選用哪一根規尺裁量今天,即選用哪一種價值標準安排未來,茲事體大呵!對中共歷史的闡釋與判認自然不能任憑中共自評自擺,對延安一代的評議也不能由延安人自裁自量。
延安一代紅色士林,時代特徵烈然鮮明,價值取向渾然整一。無法複製的一段歷史使他們裹帶上濃密的紅色資訊,身後倚托著百年國史,腳下也就埋有史家最感興趣的史料,成為共產革命的重要標本。
「東風」「西風」,誰的「主義」真,是騾是馬還不得看政經效績?取決為社會帶來什麼。如今,俄中東歐越柬等赤國東風落篷,「風向」大致已定。雖然馬列旗幟尚在大陸飄揚,誰都明白:紅旗打不久了。事實上,文革後中共改革轉向,第一站就必須摘除毛澤東思想,必須與馬列主義有所剝離。雖然至今仍閃左燈,經濟實體畢竟早已右拐,資本主義早已復辟,「西風」已經壓倒「東風」。大陸今天的「言」「行」不一(打左燈向右行),當然是特殊的歷史產物,「言」「行」終將合一。
延安一代與馬列主義相始終,一輩子高舉赤色大旗,由延安人自己去降旗,雖然只是少數「兩頭真」,其間史蘊已夠史家啜吸。僅僅這一大轉折,就值得後人循階上山,嚼延安橄欖,覽紅色風景。延安一代,風景獨異呵!研析延安一代,釐清這代赤士何以整體走歪走斜,等於解剖赤色時代的骨骼,刨挖赤潮根鬚。
太陽明天還會重新升起,中國已從極左深巷折返,二十世紀一路滴淌的鮮血都將在二十一世紀模糊褪色,但對於那些註定在黎明前走進歷史褶皺的數代紅色士林,卻是真正的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如果後人不從他們那兒提煉經驗教訓,不從他們巨大的價值背反中找到悲劇成因,不從他們的腳步中總結出「千萬不要忘記」,認清「奪權大於原則」的延安之痛,那才叫最大的悲劇─還會在原地再摔第二跤。
延安一代的悲劇也許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無法規避的「俄狄浦斯命運」,但存在並非必然合理,今人有權要求終止這一「必然」。擴大每一代人的選擇權,而非限制甚至褫奪後人的選擇權,乃是歷史發展的前提,也是人類必須持守的基本人文價值。否則,自由的內涵還剩下什麼?
延安一代演出結束了,大幕即將合閉,惟少數耄耋延安老者「人還在,心未死」,憑藉歷史形成的高度發揮餘熱,對當下仍有重大影響,個別重要人物(如李銳、萬里、杜潤生、杜導正)餘熱尚熾。京中流諺:「老年燃燒,青年取暖。」觀之前人、驗之當世、參之後人,研析延安一代似有歷史、現實與未來三重意義。
黑格爾(1770~1831):「密納發的貓頭鷹要等黃昏到來,才會起飛。」對某一大型社會現象的理性認識,須待其形成過程結束才會開始。延安一代,變數幾盡,「密納發的貓頭鷹」庶可起飛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