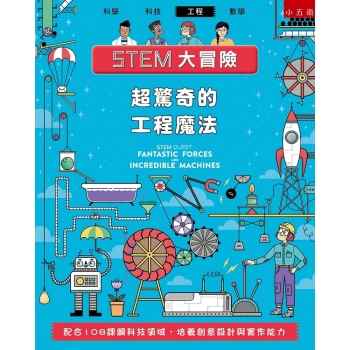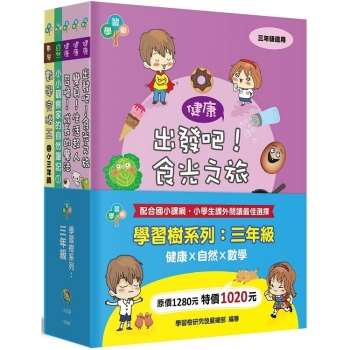烽火儷人
一切均在暗處流動
如一首風裡的情歌
張 錯 詩《浪遊者之歌》
一 傷兵
秋,似乎已在人飄起的衣角和幾片落葉的沙沙聲中。
他來到湖南的省府長沙,去找他的妻子和他失散的官兵。他曾在京滬的戰役中受了重傷、暈死在血泊裡,醒後幾不知人間歲月。現在總算已全癒,但左手仍需用白紗布吊著。他知道自己總會恢復健康,只是抗日戰爭已到了寸土必爭的時候。他知道妻已回老家、和她的母親住在湘江那邊的廟裡。他的基層部隊也多散居在這一帶;他要把他們聚集起來,繼續投入抗日戰爭,因為這是中華民族存亡的關頭。
他曾來過這古城,也許因天有些涼瑟,也許因兵馬的苦戰和失散,使他感到有些孤獨。下了火車,看到火車站對面被炸過的頹垣破瓦,他當然不知道,那是日本飛機曾來轟炸長沙火車站,沒有炸著,卻炸到了在對面旅館結婚的新娘新郎和賓客。那時長沙尚未有放警報的完整設備,敵機來了也不知道。這三千多年的古城,第一次遭受飛機的轟炸,如此突兀,留下時代的錯愕與驚惶。
他轉彎走到一麻石街上,見一小店鋪開著。他想問問店裡的人,到河邊去嶽麓山還有多遠。他右手提著一只小箱子。小店裡,高高的櫃台後面坐著一位老闆娘,正兇狠地對幾個募捐的女童子軍罵:「天天來捐錢捐鐵,都捐光了,沒有了,快走開去。」說罷,便用力地拍著櫃台,又揮手;抬頭見他進來,便有些畏懼地低下頭。那四、五個女童軍,仍不死心地在說愛國的道理。另一沒穿女童軍服、穿黑色校服的小女孩,正雙手平伸,走鋼索似地在店門檻上走著。當他跨進門時,那小女孩抬頭看著他並喊道:「姐姐,傷兵老爺來了。」
那時,從前線退到長沙的傷兵很多,醫院設備不夠容納,很多傷兵被忽視。那些尚可走動的,便拿起醫院外正要蓋房子的鐵條作手杖,動輒打人、扎東西,人見人怕。但他們到底是要為國捐軀的人,大家便只好尊稱他們為傷兵老爺了。
他看了看這女孩,十分端莊秀麗,便笑道:「怎麼又是傷兵老爺了哩?」小女孩低下頭去,從門檻上跳了下來。那幾個女童軍也掉過頭來看他,便你推我、我推你細聲商量,是否應為這和氣的傷兵唱慰勞歌,如電影《桃李劫》中唱的:「你們正為著我們老百姓……」 。還在羞澀猶豫,聽那傷兵問老闆娘離河邊還有多遠,老闆娘尚未答覆,幾個女童軍便搶著回說:「不遠了。」但也有說還是要走很遠的。那為首的,就是剛被那小女孩稱呼姐姐的說:「還是要走很久的。傷兵伯伯,你還是叫部人力車去吧,何況你又受了傷。」他向那建議的女童軍點頭說了聲謝謝,並問老闆娘:「這些女孩子問妳要什麼?」老闆娘氣呼呼地叨唸:「學生不去讀書,一群群天天來募捐、募鐵。做點小生意打發他們還不夠,叫化子一樣,又纏人。」他連忙從口袋中掏出幾枚銅板,放在櫃台上說:「你就把這捐給她們吧,她們也是因為愛國。」老闆娘心不甘情不願地,把錢推向櫃台邊。那為首的,踮著腳把錢撥過來,放入另一女孩手提的一只布口袋裡,並急著要同學們向他行童軍禮。他覺得這群女孩真可愛,便用右手向他們做敬禮狀的揮一揮手。
他走過三、四家店鋪,見到一照相鋪。那照相鋪的玻璃櫃台內,只放了一張幾乎占滿整個玻璃櫃的兩個女孩的放大照片,還填了彩色;他覺得好面熟。他掉頭去看那群女童軍;她們正移去下一家店鋪,那小的一個沒去店裡,卻站在街邊的梧桐樹下。「對了,就是她和她的姐姐。這小女孩怎麼有些像照片上的宛容皇后?」
但他覺得自己把這樣小的女孩做這種比較,是很可笑的,又忍不住掉轉頭去看那女孩,那女孩在看著一片凋黃了的梧桐葉飄落、緩緩輕輕地飄向街心。 有部人力車正停在路邊,車夫問他要不要坐車,他便上車去了。
二 風雲
一九四九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動盪的一年。小孩的命運被決定,中年人的理念混亂、無所適從,老年人在觀望,卻不抱希望,只有年輕人理直氣壯地四處亂跑。
蕭湘和珍,幾乎是同時到台灣的,他們打算在台灣繼續完成大學學業。蕭湘在中學便和珍同學,不過蕭湘才讀初中,珍已是高中生了。一九四九年早春,南京的國民政府似已開始崩潰,學校也都草草結束了那一學期,大逃亡開始了。
蕭湘和姐姐離開南京的女子大學,一同到廣州的中山大學借讀。在那兒竟遇到正在讀三年級的珍。反正是亂世,年齡和班級是不能劃清界線的。又因為珍的緣故,認識了珍的同班同系男同學張兆。
蕭湘是春季入大學的學生,本應讀三年一級,但此時是下半年,學校要她先讀三年二級,九月開學時再讀三年一級。蕭湘因此笑了好些日子――真是亂世啊,書都可倒著讀,尤其讀歷史系的,先讀朝代的衰亡,再看那朝代的革命興起,也許會很乏味吧,但仍是感謝學校對借讀生的變通。這時又發現從南京來借讀的學生竟有十幾位,大家頗有他鄉遇故知的親切,無意間也成了一個小團體,所以當時蕭湘並不和珍走在一起,而現在卻在台灣相遇,又都寄居在軍屬的親戚家,家鄉都已無音訊,兩人便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悲情,便常找機會見面,有關借讀的事,兩人更要交換消息,知道離開學之日尚早。
一日,兩人又約去逛街,坐在三輪車上,只說要去熱鬧的地方。那車夫知道這兩位外省小姐只是「迪拖」而己,便慢慢地踏車。那時台北並不擁擠,街兩旁有很齊整的棕櫚樹,大大的樹葉在南風中有韻有緻的輕搧,藍色的天上白雲悠悠舒捲,蕭湘正自覺有趣,珍卻大聲叫停,車夫果真停了。
蕭湘看這兒並無店鋪,便問:「為什麼在這兒停?」
「我們去看看張兆。」珍說。
「我和他並不很熟。」她說。
「哎唷,你不知道嗎?他住在一位很有名的大將軍家。」珍還用手指著路旁一大房子。
「那又怎樣!怎可這樣俗不堪耐。」
「那房子好大,我們去看看那大房子也好玩嘛。來台灣後,住在嬸嬸家,那日本房子嘴巴碰牙齒的,煩死人了。」
「我不要去看人家的大房子。」蕭湘仍很堅持。
「去看看嘛,這將軍是很有名的。」珍還把名字報了出來,以為蕭湘會有興趣。
「不曾聽見過呀。他有沒有兒子?」蕭湘板著臉問,仍不下車來。
「沒有,沒有,一個也沒有。」
「那就去吧。」蕭湘像鬆了一口氣似的下了車。珍有些奇怪了,原以為若有兒子,她才會下車,但她不撒謊說沒兒子,倒大大方方下車了。
珍急忙把車錢付了,怕蕭湘變掛,而後問道:「為什麼要沒有兒子才去看看?」
「我很煩那些公子哥兒。」蕭湘笑了。珍也大笑起來。
張兆的母親年輕守寡,一心一意養大張兆,因為信佛,無意中在廟中結識了一位將軍夫人,而且結拜為姐妹,也就是現在他母子二人寄居的主人家。
張兆的母親很慈祥,看到她倆以為是兒子的女朋友來了,便格外熱絡。這樣的熱鬧……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烽火儷人:六篇亂世兒女的真情故事的圖書 |
 |
$ 332 ~ 378 | 烽火儷人: 六篇亂世兒女的真情故事
作者:黃美之 出版社: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11-10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烽火儷人:六篇亂世兒女的真情故事
〈烽火儷人〉一篇,作者敘述自己一段難忘的感情,與孫立人將軍在大時代的感情,雖然礙於世俗眼光,情遷此時才公開,作者卻是下定很大的決心,才動筆留下這一段亂世的美麗回憶。深具歷史性與深情的代表作,值得一起走入大時代的背景之中,慢慢品味。
〈流轉〉一篇是作者描寫一九四九年代,一群無憂的大學生的悲歡離合,因戰火的延漫,他們其中有三分之二移來了台灣的故事。作者因一時想著王維的詩,而寫了這故事,寫的雖是兒女私情,但都是温釀在那一個天翻地覆的大時代裡。
〈糖水與同情〉及〈心中的仙人掌〉描述的是兩位資深情報員的經歷,是作者在桃園感訓所親耳聽聞的情報員親身故事。
〈回家〉一篇是作者與家人之間談起了民國十九年躲紅軍的事情,用較輕鬆的寫法,寫出了當時的變遷和中國人當時勇敢流著血、低著汗,所創造出來的新局面。
〈月白刀傳奇〉一篇作者描寫了過去二十個世紀,中國內憂外患不斷,但中華民族的人民卻擁有強大的韌性,堅忍不拔、自省自新的精神,進而擁有現在美麗的國家。作者希望大家也和她一樣,對於身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感到驕傲。
作者簡介:
黃美之
湖南人,南京金陵女大歷史系肆業,一九四九年來台灣升學,開學前去軍中工作,後因孫立人將軍之政治困境,一九五O年被幽禁十年,一九六O年獲釋放。婚後長居海外,開始從事寫作。作品有《八千里路雲和月》遊記、《傷痕》、《不與紅塵結怨》、《歡喜》及《深情》等散文集。並用政府二OO一年給她的冤獄補賞金組德維文學會,以助海外華文文學活動。
章節試閱
烽火儷人
一切均在暗處流動
如一首風裡的情歌
張 錯 詩《浪遊者之歌》
一 傷兵
秋,似乎已在人飄起的衣角和幾片落葉的沙沙聲中。
他來到湖南的省府長沙,去找他的妻子和他失散的官兵。他曾在京滬的戰役中受了重傷、暈死在血泊裡,醒後幾不知人間歲月。現在總算已全癒,但左手仍需用白紗布吊著。他知道自己總會恢復健康,只是抗日戰爭已到了寸土必爭的時候。他知道妻已回老家、和她的母親住在湘江那邊的廟裡。他的基層部隊也多散居在這一帶;他要把他們聚集起來,繼續投入抗日戰爭,因為這是中華民族存亡的關頭。
他曾來過這古城,也許...
一切均在暗處流動
如一首風裡的情歌
張 錯 詩《浪遊者之歌》
一 傷兵
秋,似乎已在人飄起的衣角和幾片落葉的沙沙聲中。
他來到湖南的省府長沙,去找他的妻子和他失散的官兵。他曾在京滬的戰役中受了重傷、暈死在血泊裡,醒後幾不知人間歲月。現在總算已全癒,但左手仍需用白紗布吊著。他知道自己總會恢復健康,只是抗日戰爭已到了寸土必爭的時候。他知道妻已回老家、和她的母親住在湘江那邊的廟裡。他的基層部隊也多散居在這一帶;他要把他們聚集起來,繼續投入抗日戰爭,因為這是中華民族存亡的關頭。
他曾來過這古城,也許...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
自序
烽火儷人
1. 傷兵
2. 風雲
3. 朦朧
4. 等待
5. 茶會
6. 無題
7. 花淚
8. 馬革
9. 鷇緣
10. 芳草
11. 藏嬌
12. 海濱
13. 神在
14. 漣漪
15. 無猜
16. 冷暖
17. 驚喜
18. 定居
19. 繫舟
20. 木蘭
21. 女箋
22. 福兮
23. 無常
24. 雨淋
25. 如夢
26. 如煙
流轉
心中的仙人掌
糖水與同情
回家
月白刀傳奇
出版後記
自序
烽火儷人
1. 傷兵
2. 風雲
3. 朦朧
4. 等待
5. 茶會
6. 無題
7. 花淚
8. 馬革
9. 鷇緣
10. 芳草
11. 藏嬌
12. 海濱
13. 神在
14. 漣漪
15. 無猜
16. 冷暖
17. 驚喜
18. 定居
19. 繫舟
20. 木蘭
21. 女箋
22. 福兮
23. 無常
24. 雨淋
25. 如夢
26. 如煙
流轉
心中的仙人掌
糖水與同情
回家
月白刀傳奇
出版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