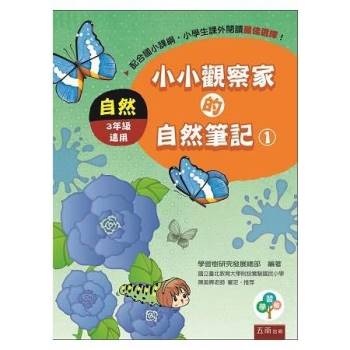不管時移事往
西門町在哪
青春就在哪
不可思議的作家陣容——
王偉忠、李立群、阮慶岳、范可欽、郎祖筠、倪重華、張國立、舒國治、溫慶珠、賴正哲、駱以軍、隱地、顏忠賢……(依姓名筆畫排列)
以時序為經緯,串起每個人青春的代表作。
跨世代跨界作家陣容,就為了一座不老之城。
王偉忠:「這樣的地方,就是好玩。」
李立群:「西門町,一個即使被淡忘,也終究會回來的浪漫地區。」
阮慶岳:「全臺灣再找不到一個像西門町這樣對各社群皆具有強烈包容力的地方。」
范可欽:「西門町就是我的沈佳宜。」
郎祖筠:「西門町是一充滿多彩霓虹燈、隨時都在改變的黑洞。」
倪重華:「我們那個時代的西門町啊,是很有氛圍的……」
張國立:「過去的西門町對我們而言,是根、是靈魂。」
舒國治:「西門町是個藏著美好回憶的地方。」
溫慶珠:「關於西門町的記憶,是我一輩子最感珍貴的時光。」
賴正哲:「西門町是個很可愛、有趣、三八的小女孩。」
駱以軍:「西門町是一個彩色瑣碎的微宇宙所創造出的繁華夢境。」
隱地:「我老了,西門町仍年輕。」
顏忠賢:「西門町好像年輕人亦正亦邪的幻覺。」
每一次的毀敗,都以最快、最炫目的形式重生——
這是專屬於西門町的特技魔術。
作者簡介
蘇承修(企劃統籌)
知名室內設計師,複合式餐飲經營人。代表作包含被譽為台灣夜店指標的Roxy,以及現代啟示錄、上海茶館、喜瑞飯店、舞衣新宿、HOME HOTEL……等三十多處流行娛樂空間。作品具強烈個人風格,並結合商業和藝術理念。
二○一一年於西門町開設Inhouse Hotel,有感於其領引庶民時尚及各類表演藝術的代表性地位,遂企劃此書,邀請各界知名創作人談論、書寫西門町。
相對於西門町的人文底氣、歷史意義,此書哪怕只是聊備一格地留下紀錄,仍可視為台北文化發跡、興盛的重要里程。
Inhouse Hotel粉絲團:www.facebook.com/inhousehotel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