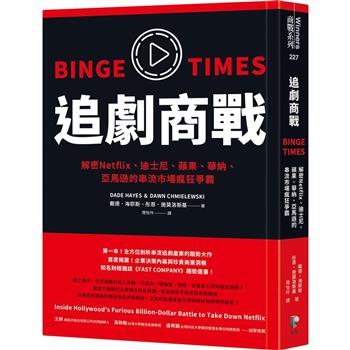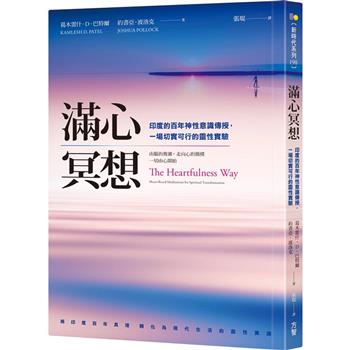《牆上的將軍》是一部由陳鉞撰寫的短篇小說集,共包含22個獨立的故事。這部小說集以冷靜而克制的筆觸,深入描繪了當代中國大城市中產階級小人物的生活,並以諷刺的方式呈現。
作者在寫作手法上進行了一些較激的嘗試,特別體現在被稱為〈無標題作品〉的章節中,作者展現出了在小說形式和技法上尋求突破的決心。這種嘗試使得故事更具有新穎感和視覺效果,讓讀者對故事內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感受。
在《牆上的將軍》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各種各樣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場景。從童話般的故事開始,到現代社會中的人情世故,每個故事都有其獨特的魅力和啟發。特別是在《童話一則》這個故事中,作者以輕鬆幽默的筆法,將公主和寶貝兒的愛情故事哲理重新演繹,讓人不禁捧腹大笑。
此外,作者對於現代社會中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進行了深刻的探討,通過小說中的人物和情節,反映出了人性的複雜性和社會的現實。每個故事都給人以思考,引發讀者對於生活中種種問題的反思。
另,《牆上的將軍》也是一部充滿智慧和幽默感的作品,作者以獨特的視角和敏銳的筆觸,描繪出了當代中國社會中各種人物的生活和命運。這部小說集不僅給人以娛樂,更讓讀者在閱讀中獲得了對於生活和人性的深刻思考。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牆上的將軍:短篇小說集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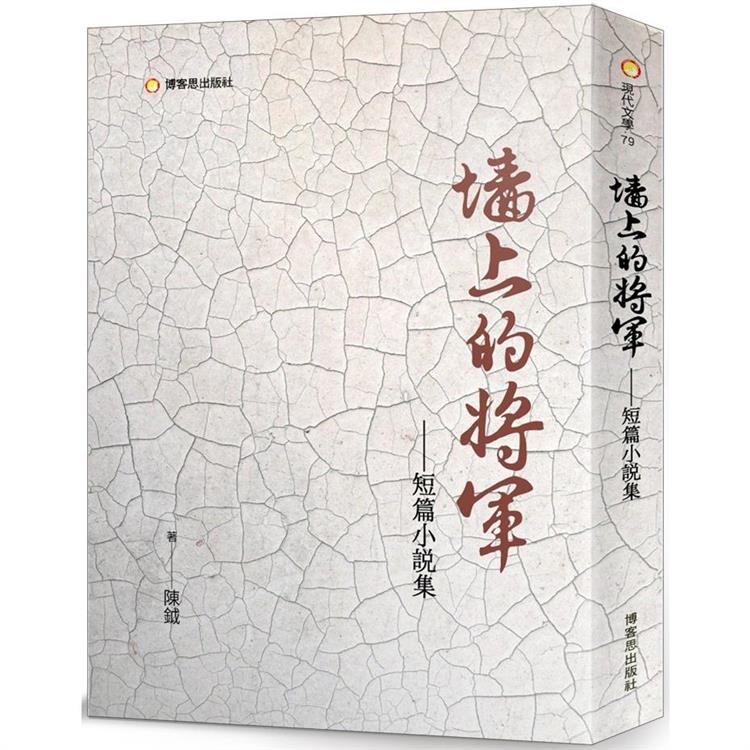 |
$ 237 ~ 270 | 牆上的將軍【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陳鉞 出版社:博客思-蘭臺 出版日期:2024-04-12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牆上的將軍:短篇小說集
內容簡介
目錄
童話一則 6
未解之謎 11
樂隊指揮37
蛇 47
無標題作品 62
二十年後 66
無標題作品 83
雲 89
無標題作品 105
一樁謀殺 113
無標題作品 132
孤獨的旅程 141
第三十八周 186
相親 192
做功課 204
俄爾浦斯在北京 213
Watchman and man watch what 227
黑美人 232
墻上的將軍 248
獨身者 253
香港之戀 296
諾亞 310
未解之謎 11
樂隊指揮37
蛇 47
無標題作品 62
二十年後 66
無標題作品 83
雲 89
無標題作品 105
一樁謀殺 113
無標題作品 132
孤獨的旅程 141
第三十八周 186
相親 192
做功課 204
俄爾浦斯在北京 213
Watchman and man watch what 227
黑美人 232
墻上的將軍 248
獨身者 253
香港之戀 296
諾亞 310
序
序
童話一則
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時人們的願望往往能夠變成現實——城外的一處地方生活著一對老夫妻,他們的兒子名叫寶貝兒。寶貝兒出生的時候,國王的星象家正巧路過,他聽到了嬰兒的哭聲便預言說:「這是一個了不得的孩子,他將來會和公主結婚。」鄰居們聽了他的話都向夫妻倆道喜。
星象家回到城裡,把這件事稟報了國王。國王生氣地說:「我的女兒只能嫁給高貴的人,我絕不把嫁妝送給窮鬼!」他命令把公主送到了遙遠的海島上,關進城堡並且由一個巨人負責看守。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寶貝長成了大人。他想結婚了,於是就對老父親說:「親愛的爹,我要成家。既然我註定要和公主結婚,那我現在就去找她。」
「可是我的兒,公主被關在海島上,你需要翻過七座高山,趟過七條大河,穿過七片森林,還要在汪洋大海上航行七個晝夜才能到達那裡。她身旁有一個兇殘的巨人做看守。我的兒,你會送命的。」
寶貝兒滿不在乎地回答:
「那又怎麼樣,如果我命中註定要和公主結婚,就沒有什麼能阻擋我。」
「可是,我們都老了,恐怕等不到你回來。」
「放心吧爹,我早去早回,明天天一亮我就出發。」
第二天,寶貝兒上路了。老夫妻把他送到了門口,老頭連連歎息,老奶奶止不住地流淚。他們說:「我們恐怕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兒子了。」寶貝兒向他倆揮揮手,就上路了。
他翻過了七座險峻的高山,趟過了七條湍急的大河,穿過了七片陰暗的森林,又在汪洋大海上航行了七個晝夜,終於來到了一個小島。寶貝兒上了岸,想辦法溜進了囚禁公主的城堡,公主正坐在窗口歎氣呢。
寶貝兒走上前去大聲說道:「美麗的殿下,我是你命中註定的丈夫,請接受我的求婚吧。」
公主吃了一驚,等問明原委,她便笑著說:「哦,你看我說的對不對,你的名字叫寶貝兒,家住在郊區,父母都是種地的。你既沒有爵位也沒有產業,唯一的優點就是消化好。」
「正是如此!」
「那你來幹什麼?」她問。
「我來向你求婚,問你願不願意做我的妻子?」
公主想了想,說道:「沒問題,我願意!」
寶貝高興壞了,他說:「那親愛的未婚妻,請你馬上去收拾行李,咱們還有好多的路要走,一刻也耽擱不得。」
聽了這話,公主不高興了:「怎麼,要我走路。你連汽車都沒有?那以後我想進城看望我的父王可怎麼辦?難道要讓石子磨破我的腳趾不成。不行,我不能嫁給你!」
正在這時,巨人回來了,公主趕緊把寶貝兒藏在了門後面。
巨人一進屋就嚷道:「這裡有生人的氣味,誰來過了!」
「誰也沒來過,」公主說:「是你的鼻子發炎了,熱敷一下就好。」說著用一條熱毛巾堵住了他的鼻子。
寶貝兒趁機逃了出來。他回到家,見到了爹娘。老夫妻又驚又喜,連忙問道:「怎麼樣孩子,公主答應嫁給你了麼?」
「沒答應,不過就差一點。她說如果沒有汽車就不跟我回家。」
夫妻倆互相看了看,說道:「讓我們想想辦法吧。」
於是,他們賣掉了房子和牲口,給寶貝兒買了一輛汽車。
第二天,寶貝兒又上路了。老夫妻把他送到門口,老頭皺著眉頭歎氣,老奶奶用衣角抹淚。他們心想:「我們的兒子恐怕不會回來了。」
寶貝向他們揮揮手,開著車一溜煙地跑了。他翻過了七座高山,越過了七條大河,穿過了七片森林,又在大海上航行了七個晝夜,終於來到了囚禁公主的小島。寶貝像上次一樣進入了城堡。這時公主正坐在窗邊打哈欠呢。
寶貝兒走上前大聲說道:「美麗的殿下,我是你命中註定的丈夫,請接受我的求婚吧。」
公主認出了他,說道:「哦,原來是你,你的名字叫寶貝兒,家住在郊區,父母都是種地的。你既沒有爵位也沒有產業,唯一的優點就是消化好。對麼?」
「正是如此。」
「你來幹什麼?」
「我來向你求婚,問你願不願意做我的妻子,和我一起開車回家去。」
「我當然願意!」公主說
「太好了!咱們馬上就出發,我的爹娘正在家裡等著咱們呢。」
可是公主又不高興了:「怎麼,你居然沒有自己的房子?那日後我高貴的朋友來拜訪咱們可怎麼辦,多不方便。不行,我不能嫁給你!」
寶貝兒剛想解釋,想不到巨人回來了,公主連忙把他藏在了衣櫥裡。
巨人進了門,皺著鼻子聞了聞,說道:「這裡怎麼有人的氣味,是誰來過了?」
「誰也沒有來,是你的鼻炎又犯了,得熱敷。」
趁著混亂,寶貝趕快逃了出來。他回家見到了爹娘。
「怎麼樣孩子,公主答應嫁給你了吧?」他們問。
寶貝兒懊惱地答道:「就差了一點,她不願意跟我回來,因為我沒有自己的房子。」
「那讓我們去想辦法吧。」
夫妻倆投靠了一家財主,拿典身錢給寶貝兒蓋了新房。房子蓋成他們就病了。這一天寶貝兒來到病床前向父母告別。老頭搖著腦袋歎氣,老奶奶默默地流淚,他們覺得自己的兒子肯定回不來了。
寶貝兒揮了揮手,上路了。他翻過了七座大山,跨過了七條大河,穿過了七片森林,又在海上航行了七個晝夜,再一次來到了囚禁公主的小島。當他走進城堡的時候,公主正在窗邊挖鼻孔呢。
寶貝兒上前大聲說道:「美麗的殿下,我是你命中註定的丈夫,請接受我的求婚吧。」
「你又來了,」公主說:「我還沒有忘記你呢,你的名字叫寶貝兒,家住在郊區,父母都是種地的。你既沒有爵位也沒有產業,唯一的優點就是能吃能喝。對不對?」
「正是如此。」
「那麼,你來幹啥?」
寶貝兒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我來向你求婚,問你願不願意做我的妻子,和我一起開車回我自己的家︙︙」
話還沒說完,公主就跳起來叫道:「我願意!願意得不能再願意了!」
於是,他們擁抱,接吻,像小麻雀一樣又蹦又跳。
正在這時,巨人回來了。公主急忙把寶貝藏在了床底下。
巨人在房間裡轉了一圈,疑惑地說:「我聞見了一股味道,不知是從哪兒發出來的。沒准是我的鼻子壞了吧?」
「恰恰相反,這說明你的鼻炎已經好了,祝賀你!」公主說。
當天晚上,寶貝兒和公主一起逃出了小島。當他們回到家的時候,發現爹媽已經死掉了。
寶貝兒這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漂泊得太久了。於是他發誓在有生之年絕不再離開家鄉和親人。公主對他的誓言感到滿意。
從此以後,他們就在一起過著幸福的生活,如果沒有死的話,到今天還仍舊活著呢!
童話一則
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時人們的願望往往能夠變成現實——城外的一處地方生活著一對老夫妻,他們的兒子名叫寶貝兒。寶貝兒出生的時候,國王的星象家正巧路過,他聽到了嬰兒的哭聲便預言說:「這是一個了不得的孩子,他將來會和公主結婚。」鄰居們聽了他的話都向夫妻倆道喜。
星象家回到城裡,把這件事稟報了國王。國王生氣地說:「我的女兒只能嫁給高貴的人,我絕不把嫁妝送給窮鬼!」他命令把公主送到了遙遠的海島上,關進城堡並且由一個巨人負責看守。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寶貝長成了大人。他想結婚了,於是就對老父親說:「親愛的爹,我要成家。既然我註定要和公主結婚,那我現在就去找她。」
「可是我的兒,公主被關在海島上,你需要翻過七座高山,趟過七條大河,穿過七片森林,還要在汪洋大海上航行七個晝夜才能到達那裡。她身旁有一個兇殘的巨人做看守。我的兒,你會送命的。」
寶貝兒滿不在乎地回答:
「那又怎麼樣,如果我命中註定要和公主結婚,就沒有什麼能阻擋我。」
「可是,我們都老了,恐怕等不到你回來。」
「放心吧爹,我早去早回,明天天一亮我就出發。」
第二天,寶貝兒上路了。老夫妻把他送到了門口,老頭連連歎息,老奶奶止不住地流淚。他們說:「我們恐怕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兒子了。」寶貝兒向他倆揮揮手,就上路了。
他翻過了七座險峻的高山,趟過了七條湍急的大河,穿過了七片陰暗的森林,又在汪洋大海上航行了七個晝夜,終於來到了一個小島。寶貝兒上了岸,想辦法溜進了囚禁公主的城堡,公主正坐在窗口歎氣呢。
寶貝兒走上前去大聲說道:「美麗的殿下,我是你命中註定的丈夫,請接受我的求婚吧。」
公主吃了一驚,等問明原委,她便笑著說:「哦,你看我說的對不對,你的名字叫寶貝兒,家住在郊區,父母都是種地的。你既沒有爵位也沒有產業,唯一的優點就是消化好。」
「正是如此!」
「那你來幹什麼?」她問。
「我來向你求婚,問你願不願意做我的妻子?」
公主想了想,說道:「沒問題,我願意!」
寶貝高興壞了,他說:「那親愛的未婚妻,請你馬上去收拾行李,咱們還有好多的路要走,一刻也耽擱不得。」
聽了這話,公主不高興了:「怎麼,要我走路。你連汽車都沒有?那以後我想進城看望我的父王可怎麼辦?難道要讓石子磨破我的腳趾不成。不行,我不能嫁給你!」
正在這時,巨人回來了,公主趕緊把寶貝兒藏在了門後面。
巨人一進屋就嚷道:「這裡有生人的氣味,誰來過了!」
「誰也沒來過,」公主說:「是你的鼻子發炎了,熱敷一下就好。」說著用一條熱毛巾堵住了他的鼻子。
寶貝兒趁機逃了出來。他回到家,見到了爹娘。老夫妻又驚又喜,連忙問道:「怎麼樣孩子,公主答應嫁給你了麼?」
「沒答應,不過就差一點。她說如果沒有汽車就不跟我回家。」
夫妻倆互相看了看,說道:「讓我們想想辦法吧。」
於是,他們賣掉了房子和牲口,給寶貝兒買了一輛汽車。
第二天,寶貝兒又上路了。老夫妻把他送到門口,老頭皺著眉頭歎氣,老奶奶用衣角抹淚。他們心想:「我們的兒子恐怕不會回來了。」
寶貝向他們揮揮手,開著車一溜煙地跑了。他翻過了七座高山,越過了七條大河,穿過了七片森林,又在大海上航行了七個晝夜,終於來到了囚禁公主的小島。寶貝像上次一樣進入了城堡。這時公主正坐在窗邊打哈欠呢。
寶貝兒走上前大聲說道:「美麗的殿下,我是你命中註定的丈夫,請接受我的求婚吧。」
公主認出了他,說道:「哦,原來是你,你的名字叫寶貝兒,家住在郊區,父母都是種地的。你既沒有爵位也沒有產業,唯一的優點就是消化好。對麼?」
「正是如此。」
「你來幹什麼?」
「我來向你求婚,問你願不願意做我的妻子,和我一起開車回家去。」
「我當然願意!」公主說
「太好了!咱們馬上就出發,我的爹娘正在家裡等著咱們呢。」
可是公主又不高興了:「怎麼,你居然沒有自己的房子?那日後我高貴的朋友來拜訪咱們可怎麼辦,多不方便。不行,我不能嫁給你!」
寶貝兒剛想解釋,想不到巨人回來了,公主連忙把他藏在了衣櫥裡。
巨人進了門,皺著鼻子聞了聞,說道:「這裡怎麼有人的氣味,是誰來過了?」
「誰也沒有來,是你的鼻炎又犯了,得熱敷。」
趁著混亂,寶貝趕快逃了出來。他回家見到了爹娘。
「怎麼樣孩子,公主答應嫁給你了吧?」他們問。
寶貝兒懊惱地答道:「就差了一點,她不願意跟我回來,因為我沒有自己的房子。」
「那讓我們去想辦法吧。」
夫妻倆投靠了一家財主,拿典身錢給寶貝兒蓋了新房。房子蓋成他們就病了。這一天寶貝兒來到病床前向父母告別。老頭搖著腦袋歎氣,老奶奶默默地流淚,他們覺得自己的兒子肯定回不來了。
寶貝兒揮了揮手,上路了。他翻過了七座大山,跨過了七條大河,穿過了七片森林,又在海上航行了七個晝夜,再一次來到了囚禁公主的小島。當他走進城堡的時候,公主正在窗邊挖鼻孔呢。
寶貝兒上前大聲說道:「美麗的殿下,我是你命中註定的丈夫,請接受我的求婚吧。」
「你又來了,」公主說:「我還沒有忘記你呢,你的名字叫寶貝兒,家住在郊區,父母都是種地的。你既沒有爵位也沒有產業,唯一的優點就是能吃能喝。對不對?」
「正是如此。」
「那麼,你來幹啥?」
寶貝兒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我來向你求婚,問你願不願意做我的妻子,和我一起開車回我自己的家︙︙」
話還沒說完,公主就跳起來叫道:「我願意!願意得不能再願意了!」
於是,他們擁抱,接吻,像小麻雀一樣又蹦又跳。
正在這時,巨人回來了。公主急忙把寶貝藏在了床底下。
巨人在房間裡轉了一圈,疑惑地說:「我聞見了一股味道,不知是從哪兒發出來的。沒准是我的鼻子壞了吧?」
「恰恰相反,這說明你的鼻炎已經好了,祝賀你!」公主說。
當天晚上,寶貝兒和公主一起逃出了小島。當他們回到家的時候,發現爹媽已經死掉了。
寶貝兒這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漂泊得太久了。於是他發誓在有生之年絕不再離開家鄉和親人。公主對他的誓言感到滿意。
從此以後,他們就在一起過著幸福的生活,如果沒有死的話,到今天還仍舊活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