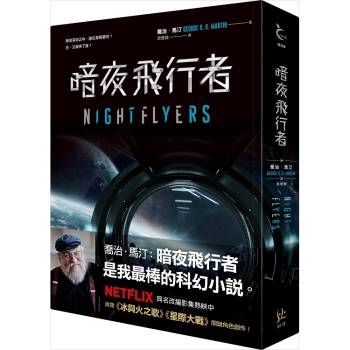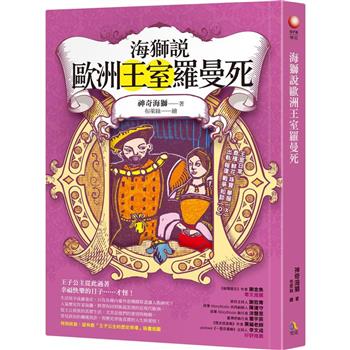序章
深夜,一場大雨降臨了。
遼闊的明石潭上,細密的漣漪圈圈盪出,湖魚潛到了深處,萬物的輪廓都變得朦朧起來。
潭邊的半山腰上,一間破破爛爛的小廟亮起了燈。
年近九旬的老廟公裹著厚外套,呼著霧氣走過長廊,從廁所裡拿了幾個塑膠盆,準備去那些逢雨必漏的地方擺一擺。
正忙碌著,突然,側殿那邊傳來一陣怪異的聲響。低低沉沉,忽隱忽現……
老廟公睏乏的腳步頓住。仔細一聽,居然像是有人在笑。
老廟公咕噥著:「啊……是……誰在笑啊?」遂拿著塑膠盆,循著聲音慢吞吞地走過去。
恰逢一道銀白閃電掠過,天地間大亮了一瞬,隆隆雷聲中,轉過廟廊的老廟公看見一個高大的男人。
雨瀑順著廟簷嘩啦而落,這男人就站在濺雨的石製洗手台前,似乎在洗手。
老廟公混濁的眼睛瞇了瞇。
深冬時節,這男人連外套都沒穿,只穿著一件濕透的黑色長袖帽T,寬大的帽子遮住了臉,濃重的陰影讓人看不清面容。後方,從廟窗透出來的暗紅光線照映在男人的背上,就好似照著一團裹著血色的黏膩鬼影般,在這陰冷的雨夜裡,顯得極度不祥。
男人根本沒注意到老廟公,自顧自地低著頭,將手遞在水龍頭下,不斷地搓洗。
洗著洗著,喉嚨裡又洩出詭譎的笑音,貌似心情非常好。
老廟公不明白為何有人會在大半夜的跑進來洗手,還洗得這麼高興。
不過老廟公還是想到了一個原因,和藹地說:「啊……是來……躲……雨的嗎?」
突如其來的嗓音讓男人猛頓了一下!
可這一頓之後,男人並沒有轉過來,而是低著頭,繼續用力地搓洗指甲縫。回答時,男人的聲音浸在大雨聲裡,聽起來格外飄忽。「不,我是特地冒雨過來的,這裡,嗯……」他突然興奮地笑了,笑得渾身顫抖。「這裡的月老很靈驗啊!雖然知道這個時間點廟已經關了,但我還是迫不及待地趕過來表示感謝。真的是,哈,真的是太靈驗了!」
老廟公聞言,也笑了,那張布滿皺紋的老臉被笑容擠出了恐怖的溝壑。蒼老又沙啞的嗓音和善地道:「哦,看來……得……了好姻緣呢?」
濃深的陰影裡,男人拿起擱在水槽裡的空瓶,撕掉柳橙汁標籤,仔仔細細地沖了沖。
「是啊,很棒的姻緣……」
男人回味似的搓了搓指尖,滿足喟嘆。
「棒極了。」
第一章 見鬼的贖命戀愛
暴雨嘩啦啦地敲擊著小小的氣窗。
一間狹小老舊的浴室裡,陸子涼睜開了眼睛。
四周黑漆漆的,只有一點微弱的街燈從氣窗透進來,他倒臥在冰冷的地板上,眼神有一瞬茫然。
身上很冷,而且說不出來的不舒服,陸子涼撐著地板坐起來,一時間想不起自己在什麼地方,只覺得腦子昏昏沉沉,胸腔內彷彿堆積了某種強烈的恐怖感,至今都還在發酵著。
陸子涼按住心口,修長的眉毛輕輕蹙著。
「好難受,是宿醉嗎……奇怪,我原本在幹什麼?這裡是……嘖,燈在哪裡?」
手腳有些使不上力,陸子涼瞇起眼,在黑暗中胡亂地摸,終於摸到了一旁的浴缸。他剛想扶著站起來,手一滑,猝不及防摸到一手潮濕的頭髮!
「──!」
他嚇了一大跳,猛地抽手摔回了地面,就著隱約的光芒看見浴缸邊上竟倚著一顆腦袋,髮頂濕漉漉的,滴著水珠。
浴缸裡面有人。
陸子涼嚇得腦子都清醒了一層。「靠!嚇死,泡澡不開燈的啊!」
浴缸裡的人沒回應。
「喂,燈在哪?這是你家嗎?」
陸子涼攥起僅剩的力氣,搖搖晃晃地從地上爬起來。
他感到莫名虛弱,眉毛一直輕輕蹙著,彷彿連游了好幾十公里的長泳似的,體力透支到離譜的程度。可作為一名專業的運動員,調節體力早已是刻在本能裡的東西,若非必要,他幾乎不會把自己搞得這樣虛脫,何況這裡也不是泳池,而是一間陌生的黑暗浴室。
陸子涼簡直匪夷所思。
難道他喝掛了,跟著陌生人嗨到家裡了?
這種事情確實久久會發生一次。
在浴缸裡忘情泡澡的那位仁兄一直沒有回應,恐怕也是醉慘了,陸子涼忍著難受,微瞇著眼張望了下,試圖找到電源開關,並續道:「你快醒醒吧,大冬天的,水早就冷了,再泡下去會凍死的。」
浴缸裡還是沒人回應。
陸子涼嘖一聲,暫時放棄開燈,轉而望向浴缸,打算在這人因泡澡而死之前先救出來再說。
可這一看又狠狠嚇了一跳,浴缸裡的人靜靜地斜倚著浴缸壁,口鼻竟然都浸在了水裡!
陸子涼瞳孔一縮,即刻攬住那人的後背將人給用力撈出水面,可他忘了自己此刻也是極度虛弱的,突然這麼使力,強烈的虛脫感再次從四肢百骸湧出,他猛晃一下,差點跟著跌進浴缸裡。
他立刻撐住浴缸壁,撈著那人的手也穩住沒放,嘴裡下意識地就道:「先生,你聽得見嗎?你──」
他的話音頓住了。
他感覺到臂彎裡攬著的這具軀體僵冷得如冰塊一般。
這人無力地仰著頭,髮梢滴著冷水,脆弱的頸項毫無防禦暴露出來,胸膛也沒有絲毫起伏。
「……」陸子涼的目光掃回這人的臉上,定住了。
晦澀的光線中,那容貌的輪廓有些熟悉,熟悉到陸子涼尚未反應過來,就已經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
正在此時,如雷的暴雨中有一道閃電橫過天際,銀白的炫光從氣窗刺入,老舊的浴室大亮一瞬!
被攬在臂彎中的人,霎時暴露得清清楚楚。
柔軟的黑髮,修長的眉,濃密的睫毛,英挺的鼻梁,單薄優美的唇瓣……
陸子涼瞳孔震動。
……這是他自己的臉!
自甦醒起就囤積在胸膛內的強烈恐懼感忽然爆發,腦子裡登時閃過一幀幀恐怖的片段──
鮮血。
劇痛。
被拖行的軀體。
逐漸淹過口鼻的窒息感……
陸子涼猛地抽回手,屍體嘩啦地摔回浴缸裡,濺起的冷水潑了他一身!
可他不躲不閃,腦子當機似的呆了幾許,呢喃道:「搞什麼?什麼意思……」
他抬起顫抖的雙手看了看,又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身體,滿臉茫然。
旋即,他像是想到了什麼,表情驀然變得恐怖,再次將手臂探入冷水撈起屍體的上半身,用力扯開屍體的衣領,往左肩頭看去──
一個鬼畫符似的紅色刺青暴露出來。
陸子涼表情一鬆。「不是他。是我自己沒錯……」
可這份輕鬆只出現短短幾秒,便再次被難以言喻的恐怖和茫然給取代。
他被人殺害了。
……所以他現在就是一隻鬼?
陸子涼徹底沉默了,滿臉都是不可置信。
他佇立在原地,驚呆了似的,簡直無法動彈。
外頭的暴雨聲迴盪在這狹小的破浴室裡,鬼哭狼嚎似的,一聲急過一聲,在轟隆的雷鳴裡彷彿化作了一句話,在陸子涼的記憶深處甦醒過來──
「天雨共患難,必是有緣人。」
晴朗的午後,在一道長滿青苔的小廟石階上,陸子涼回過頭,詫異道:「什麼?」
說話的是那小廟的老廟公。
老廟公非常非常老,陸子涼記憶裡似乎沒見過這麼老的老人。白髮稀疏,雙目混濁,暮氣沉沉,滿臉都是深刻的皺紋,在樹蔭下笑起來時異常悚人,當時的陸子涼覺得光看著那張老臉,就能想像出他說話時沙啞可怖的嗓音。
可很顯然,老廟公的嗓音非但沒有半點氣虛,還低沉渾厚,口齒清晰。
老廟公道:「來都來了,不求個紅線再走嗎?你是來拜月老的吧。」
陸子涼哦了一聲,笑道:「還是算了,我求不到的啦。來這裡之前我已經去拜過好幾間月老了,沒有一次擲得到聖筊,擲到後來都會被圍觀,怪尷尬的。」
「可你這次連擲都沒擲,怎麼知道不是聖筊呢?」
「剛才進到殿裡,不知道為什麼忽然就覺得很沒意思,沒那麼想求了。我先走了,有機會的話下次再見啊爺爺。」
老廟公卻道:「我跟你講,你啊,今天一定可以求到紅線。」
陸子涼停住腳步。半晌,他再次回頭,半信半疑又心懷希冀地問:「真的?」
老廟公衝他一笑,抬起滿是皺紋的手,招了招。「來。你來。」
邊說著,佝僂的身軀已經轉過身,往回走。
陸子涼原地掙扎了一會兒,忍不住快步跟上。
自從被交往一年半的前任狠甩之後,陸子涼開始做什麼都不順。
諸如屋子漏水、遭小偷、被騙錢、騎車雷殘,甚至到最後還因受傷而從游泳隊退役,被體育媒體報導了一番。
陸子涼整個人像丟了魂似的。
朋友聽聞他的慘況,就神神叨叨地說他是被失戀奪了心魂,硬拉著他去拜月老。
「趕緊牽個紅線,來段新的姻緣,你的厄運就會終結啦。」
「放屁。」
「唉呦,我知道,我知道你不信神,那你就當是玩一場賭博嘛,不用花錢,上香擲筊就行了。」
於是從來不燒香拜佛的陸子涼被硬拉著去拜月老。
本以為這會是他此生僅限一次的迷信,誰知道,他居然連紅線都沒有求到。
月老不賜給他。
朋友尷尬道:「啊這……唉,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我們換一間!」
爾後第二間、第三間……無論朋友拉他去拜哪間廟的月老,竟然都沒有一位月老願意賜紅線給他。
好勝心極強的陸子涼徹底被激到了。
他獨自展開一場旅行,找全台大大小小有供俸月老的廟宇求紅線。然而這趟旅程就彷彿某種難堪的輪迴,他獨自站在神明面前,擲了數不清的筊,沒有一次能得到應允。
直到這間位在明石潭半山腰上的小破廟。
「跟我來。」
陸子涼跟著老廟公回到主祀月老的左偏殿,例行的參拜之後,居然真的求到了此生第一條紅線。
在拿到裝有紅線的小袋子的當下,陸子涼簡直熱淚盈眶,都忘了自己原本的目的是什麼,只覺得心滿意足。
心情大好的他給了一大筆香油錢,就聽老廟公重複了方才在石階上說的那句話。
「天雨共患難,必是有緣人。」
陸子涼循聲看向老廟公。
老廟公道:「這話是月老和你說的。時機已經到了,你啊,要多注意一下,機會來了一定要把握嘿。錯過就糟糕囉,要打一輩子光棍的!」
「什麼!」陸子涼的驚喜變成了驚嚇。「等等,居然是一次定生死的嗎?您、您剛剛說什麼,您說天雨共患難是嗎?是指我下雨時會遇到的人?」
「哎,月老好久沒有和我說話了。很難得,難得啊。」
老廟公卻不再多解釋,只拍拍他的肩膀,又一把抓住他的左手,鼓勵地說:「月老要你一定要把握啊,小子。要把握!」
老廟公的力道莫名巨大,把陸子涼的手都抓痛了,但許是「打一輩子光棍」這個消息太過駭人,陸子涼腦子裡忽然一陣暈眩,竟也沒注意到那陣古怪的刺痛。
等陸子涼終於回過神時,老廟公已經離開偏殿了。陸子涼甩了甩發疼的手,覺得求到紅線的欣喜都被澆熄了半數,他一向不信神的,但想到一旦錯過這位「有緣人」就要永遠單身,他就莫名有些心慌。
「不會真的那麼靈吧?嘖……不然,最近下雨的時候,哪裡人多我就去哪。」
陸子涼出了廟,正徒步走下陡峭的石階時,一場突如其來的陣雨從明石潭的那端捲來,瓢潑而下。
雨水又急又猛,寒冷至極。
陸子涼猝不及防,忙抓起背包擋在頭上,正想趕到途中的那座涼亭避雨,忽然,有個人從後面遞出一把傘,將他罩在了傘下。
那是一把漏雨的破傘,實在沒什麼大用。
但那鋪天蓋地的雨水,確實輕了半數。
──天雨共患難。
陸子涼心頭一動,意識到神明的話語似乎正在應驗。他詫異地轉過頭,發現對方竟是個比他高大的男人,因為站的地勢較高,陸子涼一下子只看見他的胸膛。
於是陸子涼仰起了頭,想看清他的面容──
記憶中的畫面忽然破碎!
黑漆漆的浴室中,陸子涼痛苦地按住腦袋。
……想不起來。
想不起凶手的容貌,也想不起凶手的聲音。
甚至也想不起自己具體是怎麼被殺害的。
他只記得自己那幾個小時像是被某種古怪的力量給蠱惑了一般,在和那男人相遇的當下就中了迷魂藥似的,接受了對方的所有邀約。
──接著他就死了。
他在求到紅線後的第一場約會,被殺死在這陰冷狹小的浴室裡。
陸子涼看著那嵌在牆角裡的老舊方型浴缸,看著那根本不足為懼的淺水,看著那一動不動的屍體,喉嚨裡忽然滾出一聲笑。
「哈。」
他撩起額前的碎髮,發出輕啞的笑聲。
「淹死的?居然是淹死?不會吧陸子涼,哈哈,不會吧你……這像話嗎?太離譜了。」
笑聲逐漸被雨聲蓋過。
他獨自站在黑暗裡,輕輕呢喃:「太離譜了……」
一陣靜默之後,陸子涼忽然將雙手都探進浴缸水裡,使勁地往屍體上按,想看看能不能像電影一樣穿回身體裡去直接復活。可惜屍體似乎長了層軟膜似的屏障,將他這個魂魄阻隔在外,不允許進入。
陸子涼爆了句粗話,洩憤似的往一旁的塑膠椅踹了一腳,怎料那本該輕飄飄的塑膠椅居然重如千斤,紋絲不動。
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次狠踹,塑膠椅只挪動了一公分不到,隨之而來的是體內更加透支的虛脫感。
陸子涼怔住了。他又試著去推塑膠置物架和洗手乳,發現除了他自己的屍體,人間的萬物變得沉重如山。
眼前所看見的一切依舊可以碰觸,卻全都難以移動。
……他真的不屬於人間了。
陸子涼的黑眸裡閃過極致的恐慌。
他用力地按住胸口,胸膛急促起伏,卻好像沒能吸進什麼空氣,死亡的餘韻在他體內不斷發酵,巨大的痛苦和壓力擠壓著理智,他發覺自己的感官彷彿都先被鍍上了一層恐懼,讓人無法動彈,似要發狂。
像是冥冥之中存在著某種規則,要把鬼魂困在原地發瘋似的。
陸子涼閉了閉眼,深呼吸數次。
時間一點一滴的過去,被死亡給震懾的靈魂,逐漸被他自己給穩定下來。
如今細想,那老廟公叫他折返回去求紅線這件事,處處透著異樣。
怎麼就這麼巧,求了那麼多間月老都說不行,偏偏就只有那間小破廟的月老願意賜紅線?而剛求得了紅線,他就遇上了個「天雨共患難」的殺人犯,還被老廟公反覆強調絕不能錯過?
那間小破廟絕對是刻意將他引向死路的。
陸子涼豁然睜眼。
他是個極度惜命的人。
從小到大,他為了存活,什麼苦頭都吃過,什麼折磨都受過,他自己一個人千辛萬苦才熬到今日,對他來說,這世上最珍貴的就是他自己的命。
為了活命,他沒什麼底線的。
陸子涼神色冰冷地衝出了浴室!
他是不記得凶手的樣子了,但他完全記得那間坑人的破廟在哪裡,就連那廟前有幾根柱子都記得清清楚楚!
正當腦海中的小廟畫面清晰到極致時,伴隨心念一動,陸子涼突然就眼前一花,下一秒居然直接就出現在那間坑人的小破廟前!
原來做鬼竟能瞬移?
陸子涼踉蹌了一下才站穩,腦子還暈暈呼呼的,身體就已經迫不及待地衝上前猛推廟門。
廟門如意料之中緊緊閉合,紋絲不動。
「出來!」陸子涼拍著廟門,在暴雨聲中大吼道:「老廟公你給我出來!你們怎麼牽線的居然把我和殺人犯牽在一起!我直接被他給殺了啊!你害死人了你知不知道!你們得陪我一條命──」
雷雨之中,廟門內毫無動靜。
陸子涼怒道:「不要裝作沒聽到!人的願望你們聽得見,換成了鬼你們就聽不見了嗎!少在那裡裝聾作啞!我跑那麼遠來參拜,求個姻緣,結果居然求到連命都沒了,這像什麼話?你們自己不覺得離譜嗎!我還給了香油錢──」
廟門依舊毫無動靜。
陸子涼張望一下,注意到不遠處有棵長過了廟牆的老榕樹,拍門的動作停了停,身手矯健地爬上老榕樹,踩上廟牆,往下一躍──
下一秒,他直接被一股力量定在了空中!
「──?」陸子涼睜大眼睛。
「才出去一會兒就有人翻牆,真是不把我放在眼裡。」
陸子涼抬頭,看見一名穿著奇怪的紅色衣衫的少年凌空站在眼前。
少年留著一頭柔軟的黑髮,長相雌雄莫辨,蒼白的臉頰上沾著血,正摀著流血的左臂,神色不耐地盯著他。
陸子涼看看那少年騰空的身體,又看看那血,露出錯愕的表情,就聽那少年雌雄莫辨的嗓音再度響起,唸出了他的名字。「哦,陸子涼?看來是來興師問罪的……嘖,麻煩事真是一樁接著一樁。進來吧。」
旋即,一道疾風捲起,被定在半空中的陸子涼就如紙片一般,嗖的一下被捲進了廟門裡!
單薄的門板在身後轟然關上,粗暴的力道讓他一下子沒站穩,直接撲倒在地。
「哦,免禮。」
「……」
陸子涼神色錯愕地抬起頭,注意到周圍的陳設相當熟悉,正是他求到了紅線的地方。
──主祀月老的左偏殿。
空氣中飄著淡淡的線香味,神龕上亮著詭譎的紅光,牆角還不時傳來滴答的漏雨聲,夜晚的小廟褪去了白日的祥和,瀰漫起詭異的氛圍。
「坐。我們聊聊。」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牽到殺人魔(全)的圖書 |
 |
$ 170 ~ 316 | 牽到殺人魔(全)【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冰殊靛 出版社: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07-27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牽到殺人魔(全)
★2022KadoKado百萬小說創作大賞文化內容策進院跨域特別獎&Dokific遊戲化潛力獎!
★陰陽眼冰山法醫攻X慘遭殺害俊帥誘人受
★我想把你剖開,直接感受你的體溫,觸碰你的內臟,聽你痛苦無助的聲音……
★獨家收錄單行本限定全新番外篇「青澀的校服」!
【首刷限定】
1.Q版印刷簽名明信片X1
2.精美票卡貼X1
3.特典漫畫1P
4.「KadoKado角角者」閱讀金50角點
(※首刷售完即無贈品)
「只要他足夠愛你,你就能活。」
無意間來到月老廟求紅線的陸子涼,在求到紅線後的第一場約會中,慘遭殺害。成了鬼的他要想贖回自己的命,只能按照月老的規則走。他必須以脆弱的紙紮人偶為身體,在自己徹底損毀之前選定一個人,從此人身上獲取足夠的愛。可陸子涼的運氣總是差到極致,他意外選中的這個男人似乎很不對勁啊。不只眼神危險,行徑詭異,還貌似對他有著情慾以外的不明欲望。陸子涼忍不住懷疑,這個男人,難道就是殺死他後,依舊逍遙法外的那個殺人魔……
作者簡介:
作者
冰殊靛
吃貨與廢宅的融合體,經常因為地盤問題和貓決鬥,然至今尚無贏面。喜歡欣賞讓人忍不住尖叫的東西,熱愛寫又強又香的小受~~
FB:冰殊靛.bingshudian
IG:bingshudian
插畫
重花
重疊的重。可唸成蟲花。目前大概勉強可說得上是漫畫、小說、插畫三棲,但因為跟大家一樣,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所以總覺得時間永遠不夠。動力歉收期,復健中。
FB:重花(塚本 月)
Plurk:taukamoto
章節試閱
序章
深夜,一場大雨降臨了。
遼闊的明石潭上,細密的漣漪圈圈盪出,湖魚潛到了深處,萬物的輪廓都變得朦朧起來。
潭邊的半山腰上,一間破破爛爛的小廟亮起了燈。
年近九旬的老廟公裹著厚外套,呼著霧氣走過長廊,從廁所裡拿了幾個塑膠盆,準備去那些逢雨必漏的地方擺一擺。
正忙碌著,突然,側殿那邊傳來一陣怪異的聲響。低低沉沉,忽隱忽現……
老廟公睏乏的腳步頓住。仔細一聽,居然像是有人在笑。
老廟公咕噥著:「啊……是……誰在笑啊?」遂拿著塑膠盆,循著聲音慢吞吞地走過去。
恰逢一道銀白閃電掠過,天地間大亮了一...
深夜,一場大雨降臨了。
遼闊的明石潭上,細密的漣漪圈圈盪出,湖魚潛到了深處,萬物的輪廓都變得朦朧起來。
潭邊的半山腰上,一間破破爛爛的小廟亮起了燈。
年近九旬的老廟公裹著厚外套,呼著霧氣走過長廊,從廁所裡拿了幾個塑膠盆,準備去那些逢雨必漏的地方擺一擺。
正忙碌著,突然,側殿那邊傳來一陣怪異的聲響。低低沉沉,忽隱忽現……
老廟公睏乏的腳步頓住。仔細一聽,居然像是有人在笑。
老廟公咕噥著:「啊……是……誰在笑啊?」遂拿著塑膠盆,循著聲音慢吞吞地走過去。
恰逢一道銀白閃電掠過,天地間大亮了一...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