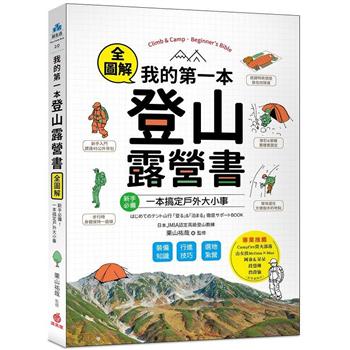一個國家不論因何理由而遭逢戰禍,我們都應放過那些能榮顯人類社會文明的建物,切末助長了敵人的力量——譬如神殿、陵墓、公共建築,以及所有具備超凡之美的成果……如此肆意剝奪對方的藝術成果,無異於宣告自己為全人類之公敵。
——瓦特爾,《萬國公法》,一七五八年
我曾經深入研究過在彼得城、沙皇村,還有巴甫洛夫斯克等地的歷史古蹟,並且在這三座城鎮裡見識到了對古蹟極端野蠻的對待。更過份的是,從破壞的狀況——已經無法詳加列舉,因為實在太多太多了——可以明顯看出那是早有預謀的。
——艾米塔吉博物館館長,伊歐瑟夫•歐貝里,在紐倫堡審判前所做之證詞,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序章
奧地利,毛特豪森集中營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日
囚犯們都叫他「耳朵」,因為他是八號營房裡唯一懂德文的俄國人。沒有人叫過他的名字,卡洛•波爾亞。打自他一年多前進入這座集中營的第一天開始,耳朵——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琥珀廳的圖書 |
 |
$ 170 ~ 351 | 琥珀廳
作者:史帝夫.貝利(Steve Berry) / 譯者:許文達 出版社:尖端 出版日期:2010-03-09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24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琥珀廳
巧奪天工的「琥珀廳」不僅是人類史上最珍貴的寶藏,也是最難解的歷史謎題。德國部隊在一九四一年入侵蘇聯,奪走了「琥珀廳」。而當盟軍展開轟炸時,「琥珀廳」則被藏了起來,從此消失蹤影。如今,尋寶的冒險又再度啟程……
亞特蘭大城的法官瑞秋.庫特勒熱愛她的工作和兩個孩子,而且和前夫保羅維持著彬彬有禮的關係。但是在她的父親神祕過世之後,她的人生一切都改觀了。她父親留下了某個關於琥珀廳的祕密線索,急於找出真相,瑞秋啟程飛往德國,而保羅也隨後跟了過去。然而這趟旅程讓他們身陷險境,與職業殺手展開危險的對峙。
瑞秋和保羅驚覺他們已被捲入了貪婪、權力,以及歷史洪流所匯集而成的漩渦之中。
章節試閱
一個國家不論因何理由而遭逢戰禍,我們都應放過那些能榮顯人類社會文明的建物,切末助長了敵人的力量——譬如神殿、陵墓、公共建築,以及所有具備超凡之美的成果……如此肆意剝奪對方的藝術成果,無異於宣告自己為全人類之公敵。——瓦特爾,《萬國公法》,一七五八年我曾經深入研究過在彼得城、沙皇村,還有巴甫洛夫斯克等地的歷史古蹟,並且在這三座城鎮裡見識到了對古蹟極端野蠻的對待。更過份的是,從破壞的狀況——已經無法詳加列舉,因為實在太多太多了——可以明顯看出那是早有預謀的。——艾米塔吉博物館館長,伊歐瑟夫•歐貝里,...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史帝夫‧貝利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10-03-08 ISBN/ISSN:978957104242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56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