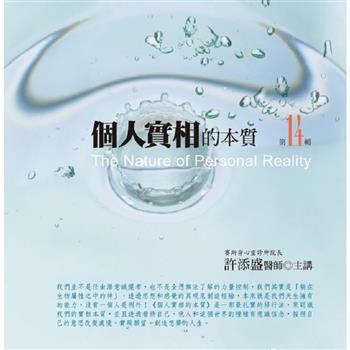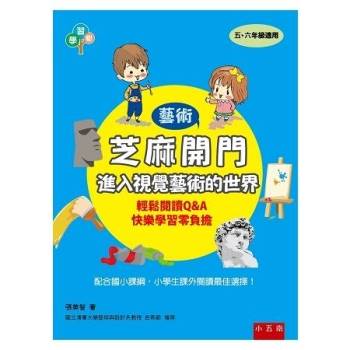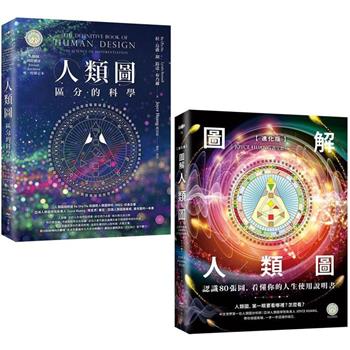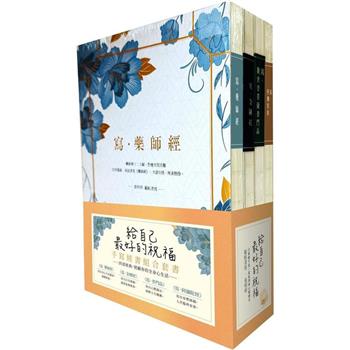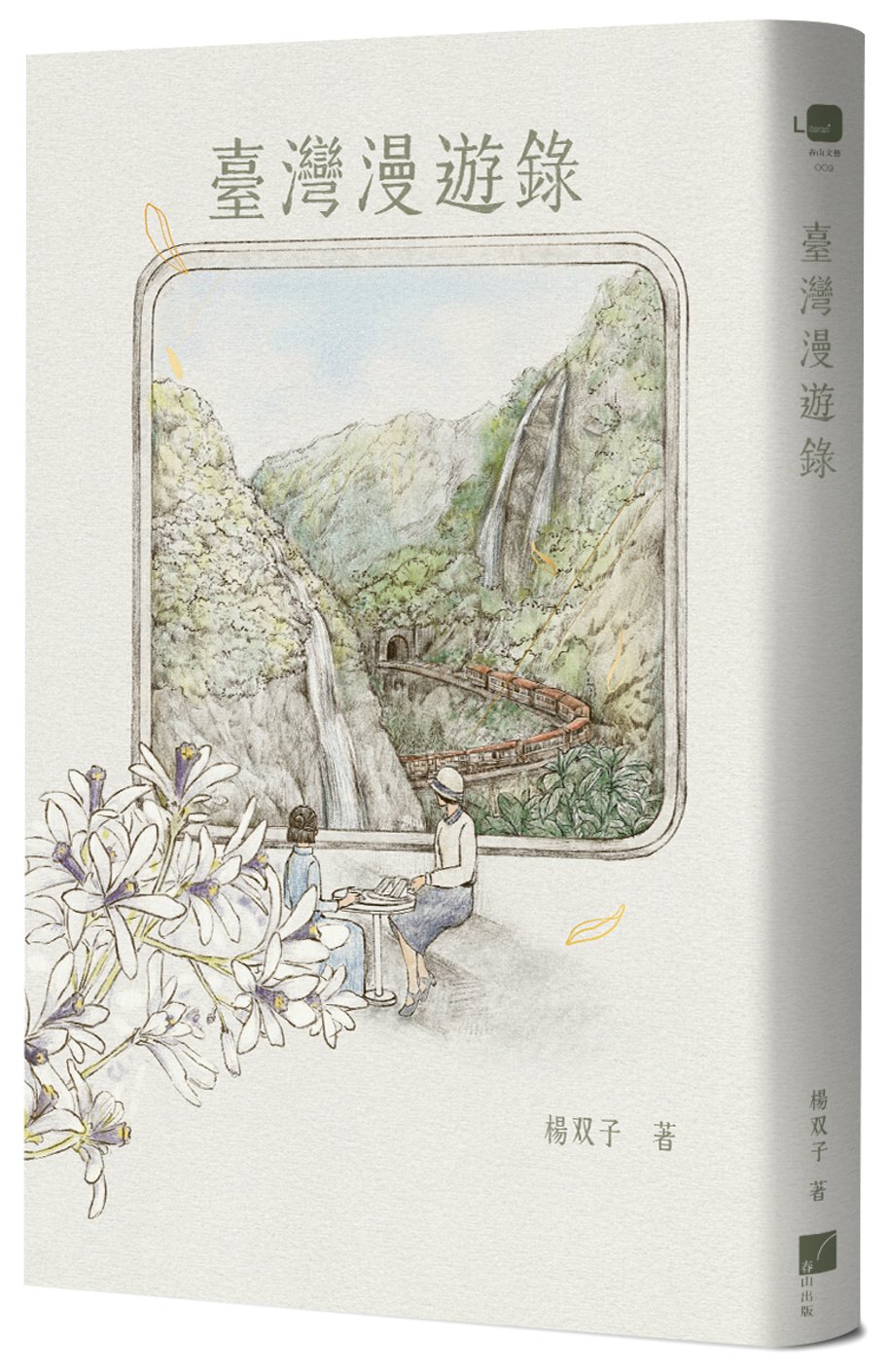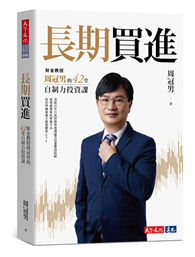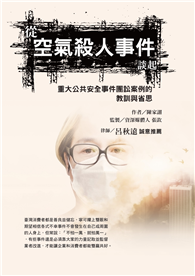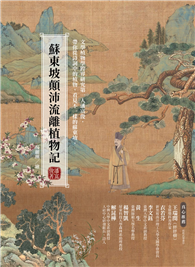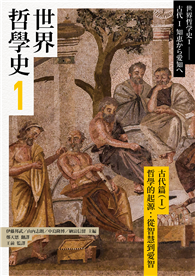導讀
近幾年來,在許多的業界出現一種競爭,對手和以往「熟悉的宿敵」完全不同,它指的是與多國企業間的競爭、不同產業間的競爭以及和突然出現的創業公司間的競爭。換言之,與「異文化」之間的競爭逐漸趨向於白熱化。
另外,因為日本勞動人口有逐漸減少的趨向,為了要得到不斷減少的投資獲益機會,企業進行的巨額資本瞬間轉移也會讓泡沫化現象變得容易反覆生成跟消滅,這些因素可以讓我們預測到,今後日本企業所處的環境本身將全面性地變得更加嚴峻。
在經濟如此嚴峻的時代,我思考著該如何超越國家,產業種類以及新舊的框架,並廣泛收集智慧、人才、商業夥伴等等資源,讓那些能將資源有創意地應用並整合的企業得以留存下來。我認為應該要包容不同性質的文化以增加選擇性、融入不同性質的文化以提高企業方針的正確性以及提升企業競爭戰略的精準度。也就是說,要打一場異文化的戰爭,就要活用異文化。在這部分,以我個人來看所應要做到的,就是本書的標題「異文化包容力」。
本書是以「異文化」( 指的是包含各個不同國籍、文化及語言的人們) 為中心,以實際發生的例子以及我自身的經驗作為基礎來展開論述。
但是,我所要談的並非如同大家所想像,只是異國企業的加入,或者是前進海外市場這樣的事情而已。當日本企業之間,也必須與那些引進海外資金、智慧及人才的日本企業對戰時,會發現競爭對手的樣貌跟武器出處變得難以判定,或者是你會覺得那些競爭瞬息萬變且概念廣泛。
2008年我開始前往日本以外的國家工作。以戰略諮詢顧問的身分在上海發展。在國外,我親眼見識了國際企業的活躍以及困境。在那之後,到了東方與西方價值觀劇烈碰撞的香港HKUST(香港科學技術大學)念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工程管理碩士),與聚集於亞洲的年輕菁英們共同渡過一段留學生活。之後,又與多種不同國籍的員工一起投身於紅馬集團,現在擔任集團的執行總裁(CEO)。
日本的許多製品、服務、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受到全球的誇讚。而且,以個人能力來說,日本與其他國家相比完全沒有處於劣勢的部分。
我甚至認為,潛在中,有很多日本企業是能活耀在更遼闊的世界中的。
然而我覺得以個人的能力來看,出了日本能夠大顯身手,特別是以領導者角色活躍於各國的人並不多,這也的確是目前的現狀。
多年來不斷思考其原因,我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日本人在遇到擁有不同性質文化與思想的海外人士時,無法順利地「融入異文化」,以至於無法發揮原本自己所擁有的實力吧!也因為這個部分,造成了日本企業發展國際化的最大障礙。
當日本人在超越國籍與異文化接觸時,給人的印象是行動容易傾向兩極化。他們容易過度依賴在日本的常識,或者是極端到捨棄對自己民族文化的認同。
前者起因在於同性質文化。許多的日本人,以相同的人種、歷史、文化、宗教教育為中心思想。像「無聲的交流」以及「彼此的默契」等等這些心靈相通的感覺,只有在同質文化中才能彼此理解。這些用在完全不同的人種、歷史、文化、宗教、與教育孕育出來的人身上是完全行不通的。
在與「異文化」接觸的時候,理解對方的背景然後必須有意識地改變自己的言行舉止,這對日本人來說似乎是相當困難。
後者我發現似乎是因為對國際人才的認知有誤所引起的。我看到為數不少的日本人,很不可思議地,完全對自己的國家背景毫無自豪地在海外生活。彷彿只要抹去了日本人的個性,就可以成為中立的國際化人才。這種作法雖然能夠學習到異文化,卻無法達到融入的境地。
去了解不同文化的人,傳達自己的想法、進行交流、說服對方、談判,甚至更進一步地,擔任組織的領導者,這些與異文化相容的做法,並非只是將同文化與異文化進行相接然後延伸而已,而是必須去重新認識這些似是而非的東西。還有,如果在同性質的社會中無法自然而然地習得這些能力的話,那除了有目的地訓練之外就別無他法了。
我在海外遇到的許多優秀人才,他們都具備了超越國境與文化並能夠協同合作的能力。一個人能做到的事情有限,這是世界共通的道理。
愈是接近領導者的地位,就愈會被要求要擁有能夠超越國籍與文化的界限,為了達成目的包容周遭一切的能力。
我相信日本人的潛在能力。但是,很明顯地目前最為薄弱的也就是本書所談的「異文化包容力」。雖然我自己仍在學習中,未有任何成就,但是總覺得從現在我所學習的過程中,應該有一些能傳達給日本的東西吧!再加上與PHP 研究所諸位的緣分,我便以此為題,試著執筆寫下了這本書。
本書的內容,正如前面所述,以包容不同國籍、文化、語言的人士為主要目的來進行研究,但實質上是日本的日常商業活動中也能夠活用的內容。就算同為日本,但由於世代、專業領域、價值觀等等的不同,或多或少也會出現不同性質的文化,相信很多人會問,對於這些又該如何去相互融入呢?我的經驗及研究,超越了各種既有的框架,希望可以助各位一臂之力,在日後能一展長才。
2014年10月吉日
紅馬集團CEO
Odigo Founder and Chairman
川崎貴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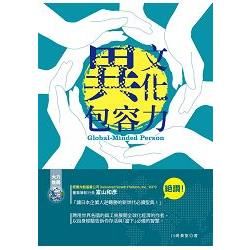
 共
共  文化是由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首次使用拉丁文「cultura animi」定義,原意是「靈魂的培養」,由此衍生為生物在其發展過程中積累起跟自身生活相關的知識或經驗,使其適應自然或周圍的環境,是一群共同生活在相同自然環境及經濟生產方式所形成的一種約定俗成潛意識的外在表現。
文化是由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首次使用拉丁文「cultura animi」定義,原意是「靈魂的培養」,由此衍生為生物在其發展過程中積累起跟自身生活相關的知識或經驗,使其適應自然或周圍的環境,是一群共同生活在相同自然環境及經濟生產方式所形成的一種約定俗成潛意識的外在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