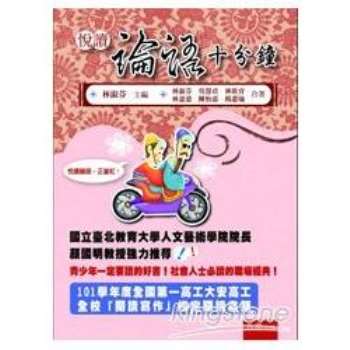「原來這就是離別的心情。
無論對方是戀人還是好友,也無論是短暫的分離還是永別,
都是失去了一個世界。」
當生命到了盡頭,你是我最想見到的人。
你也一樣,想念著我嗎?
男人在退休當天,病倒在回程的地鐵上。距離到家,只剩短短四站。
這一瞬間,他該問的是,
「我這輩子的『幸福』是什麼?」
★《穿越時空‧地下鐵》、《鐵道員》作家淺田次郎,最極致的生死與道別議題書寫!
★《流》、《解憂雜貨店》譯者王蘊潔跨刀加盟,還原最精準的感動!
「淚流不止!」各方人士★★★★★五星滿分好評!
▎日本讀者爆淚推薦:
「在閱讀的過程中,忍不住對照自己的人生。」
「最後的最後,淚水就像潰堤般失去控制地奪眶而出!」
「極致的奇幻小說,內心無可取代的記憶不斷湧現。」
▎責任編輯老淚縱橫推薦:
「這是我編輯生涯中遇過最真摯、最感動的書之一。我現在只想放下一切,慎重地,重頭再看一次這本書。」
▎網友紅著眼眶推薦:
「不可多得的好故事!我彷彿閱讀著我的人生。」
「一頁接著一頁翻下去,無法預期結果究竟是好是壞……但這對讀者來說是最棒的事!」
「過程中的鼻酸或泛淚都還能忍住,但是最後還是哭到無法呼吸!」
得獎無數的淺田次郎,在二○一五年獲頒表揚在日本學術藝文界有偉大功績的紫綬褒章後,於二○一七年完成了這部作品。
「他可能和你出現在同一間教室、可能在同一個地方打工;可能是你的同事,也可能和你搭同一班通勤地鐵。」他為這本書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
★淺田次郎作品獲獎紀錄
《穿越時空.地下鐵》榮獲第十六屆吉川英治文學新人獎
《鐵道員》榮獲第十六屆日本冒險小說協會獎特別獎、第一一七屆直木獎
《一路》榮獲第3屆本屋時代小說賞得獎作
《壬生義士傳》榮獲第十三屆柴田鍊三郎獎
《中原之虹》榮獲第四十二屆吉川英治文學獎
《終わらざる夏》榮獲每日出版文化獎
《お腹召しませ》榮獲第一屆中央公論文藝獎、第十屆司馬遼太郎獎
《帰郷》榮獲第43屆大佛次郎獎
「那天晚上,他找不到回家的路。」
通勤上班四十多年的男人,於退休的歡送會結束後,一如往常地搭了地鐵回家。
正式退休的最後一天、在離家只剩下四站時,
他耗盡了生命的力氣,在車廂裡倒了下去。
他這輩子的「幸福」究竟是什麼?他是不是已經擁有過?
愛是不是人生所有的真相?
如果不遺忘,是不是就無法活下去?
作者簡介:
淺田次郎
一九五一年出生於東京都。一九九五年,以《穿越時空.地下鐵》獲得吉川英治文學新人獎。一九九七年以《鐵道員》獲得直木獎,二〇〇〇年以《壬生義士傳》獲得柴田鍊三郎獎,二〇〇六年以《切腹》獲得中央公論文藝獎、司馬遼太郎獎,二〇〇八年以《中原之虹》獲得吉川英治文學獎,二〇一〇年以《無盡的夏天》獲得每日出版文化獎。二〇一六年以《歸鄉》獲得大佛次郎獎,二〇一五年獲頒紫綬褒章。另著有《監獄飯店》、《蒼穹之昴》、《憑神》、《赤貓異聞》、《我內心的珍妮佛》。
譯者簡介:
王蘊潔
樂在一個又一個截稿期串起的生活,用一本又一本譯介的書寫下人生軌跡。譯有《永遠的0》、《解憂雜貨店》、《哪啊哪啊神去村》、《博士熱愛的算式》和「十二國記」系列等作品。著有《譯界天后親授!這樣做,案子永遠接不完。》
臉書交流專頁:
綿羊的譯心譯意
www.facebook.com/sheepheart
章節試閱
第一章
1
老友
向晚時分,天空下起了雪。
既不是傾盆大雪,也不是飄然而落,而是像牡丹花瓣的牡丹雪。打到擋風玻璃上變了形,馬上被雨刷抹掉的雪片宛如無常的生命。
時間很充裕,嘮叨的秘書也不在。
「對不起,可不可以繞去醫院一下?」
他沒有再多說什麼,看到司機在後視鏡內瞪大了眼睛。
「你身體不舒服嗎?」
「不,我朋友住院了。」
他可以感受到司機鬆了一口氣。公務車的司機就像是隱形人,但他覺得這個司機其實比秘書和下屬,甚至可能比家人更關心自己。即使沒有面對面,兩個人相處的時間也很長。更何況他在成為常務董事,有了自己專屬的公務車之後,他就一直是堀田憲雄的專屬司機。
「是。請問要去哪一家醫院?」
「中野的國際醫院。你知道嗎?就在青梅街道再往裡面一點。」
「是,我知道。」
司機瞥了一眼用車時間表。雖說時間充裕,但如果先去中野的醫院,之後再去青山的餐廳,時間就有點來不及。司機可能在猜測,要不病人的病情很嚴重,要不就是等一下一起用餐的是讓對方稍微等一下也不會失禮的對象。
兩者都是正確答案。這個司機跟了他七年都沒有換,就是因為沉默寡言,而且直覺很敏銳。
車子駛上高速公路後加快了速度。每經過一個隧道,牡丹雪的數量似乎就增加了。比起晚餐的聚餐,是否能夠順利回去位在郊區斜坡地上的住家似乎更令人擔心。
「齋藤,你到什麼時候?」
他刻意避開了退休這個字眼問道。
「是,再僱用也只到明年為止。」
雖然這個問題很唐突,但聽到了好像早就準備好的答案。
路燈的燈光把車內染成橘色,然後被拋在車後。他忍不住想,那傢伙是不是也曾經像這樣計算還有多久退休?
他和竹脇正一有很長一段時間都關係疏遠,即使再怎麼絞盡腦汁,也想不起最後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
當他從總公司的部長調去關係企業當高階主管時,曾經來拜訪當時升上專務的堀田。竹脇特地事先透過秘書室預約了十五分鐘面談時間,的確很像他一板一眼的行事風格。
竹脇在退休前一年被調去關係企業,這是很順理成章的人事調度,堀田並沒有費心為他安排。雖然薪水稍微降了一些,但可以延長五年再退休。說起來,算是集團內的空降。除非很乾脆離職,否則比申請再僱用,最後被分配到一些有名無實的閒職好多了。
——多虧了你,我總算保住了飯碗。
——喂喂,我可是什麼都沒做,根本把你忘得一乾二淨了。
在這番對話之後,他們聊了家人的近況。竹脇不時看時間,在十五分鐘後站了起來。
——等你有空時,希望有時間喝一杯。
——好啊,一言為定。我會和你聯絡。
雖然當時說這句話並不是敷衍,但終究還是沒有完成這個約定。他並不至於忙到無法安排一晚和老友見面,而是根本把這個約定忘得一乾二淨。否則就是把竹脇視為沒有任何利害關係的人,根本沒放在心上。
車子在初台下了首都高速公路。雪仍然下個不停,但這麼大片的雪並不會造成積雪。
「齋藤,你向來不看衛星導航。」
「對,因為我不相信它。」
「是啊,這個世界上充滿了無法相信的東西。」
「經驗和直覺更加可靠。」
至今已經過了六年。在這六年期間內,不可能從來沒有遇見過竹脇。竹脇去的那家關係企業的辦公室就在附近,業務內容也和總公司有密切關係。這段期間內應該多次擦身而過,也曾經搭過同一部電梯。竹脇應該向自己鞠躬打招呼,但自己並沒有開口。不,因為完全沒有記憶,所以應該是完全沒有看竹脇一眼。當年的知心好友漸漸變成了四千名員工中的一份子,不,正確地說,是把竹脇視為集團旗下幾萬名員工之一。
他在董事會會議資料所附的離職者名單上看到了「竹脇正一」的名字。
六年前的離職名單上記載了竹脇即將轉任的公司,第二次的離職原因是「退休」,同時附上了六十四歲又三百六十四天的日期。
名單上有許多堀田熟悉的名字。同年進公司的同事中,除了堀田以外,無論是退休後再僱用的人,或是像竹脇那樣去關係企業擔任高階主管的人,都只做到今年為止。
他並沒有因此產生特別的感慨。錄用了一百名新員工,就會有一百名老員工離職,只不過離職日期並不統一,所以每個月都會收到相關報告。
散會之後,一名常務董事走過來,指著資料問他。
——董事長,您認識這位竹脇先生吧?
——是啊,我們同一年進公司。
竹脇的退休日期已過,退休後被調去擔任高階主管的那家關係企業負責服裝品牌生產和銷售,那位常務董事主管纖維部門,堀田以為他打算在部門內為竹脇舉辦歡送會,所以邀請和竹脇同年進公司的董事長一起參加。
沒想到常董說的內容完全出乎意料。
三天前為竹脇舉辦了歡送會。竹脇說,董事長太忙了,不要驚動他。竹脇在參加完歡送會的回家路上,昏倒在地鐵的車廂內。
那是星期五晚上發生的事。他當然不至於為在星期一的會議之後才接獲通知這件事責備下屬。
——他目前的情況如何?
——還不瞭解詳細情況,只是覺得應該先通知您這件事。
在總公司內主管那家關係企業業務的常董應該是歡送會的主要客人,八成在帶領大家乾杯之後就早早離席,當然不可能瞭解詳細情況,而且也沒有必要瞭解。
堀田回到董事長室後,打電話去竹脇家,電話沒有接通。他靈機一動,撥打了之前從來沒有打過的手機號碼,沒想到竹脇的太太接了電話。
堀田記得以前同住在員工宿舍時,幾乎每天聽到的那個聲音。
那個聲音告訴他,竹脇仍然沒有清醒,還說,堀田應該日理萬機,不必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你在這裡等我一下,我最多十分鐘或是十五分鐘就回來。」
他沒有在醫院門口下車,而是請司機把車子停去停車場。因為他不希望竹脇的家人或公司的人看到他上下公務車的那一刻。
他拒絕了司機準備為他撐的傘,走進紛飛的大雪中。最多十到十五分鐘。既然竹脇已經昏迷不醒,逗留太久也沒有意義。
也許正值晚餐時間,病房的窗戶都亮著燈光,也有許多人影晃動。
這是一家經過多次擴建的舊醫院,一看就知道來不及改建成高樓病房,只能用這種方式擴建。一部分立體化停車場在門診時間恐怕一位難求。
堀田突然想到大手町的總公司大樓改建時的狀況。
總公司建於戰前的六層樓大樓躲過了空襲,一度被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接收。雖然他只在那棟舊大樓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但至今仍然可以清楚回想起埋了化石的大理石階梯,和黃銅折疊門的電梯。
堀田和竹脇曾經是纖維部門營業部的同事,進公司第一年的主要業務就是辦公室搬家。如果是現在,這種事會交給搬家業者處理,但在那個時代,即使公司的景氣再好,也不會考慮事情的合理性這種問題。新進員工的訓練一結束,就在盛夏季節扛著紙箱,在大手町的辦公街上來來回回。
佇立在雪幕中的舊醫院令堀田想起了公司的舊大樓。這家醫院內有好幾百張病床,每張病床都維繫了一條生命,所以無法同時改建。東京都內有很多舊醫院都只能採用這種方式不斷擴建。
漸漸靠近時,發現白色的外牆、小窗戶,以及窗戶下整齊排列的空調室外機,都很像公司舊大樓的外觀。
聽說竹脇在參加完歡送會回家的路上昏倒在地鐵車廂內。那是他從位在荻窪的住家到公司、搭了無數次的丸之內線的車內,堀田猜想他應該在新中野的車站被送去醫院。
堀田抬頭看著病房大樓,忍不住嘆了一口氣,覺得那天晚上,老友找不到回家的路,結果誤闖進和充滿懷念的公司大樓很像的這家醫院。
堀田在探病登記櫃檯準備寫病人名字時,停下了手上的原子筆。因為他一時想不起竹脇的全名叫什麼。
雖然努力回想,但還是想不起漢字,最後只好根據他名字的發音「Masa-Kazu」,寫下了片假名。職員輸入電腦時,螢幕上出現了「竹脇正一」這個名字。他覺得這個名字有一種寂寞的感覺。
「他目前在加護病房,請去護理站問一下是否可以探視。」
堀田對職員有點冷漠的回應感到生氣,但隨即覺得如果職員整天在意探病者的心情,根本無法工作。也就是說,並不是對方態度不好,只是自己無法適應別人用這種語氣對自己說話。
他看著職員遞過來的醫院示意圖前往加護病房。加護病房位在東樓的二樓,醫院內部因為不斷擴建,所以動線變得很複雜。
堀田憲雄並沒有任何宿疾,這在同年齡的人中應該很少見。現在回想起來,自己能夠在職場上平步青雲,很大一部分必須歸功於體力和健康。
他向來不太在意所謂的人情世故,所以幾乎很少去探病,甚至對自己臨時想去探視竹脇感到意外。
病房大樓因為配膳車忙碌地在走廊上的奔波陷入一片嘈雜,東樓二樓卻一片靜謐。每走一步,就又更確實地遠離生命,任憑死亡漸漸滲透。
堀田對自己限定了十到十五分鐘的時間感到驚訝。這裡都是垂危的生命,沒有任何需要用時針計時的行為。
他在隔著病房的門前停下了腳步,一度打算掉頭離開。
堀田為自己對老友持續冷淡感到羞恥。這是因為始終對公司向來根據規定決定人事的現實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即使如此,竹脇正一也不是需要刻意疏遠的壞人。不,他曾經是堀田無可取代的好友。
結果反而造成了提拔主動靠近的人,排斥了沒有野心的人這種結果。
脫下淋濕的大衣,他才終於下定決心。因為他覺得即使冷淡,也不能怯懦。
「請問要探病嗎?」
護理師問道,堀田小聲地回答了老友的名字。
半圓形櫃檯圍起的護理站位在明亮的空間中央,用簾子隔開的病床排列在護理站視線可及的範圍。
站在生死邊緣的病人身影一目瞭然。第一次看到這片景象的自己無疑是極其幸運的人,同年齡的竹脇正一此刻正在加護病房的某個角落昏迷不醒。
父親在二十年前因為心肌梗塞驟逝。因為當時他被調往海外工作,所以沒有見到父親最後一面。今年九十歲的母親至今身體仍然硬朗,非但不需要妻子照顧,甚至還為妻子分擔家事。
他努力思考,還是想不起至今為止,曾經見過在生死關頭掙扎的人。他活到這個歲數,當然經歷過不少辛苦,但並沒有直接接觸過生老病死或是意外這種不幸的事。
堀田甚至開始懷疑自己能夠成為這家公司的董事長,並不是靠上司的提拔或是自己的實力,而是自己與生俱來的好運氣。
從這個角度來說,竹脇的運氣就很差。他的身世坎坷,一旦談論,無論說的人還是聽的人都會很難過,所以之前都盡可能避免提起這件事。
他年幼的孩子因為車禍喪生。因為當時堀田和他住在同一個員工宿舍,家中又有同齡的孩子,所以感同身受。堀田當時費盡心思,避免他們夫妻因為情緒失控鬧離婚。
竹脇在工作上也衰事不斷,大部分都並非他的過錯,只是因為他剛好在場,或是因為他是不夠機靈的老實人,所以全都怪罪到他頭上。
「竹脇先生,有人來探病。」
護理師沒有說其他廢話就轉身離開了。
老友被許多醫療儀器包圍,身上插了很多管子躺在那裡。窗外的雪彷佛落在他一頭濃密的白髮上,增添了幾分悲傷。
啊啊,啊啊。堀田發出無聲的聲音,嘴唇忍不住顫抖。
「啊,阿竹,怎麼會這樣?」
堀田抓住病床的邊緣支撐自己的聲音,呼喚著幾乎遺忘的老友名字。
妻子
節子完全沒有想到堀田憲雄會來醫院探視丈夫。
他們之間已經變得很疏遠,當堀田打電話到丈夫手機時,她也沒有馬上聽出來。更何況堀田已經是總公司的董事長,讓人不敢輕易提起和他是舊識。
堀田問及丈夫目前的狀況,她回答說「目前還沒有清醒」,堀田在電話彼端陷入了沉默。節子當時也亂了方寸,不記得自己是否向堀田說明了事發經過和詳細的病情。
這應該是睽違二十年的第一次見面。自從堀田順道拜訪丈夫外派的上海事務所,一起吃晚餐後,就不曾再見過他。
節子不知道這二十年來,他們之間的交情如何。丈夫向來不提工作上的事,更何況堀田是同期進公司的員工中升遷最快的人,所以也不便打聽他的消息。
他太厲害了,真是自嘆不如啊。
堀田每次升遷,丈夫就好像自己升遷一樣,高興地告訴節子,完全感受不到絲毫的嫉妒心,似乎發自內心為好友感到驕傲。
他應該也會拉你一把。
節子沒有多想,脫口這麼說道,丈夫立刻皺起了眉頭。
我在開玩笑。節子立刻支支吾吾起來。丈夫就像是小時候的優等生班長直接變成了大人,性格有潔癖,經常聽不懂別人的玩笑話。
因為丈夫屬於這種個性,所以在堀田步步高升後,丈夫應該主動和他保持了距離。節子並不會覺得心有不甘,在丈夫所有的特徵中,節子最愛的並不是他看起來很有型的高個子,也不是幽默的品味,或是不拘小節的開朗,而是他在重要的部分擇善固執的潔癖。
奇妙的是,堀田突如其來走進加護病房時,似乎完全沒看到從椅子上站起身的節子。他緊緊抓著病床的鐵管,掛在手臂上的大衣掉落在地上,好像在呻吟般地問:「啊,阿竹,怎麼會這樣?」節子還來不及反應,他就雙手捂著臉痛哭起來。來探病的訪客絡繹不絕,每個人都鼓勵她,從來沒有人感到悲傷。
丈夫可能不久於人世了。節子第一次產生了這種想法。
「啊啊,好久不見。」
堀田終於抬起頭對她說。不知道剛才是沒發現節子,還是雖然注意到了,但忍不住情緒失控。
「我今天才得知這件事,真的大吃一驚。」
堀田用手帕擦拭著眼皮,並沒有為自己的情緒失控感到難為情。於是節子知道,社會地位的差異讓這兩個昔日好友漸行漸遠。
「你應該很忙,謝謝你特地抽空來看他。」
她在措詞上很小心謹慎。因為總覺得無論說什麼,可能聽起來都像是挖苦或是抱怨。
「目前的情況怎麼樣?」
節子猶豫起來,不知道該不該據實以告,但又覺得堀田為丈夫感到這麼難過,如果對他含糊其詞有點太見外了。
「聽說不太樂觀,因為出血情況很嚴重,腦壓也很高,所以無法動手術。」
堀田抬頭看著窗戶,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不樂觀」這幾個字出自醫生之口,節子知道這句話代表徘徊在生死邊緣的意思。說白了,應該就是「病危」,只不過節子完全沒有真實感。
她之前曾經聽人說過,如果腦出血有救,就會動手術。如果沒有希望,就不會動手術。電腦斷層掃瞄的影像應該可以讓醫生做出正確的判斷。
她沒有勇氣問醫生,但醫生對丈夫做出了這樣的判斷。
「我也不知道公司同事在星期五為他舉辦歡送會的事,如果知道的話,一定會排除萬難參加。聽說妳也沒有參加?」
「他問我要不要參加,我實在⋯⋯」
堀田應該能夠瞭解。應該是為竹脇舉辦歡送會的人提出邀請,但竹脇向來不希望太太拋頭露面,節子也不擅長和別人打交道。他們是很傳統的夫妻。
「但是阿節,這不是妳的過錯。」
堀田抬頭看著窗外的雪,突然用以前說話的口吻說道。雖然有一種時空錯亂的唐突,但節子內心湧起一股暖流。
她打開鐵管椅請堀田坐下。他雖然胖了些,但並沒有老態。
「堀田先生,你一點都沒變。」
「不,妳才是完全沒變。竹脇太幸福了。」
節子不知不覺說起了三天前發生的事。
十二月十六日舉辦歡送會這一天,剛好是丈夫六十五歲生日的隔天,也就是他退休的隔天。雖然節子覺得也未免太巧了,丈夫說「總比在職期間舉辦好」。在大家都很忙碌的臘月,配合所有和丈夫關係密切的下屬行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後決定在星期五下午五點這個奇怪的時間舉行歡送會。
在這個時間舉辦歡送會,其他人可以在結束之後回去工作,或是再去和客戶應酬。
丈夫早早就開始做出門的準備。他穿上和前一天完全相同的衣服,白襯衫配不起眼的領帶。他從年輕時就一直穿深藍色西裝。
丈夫的健康向來沒有問題。喝酒向來不會過量,菸也早就戒了。雖然以他這個年紀,血壓有點高,但應該不至於太擔心。雖然在服用降低膽固醇和中性脂肪的藥,但並不算是疾病。
他看起來毫無異狀,他們和平時完全一樣,在家門口說著「我出門了」、「路上小心」。
前一天還沒有特別的感慨,但節子看著他在冬日看起來有點淒涼的櫻花樹下漸漸遠去的背影,覺得這是最後一次了。也許這就是所謂的第六感。
送他出門後,節子回到客廳,打開了廣告單,開始安排如果交給丈夫處理,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會實現的出國旅行計畫。
她以為夫妻兩人接下來會有很多時間,會多到不知道要幹嘛。
丈夫在上海和北京工作了六年,她不想再去中國,這次當然要去以前從來沒去過的歐洲走走。跟團旅行雖然很省事,但丈夫和節子都不擅長和別人打交道,既然這樣,不妨安排一場不惜時間和金錢的自助旅行。
丈夫的英文很好,也很習慣到國外出差,把這次旅行視為邁向新人生的二度蜜月,就不會覺得太奢侈。
她翻著廣告單和雜誌,然後又打開電視看了衛星電視的旅遊節目。那是沒有任何不安的富足時光。
她躺在沙發上打瞌睡時,電話響了。她立刻看向時鐘,可能是有了某種不祥的預感。她清楚記得八點十五分這個時間。節子富足的時光在這個瞬間結束了。
——請問是竹脇正一先生的府上嗎?
對方開口說第一句話時,她覺得自己已經猜到了大致的狀況。雖然完全出乎意料,但她就像打開禮物盒的瞬間般立刻瞭解了一切,所以對之後的對話完全沒有記憶。
但她之所以格外鎮定,是因為她覺得生病、死亡這種事和丈夫無關。不知道為什麼,節子接到那通緊急電話時,有一種置身事外的感覺。
她確認關了瓦斯,在家中留了燈光,避免被人發現家中無人,然後鎖好門外出。她走到青梅大道,對著很少搭乘的計程車舉起手時,才終於瞭解事態的嚴重性。清醒的身體命令還沒有進入狀況的心,現在沒時間搭公車或地鐵。
「既然是歡送會,應該派車接送。真的很抱歉。」
「堀田先生,這不是你的過錯,早晚會發生這種情況,請你不必放在心上。」
節子知道,一定是丈夫婉拒了公司派車接送。
節子想像著丈夫抱著別人送的花束,從飯店門口離開的身影。
「對了對了,大家送了很漂亮的花束,他在地鐵上也一直拿在手上。別人一看就知道他剛參加歡送會,難道他不覺得難為情嗎?」
堀田的視線尋找著花束。花束和丈夫一起送上了救護車,但無法帶進加護病房。希望那束花此刻正在醫院的某個地方綻放。
「很像是竹脇的風格。」
「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不是,他不會把別人送的花束轉送給他人,也不會留在飯店。不,他可能根本沒想到這種事。」
「這是大家的心意。這很像他的風格嗎?」
「嗯。」堀田出聲回答後,點了點頭,「妳應該瞭解吧。」
「當然瞭解。」
結婚四十年,丈夫仍然有節子不知道的一面。在丈夫眼中,節子也一樣。節子不知道其他夫妻的情況,但他們向來都有默契,不會過問彼此的過去。
「不好意思,沒辦法為你倒杯茶。」
「我才不好意思,稀里糊塗的,也沒帶伴手禮。」
「雖然他昏迷,但聽說也許可以聽到別人說話。」
「喔,是這樣啊,那要小心不能隨便亂說話。」
「他根本不懂得欣賞花,家裡多放幾盆觀葉植物,他就說像叢林一樣。」
「男人都一樣,我也差不多。不會覺得漂亮,只覺得很煩。」
「你太太最近還好嗎?」
「還是忙著在陽台上種花,她可以來探視嗎?」
「雖然我很想和她見面,但你們真的不必太費心。」
堀田隔著薄被,握住了丈夫的腳。
「他可能想把花帶回家給妳吧。」
這句話打動了節子。節子眼前浮現出丈夫抱著花束,靠在地鐵門上的身影。
也許是這樣。節子心想。
「很抱歉,我等一下還有事。」
堀田看著手錶說。
「啊喲,不好意思,耽誤你時間了,謝謝你特地來看他。」
節子發自內心地鞠躬道謝。原來堀田不是在回家前順道過來探視,等一下應該還要趕回都心。他在滿檔的行程中抽空趕來這裡。
「小茜還好嗎?」
「她很好,目前正在休產假,所以沒辦法來醫院。」
「是喔,我完全不知道,原來竹脇也當阿公了,我都沒有包紅包。」
「這已經是第二個外孫女了,兩個孩子只差一歲。」
節子為堀田仍然記得女兒的名字感到高興。
「堀田先生,你抱孫子了嗎?」
「我家也有兩個,但不是孫子,是兒女的兒女。」
「啊?兒女的兒女?」
「對,我還不願面對有孫子這件事。」
堀田竊聲笑了起來。丈夫也一樣,他曾經說,無論如何都不能讓外孫女叫自己「阿公」。
堀田臨走前探頭看著丈夫的臉,小聲對他說:
「喂,竹脇,你趕快醒過來,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
堀田的語氣聽起來不像在開玩笑。節子體會到丈夫曾經生活在家人無法瞭解的公司這個世界。
「呃,堀田先生,」節子對著堀田準備離去的背影叫了一聲,她必須告訴他這句話,「我老公很感謝你,他經常說,在各方面都多虧了你的照顧。真的很感謝你。」
堀田背對著她,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認,只說了一聲「告辭了」,就走出了病房。節子說這句話並沒有特別的意思,只是想代替丈夫說出心聲,但可能反而讓堀田不知所措。節子對名為公司的另一個世界一無所知。
她倚靠在窗邊,目送著堀田沒有撐雨傘,在紛飛大雪中離去的身影。
女婿
一個大叔在我面前滑了一跤。
大叔的雙腳踩空,然後整個人跌坐在地上。因為摔得太慘了,我忍不住笑了出來。
這可不關我的事。但既然在我面前跌倒,當然不能假裝沒看到。幸好這裡是醫院,即使受了傷,也不會有問題。
「你沒事吧?沒有撞到頭嗎?」
我把大叔扶了起來。他好重啊。千萬別把我也拉下去啊。
他似乎沒有撞到頭,但手肘好像很痛。
「手有沒有摔斷?要不要去急診室?反正就在旁邊。」
「不,沒什麼大礙。」
原本以為他是大叔,沒想到是個老頭。他看起來派頭十足,搞不好是哪家公司的董事長。
董事長?——該不會是總公司的董事長?聽說和丈人是同期進公司的同事,以前都住在員工宿舍,我老婆小時候很受他的寵愛。
不可能?那家大公司的董事長,怎麼可能來看我的丈人?
那個老頭看了我一眼。如果真的是董事長就慘了。因為我剛離開工地,身上還穿著工作服。
「皮鞋不行啦,雪開始積了起來,你看,要穿我這種鞋子。」
我用新買的安全鞋踢著地面。二十七公分。新宿萬年屋買的名牌貨。這是我老婆送我的生日禮物。真是太令人感動了。
「讓你見笑了,謝謝你。」
要跟我握手嗎?普通的老頭不會有這種舉動,他搞不好真的在貿易公司上班。
我決定放棄思考,邁開了步伐。因為丈人快死了,我現在沒這種閒工夫。
今天在工地時也一直沒辦法專心工作。手機一響起,我的心臟好像就快停止了。因為我太恍神,師父叫我不要爬上鷹架。
每走一步,安全鞋就更沉重。我很希望這是一場夢。我不希望丈人就這麼死了。無論如何都不希望,哪怕一直昏迷不醒也沒有關係,我希望他可以留在我身邊。
來到通往東樓病房的通道時,覺得自己無法承受。因為我不想看到丈人昏睡的樣子,也不想看到丈母娘突然老去的臉。
我買了一罐咖啡,在長椅上坐了下來。啊,好想抽菸。
照理說,我應該在家照顧孩子,讓老婆來醫院陪她老爸。無論哪個家庭應該都會這麼做。
但我盡可能不希望老婆難過,所以推說不知道怎麼泡牛奶,不想換尿布,自己跑來醫院。就連沒有血緣關係的我也這麼難過,我老婆是親生女兒,一定比我難過一百倍。
我隔著窗戶,抬頭看著窗外的雪。為什麼偏偏在這種日子下雪?一點都不美,也不浪漫,但罐裝咖啡還是這麼好喝,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我不由地想起第一次見到丈人的那一天。媽的,這樣不是會更難過嗎?
那也是一個飄著小雪的日子,師父帶了一個打著領帶的紳士來到工地。大家都以為他是屋主,但我立刻猜到他是茜的老爸。我真的很想找個地洞鑽下去,因為我還在想必須找一天去拜訪茜的父母,沒想到對方先找上了門。
在自動販賣機買了罐裝的熱咖啡後,並肩坐在木料上。師父不知道去了哪裡,那些工人都看著我們嘿嘿笑著。我真心希望那一刻爆發核武大戰。
——沒想到這麼好喝。
——啊?你平時不喝咖啡嗎?
——不,我喜歡喝咖啡,但從來沒有喝過罐裝咖啡。
然後,丈人一本正經地告訴我,暢銷商品之所以暢銷,並不是因為大家都買,而是因為一部分重度使用者每天都購買。
我完全不知道這種事,但總覺得丈人告訴了我很重要的道理,忍不住流下了眼淚。我流著淚問他。
——我不行嗎?
——沒有不行,完全沒有。
——我沒有父母。
——那又怎麼樣呢?
——而且年紀比她小,小了三歲。
——娶某大姊,坐金交椅。
——啊?什麼意思?
——男人娶年紀比自己大的老婆,以後會飛黃騰達。
當時,我有點打退堂鼓。不是當場想要逃走,而是如果道歉可以解決問題,我願意和茜分手。雖然我長得高頭大馬,但膽子很小。
——我高中也沒讀完,如果不是師父收留,我一定會去混黑道。
——你師父說你靠得住。
我忍不住站起來尋找師父的身影。別開玩笑了,他去了哪裡?
——雖然你年紀輕輕,的確有不少缺點。
我抬頭看著鷹架,斥責後輩:「喂,趕快做事。」他們都是高中或是高職畢業,甚至有人大學畢業,有建築師的執照,但因為我當年誤入歧途,所以資歷比他們深。不,不光是資歷而已,我天生手巧,再加上因為膽小,做事也很細心。
——我一無所有。
——這是理所當然,你出生的時候有帶來什麼嗎?
——但途中會擁有很多東西。
——人死的時候,什麼都帶不走。
我並不感激丈人說的話,但那些話就像是師父在刨木頭一樣,刨走了我的膽怯和自卑,我覺得自己深愛著茜。
——對不起,還勞駕你親自來工地。
我用在少年院學到的方式立正站好,向丈人鞠了一躬,我無法照本宣科地說什麼「請你同意茜嫁給我」,雖然我很想說,但在開口之前就先哭了。
師父終於現了身。太過分了,剛才到底去了哪裡?但我還是很慶幸並沒有爆發核武大戰。
那天晚上,丈人、師父和我一起去附近的居酒屋喝到不醒人事。三更半夜一起闖進位在荻窪的家,丈母娘和我老婆都嚇了一大跳。
怎麼樣?房子造得很不錯吧?師父說話的語氣,好像那裡是他的家。據說那是師父自立門戶後造的第一棟房子。
熱咖啡滲入冰冷身體的每個角落。我很想和丈人分享,但總不能把咖啡加在點滴裡。
他已經整整三天沒吃沒喝了,所以我也沒有吃午餐。我不是為了減肥,而是因為除此以外,無法為丈人做任何事。
我靈機一動,為丈母娘買了一罐咖啡。她以前應該沒喝過吧。我在工作外套的口袋裡緊緊握著熱騰騰的咖啡罐,為自己無能為力感到悲哀。
丈母娘應該反對我們結婚,她怎麼可能願意含在嘴裡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摔了的寶貝獨生女兒嫁給我這種人,但她自始至終沒有抱怨過一個字。
如果我知道在辦公室打工的工讀生是屋主的女兒,怎麼可能去招惹她?別看我這樣,我和女人之間從來沒有感情糾紛。
在交往一年之後,才知道丈人和師父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死黨。在茜的口中,就變成了「我爸和老闆」。
笨蛋,這種事為什麼不早說?而且酒後亂性這件事也很嚴重啊。雖然我老婆很聰明,也很漂亮,個性也很好,只是有點天然呆,她一定覺得這種事根本不重要。
當然很重要。我當晚就把師父叫醒,做好了被他用鎯頭敲破腦袋的心理準備向他坦白了一切。如果不是師母勸阻,差一點發生「木工慘殺事件」。
師父問我有什麼打算,我立刻回答:「我會娶她。」在向老婆求婚之前,就向師父拍胸脯保證這種事,真是太老土了。
那時候,茜在一家大型百貨公司上班。她不是普通的專櫃小姐,而是很氣派的儲備幹部。在因為下雨,工地停工的日子,我第一次去了新宿的百貨公司,買了訂婚戒指。
因為戒指很貴,我想可以為茜增加點業績,而且員工折扣也很優惠。晚上和她約在星巴克見面,然後去吃茜很喜歡的越南菜。雖然星巴克禁菸,我也很討厭香料。
你傻了嗎?茜嘴上這麼說,但用戴了戒指的手捂住臉哭了。
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遲遲不敢去荻窪的家。
即使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了,我仍然和當時沒什麼兩樣。現在仍然很害怕去加護病房,所以才會在這裡喝罐裝咖啡。
當時我打算入贅。反正我沒有父母,也沒有房子,對「大野武志」這個名字沒有任何眷戀。應該說,我根本不喜歡這個名字。
——如果你改叫竹脇武志(Takewaki Takeshi),別人不是一眼就會看出你是贅婿嗎?千萬別這麼做。
丈人很乾脆地說,好像什麼都沒有想。
不,他真的什麼都沒想,只覺得竹脇武志這個名字讀起來很奇怪。
他還說,不辦婚禮也沒關係,但我覺得不辦婚禮,茜未免太可憐了,所以辦了一場很低調的婚禮。其實也稱不上是婚禮,宴會上只有新郎和新娘穿著租來的衣服,其他人都穿便服。
我一直覺得,他們一定不喜歡我,不想讓親朋好友看到我這個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做粗活的男人。雖然我為這件事很煩惱,但不敢問任何人。
我和茜在交往時並沒有整天黏在一起,因為我們休假的日子不一樣,所以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這個世界上,遇到下雨才休息的工作並不多。如果工期很趕,會從天亮一直做到天黑,簡直和江戶時代的木工沒什麼兩樣。
所以,我和茜一起生活之後,才一點一點得知丈人和丈母娘的事。而且茜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雙方都沒有親戚。
我想,我應該一輩子都不會問。人生在世,能夠說出口的辛苦少之又少。我當然知道這個道理。
我一無所知,只知道丈人是國立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竟然同意茜嫁給我。是不是超厲害?
慘了,咖啡冷掉了。我激勵著沒出息的自己,邁開了步伐。走廊前方區隔這個世界和那個世界的白門越來越近。
我說老丈人啊,你還沒到嗝屁的年紀吧?我以後會為兩個女兒辦風風光光的婚禮,你一定要來參加。
丈人在開放的白色病房內沉睡。
窗外下著雪。簾子不要拉起來比較好,病房內很溫暖,冰冷的牆壁上染上了橫條紋的圖案,還有大小不一的影子。我覺得如果有這種壁紙似乎也不錯。
丈母娘撫摸著丈人的頭,在我遞上咖啡之前,她都沒有發現我來了。
「妳以前可能沒喝過。」
「當然有喝過。」
喔,是這樣啊。我打開拉環,遞給丈母娘。
「情況怎麼樣?」
「還是老樣子,要繼續觀察。」
雖然我不願往壞處想,但我總覺得有一種絕望的感覺。而且一直觀察,應該也不會有什麼改變。
「我今天會留在這裡,妳回家睡一下。」
丈母娘用嘆息回答。
「回去吧,我們兩個人都在這裡觀察也沒用。」
我老婆也說,一定要讓媽媽回家休息。病房內只有鐵管椅,只能去走廊上的長椅躺下來休息。
我還是不行嗎?如果我在家裡照顧孩子,茜來醫院照顧丈人,丈母娘就願意回家休息嗎?
不,不對,這是我的職責。我不會忘記結婚時,師父對我說的話。
「武志,你聽好了,當人家女婿要盡責。」師父平時向來不會說什麼令人費解的話,但那天我穿著租來的那件有家徽的和服禮服,他抓著我的肩膀,明確地對我這麼說。
我猜想他的意思是,有血緣關係的親子之間,即使敷衍一下也會彼此原諒,但如果是姻親關係,無論做任何事都必須盡責。
所以,我目前的職責並不是在家裡哄孩子睡覺。
「那我就去那裡躺一下。」
「不要躺那裡啦,妳去便利商店買個便當,趕快回家睡一覺。如果不去沖個澡,小心爸爸會討厭你。」
雖然我很希望可以說得親切動聽,但我就是做不到,我的詞彙量太少了。
「武志,謝謝你。」
看到丈母娘鞠躬道謝,我心裡超難過。
第一章
1
老友
向晚時分,天空下起了雪。
既不是傾盆大雪,也不是飄然而落,而是像牡丹花瓣的牡丹雪。打到擋風玻璃上變了形,馬上被雨刷抹掉的雪片宛如無常的生命。
時間很充裕,嘮叨的秘書也不在。
「對不起,可不可以繞去醫院一下?」
他沒有再多說什麼,看到司機在後視鏡內瞪大了眼睛。
「你身體不舒服嗎?」
「不,我朋友住院了。」
他可以感受到司機鬆了一口氣。公務車的司機就像是隱形人,但他覺得這個司機其實比秘書和下屬,甚至可能比家人更關心自己。即使沒有面對面,兩個人相處的時間也很長。更何況他在成為常務董事,有了自...

 3 則評論
3 則評論  共 1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2020/07/17
2020/07/17 2020/07/06
20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