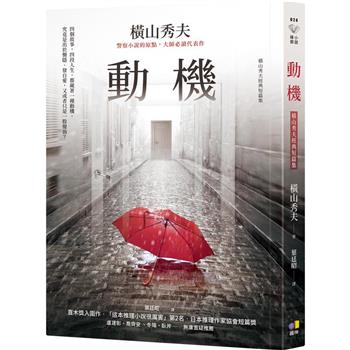自序
任何一個王朝的創立都是一次革命,任何一個國家的延續都需要建設,從「革命」到「建設」,需要一個戰略轉型,這個轉型是「驚險的一躍」,借用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話說就是突破一個「瓶頸」。
「革命」也好,「建設」也罷,這都是現代人用詞,在中國古人那裡,他們更多使用的是「創業」與「守成」。
或者用中國西漢時期著名的政治家陸賈的話來加以表述,那就是「取天下」與「治天下」。
在有案可稽的歷史中,陸賈是較早注意到「革命」與「建設」之不同的政治家,他那句「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至今讀來仍令人掩卷深思。
在由「革命」向「建設」、「驚險的一躍」的過程中,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可或缺,但第一位的要素仍然是人。
這裡所說的「人」形形色色,但細細想來,無非就是兩大類,一大類是所謂的「革命家」,一大類是所謂的「建設者」。
前者用古代話語體系加以表述就是「創業者」,後者則是所謂的「守成者」。唐太宗李世民曾經給臣子出過一個題目,叫做「創業與守成孰難」,這個問題還真的難住了不少臣子,從某種意義上說,創業難,守成亦不易。而由「創業」向「守成」平穩過度則是難上加難!
其故何在?
苦思冥想之後有以下幾點感悟:
一是「革命者」自身的原因,使得由「創業」向「守成」平穩過度異常困難。
由於天下是自己打下的,所以難免睥睨天下。在這些打天下者看來,曹操曹孟德的那句「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爾」都顯得有些過於謙虛。
在相當一部分打天下者看來,「天下英雄捨我其誰」才是唯一正確的標準答案!
這種心態往往決定了他們特別自戀、自愛、自以為是,以為真理永遠掌握在自己手裡,真知灼見也只能出自自己大腦,對於在「打天下」過程中所積累下的東西,無論是否合乎「治天下」,都一概照單全收、照方全錄。
於是乎,「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
現代經濟學中經常提到的概念「路徑相依」就此形成,而且憑藉路徑相依者自身所掌握的各類資源,特別是各類國家機器而日益「自我強化」。
有意思的是,「受命於天,人莫予毒」的心理,不僅使得這些創業者們在治國理政時特別自信,而且對於自己肉體生命的長生不老也超乎常人想像地自信——前些時候,一部電視劇中的主題歌以康熙皇帝的口吻說他「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
有許多評論家對此頗不以為然,以為是電視劇主創人員瞎編亂造,這實在有點冤枉了這些手無縛雞之力,只能靠一點稿費度日的文化人。
在筆者看來,「再活五百年」都有些保守,哪個帝王不想長生不老?要不然你把「萬歲」換成「百歲」或「幾十歲」試試,看他們會不會龍顏大怒,把你「即刻推出午門問斬」——假如你有幸生活在古代的話!
正是因為「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乃至長生不老,才會有秦代的徐福率五百童男童女東渡,才會有明朝的嚴嵩父子因善於與神仙溝通(撰寫所謂的「青詞」)而得寵。
正是因為對於自己的肉體生命過於自信或過於自愛,那些創業者們往往都很難在神志清醒的有生之年自動自願地把權力交到可能的「建設者」手裡,哪怕這個建設者是他的親生兒子——遍觀中國歷史,在生前神志清醒的情況下,出於自願將皇帝的權杖交到接班人手裡的帝王們幾乎為零。
至於形形色色的「太上皇」們,初看起來似乎是在神志清醒的有生之年把皇位傳給後代,但細細想來,他們往往都是出於不得已而交班。唐高祖、唐玄宗可謂其中的代表。而那些自願交班的太上皇們則往往是「形交而實不交」,自己雖不「垂簾」,但卻屢屢「干政」,宋高宗、清高宗乃是他們中的典型。
正是因為權力的交接往往是在交權者生命結束之後進行,遂使得接班者往往未經「ㄐ邀接」就先「上朝」,有心要有一番作為者也只能「半工半讀」,在做中學、學中做,無雄心大志者往往只能「蕭規曹隨」,等而下之者則往往只能「醉生夢死」!何談由「革命」向「建設」過度!?何談由「創業」向「守成」轉型!?
二是建設者的原因使得由「創業」向「守成」平穩過度難上加難。
從「建設者」的角度加以考量,可以有「能」與「為」兩個視角:孟子他老人家曾經說過:「挾泰山以超北海,此不能也,非不為也;為長者折枝,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如能解決好「能」與「為」的問題,「二代現象」就有可能「只是一個傳說」。
但令人遺憾的是,從秦二世到清世祖,「二代現象」一直如影隨形,揮之難去,成為一個「歷史鐵律」。
個中原因首先是個「能」的問題。許多二世之所以是二世,首先是因為他們在能力和水平上確實有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其自身所具備的能力與其所應承擔的職責之間往往存在著巨大的不對稱。
造成他們「不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來自外部的原因,也有來自內部的原因。
老爸希望他學的和他所應當學習和掌握的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不對稱,有時甚至是很不對稱;老爸所應教他的東西如「權謀之術」、「馭下之法」和實際上所教給他的東西之間往往也存在著一定的不對稱,有時甚至是很不對稱。
用現代術語來加以表述,就是老爸為他營造了一個理想化的「虛擬空間」,在這個理想化的「虛擬空間」裡,一切都非常和諧,非常有秩序!而現實生活中的真實物理時空卻處處是「非理性競爭」。
有老爸在的時候,這種「虛擬空間」就像當今流行的「second life」(第二人生)一樣,玩玩遊戲可以,一旦「game over」(遊戲結束),轉到現實中來,失去了老爸的羽翼,這些二世極有可能會顯得缺氧,甚至「腦殘」,最終或庸庸碌碌或抱恨九泉,這可真辛酸。
與「能」相比,「為」也同樣重要。由於江山並非靠一刀一槍搏殺得來,而是輕而易舉地獲得,遂造成了這些二世們的一種普遍心理,既然一切都早由命定,天上可以輕易掉下餡餅,那還有什麼必要費盡氣力有所作為呢?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由於其老爸是人中之傑,「叱吒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與老爸相比,難免使得這些二世們產生強烈的自卑心理,老爸生前便已往往生活在父輩巨大陰影裡,而且老爸與世長辭之後往往也自愧不如,不求進取,覺得再怎麼「為」也「為」不過老爸,既然如此何必再「為」呢!?
於是乎,及時享樂,「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就成了座右銘,什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他們看來實在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換句話說,「這個可以沒有」!
當然,「建設者」中也並非個個都是二世祖胡亥,也不乏一些想要有所作為,自身也具備一定的能力與水平者,但這些人往往也並不一定能順利穿越歷史的「瓶頸」,完成「驚險的一躍」,其中原因又何在呢?
在筆者看來,這其中又涉及到了「制度設計」和「文化環境」。縱觀中國歷朝歷代封建王朝,主要有兩項制度設計,一個是所謂的「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另一種是當繼承人繼承皇位年紀尚小時,為其選擇一個「總經理」輔助團隊——假如我們把整個帝國比作一間巨大的公司,把皇帝比作「董事長」的話。
前一種制度設計形成了所謂的「家天下」,其含義是整個江山都是我們家的,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也;而後者則形成了所謂的「托孤」和「顧命大臣」制度。由於人都是生活在物質世界裡,「唯有人心深似海,近在咫尺不能測」,生前的托孤往往難以抵擋死後花花世界的名與利的誘惑。
清代著名詞人納蘭性德曾經不無感慨地寫道「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寫的雖是「男女之情」,但以之來形容「君臣之誼」也並非不可。
歷史的經驗證明,那些被托孤的顧命大臣,並不一定像在開國皇帝病榻前那樣指天畫地、信誓旦旦地鞠躬盡瘁,有時反倒成了「廢孤」、「害孤」的「要命大臣」。
駱賓王在《為徐敬業討武曌檄》中說「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罵的雖然是被稱為「牝雞司晨」的武則天,實際上以之來形容那些並不忠心耿耿的顧命大臣「總經理」團隊也不為過!
影響「二世」成為短命的「二世祖」的因素當然還包括「文化氛圍」。
縱觀中國歷史,雖然孔子被一代代累積抬高到「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的高位,但在很多時候人們卻更崇奉「power is right」(強權即真理),尤其是在兵荒馬亂的亂世,當廢掉一個君王就像換一件衣服一樣不受社會輿論譴責時,二世皇帝成為「短命的胡亥」的機率就顯得異乎尋常的大了。
那麼,怎樣才能避免自己的繼承人不成為短命的二世呢?
這是每個開國皇帝無時無刻不思茲念茲的問題。這個問題,秦始皇想過,但他只想到了結果:使子孫千秋萬代而為君,卻沒告訴繼承者方法,只想尋求長生不老之藥延長自己的生命;漢高祖劉邦想過,但他只是給兒子寫了一封書信,信中說:「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他想通過讀書以史為鑑轉型,但並沒有真正去做!
在不才如我看來,不提供方法而僅提供結果,或者想了而不去做,那說好聽點是有理想,說得難聽一點則是白日做夢痴心妄想!
也許有讀者問,秦始皇不行,漢高祖不靈,你有什麼「藥方」沒有?
我?本人雖然姓「張」,但並非「悟本」大師,既不能「蒜你狠」,也不會「『豆』你玩」,但還是想提供一點思路與讀者諸君分享:
在我看來,要解決「二代問題」,不妨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著手。
所謂「時間維度」就是要「打提前量」。
我的另外一個本姓前輩、名作家張愛玲女士曾經說過「出名要趁早」,在不才如我看來,培養接班人也要趁早。
據說李鴻章當年曾以學生的身分向老師曾國藩討教怎樣才能做大事,曾國藩不假思索地說了一句話,叫做「做大事以找替手為先」,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為先」曾國藩沒有說出來,那就是「找替手應以早發現早培養為先」。應當通過相應的制度設計,讓自己滿意的接班人早點進入「實際操作」階段,最好能夠「扶上馬,送一程」。
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其實很難,難就難在最高權力的誘惑,難就難在相關的信任成本過高,溝通成本過大!
所謂「空間維度」,就是要拓寬「總經理」團隊的遴選渠道,「顧命團隊」應五湖四海,而且要錯落有致。
事實證明,在一個小圈子裡遴選出來的人往往不一定有利於國家的治理,不一定對二代皇帝百分之百的忠誠,而拓展遴選範圍不僅可以解決顧命者的「才」的問題,也可以通過相應的制度設計解決其「德」的問題。
當然,如果能跳出「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局限更大範圍地選擇接班人,如果能夠將「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可能會更好。
前者用現代話加以表述就是「打破家天下」,後者用現代話加以表述就是「君主立憲」或「實行現代企業制度」——可惜的是,歷史是不容許「彩排」的,我們可以通過「假如」超越歷史,但真實的歷史是不能超越的。
「人事有代謝,往事成古今,江山留勝蹟,我輩復登臨!」
真實的歷史不能彩排,真實的當下和理想的未來卻可以設計。
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李世民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衷心希望這本「卑之無甚高論」的小書能夠給讀者諸君一些啟發。
張志君
二○一○年九月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