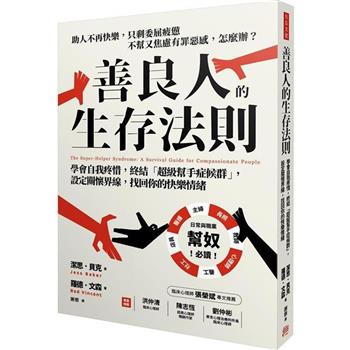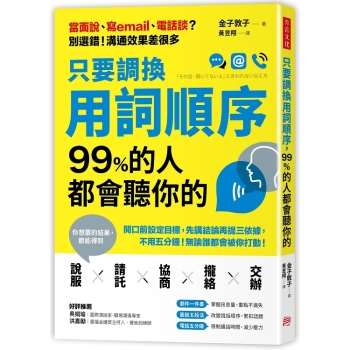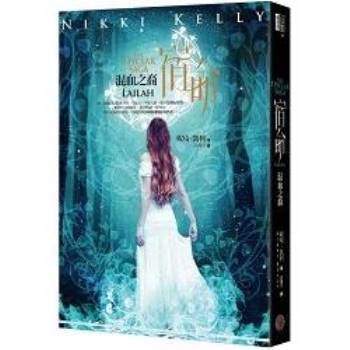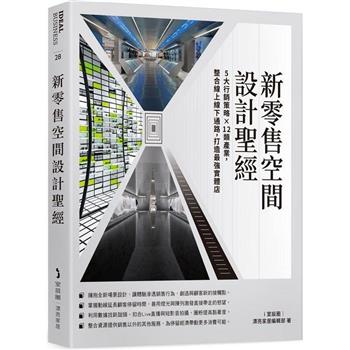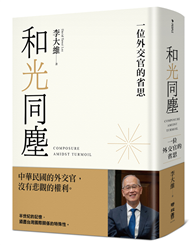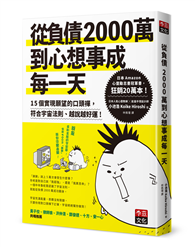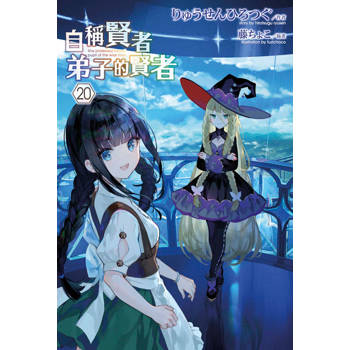名人推薦:
【媒體高度推薦】
◆這本回憶錄偉大的力量在於它既貪婪又謙遜的好奇心。在失去視力的情況下,以盲文化史作為切入點,自始至終都把失去視力視為一個探索的契機,而非一場悲劇。——《大西洋雜誌》
◆苦澀脆弱、深思熟慮而充滿希望的寫作!它迫使視力正常的讀者不僅要面對失明的悖論,還要面對看得見的迷思。本書探索了殘疾最令人不安的角落,堪稱奇妙的跨學科漫步!——《紐約時報書評》
◆令人振奮又令人心碎!書中最深刻的部分是純粹自傳的親密時刻。他以自身經驗作為盲人和明眼人之間的橋樑。——《華爾街日報》
◆結合知性與感性的細膩筆觸,邀讀者共同記錄感官新世界,以及對常態性的盲目來場大冒險。——《華盛頓郵報》
◆深刻動人的回憶錄!作者講故事、探索歷史和文學的敏銳度在記錄自身遭遇時隨處可見,以細膩幽默的敘事和對主題的謹慎處理,邀所有人重新思考對世界的認知、面對不確定性和承擔新身分的意義。——《衛報》
◆直截了當地說,這是我今年讀過最棒的一本書,也是我一生中認為的最佳書籍之一。這是一部帶有研究性質的回憶錄、動人的文化史,以及關於失明、殘疾和適應的傑出故事。我對本書的熱愛和敬佩無以言表,更對它能出版所預示的殘疾寫作新時代感到興奮!——索非亞•M•斯圖爾特(Sophia M. Stewart),2023年最受期待書籍
◆李蘭用文化歷史和殘疾政治寫下他逐漸失明的過程,顛覆了我們自以為理解的事。這是今年最好的書籍之一。——《芝加哥論壇報》
◆李蘭以引人入勝的方式寫下他與視力不斷變化的關係。本書堪稱回憶錄、報導和文化評論的挑釁性結合佳作。——《國家報》
◆李蘭提供了失明議題的迷人簡史,例如對殘疾權利運動的調查,以及自身如何理解失明的意義、掙扎與深刻的洞見。他以誠實而脆弱的方式表述自我,最終讓讀者理解他何以做出結論:視網膜退化的過程,成為我生命中最具生產力的經歷之一。他的情感真摯而不矯飾,這場探索為讀者帶來了豐富的回報。——《科克斯書評》
◆這本資訊豐富而引人入勝的回憶錄,將吸引那些期待以輕鬆方式拓寬對殘疾生活的認識的讀者。——《圖書館期刊》
◆李蘭敏感深刻地講述他逐漸過渡到盲人社群的故事,生動描述了新的感官知覺和情感,並概述了有關盲人訓練的爭議。他的經歷將與自閉症社群及更廣泛的群體產生強烈共鳴,極具價值!——天寶‧葛蘭汀(Temple Grandin,《圖像思考》作者)
◆李蘭巧妙平衡了個人、歷史和政治,他輕柔歌頌(用「記錄」一詞太冰冷)逐漸失明的過程,這是一本關於失明史和那些建立無障礙世界先驅者的偉大著作。更重要的是,他將他和家人面對無數新挑戰的感人故事編織進這幅更大的畫布中——以開放心態和豐富智慧,無畏地共同面對。——大衛‧艾格斯(Dave Eggers,《怪才的荒誕與憂傷》作者)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前言——結束開始了
我寫作的此時,即將失明。這種感覺沒聽起來的那麼戲劇性。眼前的文字並沒有在我打字同時隨之消失,我舒服地坐在日光浴室,太陽如常升起。我可以清楚看到莉莉坐在我旁邊,身上穿著條紋睡衣在閱讀。看得見的世界正在消失中,不過倒不匆忙。同時間,它既像是大災難、也像是平常事——就像是閱讀一篇關於文明因為氣候危機而即將崩塌的報導文章,然後放下雜誌,騎著單車徜徉在和煦的春日早晨。
視網膜色素病變(簡稱RP)無藥可醫。我二十多年前就被診斷出這種病,因此通常每兩年要見一次眼科醫師。每次去,我都會進行一整天的測試,但這些檢查只不過是在追蹤它退化的情況。檢查結束之後,我們會簡短討論關於幹細胞或基因療法在將來的承諾。
上回看診,醫師讓我看了顯示我還剩下多少視力的圖表。它讓我想起在熱水裡融化的冰塊:兩小片搖搖晃晃的橢圓形在中間,在它兩邊是兩個細長條的形狀。搖搖晃晃的橢圓形代表我仍然擁有的「中心視力」,而旁邊條狀的是我的「周邊視力」。我擁有的視力大概是有完整視力的人的6%。我的醫生優雅地皺起眉頭,指著那細長如薯條的形狀:「當它們消失了之後,你的行動力會有更多限制。現在你四處走動,靠的就是這兩條殘留的周邊視力。」她一派專業且面無表情,說話時既無欣喜也不憂傷。
要描述我看不到什麼,有些出乎意料的困難,主要是因為我的大腦很快就適應了。我有嚴重的「隧道視力」,但我所看到的並不像一條隧道;隧道周邊的牆壁並不可見。我對自己失明的樣貌有最強烈感受是在視力出現變化時——當我應該能看到的東西、最近還看得到的東西,突然間看不到了!
我在自己家裡,走路會撞上多年來不曾移動過的家具。我把杯子暫時放下,然後它就不見了。我費盡千辛萬苦,用我搖搖晃晃的橢圓體和細長薯條狀組成的殘餘視力,反覆翻耙整個桌面,當我終於找到杯子,它其實正好端端立在短短幾星期前還可稱之為「顯而易見」的位置。它依然明顯——只不過我的視力越來越不容易看見。
RP 並無痛感,除非你把猛烈碰撞無生命物體所累積的瘀青也算進來,像是撞到沒推進去的椅子,或是沒有關好門的櫥櫃。目前為止,最痛苦的部分在於不知道。這些日子,我過的是推測模式的生活,就像科幻小說作家一樣,看著現在,試著想像未來。
當我煮晚餐,接兒子奧斯卡從學校回家,或是在不熟悉的城市尋找從機場到火車站的路,我會問我自己:等我看不到時,這會是什麼樣子?我感受每件事都是用這種弔詭的雙重視野:透過看得到的雙眼,以及透過看不到的雙眼。雖然大部分的未來都難以看分明,被各種偶然意外的迷霧所籠罩,但我的未來可說是雙倍的難以預想。水晶球依然雲遮霧罩。
但是我不能就此接受失明是眼睛的死刑。我的視力越弱,我對失明的世界,以及在那裡存在著哪些可能,就變得益加好奇。於是,我出發去找尋,想找出在眼前等待著我的世界,一個更準確的圖像。
***
失明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人類在根本上是憑著視覺去理解和體驗,以致於失明者有必要自成一格。早期科幻作家H.G.威爾斯的短篇小說〈盲人國度〉直接從字面上採用這個想法,想像一個盲人的文明,他們活在隱密的山谷,對明眼人的世界一無所知也毫無需求。
某天,探險家努涅茲因落石坍方而與探險隊分散,結果跌入了這個被遺忘的山谷。在那裡,他發現了盲者的傳奇國度,他們失去視力已經存活了經歷十五個世代。他所見的每個人都是天生眼盲,一如在他們歷來好幾代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他們甚至不理解「視力」的概念;他們的語言裡沒有「看見」這個詞。隨著他逐漸掌握狀況,努涅茲帶著高度自信,彷彿唸咒般反覆重述古老的諺語:「在盲人國度,獨眼者稱王。」
我發現自己朝著失明方向前進的方式有點像努涅茲,如同一個意外、好奇、時而戒懼的訪客來到這個陌生而經常是美麗的國度。就目前而言,我感覺自己是個外地人。我的部分視力,讓我跟那些無法和我一樣讀取所有視覺訊息的人們隔了一層;我永遠無法像天生盲目的人一樣,成為盲人世界的「在地原住民」。我的大腦以視覺的方式發展,而要學習盲人的技能,從用手指和耳朵來閱讀、到在腦中繪出城市地圖,都需要我與周遭世界的連結方式做出劇烈的轉變。但是不同於威爾斯的角色最終逃離了盲人國度,我必須留下來,慢慢成為歸化的公民。
一個盲人,只要在公共場合待得夠久,保證會聽到一套例行的尋常問題,至少在美國是如此。在公車上或是人行道上,會有陌生人轉頭來問,你怎麼吃飯?誰幫你穿衣服?你有辦法自己簽支票嗎?這類問題著實令人惱火,它暗示著盲人世界就像小嬰兒的世界,在這裡,盲人沒有明眼人的幫助甚至無法套上襯衫,或是用叉子把食物放進嘴裡。它們加劇了殘障的體驗所帶來令人苦痛的差異——別人不會在排隊買早餐的墨西哥捲餅時,被問到他要如何完成日常生活裡最基本的任務。
不過,像我這樣的人(自覺仍只是盲人國度裡的觀光客,還不確知何時會真正搬過來),這些問題則帶有迫切感:我需要知道我將如何生活,以及我會成為什麼樣的盲人。我要如何獨力旅行?我如何寫字、閱讀和工作?我要如何看電影、欣賞藝術?做為一個盲人爸爸,我要如何體驗兒子從小男孩轉變成青少年的旅程?
這本書不僅是我對視力喪失的個人體驗的描述;它是我有意識地進入廣大盲世界旅程的一部年代記。寫這本書,讓我比現階段視網膜的退化程度更深入地進入失明的世界。隨著視力逐漸喪失,我感覺到自己有了新的動機,要運用知識和直接的體驗來緩和我的猜測和恐懼。
過去幾年來,我在全國各處旅行,探索每一個我所能想到失明和當代生活有所交集的地方。盲人不像聾人,可以從聾人群體所打造組織良好的大型機構中得到助益。部分原因或許是,聽得見的盲人並不會遭遇聾人具備的語言溝通障礙,也因此,他們從不需要去發展一套獨特的共用語言。
語言是建構群體最重要的一項功能,手語也不例外。在美國,手語群體在語言學上和文化上都是豐富多樣,就和其他的語言群體一樣。許多聾人學生形容他們初次來到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全世界唯一專門為聾人設立的高立德大學,有如一場神啟的體驗。他們整個童年時光都感受被孤立於聽人的家人和同齡者之外,突然之間,他們置身於聾人文化和語言世界,無需再依賴輔助工具來偷聽對話或參與課程。
然而,我還是發現了幾個盲人集中活動的地方。在佛羅里達,我參加了全美最大的盲人組織的全國大會,在奧蘭多巨大的會議中心,我漫步在數以千計的盲人之間,彷如無數手杖敲擊和碰撞的森林,我第一次感受到在一個空間裡盲人數量多於明眼人的力量。我會見來自不同政治光譜的盲人運動人士,有些人每年會拜訪他們的國會議員,有些人則一手拿著白手杖、一手拿著抗議紙牌上街示威。
在加州和紐約,我遇到了在數位無障礙尖端領域工作的盲人天才,他們鎮日焊接電路板、設計3D列印物件和剪輯電視原聲帶。我感覺自己被這些沈迷於媒體的創客所吸引,他們似乎把失明當成了刺激創意和發明的一項特徵。
我遇過有人說,他們的失明根本不算什麼——那只是身上的一個屬性,就像頭髮的顏色——也有人讓失明完全定義並翻轉了他們的人生。有的人對談論失明的醫學原因避之唯恐不及,更遑論治療的可能性;但也有人與做研究的眼科醫師培養出私人情誼,關於細胞和分子療法的各種專業術語都能信手拈來。我對所有這些立場都抱持同情,甚至會思考自己該採取哪一種態度。
我試圖去理解失明如何改變我做為一個讀者和作者、做為丈夫和父親、乃至做為公民和天生獨享特權的白人男子的身分。COVID-19 疫情期間,我去了一趟科羅拉多,在一個激進的盲人訓練中心待了兩個星期。每星期五天,每天八個小時,我戴著遮蔽視力的眼罩,只仰賴一組盲人指導員,重新學習如何使用瓦斯爐和廚師的刀具,以及如何穿越丹佛繁忙的十字路口。這只是對失明的一個模擬,但是它幫助我理解,當我殘留的視力冰消瓦解後,我可能需要如何對應,以及我可能會變成什麼模樣。
從某些方面來看,想弄清楚自己會成為什麼樣的盲人,已經和我持續想弄清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或者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難以區分,這和我殘障無關。隨著我邁入四十歲大關,情況似乎變得很明顯,沒有人能夠完全逃脫始於青春期的、既痛苦但也令人興奮的自我探索和自我重塑的過程。我越是探索失明的世界,就越覺它是個遠超乎殘障的領域。
所有盲人與更廣泛世界的交集和介入,都伴隨盲者認知到與明眼人的社會接觸所經驗的邊緣化,不論是直接明白的壓迫形式(盲人基於殘障而遭拒絕就業或教育的機會),或是更隱蔽和細微的貶抑(盲人在完成生活基本任務時,令人感覺無能或是神奇的日常經驗)。我感受到與這個世界強大的連結,同時也感受到持續的不適和疏離。這是變成殘障者的一部分體驗——進入到一個每年有數百萬人無奈加入的社團。
蘇珊.歐琳(Susan Orlean)在一九九八年作品《蘭花賊》中描述「蘭花收藏圈」這個激烈競爭又孤絕封閉的世界,在她筆下,他們也像是一個家庭:「這是在做為個人,和成為某個大我的一部分之間,取得平衡的方式,儘管等號的兩端彼此會危及另一方。」失明正把我帶入這一切:一個吵鬧、煩人的家庭和一個充滿愛和支持的家庭;一個有趣的嗜好,這裡的同好可以帶來激勵和喜悅,同樣也令我惱怒和沮喪;一個我既擁抱又嫌惡、定義我又與真正的我全然無涉的身分認同。
視網膜色素病變(RP)的病情進展——緩慢、逐漸變窄的隧道視力,通常以未知日期的喪失視力告終——是製造含糊不明的強大生產機器。我已經非常熟悉生活在其中的痛苦:不是完全失明、但也不完全視力正常。我曾經打電話給一個在幾十年前就失去可用視力的RP 患者,詢問他關於電腦的建議。他說我是個「幸運的混蛋」,在我這樣的年紀還能擁有中心視力,並說,他要是能看到電視或筆電螢幕,「要他死都願意!」
不過接著他由衷地感嘆:他覺得現在的日子要比他逐漸失去視力的那段期間容易得多。「我不需要從一起床就開始擔心今天視力會變什麼樣子!」他告訴我:「我知道眼睛看不到了,我可以繼續過我的生活。」
RP 的臉書頁面每天都有更新的內容,有人不敢在大庭廣眾打開折疊手杖,因為怕被指責是「假瞎子」,他們部分失明的困境(打翻飲料、要求協助搭車)被即將「真正」失明的陰影所籠罩,他們不斷跟自己保證「還能開車」或「還能工作」或「四處走動都還沒問題」,因為他們如此幸運仍能擁有逐漸縮小的中心視力。但如果有一天,他們無法再依賴眼睛,只能希望上帝保佑。
閱讀那個網頁,是我最有罪惡感的樂趣之一。捲動無止盡自憐自艾的貼文,中間穿插著啦啦隊式的回應(「你辦得到!」「RP 的強者!」),我感受到另一種疏離:它不像盲人社群,而比較像疾病受苦者的社群,祈禱著某種療法的出現,同時活在無可避免的失明終將到來的恐懼之中。不過,正如評斷這些同行的旅人那般容易,我同樣陷入——以我自己的方式,通常不是在臉書上——一模一樣的自憐自艾、恐懼、和足球教練式鼓勵的循環。
我們全都活在這種含混不明之中:從2021年開始,許多我認識的人一次又一次慶祝COVID-19 疫情的結束,每次又被另一個新的變種病毒、新的死亡數陡升所打消,直到我們終於不得不接受病毒永遠不會離去,而一個更複雜、更令人困惑、且更令人無比不適的流行病現實將持續存在。
如此多的生命與消逝,存在於二元對立的空間之間:一樁從未真正結束關係的離婚;帶著太多包袱到新目的地的遷移;或臥病多年、已不復記憶中的模樣、行將就木的親人。在這些情況下,極端或許令人痛苦——斬斷關係、遺忘故鄉、哀悼逝者——但事物的終結也帶給我解脫。在盲目和視力健全間怪異的模糊陰影中生活,迫使我去正視這點,並試著去放棄讓問題得到解決的迫切渴望。我傾向全力以赴,正面迎戰失明,熟練掌握所有需要的技能,然後繼續我的生活。但是RP 的現實卻讓人難以全然擺脫視力。我感覺受困於既有視力,正如我受困於我所失去的視力一樣。
在科羅拉多,我帶著眼罩學習拿著白手杖摸索路途,我必須進入不熟悉的環境並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我會聽著手杖金屬尾端撞擊不同表面的回聲——那是地毯、那是地磚、這聽起來應該是金屬防火門…….與每種不熟悉的事物互動大抵如此——我們逐步摸索穿過一個原先可能顯得怪異而不友善的環境,但是只要有足夠的堅持、一點探索的精神,踏實而明確的輪廓就會逐漸顯現。空間變得熟悉,最後就感覺就是你處在已經住了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房間。
這是寫作「失明」這個題材所帶給我的,它不再是一個傳說中的科幻國度,反倒已成為一個真實的所在,住著真實的人。我希望這本書能鼓勵明眼讀者同樣去發現失明這個原本看不到的領域,以及他們原先可能不曾考慮過的生活和思考方式。
明眼的觀光客到「盲人國度」一日遊,往往會帶走幾個常見的紀念品。其中一個是偽裝成為同理心的憐憫:「他們的生活是多麼困難啊!」有人會做出如此結論,更多人則默默確認,感謝老天爺給我的視力。此外,它也滿足了偷窺式的好奇:他們怎麼吃飯,或怎樣從商店找到回家的路,或是,他們真的知道自己的伴侶長得多迷人?不過,待的稍久一點,則會帶來較多的哲學問題:我們是怎麼認識這個世界的?在我們感官的階級中,視力是否真有最頂端的獨尊地位?有多少感知是在眼中發生?又有多少是在我們腦中發生,不論提供它刺激的是哪一個感官?
這些仍然困擾我的問題,來自於我所見到、存在於殘障的價值——我從失明發現的美和力量——以及殘障所帶來如此明確的失落感和排斥感之間的衝突。導致嚴重疏離感的東西,如何成為帶來成長和喜悅的來源?讓我們與大部分世界格格不入的東西,為何又讓我們更接近世界?活動人士有時候用呼應其他被邊緣化群體的說法,來定義他們的殘障——從他們受壓迫的身分找出自豪之處。但是,盲者的自豪是否需要全然棄絕視力?比如說,能不能有一種辦法,讓我即便接受了剛好出現的神奇療法,但依舊真心擁抱自己的失明?
隨著我失去視力,我希望在奧斯卡、還有莉莉、在我心中、以及在世界上,培養這種盲人的形象——這個盲人,在自己的人生裡是積極主動的主角。我在許多呈現盲人的電影、書籍、藝術或是電視影集裡還沒有見過這樣的形象,這些作品往往若不是嘲笑或貶抑失明,便是把它當成密教超能力的來源,再不就是以高人一等的憐憫態度看待失明——將它視為一種隱喻,而非一個日常的生活方式。
然而,在別處,我尋到了我想見到的形象:那就是,在真實盲人國度我所遇到的人身上,在他們多彩豐富的奮鬥、適應、和探險的故事裡。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