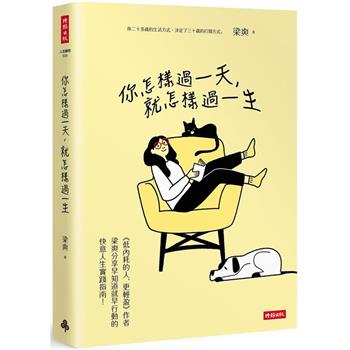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約書亞.史柏林的圖書 |
 |
$ 364 ~ 468 | 凝視約翰.伯格: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
作者:約書亞˙史柏林 / 譯者:林鶯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1-20 語言:繁體書  共 1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柏林是德國首都,也是德國最大的城市,現有居民約340萬人。柏林位於德國東北部,四面被布蘭登堡邦環繞,施普雷河和哈弗爾河流經該市。柏林也是德國十六個邦之一,和漢堡、不來梅同為德國僅有的三個城邦。
柏林是德國首都,也是德國最大的城市,現有居民約340萬人。柏林位於德國東北部,四面被布蘭登堡邦環繞,施普雷河和哈弗爾河流經該市。柏林也是德國十六個邦之一,和漢堡、不來梅同為德國僅有的三個城邦。 柏林是歐盟區內人口第3多的城市以及城市面積第8大的城市。它是柏林-布蘭登堡都會區的中心,有來自超過190個國家的5百萬人口。地理上位於歐洲平原,受溫帶季節性氣候影響。城市周圍三分之一的土地由森林、公園、花園、河流和湖泊組成。據有關統數據統計,柏林總人口共有3,405,259人。
該根據考古發掘,柏林地區在八萬年前已經有人類活動。該第一次有文字記載是在13世紀,柏林連續的成為以下這些國家的首都:普魯士王國、德意志帝國、威瑪共和國、納粹德國。在1920年代,柏林是世界第3大自治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城市被分割;東柏林成為東德的首都,而西柏林事實上成為西德在東德的一塊飛地,被柏林圍牆圍住。直到1990年兩德統一,該市重新獲得全德國首都的地位,駐有147個外國大使館。
柏林無論是從文化、政治、傳媒還是科學上講都稱的上是世界級城市。該市經濟主要基於服務業,包括多種多樣的創造性產業、傳媒集團、議會舉辦地點。柏林扮演歐洲大陸上航空與鐵路運輸交通樞紐的角色,同時它也是歐盟內遊客數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主要的產業包括信息技術、製藥、生物工程、生物科技、光學電子、交通工程和可再生能源。
柏林都會區有知名大學、研究院、體育賽事、管弦樂隊、博物館和知名人士。城市的歷史遺存使該市成為國際電影產品的交流中心。該市在節日活動、建築的多樣化、夜生活、當代藝術、公共運輸網絡以及高質量生活方面得到廣泛認可。柏林已經發展成一個全球焦點城市,以崇尚自由生活方式和現代精神的年輕人和藝術家而聞名。
![]()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影像評論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郭力昕|專文推介】
「除了當畫家之外,我也努力思考藝術,同時為藝術而思考。不過我努力超越畫筆之尖來思考,結果,主要是我對藝術的關懷催生了我整體的政治信仰和社會信念。根本不是我把政治拖入藝術裡,而是藝術把我拖入政治裡。」——約翰·伯格
約翰˙伯格是戰後歐洲舉足輕重的左翼人文思想家和創作者之一。身為小說家,他贏得一九七二年的布克獎,卻於領獎時大力抨擊該獎項,並把他一半的獎金捐贈給左派政治組織「黑豹黨」;身為電視節目主持人,他以《觀看的方式》改變了人們觀賞藝術的方式;身為說故事的人和積極參與政治的行動者,透過他的著述捍衛勞工、移民和全世界受壓迫者的權利和尊嚴——直至二〇一七年一月過世,他始終如一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家。
藝術及受壓迫者是約翰˙伯格終其一生最重要的關懷主題,並深遠地影響其生命及作品。《凝視約翰·伯格: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A Writer of Our Time: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Berger)圍繞著一系列既關於個人又屬於大時代歷史的分水嶺事件建構,追溯伯格的發展,從早年為英國報刊撰文的文化批評鬥士,歷經一九六〇革命年代意氣風發的歲月,直到晚近伯格重塑自己成為鄉間說故事的人。
本書作者——約書亞˙史柏林(Joshua Sperling)爬梳大量資料與原始檔案,利用未曾發表過的第一手訪談,旁徵博引撰寫約翰·伯格生命軌跡的細節,陳述與論評深入挖掘爭議的關鍵,完整揭露出伯格這位異常複雜且韌性十足的人物。伯格的思考及關懷從何而來?又將引領眾人往哪去?終將成為我們叩問困擾整個世代宏大命題的關鍵。
作者簡介
約書亞˙史柏林(Joshua Sperling)
約書亞˙史柏林生於紐約市,在加州長大。他的文章出現於《布魯克林軌道》(Brooklyn Rail)、《格爾尼卡》(Guernica)、《電影季刊》(Film Quarterly)、《跳接》(Jump Cut)和《布列特雜誌》(Bullett Magazine)等刊物上。他擁有耶魯大學「比較文學、影片與媒體研究」的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
譯者簡介
林鶯
畢業於臺灣大學外文系。曾任職於漢聲和張老師月刊,現專事翻譯。譯有《艾倫.圖靈傳》、《天翻地覆》、《一次讀懂心理學經典》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