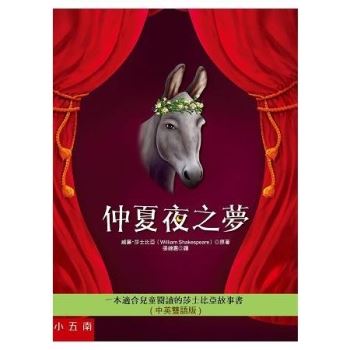諾貝爾文學獎大師葛拉斯非小說的第一次
首度對台灣讀者公開的詩與畫
台北市立美術館11月28日同步展出!
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是當代德語文壇的國寶,但鮮少人知道他也是當今極少數跨領域的傑出藝術工作者。自1948年起,葛拉斯便進入杜塞道夫藝術學院(Düsseldorf Academy of Arts)學習,是一位深受專業薰陶的藝術創作者,舉凡水彩、雕塑與版畫都有豐富的作品。今年適逢葛拉斯八十歲生日,北美館將於2007年11月28日與德國伍茲美術館(Wuerth Museum)、台北德國文化中心合作,展出葛拉斯手繪的110餘件水彩作品,這批畫作可說是葛拉斯創作生涯中獨具特色、文學價值極高的繪畫創作。
本書正是這次精彩展出的作品全集。這批作品創作於葛拉斯心境苦悶的階段,藉由水彩透明澄澈的質感,他將德國鄉間各種自然景緻、動植物,甚至是人工物,一一描繪下來,並以詩篇敘述它╱牠們,讓文字成為繪畫的內涵,彼此言說、對話,傳達豐富的想像色彩,同時流露幽暗深邃的寓意。
當中有葛拉斯的自述心境、雜詠,也暗藏深刻的政治暗喻與他對社會議題的影射,是帶領讀者深入德國經典作家幽微心境的難得之作,一同分享文學大師深邃的眼中世界。
作者簡介:
鈞特‧葛拉斯 Günter Grass
德國作家,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的成長身受世局動盪的影響,作品具有強烈的自傳色彩,取自鄉間見聞,使用地方俚語;加上豐富的想像力與犀利的文字精準地掌握德國人對戰爭的反省心理,形成史詩般的寫作風格。
《錫鼓》(1959)是葛拉斯發表的第一篇長篇小說,因其對人性的細緻描寫、主題的聳動與深入的批判性,使得他得以揚名國際。瑞典皇家學院榮此形容葛拉斯:「他肩負起回顧現代史的艱鉅任務,一一喚起眾人所否認、所遺忘的一切,他追溯受難者、失敗者和人類想要拋諸腦後的各種謊言,原因是世人曾一度相信這些謊言。文學獎是獎勵葛拉斯所有的作品,包括他今年才問世的新作「我的世紀」;他的成名代表作《錫鼓》將毫無疑義地成為二十世紀流傳千古的文學作品。」
葛拉斯不但以小說馳名,也是傑出的詩人、劇作家、雕刻家與畫家。他曾著有詩集《風信雞的長處》、《三角軌道》等;劇本《洪水》、《平民試驗起義》以及為數眾多繪畫與雕塑。葛拉斯的藝術猶如他心靈世界的反映,通過豐富的創作經驗,他以視覺藝術再現小說的意境,讓其敏銳幽微的情感與心靈不僅行諸文字,也具體呈現在視覺的形式語彙中。
譯者簡介:
張善穎
˙1963年出生於台北。
˙畢業於台灣大學哲學系、三民主義研究所。
˙1995年獲時報文學獎新詩首獎
˙德國蔚慈堡大學(Universität Würzburg)哲學系。
˙2001-2004年間,旅居德國。
˙台北護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曾出版《女人是天生的收藏家》、詩集《描金的影子》、《Paris, Paris》。
章節試閱
《給不讀詩的人》譯後記
文/張善穎
細心的讀者很快會注意到,本集中的譯詩似乎比原詩來得長些。
我並非沒有試過像葛拉斯一樣,使用更簡潔的表達方式,但就是行不通。原詩有時候兩三個字就另起一行,這不僅對譯詩的達意是一種嚴苛的考驗,即使只是就詩句的形式來看,長短差距過大也不很像樣。如果勉強保持簡潔,結果或許就會成了「不可卒讀」。詩本身已經是一種不那麼貼近讀者的文類了,現在又可能因為譯詩的形式而增添幾分閱讀上的唐突感,這一點兒都不是譯者的期盼,而且似乎也有違葛拉斯為「非讀者」寫作的本意。因此,正如〈譯例〉中所說的,我採取了意譯。
為求將原詩中個別語詞所蘊涵的文化內容適當地以中文表達,譯詩多少難免透露出某種「詮釋」的意味。在這個意義上,譯詩頗不同於一般非韻文作品的翻譯,而更像是以西方當代語言嘗試譯解中國古代經典(《論語》、《老子》之類),譯詩因此不能是「逐字的」或「按其字面的」(wörtlich)直譯,而應該是「按其意義的」(sinngemäß)意譯。事實上,翻譯就是一種「轉化」,而譯詩也就意味著是對原詩的一種詮釋性的解讀。好在翻譯並不是複製,不然我們所需要的就會只是一部更完備一點的翻譯機器就夠了。
然而翻譯也絕對不等於創作。各首譯詩所對應的原詩文本(在本集中還有圖像)像一面鏡子,時時提醒著譯者的真實身分:你不是作者,要保持忠實!在這一點上,我們當然還必須考慮到譯者的能力。因此無論是關於譯詩文句或文義的討論與指正,都是譯者所衷心歡迎的,它們也是對譯事的最佳回饋。
細心的讀者,如果對照著原文來看,就會發現在前後相次的幾首詩中,葛拉斯偶爾會重複使用一些字詞,它們在不同的詩句中涵義略有差別,既暗示著前後詩文的連續性,又凸出了語言的多義性。這種詩的語言的意義蔓延,最值得再三品嚐。
細心的讀者或許也注意到了,這本詩畫集的編排是按著時序進行的,尤其愈讀到後面,時序的流轉更加顯然。秋天過後是冬天,葛拉斯好像老是在預言著些什麼。但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是政治性、社會性的影射。那一定是有的。但除此之外呢?
在1970年的一次演說中,葛拉斯說,(抒情)詩是最適合於他的。對他而言,詩的寫作是最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一種表達形式,因為在詩歌之中,他才能坦然地懷疑、衡量自己,盤查一下自己內心最深處的存貨。那麼他到底想說什麼?
在翻譯的過程中,一首接著一首,我把德文譯成了中文--我熟悉的母語。當我就著葛拉斯所選用的個別字詞,為中文的讀者補入譯注,我自己知道得愈多,了解得愈深,我就愈是覺得,這冊詩畫集裡的短短詩句,就像葛拉斯一段段沒有明講的懺悔錄。
當我十七歲時
手裡拿著我的炊具
一如那個和我孫女露易莎
參加了童軍旅行的人一樣
站在往施普倫貝格的馬路邊
舀著吃起了豌豆仁
一顆榴彈轟了過來
湯汁潑了出來
但我只是
輕微地擦傷
並為此感到慶幸
然而葛拉斯又明明說了,詩是最直率的自我表達。那麼他真正想說的,或許就是他隱瞞不了自己的那些實情?(2006年葛拉斯終於出版了自傳《剝洋葱》[Beim Häuten der Zwiebel],我們因此知道了更多。)問題是作為讀者,我們能不能循著字裡行間,走進他的內心?不過對此我不應該再多談了。
另一方面,葛拉斯的詩句對我更像是某種贈言。
在譯詩的過程中,我已經盡了相當努力(如果不能說是最大的話),從無遠弗屆的網路資訊中,提取我所需要的,包括了直接從各個網頁中尋找合宜的內容,也包括了透過它從幾位德國朋友那裡獲得必要的協助。在這裡我尤其要感謝慕尼黑的Hr. Dr. Karl-Heinz Ludwig和德勒斯登的Hr. Conrad Drescher。我同時也要申明對當初創發了Wikipedia的先行者,和其後更多難以計數的、穿梭在國界之間(無國界?)的無名英雄的崇高敬意,他們的先見之明和繼述之功是無法估計的。
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表達對於輔仁大學德語系劉惠安教授、台北市立美術館和原點出版社的誠摯謝意。因為他們的創發構想、委託與信任,才會有本詩畫集中文版的刊行。
本集譯詩的背後還有一位「藏鏡人」王淑燕女士。在譯詩過程中,她幾乎和我討論過所有每一首詩,我們一起斟酌了文義和文句,也共同分享了譯詩的苦與樂--當然是樂的多。她身為本集譯詩的第一位讀者,也許更像是一位共同譯者。如果我不能把這本詩畫集題獻給她(因為葛拉斯已經獻給了他的兒孫們),至少我可以將本集中的譯詩部分作為我們長達二十年的愛情與友誼的小小紀念。
譯稿完成於葛拉斯先生八十歲生日前夕,「借花獻佛」,也許也能用來作為是對他的遙遠的祝壽。
這回譯詩是一次美麗的經驗。我衷心希望,不論是對讀者或「非讀者」來說,這會是(又)一次與詩的驚豔邂逅。
能讀詩真是一種幸福。
《給不讀詩的人》譯後記文/張善穎細心的讀者很快會注意到,本集中的譯詩似乎比原詩來得長些。我並非沒有試過像葛拉斯一樣,使用更簡潔的表達方式,但就是行不通。原詩有時候兩三個字就另起一行,這不僅對譯詩的達意是一種嚴苛的考驗,即使只是就詩句的形式來看,長短差距過大也不很像樣。如果勉強保持簡潔,結果或許就會成了「不可卒讀」。詩本身已經是一種不那麼貼近讀者的文類了,現在又可能因為譯詩的形式而增添幾分閱讀上的唐突感,這一點兒都不是譯者的期盼,而且似乎也有違葛拉斯為「非讀者」寫作的本意。因此,正如〈譯例〉中所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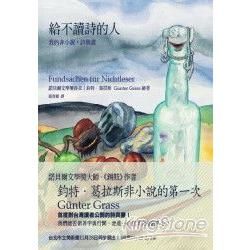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