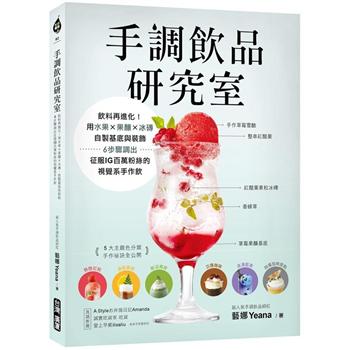◎深入賞析七大名畫,提升藝術欣賞的感受力。
◎回顧眼淚與繪畫之間的文化史,重建當代人與繪畫的完整體驗。
◎32封與知名策展人、藝術史家的往來信件,窺探藝術名人的私房經驗。
你可曾在美術館手忙腳亂,急著從包包裡抽出說明手冊,翻到正確的頁面,對照牆上的畫作,卻仍不得其門而入?你可曾在藝術展場,用心地聽著從耳機傳來的導覽解說,卻摸不著頭緒、對應不上專家的詮釋,也提不起勁?
作者認為,不論是藝術史的研究領域,或者針對大眾的藝術教育,都太重視理性的認知了,我們急著吞下關於藝術的知識,忙著認出每幅名畫,焦慮地學著分辨流派,卻忘記了繪畫與人類真正的親密關係——那就是,感動和眼淚。
從歷史的角度觀之,文藝復興之前,人類被畫作激發出淚水是件天經地義的事,那時我們與繪畫有著簡單而真誠的關係。隨著文藝復興以降,眼淚退位,藝術技巧走向舞台中心,透視技法成為偉大的發明,分析性的審視是藝評家的職責所在。除了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復興,一代接著一代,我們面對繪畫時,感受越來越貧乏,體驗越來越殘缺。
於是,作者進行一項眼淚計畫,與世界上的策展人、藝術研究者、一般的愛畫者書信往返,試著探索繪畫如何打動他們(或者無淚經驗),他們又在畫中獲得什麼樣的領悟。
好畫一定具備某種神聖性,這種神聖性不必然與宗教相關,但卻是洗鍊情感、昇華感知的重要元素。
眼淚逐漸稀少是集體的文化現象,但重建賞畫的完整體驗是個人與藝術品之間重要的一環。作者建議,下次到美術館時,不必急著閱讀牆上的解說卡片,多花些時間專注在幾幅圖畫就好,而且最好獨自前往。
作者簡介
詹姆斯.艾爾金斯James Elkins,1955 ~
美國重要的藝術評論家,任教於芝加哥藝術學院(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年輕時曾是手持畫筆、投入創作的美術系學生,後來轉修藝術史。曾在Berger on Drawing一書中與 John Berger 對談 “Distance and Drawing”。另外著有How to Use Your Eyes、What Painting is,網路作品發表於Huffington Post。
譯者簡介
陳榮彬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研究興趣為「城市文學」與「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目前為清雲科技大學兼任英文講師。著有《當電影遇上爵士》,譯作總計二十本左右,包括《喬伊斯:永遠的都柏林人》、《莎士比亞書店》、《塵世樂園》、《騙局遊戲》,以及「浪人神探」Jack Reacher系列小說四本。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