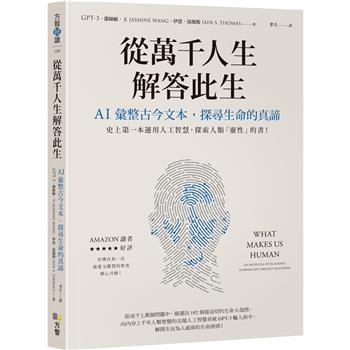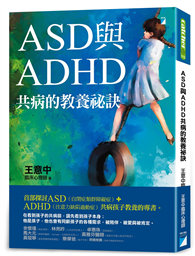作者序
「我們的知識分子在哪裡?」
為本身世代做紀錄的哈洛德.史登斯,在他一九二一年的《美國與青年知識分子》一書中提出這個疑問。他發現他們避往歐洲,而他支持此一行為,並隨即步其後塵,加入了日後最為著名的美籍知識分子團體之一,失落的世代。
史登斯的問題或許也適用於當前,他的答案卻不然。他相信,是商業文明對於一般青年、尤其是對於知識分子的敵意,將年輕作家們驅趕至歐洲。這看法並不合乎現況。時下青年是頗得寵的;知識分子若能蒙受注意,通常也就能夠博取讚譽或資助。青年們首途歐洲可不是倉皇出走,而是去逍遙度假,有時候是去參加研討會。鮮少有美國知識分子過著流亡生涯。不過問題還是存在:年輕一輩的知識分子在哪裡?這便是我的出發點。
我搜尋不到幾個年輕一輩的知識分子——我所謂「年輕」,標準約莫在四十五歲以下,這可要讓真正的年輕人感到憤慨。我的標準也並非?對,而是以出生於二十世紀頭先數十年的「上一代」美國知識分子做為基準。他們的音容風采,已非年輕一輩知識分子所能重現。
如此說,可能會造成誤導,畢竟問題不在於道德墮落,而是在於世代變遷。知識分子的經驗已不同於以往;這可不是什麼新聞,其緣由卻未獲得探究,並且至少有項後果受到忽略而貽害深遠,那便是公眾文化的貧瘠。
以旺盛活力與清晰理路來寫作的知識分子,恐怕就跟紐約和舊金山市區的低廉房租一樣地稀罕。在巨型大學的時代到臨前,成長於市區街道與咖啡館的「上一代」知識分子,是?有學識的讀者寫作的。取而代之的是些高科技知識分子、顧問和大學教授之類的無名靈魂,他們或許頗有能耐,而且還不只有能耐而已,但他們卻未能充實、滋養公眾生活。年輕一輩知識分子的生活幾乎全都在校園裡開展,他們所面對的是專業同僚,而不為外界知悉或接觸得到。公眾文化依賴著逐漸凋零的老一輩知識分子,他們所操持的通俗語言,其後繼者已愈來愈無法掌握了;這正是危險與威脅所在。
在內文的章節裡,我將審視文化世代之間的裂隙;我會提出一些可能的成因,並估算其代價。如此而已!一本面對宏大主題的小書,得要處理極其龐雜的議題,但我將略過大部分,而逐一討論其中數項。
除了略為述及一些獨樹一幟、形塑文學風貌的小說家們,我的論說乃限定在非虛構之作,特別是文學、社會學、哲學與經濟學的思想,這些領域,是我認為世代之間斷裂得最為顯著且傷害最巨之處。我排除掉音樂、舞蹈、繪畫、詩詞,以及其他藝術,畢竟沒有單一一項命題可以適用於所有的文化形式。可以確定的是,也沒有什麼文化形式是獨立自存於廣大社會之外的;而且我還認為,對其他區域進行批判性與世代的探索,也許會具有啟發效益。
舉例來說,虛構之作進入大學——「創意寫作」中心和「駐校」作家的設置;學院小說、英文學系小說的興起;數年來、甚至數十年來前衛派的缺乏——凡此種種,無不透露出新近的虛構之作承擔了與非虛構之作同樣的壓力。近年來,拉丁美洲與東歐等地人士,以及黑人婦女,他們所創作的小說鋒芒漸露,這也意謂著,正當中心地帶大建商場、廣闢校區之際,創意的汁液卻在邊陲外圍流淌著。
雖然如此,虛構之作的發展歷程卻比非虛構之作要來得複雜。這或許是因為詩人和小說家一直都是偶爾才受到關注的局外人,始終光靠撿食桌上的麵包屑也就能夠存活下去。刊登虛構之作和詩作的小型文學期刊(有時也被稱為「小小」雜誌),其數量之多,顯示出想像文學的繁榮昌盛。
然而,即使是大力推動「小小」雜誌的靈魂人物也得承認,它們的時代過去了;拜廉價平版印刷和補助津貼之賜,現在充斥著太多的刊物,而這些刊物似乎已經失去熱忱與方向了。只要它們不像以前卓越著名的刊物一樣,而只專門刊登虛構之作和詩作的話,也就證實了文化已陷於支離破碎。有位小型文學刊物的代理商指出,這些雜誌很少會「採取批判的立場;估且不提論說文,連書評與書訊也都愈來愈少見了」,而今它們所致力的,似乎僅是「縫補當前破裂的布邊罷了」。
我的概論是以美國(和加拿大)的知識分子做為基礎。我之所以排除掉生於國外與在國外受教育者(像是布魯諾.貝特罕、漢娜.鄂蘭、威爾海姆.賴希之輩),並非由於他們影響甚微(事實上正好相反),而僅是因為我想要篩濾出美國的世代生活,把他們放到一邊,才能稍窺其巨大的影響。至於我所納入探討的每一個人,加起來也僅是全體的一小部分,不管怎麼選擇知識分子,總是有另一種相對應的選擇。要了解或表現時代精神,並沒有什麼欽定、非用不可的門道。知識生活原本就難以簡明扼要地呈現;當文化本身含混不清時,若還務求精確,勢必使探討流於瑣碎。有關一個失蹤世代的討論需要一些概括性的陳述,這意謂著某些作家將受到仔細考究,其餘則權且忽略,因此確有必要在各世代熠熠生輝者中披沙揀金,而自古以來便不乏濫竽充數者,如此,犯錯的風險在所難免。
我將運用種種類別——波希米亞、知識分子、世代、文化生活等等,但不會窮極定義之能事。太多的定義和過度的考慮將戕害思想。數十年來,現代分析哲學耗費無數心力來謀求建立良好的概念方法,結果卻只是喪失思考能力而已!當然,其淒慘的紀錄並不表示我們可以妄行判斷。若能小心謹慎,便可在數十年或數世代的代表人物之間做出取捨。
由於我探究年輕一輩知識分子的整體作品(有時顯得粗魯無禮),而且我質疑大學對於文化生活的影響,所以我應該表明:我不是以局外人的身分來寫這本書的。當我說「他們」或「年輕一輩知識分子」時,我所指的是「我們」。當我提出一個「失蹤」世代時,我所討論的是我自己的世代。當我質疑學術界的貢獻時,我所審視的是我自己和朋友的寫作。我在學術刊物上發表過文章,並在一所大學出版中心出版了一本書。我閱讀學術專題論文和期刊。我喜愛大學圖書館,特別是那連綿不盡的書架與巨大的期刊室。我還在幾所大學教過書。我不會假裝自己與眾不同而出類拔萃。我對失蹤的知識分子的批評,也是對自己的批評。
然而,我還該補充說,我也不全然是學術圈內人。十二年來,我浪跡於七所大學和數個學科,還不只一次嘗試去過自由撰稿者的生活。或許我也應該指出,本書並未得到基金會的襄助或大學的經費;我也沒有研究助理和研究生團隊來讓我表達謝意;我更無須感激某個從事如此這般高深研究的中心給了我一年的支持。
就算甘冒錯誤宣傳的風險,而佯稱某事比實際上更具爭議性,我或許還是要說:沒有人會完全同意本書。本書違反傳統一貫的忠貞。我的朋友、我的世代和我自己並非英雄,也不是受害者。我珍視年輕一輩的左派知識階級,而我相信,該階級已棄守太多;我以老一代知識分子做為衡量的標竿,而我時常批評他們的作品;我看重保守的知識分子,而其可貴的活力掩蓋住沉悶乏味的虛偽與矛盾。一旦不假思索便推崇朋友與名位,思想也就枯萎了。
最後再做些說明:本書的書名‘the last intellectuals’是故意要模稜兩可——既是意謂最後一代的知識分子,也是指剛剛過去的那一個世代(如同上星期),表示很快就會有另一個世代。我撰寫此書雖未抱持樂觀的心態,但也不是要做為一個預言者。正當我完成這部作品時,多種領域之中的一些書籍開始問世,每一本都挑戰一個學科——像是《政治學的悲劇》、《經濟學的修辭》、《國際研究與學術企業》,以及《自六○年代以來的激進政治經濟學》等等。這些書並未堅持單一的立場,卻都表明對於過度專業化的不滿,也都示意應該反其道而行,儘可能亡羊補牢,以重拾公眾文化。
還有其他一些跡象。目前,有個幽靈正糾纏著美國的大學,或至少困擾其教職員,那即是厭倦。一個世代的教授在六○年代之間與隨後進入了大學,當時的校園精力充滿,大鳴大放;而今這些教授就算還不至於灰心喪志,卻已是倦態畢露。有份報告發現大專院校的教職員「深受困擾」,而有將近四成準備要離開或想要離開學界。這種潛藏的不滿可能會浮現出來,而與公眾生活再次聯結。保守派人士驚疑此事可能發生,因此持續斥責他們所想像的來自大學的威脅。我認為他們錯了,但希望他們是對的。
知識分子要在「公共性」裡面再起
南方朔
近年來,西方的「知識分子論」再度成為新的顯學,而這波知識分子的理論研究,無論在概念與視野上,都和以往不同。主要聚焦在所謂「公共知識分子」 (Public Intellectuals)的角色、失敗、以及社會變遷的相互關係,最後當然是希望藉著這些探討,而讓公共知識分子們以一種新的形貌再度走回歷史的舞台,創造出更均衡、更有價值關懷的社會。
在「知識分子論」的理論研究上,這是一次大轉向與大復興,而開啟這波新潮流的不是別人,就是雅各比於一九八七年所出的這本《最後的知識分子》。本書的原著迄今已整整二十二年,我們到了現在才有中文翻譯,這實在是遲到太久,但若因此書的翻譯而讓我們急起直追,趕上「知識分子論」的課題,也重振我們這個社會的社會及價值關懷,那還是有意義的。一個知識分子缺席的時代,註定了不會是個好的時代,這種徵候在今天的台灣已愈來愈清晰可見。
在進入這本近代極為重要的著作之前,首要之務乃是讓我們體會雅各比教授寫這本書的心情。
對美國知識分子史有理解的人都知道,在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美國與歐洲甚或全球相同,知識分子都扮演了「啟蒙」和「前鋒」的角色。以美國為例,乃是知識分子們都是以在野之身辦雜誌、出書、寫文章或演講對公眾發表意見。由於這種工作挑戰大,且必須接受公眾檢驗,因而這些知識分子多半到了後來能在學問上成一家之言,而且談起問題來也能切事並造成公眾的共感。在美國歷史上著名的所謂「紐約的才子才女幫」,即出了大批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字輩知識分子。當然也有許多當時的大字輩知識分子出身校園,但他們也和出身非學院的相同,能問學求知以及發表公共評論兩者得兼。我們熟知的名字如丹尼爾.貝爾、蘇珊.桑塔格、米爾斯、高伯瑞、孟福德、艾德蒙.威爾遜、艾文.侯伊……等皆屬之,這也就是說,以前是有「大牌知識分子」的時代。
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有「大牌知識分子」的時代即為逐漸淡出。在概念上這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衰退時代」,又被稱為知識分子的「敗北時代」(Defeatism)。就全世界範圍而言,我們可以說,自從羅素、沙特等人相繼逝世後,全世界已不再有那種以打天下之不平為志業的知識分子了!
而這種情況的造成,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二戰之後的美國,從戰後復員起,大學即快速擴張,許多不在校園的知識分子皆因此而進入校園,此外,戰後的城市空間改造、郊區開始形成,也壓擠掉了傳統知識分子的活動空間;而新的傳媒出現,也壓縮了公眾意見的表達,簡要而言,那就是戰後的發展,乃是對知識分子進行收編、吞噬消化、或是驅逐的過程。知識分子已逐漸的被邊緣化,除了這種邊緣力量和趨勢外,我們也不能疏忽了知識分子本身也在自我邊緣化。知識分子們在進入校園後,服膺新的遊戲規則,只會關心一些瑣碎的小問題,對公眾議題已缺乏觀照及掌握的能力,這叫做「引人注意的瑣碎」(conspicuous trivility),它的意思就是很瑣碎、很花俏但卻很無意義。當代雖然有些知識分子喜歡在口頭上進行「反叛」與「顛覆」,但因為都是侷限在瑣碎的事務上,因而這種「反叛」與「顛覆」遂只是剩下矯揉做作的外表。當代另一學者斯圖亞特.休斯遂稱之為「小調反叛」和「自慶行為」。雅各比教授則說它是種「抗議的微型政治學」,是一種「自我的泛政治,但卻反政治」,他是甚至用「政治自戀」來稱之。
面對知識分子在「邊緣化」和「自我邊緣化」雙重壓力下的夾殺,雅各比教授當然心以為危,並試圖為這個困境尋找新的視野與出路,於是在這樣的心情下,遂有本書的出現。
在本書裡,他對知識分子的角色失落做了極為深入的討論,他在本書裡提出「公共知識分子」這個後來已被充分延伸討論且已被廣泛使用的概念,其核心就是要恢復知識分子的「公共關懷」──只有透過「公共關懷」,知識分子始有可能向一般受教育的公眾談論他們關心的課程,從而建立起知識分子與社會間已失去的紐帶。
雅各比教授在此書之後,即再也沒有停止過他對知識分子這個課題的持續關心,後來,一九九九年他又寫了《烏托邦的終結:冷漠時代的政治與文化》(The End of Utopia: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在此書裡,他提到了一個過去的故事:兩百年前,即一七九九年,當時法國大革命已到了嘎然而止的時刻,由於革命造成的動盪與傷害等於褫奪了知識分子的正當性,於是接下來的時刻,知識分子遂告退潮冷卻,人心也變得麻木冷漠。這種保守的時代氣氛也擴散到了英國,於是高度理想主意的浪漫大詩人柯立芝遂寫了一封信給另一位大詩人華滋華斯,對當時社會的抑鬱消沉表示不安,信中並建議華滋華斯:「我希望你能寫一首白話詩,給那些因為法國大革命失敗,因而對人類的理想已放棄,並沉淪在伊壁鳩魯派的自私,退化到只關心日常軟性事務,至於對有願景的大問題則嗤之以鼻的人。」
華滋華斯一向支持法國大革命的進步價值,他受到柯立芝的激勵,遂於一八○二年寫了〈倫敦〉這首詩,詩曰:
米爾頓!你實在應當活在我們這樣的時刻,
英格蘭需要你:它已淪為一池死水的沼澤,
祭壇、刀劍、和鉛筆、爐邊,樓閣亭台這些英雄留下的財產,
已失去了英國古代內在快樂的傳統。
今天的我們已成了自私的後代人種;
啊,請喚醒我們,請重新回到我們這裡,
賜給我們格調、美德、自我及力量。
你的心靈有如星辰般長照,
你的聲音有如大海般澎湃,
它純潔如坦露的上蒼,莊嚴、自由。
你根據這道理走你自己的人生旅程,
以一種欣然的神聖態度,但你的心
卻始終揹著最基本的責任重擔。
約翰.米爾頓乃是十七世紀英國的自由先鋒:在人類的自由發展史上,乃是地位崇高的先行者,由華滋華斯在詩裡重提米爾頓,希望他的精神能重振有如死水的時代,而雅各比教授則再提柯立芝和華滋華斯的那則歷史,這其實已反映出了他的心情──目前這個知識分子凋零,停滯得有如死水般的時代,他企圖扮演的就是時代的鬧鐘,要從沉睡中把人們喚醒。
雅各比教授著作甚多,都圍繞知識分子如何重返歷史舞台這個課題。除了《最後的知識分子》有替新的知識分子理論奠基的重要意義外,其他如《社會健忘症》
(Social Amnesia)、《失敗的辨證》(Dialectic of Defeat)、《烏托邦的終結》等,也都一路深入延伸討論這個課題。根據個人多年來對他著作的理解,他之所以為世所重,乃是他的論點有著極為重要的原創性。他不像有些學者一樣,只是把知識分子角色的凋零歸因於社會的變遷、近代學院體制冷漠、以及逸樂文化的興起,體制的再封建化等。上述這些原因,的確發揮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雅各比教授更強調的,乃是知識分子自我邊緣化、自己打敗自己的這個部分。他會提出「公共知識分子」這種新的概念,其實就寓有知識分子應自我改造的寓意!
如果我們不是心中有著既定的習慣性見解,就會察覺到近代初期,由於發展程度不足,相對剝削嚴重,再加上國際關係粗糙。這些條件使得知識分子容易產生烏托邦信念,並容易把自己定位成彌賽亞。這種簡化的世界觀,的確會有助於社會動員和進步價值的凸顯,但也容易造成教條、淺薄、意識型態掛帥等缺點。進代保守勢力得以崛起、會突出技術專家角色、及貶低知識分子,其實都不是沒有原因的。當近代有些學者宣稱「意識型態的終結」時,這種話語裡即一定程度寓有「知識分子的終結」的貶義在內。
而非常令人惋惜的,乃是面對客觀形勢的不利。知識分子並未來去深入反省、自我振作,反而是順應著這種形勢。知識分子愈來愈長於講一些有的沒的,用一些「反叛」、「顛覆」、「反霸權」之類的字眼,但談的題目卻都花俏不實,只對圈內小眾有自我慶祝的意義。知識分子愈來愈無法對公眾問題做出有視野的新選擇。雅各比教授稱之為「政治自戀」、「政治獨我主義」、「知識分子從烏托邦走向近視症」(from utopia to myopia),因於知識分子不能發生作用及導正價值及方向偏差,因而系統性的問題遂日益嚴重。今天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人認為是國家走錯了方向,即可堪為證,這也是所謂的「零售聰明、批發瘋狂」」(Retail Sanity and Wholesale madness)。
因此,雅各比教授對當代知識分子的花俏無用可謂深惡痛絕。當代知識分子用「多元」、「歧義」這種說法來合理化他們自己的沒有方向感,也故意用連文法都不通的文句來?扮自己的花俏瑣碎。知識分子自己不用功不努力,它們是自己打敗自己:他們無法為人代言,這種惡果有一大半是自己造成的。
因此,知識分子太烏托邦,太意識型態是過去的偏差;而知識分子搞到太近視,只看瑣碎卻對世事讀不出道理,則是現在的偏差。而要克服這兩極的偏差,就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恢復與公眾對話的能力與態度。知識分子不能大言不慚的只看長程理想,不能看小不看大,而是至少要對中程問題做出表示,中程是理想與現實結合的中間點,它是知識分子再出發的起點,而當然,知識分子本身在知識上也必須要有更多準備了。關心中程問題,強調切事的態度與能力,建立可實現的願景,雅各比教授謂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在此!
近二十年來,我對雅各比教授的著作極為注意,認為他的知識分子理論必將對當代全世界發揮先導作用。而事實也證明如此。當代思想界的知識分子理論近年來有了極大的開展與反省,人們對「公共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也開始朗朗上口,這一切都是拜雅各比教授之賜。當今的台灣,由於社會及體制的變遷,我們其實早已進入了知識分子邊緣化的階段。我們的知識分子不用功、不關心,對許多瑣碎的事務有變態的執迷,也常會耽溺在花俏無意義的題目上自我感覺良好。美國知識分子必須奮起,台灣知識分子亦然。這也是讀雅各比教授著作應有的認知吧!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