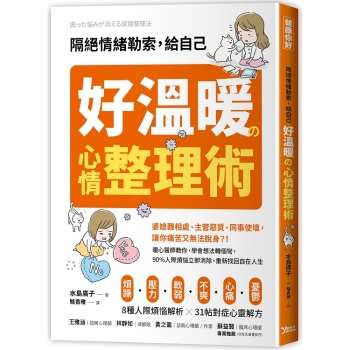本書是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這部學術經典之最佳版本。
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原著名為《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於1918年9月「寫成付印」,列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一」,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1918年2月首度出版;同年5月再版。1958年10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以《中國古代哲學史》為名,出版單行本,附有胡適親撰〈《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版自記〉與〈《中國古代哲學史》正誤表〉,當為胡適生前自行確認之定本。
本書以1958年出版之《中國古代哲學史》為底本,參考台北胡適紀念館館藏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1918年2月初版,封面有胡適「自校本」之題記)與其他版本,相互覈校,以成善本。讀者持此一編,自可領悟,本書做為引發現代中國史學革命的典範著作,實是名副其實。
本書特色
本書是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這部學術經典之最佳版本。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胡適全集: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圖書 |
 |
$ 387 ~ 466 | 胡適全集:中國古代哲學史
作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主編 出版社:秀威代理 出版日期:2023-02-20 語言:繁體書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胡適
 胡適,原名嗣穈,行名洪騂,字希彊,後改名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鐵兒等。安徽績溪上莊村人,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私立南開大學校董會董事等職。胡適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主張少談主義,主張先疑後信,主張科學佐證,盡信書不如無書。他擁有三十六個博士, 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博士學位的人之一。
胡適,原名嗣穈,行名洪騂,字希彊,後改名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鐵兒等。安徽績溪上莊村人,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私立南開大學校董會董事等職。胡適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主張少談主義,主張先疑後信,主張科學佐證,盡信書不如無書。他擁有三十六個博士, 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博士學位的人之一。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胡適全集:中國古代哲學史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編者簡介
潘光哲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歷任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講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約聘研究助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兼任胡適紀念館主任、檔案館主任、副所長、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董事長等職。嘗膺選為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訪問學者、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外国人研究員」等職。專業研究領域為近現代中國史與當代台灣史。著有《「華盛頓神話」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天方夜譚」中研院:現代學術社群史話》、《創造近代中國的『世界知識』》等專書及學術論文八十餘篇,主編《(新版)殷海光全集》、《(新版)胡適全集》、《容忍與自由:胡適思想精選》、《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等史料彙編。
潘光哲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歷任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講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約聘研究助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兼任胡適紀念館主任、檔案館主任、副所長、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董事長等職。嘗膺選為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訪問學者、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外国人研究員」等職。專業研究領域為近現代中國史與當代台灣史。著有《「華盛頓神話」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天方夜譚」中研院:現代學術社群史話》、《創造近代中國的『世界知識』》等專書及學術論文八十餘篇,主編《(新版)殷海光全集》、《(新版)胡適全集》、《容忍與自由:胡適思想精選》、《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等史料彙編。
目錄
編者序
謝辭
《胡適全集》編輯凡例
《胡適全集‧中國古代哲學史》編輯說明
《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版自記
序(蔡元培)
再版自序
第一篇 導言
第二篇 中國哲學發生的時代
第一章 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
第二章 那時代的思潮(詩人時代)
第三篇 老子
第四篇 孔子
第一章 孔子略傳
第二章 孔子的時代
第三章 易
第四章 正名主義
第五章 一以貫之
第五篇 孔門弟子
第六篇 墨子
第一章 墨子略傳
第二章 墨子的哲學方法
第三章 三表法
第四章 墨子的宗教
第七篇 楊朱
第八篇 別墨
第一章 《墨辯》與別墨
第二章 《墨辯》論知識
第三章 論辯
第四章 惠施
第五章 公孫龍及其他辯者
第六章 墨學結論
第九篇 莊子
第一章 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
第二章 莊子的名學與人生哲學
第十篇 荀子以前的儒家
第一章 《大學》與《中庸》
第二章 孟子
第十一篇 荀子
第一章 荀子
第二章 天與性
第三章 心理學與名學
第十二篇 古代哲學的終局
第一章 前三世紀的思潮
第二章 所謂法家
第三章 古代哲學之中絕
附錄 《中國哲學史大綱》凡例
謝辭
《胡適全集》編輯凡例
《胡適全集‧中國古代哲學史》編輯說明
《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版自記
序(蔡元培)
再版自序
第一篇 導言
第二篇 中國哲學發生的時代
第一章 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
第二章 那時代的思潮(詩人時代)
第三篇 老子
第四篇 孔子
第一章 孔子略傳
第二章 孔子的時代
第三章 易
第四章 正名主義
第五章 一以貫之
第五篇 孔門弟子
第六篇 墨子
第一章 墨子略傳
第二章 墨子的哲學方法
第三章 三表法
第四章 墨子的宗教
第七篇 楊朱
第八篇 別墨
第一章 《墨辯》與別墨
第二章 《墨辯》論知識
第三章 論辯
第四章 惠施
第五章 公孫龍及其他辯者
第六章 墨學結論
第九篇 莊子
第一章 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
第二章 莊子的名學與人生哲學
第十篇 荀子以前的儒家
第一章 《大學》與《中庸》
第二章 孟子
第十一篇 荀子
第一章 荀子
第二章 天與性
第三章 心理學與名學
第十二篇 古代哲學的終局
第一章 前三世紀的思潮
第二章 所謂法家
第三章 古代哲學之中絕
附錄 《中國哲學史大綱》凡例
序
序
《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版自記
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就是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民國七年九月寫成付印,民國八年二月第一版出版。今年是民國四十七年,這部書出版以來,整整三十九年了。臺北商務印書館現在用《萬有文庫》的五號字本《中國古代哲學史》重印,仍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名稱。我做了一個正誤表,附在卷尾。
《萬有文庫》本是民國十八年用五號字重排的(原書是用四號字排的)。那時候,我在上海正著手寫《中國中古思想史》的「長編」,已決定不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的名稱了。所以當時《萬有文庫》的編輯人要把我的《哲學史》上卷收在那部叢書裏,我就提議,把這個五號字重排本改稱《中國古代哲學史》。我的意思是要讓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單獨流行,將來我寫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後,我可以用我中年以後的見解來重寫一部「中國古代思想史」,我不預備修改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了。
我現在翻看我四十年前寫成的這本書,當然可以看出許多缺點。我可以舉出幾組例子:(一)我當時還相信孔子做過「刪詩書,訂禮樂」的工作,這大概是錯的。我在正誤表裏,已把這一類的話都刪去了。(二)我當時用《列子》裏的〈楊朱〉篇來代表楊朱的思想,這也是錯的。《列子》是一部東晉時人偽造的書,其中如〈說符〉篇好像摘鈔了一些先秦的語句,但〈楊朱〉篇似乎很不可信。請讀者看看我的《讀《呂氏春秋》》(收在《胡適文存》三集)。我覺得《呂氏春秋》的〈本生〉、〈重己〉、〈貴生〉、〈情欲〉諸篇很可以表現中國古代產生的一種很健全的個人主義,大可以不必用《列子》的〈楊朱〉篇了。《呂氏春秋‧不二》篇說「楊生貴己」,李善注《文選》引作「楊朱貴己」。我現在相信《呂氏春秋》的〈貴生〉、〈重己〉的理論很可能就是楊朱一派的「貴己」主義。(三)此書第九篇第一章論「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是全書裏最脆弱的一章,其中有一節述「《列子》書中的生物進化論」,也曾引用《列子》偽書,更是違背了我自己在第一篇裏提倡的「史料若不可靠,歷史便無信史的價值」的原則。我在那一章裏述「《莊子》書中的生物進化論」,用的材料,下的結論,現在看來,都大有問題。例如,《莊子‧寓言》篇說: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知其倫。是謂天均。
這一段本不好懂。但看「始卒若環,莫知其倫」八個字,這裏說的不過是一種循環的變化論罷了。我在當時竟說: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此十一個字竟是一篇《物種由來》。
這真是一個年輕人的謬妄議論,真是侮辱了《物種由來》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我現在讓臺北商務印書館把我這本四十年前的舊書重印出來,這是因為這本書雖然有不少缺點,究竟還有他自身的特別立場,特別方法,也許還可以補充這四十年中出來的幾部中國哲學史的看法。
我這本書的特別立場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個學派的「名學方法」(邏輯方法,即是知識思考的方法),認為這是哲學史的中心問題。我在第八篇裏曾說:
古代本沒有什麼「名家」。無論那一家的哲學,都有一種為學的方法。這個方法便是這一家的名學。所以老子要無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說言有三表,……這都是各家的名學。因為家家都有「名學」,所以沒有什麼「名家」。
這個看法,我認為根本不錯。試看近世思想史上,程、朱、陸、王的爭論,豈不是一個名學方法的爭論?朱晦庵把「格物」解作「即物而窮其理」,王陽明把「格物」解作「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這豈不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名學方法的爭論嗎?南宋的朱陸之爭,當時已認作「尊德性」與「道問學」兩條路子的不同,—那也是一個方法上的爭執。兩宋以來,「格物」兩個字就有幾十種不同的解釋,其實多數也還是方法上的不同。
所以我這本哲學史在這個基本立場上,在當時頗有開山的作用。可惜後來寫中國哲學史的人,很少人能夠充分瞭解這個看法。
這個看法根本就不承認司馬談把古代思想分作「六家」的辦法。我不承認古代有什麼「道家」、「名家」、「法家」的名稱。我這本書裏從沒有用「道家」二字,因為「道家」之名是先秦古書裏從沒有見過的。我也不信古代有「法家」的名稱,所以我在第十二篇第二章用了「所謂法家」的標題,在那一章裏我明說:「古代本沒有什麼『法家』。……我以為中國古代只有法理學,只有法治的學說,並無所謂『法家』」。至於劉向、劉歆父子分的「九流」,我當然更不承認了。
這樣推翻「六家」、「九流」的舊說,而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依據史料重新尋出古代思想的淵源流變:這是我四十年前的一個目標。我的成績也許沒有做到我的期望,但這個治思想史的方法是在今天還值得學人的考慮的。
在民國六年我在北京大學開講中國哲學史之前,中國哲學是要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講起的。據顧頡剛先生的記載,我第一天講中國哲學史從老子、孔子講起,幾乎引起了班上學生的抗議風潮!後來蔡元培先生給這本書寫序,他還得特別提出「從老子、孔子講起」這一點,說是「截斷眾流」的手段。其實他老人家是感覺到他應該說幾句話替我辯護這一點。
四十年來,有些學者們好像跑在我的前面去了。他們要進一步,把老子那個人和《老子》那部書都推翻,都移後兩三百年。他們講中國哲學思想,要從孔子講起。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就是這樣辦的。馮先生的書裏,先講了孔子、墨子、孟子、楊朱、陳仲子、許行、告子、尹文、宋牼、彭蒙、田駢、慎到、騶衍及其他陰陽五行家言,—到了第八章才提出「《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學」。
馮先生說:
《老子》一書,……係戰國時人所作。關於此說之證據,前人已詳舉(原注:參看崔東壁《洙泗考信錄》、汪中《老子考異》、梁啟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茲不贅述。就本書中所述關於上古時代學術界之大概情形觀之,亦可見《老子》為戰國時之作品。蓋一則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於《論語》。二則《老子》之文體非問答體,故應在《論語》、《孟子》後。三則《老子》之文為簡明之「經」體,可見其為戰國時之作品。此三端及前人所已舉之證據,若任舉其一,則不免有違邏輯所謂「丐詞」(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觀之,則《老子》之文體、學說,及各方面之旁證,皆指明其為戰國時之作品,此則必非偶然矣(參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民國三十六年增訂八版,頁210)。
馮先生舉出的證據實在都不合邏輯,都不成證據。我曾對他說:
……積聚了許多「邏輯上所謂『丐辭』」,居然可以成為定案的證據!這種考據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書喊一聲「青天大老爺,小的有冤枉上訴」!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證人自己承認的「丐辭」,究竟是「丐辭」,不是證據。
這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說的話。我到今天,還沒有看到這班懷疑的學人提出什麼可以叫我心服的證據。所以我到今天還不感覺我應該把老子這個人或《老子》這部書挪移到戰國後期去(留心這個問題的人,可以看看我的〈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及附錄。這些文字收在〈胡適論學近著〉,頁103以下;即臺北版《胡適文存》四集,頁104以下)。
二三十年過去了,我多吃了幾擔米,長了一點經驗。有一天,我忽然大覺大悟了!我忽然明白:這個老子年代的問題原來不是一個考證方法的問題,原來只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問題!像馮友蘭先生一類的學者,他們誠心相信,中國哲學史當然要認孔子是開山老祖,當然要認孔子是「萬世師表」。在這個誠心的宗教信仰裏,孔子之前當然不應該有一個老子。在這個誠心的信仰裏,當然不能承認有一個跟著老聃學禮助葬的孔子。
試看馮友蘭先生如何說法:
……在中國哲學史中,孔子實佔開山之地位。後世尊為惟一師表,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以此之故,哲學史自孔子講起(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29)。
懂得了「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的心理,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二十五年前寫幾萬字的長文討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真是白費心思,白費精力了。
民國四十七年一月十日,在紐約寓樓
序
我們今日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真的同偽的混在一處。就是真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 多。若沒有做過清朝人叫做「漢學」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形式問題: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記載。《莊子》的〈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略〉,均是平行的紀述 。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
現在治過「漢學」的人,雖還不少,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裏,就比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才 滿一年。此一年的短時期中,成了這一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可算是心靈手敏了。我曾細細讀了一遍,看出其中幾處的特長:
第一是證明的方法。我們對於一個哲學家,若是不能考實他生存的時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來源;若不能辨別他遺著的真偽,便不能揭出他實在的主義;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辯證的方法,便不能發見他有無矛盾的議論。適之先生這《大綱》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書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苦心,並且為後來的學者開無數法門。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遠在老子、孔子之前,是無可疑的。但要從此等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記載中,抽出純粹的哲學思想,編成系統,不是窮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適之先生認定所講的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發達史,不是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發達史,所以截斷眾流,從老子、孔子講起。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評判哲學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漢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諸子;近人替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這都是鬧意氣罷了!適之先生此編,對於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統的研究。古人記學術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說過了。適之先生此編,不但孔墨兩家有師承可考的,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跡,便是從老子到韓非,古人劃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經排比時代,比較論旨,都有遞次演進的脈絡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見不到的。
以上四種特長,是較大的,其他較小的長處,讀的人自能領會,我不必贅說了。我只盼望適之先生努力進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
中華民國七年八月三日 蔡元培
再版自序
一部哲學的書,在這個時代,居然能於兩個月之內再版:這是我自己不曾夢想到的事。這種出乎意外的歡迎,使我心裏歡喜感謝,自不消說得。
這部書的稿本是去年九月寄出付印的,到今年二月出版時,我自己的見解已有幾處和這書不同了。近來承各地的朋友同我討論這部書的內容,有幾點我很佩服。我本想把這幾處修正了然後再版。但是這時候各處需要這書的人很多,我又一時分不出工夫來做修正的事,所以只好暫時先把原版重印。這是我很抱歉的事(有一兩處,已在正誤表裏改正。又關於《墨辯》的一部分,我很希望讀者能參看《北京大學月刊》第三期裏我的〈《墨子‧小取》篇新詁〉一篇)。
我做這部書,對於過去的學者我最感謝的是:王懷祖、王伯申、俞蔭甫、孫仲容四人。對於近人,我最感謝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學的同事裏面,錢玄同、朱逷先兩位先生對於這書都曾給我許多幫助。這書排印校稿的時候,我正奔喪回家去了,多虧得高一涵和張申府兩位先生替我校對,我很感謝他們。
民國八年五月三日 胡適
《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版自記
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就是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民國七年九月寫成付印,民國八年二月第一版出版。今年是民國四十七年,這部書出版以來,整整三十九年了。臺北商務印書館現在用《萬有文庫》的五號字本《中國古代哲學史》重印,仍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名稱。我做了一個正誤表,附在卷尾。
《萬有文庫》本是民國十八年用五號字重排的(原書是用四號字排的)。那時候,我在上海正著手寫《中國中古思想史》的「長編」,已決定不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的名稱了。所以當時《萬有文庫》的編輯人要把我的《哲學史》上卷收在那部叢書裏,我就提議,把這個五號字重排本改稱《中國古代哲學史》。我的意思是要讓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單獨流行,將來我寫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後,我可以用我中年以後的見解來重寫一部「中國古代思想史」,我不預備修改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了。
我現在翻看我四十年前寫成的這本書,當然可以看出許多缺點。我可以舉出幾組例子:(一)我當時還相信孔子做過「刪詩書,訂禮樂」的工作,這大概是錯的。我在正誤表裏,已把這一類的話都刪去了。(二)我當時用《列子》裏的〈楊朱〉篇來代表楊朱的思想,這也是錯的。《列子》是一部東晉時人偽造的書,其中如〈說符〉篇好像摘鈔了一些先秦的語句,但〈楊朱〉篇似乎很不可信。請讀者看看我的《讀《呂氏春秋》》(收在《胡適文存》三集)。我覺得《呂氏春秋》的〈本生〉、〈重己〉、〈貴生〉、〈情欲〉諸篇很可以表現中國古代產生的一種很健全的個人主義,大可以不必用《列子》的〈楊朱〉篇了。《呂氏春秋‧不二》篇說「楊生貴己」,李善注《文選》引作「楊朱貴己」。我現在相信《呂氏春秋》的〈貴生〉、〈重己〉的理論很可能就是楊朱一派的「貴己」主義。(三)此書第九篇第一章論「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是全書裏最脆弱的一章,其中有一節述「《列子》書中的生物進化論」,也曾引用《列子》偽書,更是違背了我自己在第一篇裏提倡的「史料若不可靠,歷史便無信史的價值」的原則。我在那一章裏述「《莊子》書中的生物進化論」,用的材料,下的結論,現在看來,都大有問題。例如,《莊子‧寓言》篇說: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知其倫。是謂天均。
這一段本不好懂。但看「始卒若環,莫知其倫」八個字,這裏說的不過是一種循環的變化論罷了。我在當時竟說: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此十一個字竟是一篇《物種由來》。
這真是一個年輕人的謬妄議論,真是侮辱了《物種由來》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我現在讓臺北商務印書館把我這本四十年前的舊書重印出來,這是因為這本書雖然有不少缺點,究竟還有他自身的特別立場,特別方法,也許還可以補充這四十年中出來的幾部中國哲學史的看法。
我這本書的特別立場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個學派的「名學方法」(邏輯方法,即是知識思考的方法),認為這是哲學史的中心問題。我在第八篇裏曾說:
古代本沒有什麼「名家」。無論那一家的哲學,都有一種為學的方法。這個方法便是這一家的名學。所以老子要無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說言有三表,……這都是各家的名學。因為家家都有「名學」,所以沒有什麼「名家」。
這個看法,我認為根本不錯。試看近世思想史上,程、朱、陸、王的爭論,豈不是一個名學方法的爭論?朱晦庵把「格物」解作「即物而窮其理」,王陽明把「格物」解作「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這豈不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名學方法的爭論嗎?南宋的朱陸之爭,當時已認作「尊德性」與「道問學」兩條路子的不同,—那也是一個方法上的爭執。兩宋以來,「格物」兩個字就有幾十種不同的解釋,其實多數也還是方法上的不同。
所以我這本哲學史在這個基本立場上,在當時頗有開山的作用。可惜後來寫中國哲學史的人,很少人能夠充分瞭解這個看法。
這個看法根本就不承認司馬談把古代思想分作「六家」的辦法。我不承認古代有什麼「道家」、「名家」、「法家」的名稱。我這本書裏從沒有用「道家」二字,因為「道家」之名是先秦古書裏從沒有見過的。我也不信古代有「法家」的名稱,所以我在第十二篇第二章用了「所謂法家」的標題,在那一章裏我明說:「古代本沒有什麼『法家』。……我以為中國古代只有法理學,只有法治的學說,並無所謂『法家』」。至於劉向、劉歆父子分的「九流」,我當然更不承認了。
這樣推翻「六家」、「九流」的舊說,而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依據史料重新尋出古代思想的淵源流變:這是我四十年前的一個目標。我的成績也許沒有做到我的期望,但這個治思想史的方法是在今天還值得學人的考慮的。
在民國六年我在北京大學開講中國哲學史之前,中國哲學是要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講起的。據顧頡剛先生的記載,我第一天講中國哲學史從老子、孔子講起,幾乎引起了班上學生的抗議風潮!後來蔡元培先生給這本書寫序,他還得特別提出「從老子、孔子講起」這一點,說是「截斷眾流」的手段。其實他老人家是感覺到他應該說幾句話替我辯護這一點。
四十年來,有些學者們好像跑在我的前面去了。他們要進一步,把老子那個人和《老子》那部書都推翻,都移後兩三百年。他們講中國哲學思想,要從孔子講起。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就是這樣辦的。馮先生的書裏,先講了孔子、墨子、孟子、楊朱、陳仲子、許行、告子、尹文、宋牼、彭蒙、田駢、慎到、騶衍及其他陰陽五行家言,—到了第八章才提出「《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學」。
馮先生說:
《老子》一書,……係戰國時人所作。關於此說之證據,前人已詳舉(原注:參看崔東壁《洙泗考信錄》、汪中《老子考異》、梁啟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茲不贅述。就本書中所述關於上古時代學術界之大概情形觀之,亦可見《老子》為戰國時之作品。蓋一則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於《論語》。二則《老子》之文體非問答體,故應在《論語》、《孟子》後。三則《老子》之文為簡明之「經」體,可見其為戰國時之作品。此三端及前人所已舉之證據,若任舉其一,則不免有違邏輯所謂「丐詞」(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觀之,則《老子》之文體、學說,及各方面之旁證,皆指明其為戰國時之作品,此則必非偶然矣(參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民國三十六年增訂八版,頁210)。
馮先生舉出的證據實在都不合邏輯,都不成證據。我曾對他說:
……積聚了許多「邏輯上所謂『丐辭』」,居然可以成為定案的證據!這種考據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書喊一聲「青天大老爺,小的有冤枉上訴」!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證人自己承認的「丐辭」,究竟是「丐辭」,不是證據。
這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說的話。我到今天,還沒有看到這班懷疑的學人提出什麼可以叫我心服的證據。所以我到今天還不感覺我應該把老子這個人或《老子》這部書挪移到戰國後期去(留心這個問題的人,可以看看我的〈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及附錄。這些文字收在〈胡適論學近著〉,頁103以下;即臺北版《胡適文存》四集,頁104以下)。
二三十年過去了,我多吃了幾擔米,長了一點經驗。有一天,我忽然大覺大悟了!我忽然明白:這個老子年代的問題原來不是一個考證方法的問題,原來只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問題!像馮友蘭先生一類的學者,他們誠心相信,中國哲學史當然要認孔子是開山老祖,當然要認孔子是「萬世師表」。在這個誠心的宗教信仰裏,孔子之前當然不應該有一個老子。在這個誠心的信仰裏,當然不能承認有一個跟著老聃學禮助葬的孔子。
試看馮友蘭先生如何說法:
……在中國哲學史中,孔子實佔開山之地位。後世尊為惟一師表,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以此之故,哲學史自孔子講起(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29)。
懂得了「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的心理,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二十五年前寫幾萬字的長文討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真是白費心思,白費精力了。
民國四十七年一月十日,在紐約寓樓
序
我們今日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真的同偽的混在一處。就是真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 多。若沒有做過清朝人叫做「漢學」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形式問題: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記載。《莊子》的〈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略〉,均是平行的紀述 。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
現在治過「漢學」的人,雖還不少,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裏,就比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才 滿一年。此一年的短時期中,成了這一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可算是心靈手敏了。我曾細細讀了一遍,看出其中幾處的特長:
第一是證明的方法。我們對於一個哲學家,若是不能考實他生存的時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來源;若不能辨別他遺著的真偽,便不能揭出他實在的主義;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辯證的方法,便不能發見他有無矛盾的議論。適之先生這《大綱》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書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苦心,並且為後來的學者開無數法門。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遠在老子、孔子之前,是無可疑的。但要從此等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記載中,抽出純粹的哲學思想,編成系統,不是窮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適之先生認定所講的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發達史,不是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發達史,所以截斷眾流,從老子、孔子講起。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評判哲學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漢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諸子;近人替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這都是鬧意氣罷了!適之先生此編,對於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統的研究。古人記學術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說過了。適之先生此編,不但孔墨兩家有師承可考的,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跡,便是從老子到韓非,古人劃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經排比時代,比較論旨,都有遞次演進的脈絡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見不到的。
以上四種特長,是較大的,其他較小的長處,讀的人自能領會,我不必贅說了。我只盼望適之先生努力進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
中華民國七年八月三日 蔡元培
再版自序
一部哲學的書,在這個時代,居然能於兩個月之內再版:這是我自己不曾夢想到的事。這種出乎意外的歡迎,使我心裏歡喜感謝,自不消說得。
這部書的稿本是去年九月寄出付印的,到今年二月出版時,我自己的見解已有幾處和這書不同了。近來承各地的朋友同我討論這部書的內容,有幾點我很佩服。我本想把這幾處修正了然後再版。但是這時候各處需要這書的人很多,我又一時分不出工夫來做修正的事,所以只好暫時先把原版重印。這是我很抱歉的事(有一兩處,已在正誤表裏改正。又關於《墨辯》的一部分,我很希望讀者能參看《北京大學月刊》第三期裏我的〈《墨子‧小取》篇新詁〉一篇)。
我做這部書,對於過去的學者我最感謝的是:王懷祖、王伯申、俞蔭甫、孫仲容四人。對於近人,我最感謝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學的同事裏面,錢玄同、朱逷先兩位先生對於這書都曾給我許多幫助。這書排印校稿的時候,我正奔喪回家去了,多虧得高一涵和張申府兩位先生替我校對,我很感謝他們。
民國八年五月三日 胡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