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書集結十四年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印行之臺灣文獻叢刊之弁言及後記集印。
2. 是為研究臺灣文獻之重要史料。
周憲文先生(1908-1989年)﹐浙江黃巖縣人﹐ 1931年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 旋被聘為中華書局編輯﹐ 主持新書出版﹐ 兼事《辭海》編輯。
來臺後出任臺灣立法商學院院長﹐ 兼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院長及人文研究所所長。旋籌設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專事研究臺灣經濟。周先生的學術以「基礎文獻」為主﹐包括翻譯名著﹐ 編印史料﹑ 經濟學人及名著辭典。
本書集結十四年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印行之臺灣文獻叢刊之弁言及後記集印。計有二百九十三種﹑五百六十五冊﹑八千餘面﹐凡四萬八百一十萬字﹐定名為《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於一九七一年出版由中華書局。
章節試閱
十四年頭,匆匆過去。
十四年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共計印行臺灣文獻叢刊二九三種五六五冊,凡八千餘面,四八一○萬字。這一叢刊,真正是我「一手造成」,備極艱辛。現在,我瞬將退休,同人決定拿這十四年來我們所寫的弁言及後記集印,定名為「臺灣文獻叢刊序(指弁言)跋(指後記)彙錄」,藉留紀念,囑置一言;雅意拳拳,既感且愧!
首先,我得說明兩點。
第一、我不想在此向人訴苦。因在這一動亂的時代,這一叢刊居然能夠出版,且能延續到今天而接近完成的階段,則任何困難,都已有代價;我祇有感佩各方的支持與寬容,絕對不應再歎苦經。
第二、我不想在此自我表揚。因為一切功績(假使是有功績的話),都應歸諸臺灣銀行當局以及可以管到這一工作的有關人士;如果他們堅持不可,我有何力使它出版。
至於本叢刊在中國文化史上、特別是在臺灣文化史上的價值如何?這當留待社會人士的公斷。如其果為「浪費公帑」(這是本叢刊經常所受的責難),則我個人應負完全責任,絕不推諉。不過,有一點不妨指明:像本叢刊這樣以一省區為範圍的出版物(本叢刊原嚴格以臺灣為範圍,後來因為臺灣的歷史與南明不可分割,所以逐漸擴及南明史料),而且繼續出版至如此之久,如此之多,這不論在中國、在世界(更毋論在臺灣),都是很難得的。
歷史的研究,是件極難的工作。沒有史料,固然無從下手;沒有正確的史觀(正確的觀點與方法),則史料愈富,謊言愈多,有不如無。要是外人或後人以為我們出版這一叢刊,原有什麼周詳的計畫,凡有正確史觀的人,都會了解這是不符事實的。本叢刊出版的最初動機,祇因曹永和先生在拙著《清代台灣經濟史》上引自舊籍的文字恐有錯誤,替我做了一番「復按」的工作,因而使我想起這些舊籍不無重刊的必要;如此而已。因此,我們原是「出一本算一本」;假使事前知道要出至三百餘種,說實在的,那就一本都無法出版。因我絕不敢想像這樣的計畫,而這樣的計畫也絕不會得到通過。
說到本叢刊的弁言,我們有一原則,即凡原書已有序文者,非有必要,不再寫作。同時,弁言(或後記)的寫作者,也不就是原書的整理者。
因為本叢刊的出版,原無周詳的計畫,故其缺點是不少的。至於標點之不無錯誤、印刷之不如人意(參看臺灣研究叢刊第九十六種「二十年來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出版物」,其中還有吳幅員先生對本叢刊的詳細報導),猶其餘事。
凡是我們能夠收集的臺灣文獻,可說大體都已整理出版,今後我們所能收集的,可能不會太多。但是,不說大陸與海外,即在臺灣,據我所知,其實還有不少資料;例如某機構,就有大批明清檔案,我們曾經多次接洽,初則以尚未開箱,繼則以恐怕散失,未允抄錄;這不是我們所能收集的。還有更奇特(其實很平常)的作風;我們知道某機關持有這些資料,商請抄錄,被以「我們就要出版」婉拒;但是,多少年來,未見印行。總而言之,「私字當頭」。但我希望公開資料的風氣及早形成,這與學術進步的前途大有關係。
本叢刊「屢瀕於危」,要是沒有楊亮功先生的一再大力挽回,「起死回生」,何來今日?為公為私,我都得在此深致謝忱。
周憲文於惜餘書室
十四年頭,匆匆過去。
十四年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共計印行臺灣文獻叢刊二九三種五六五冊,凡八千餘面,四八一○萬字。這一叢刊,真正是我「一手造成」,備極艱辛。現在,我瞬將退休,同人決定拿這十四年來我們所寫的弁言及後記集印,定名為「臺灣文獻叢刊序(指弁言)跋(指後記)彙錄」,藉留紀念,囑置一言;雅意拳拳,既感且愧!
首先,我得說明兩點。
第一、我不想在此向人訴苦。因在這一動亂的時代,這一叢刊居然能夠出版,且能延續到今天而接近完成的階段,則任何困難,都已有代價;我祇有感佩各方的支持與寬容,絕對不應再歎苦經...
目錄
序/周憲文
第一章 臺灣割據志卷頭語(第一種)/周憲文
第二章 臺灣鄭氏紀事後記(第五種)/周憲文
第三章 閩海紀要弁言(第一一種)/周憲文
第四章 東征後記(第一二種)/周憲文
第五章 靖海紀事後記(第一三種)/夏德儀
第六章 治臺必告錄弁言(第一七種)/周憲文
第七章 臺灣志略弁言(第一八種)/夏德儀
第八章 陽台筆記後記( (第二十種)/夏德儀
第九章 巡臺退思錄弁言(第二一種)/夏德儀
第十章 海紀輯要弁言(第二二種)/夏德儀
第十一章 閩海紀略弁言(第二三種)/周憲文
第十二章 海上見聞錄弁言(第二四種)/夏德儀
第十三章 賜姓始末弁言(第二五種)/吳幅員
第十四章 臺灣雜詠合刻弁言(第二八種)/周憲文
第十五章 臺灣彙錄甲集弁言(第三一種)/夏德儀
第十六章 從徵實錄弁言(第三二種)/夏德儀
第十七章 靖海紀略弁言(第三三種)/周憲文
第十八章 靖海志後記(第三五種)/夏德儀
附:靖海志及海上見聞錄合校記
第十九章 臺灣紀事弁言(第三六種)/夏德儀
第二十章 雲林縣採訪冊弁言(第三七種)/周憲文
第二十一章 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弁言(第三八種)/夏德儀
第二十二章 甲戌公牘鈔存弁言(第三九種)/夏德儀
臺海思慟錄弁言(第四十種)/周憲文
第二十三章 北郭園詩鈔弁言(第四一種)/夏德儀
第二十四章 海南雜著弁言(第四二種)/夏德儀
第二十五章 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弁言(第四三種)/周憲文
第二十六章 裨海記遊弁言(第四四種)/方豪
第二十七章 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弁言(第四六種)/夏德儀
第二十八章 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後記/曹永和
附: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譯文考證
第二十九章 戴施兩案紀略弁言(第四七種)/周憲文
第三十章 苑裏志弁言(第四八種)/周憲文
第三十一章 滄海遺民謄稿後記(第五十種)/周憲文
第三十二章 臺灣生熟番紀事後記(第五一種)/周憲文
第三十三章 安平縣雜記弁言(第五二種)/周憲文
第三十四章 臺戰演義弁言(第五三種)/夏德儀
第三十五章 臺灣教育碑記弁言(第五四種)/夏德儀
第三十六章 臺灣採訪冊弁言(第五五種)/周憲文
第三十七章 臺灣採訪冊弁言(第五五種)/周憲文
第三十八章 閩海贈言弁言(第五六種)/方豪
第三十九章 割據三記弁言(第五七種)/夏德儀
第四十章 嘉義管內採訪冊弁言(第五八種)/周憲文
第四十一章 瀛海偕亡記弁言(第五九種)/洪槱
第四十二章 臺海外記弁言(第六十種)/方豪
第四十三章 新竹縣志初稿弁言(第六一種)/吳幅員
第四十四章 楊勇𢡱弁言(第六二種)/周憲文
第四十五章 樹杞林志弁言(第六三種)/林真
第四十六章 臺灣府志弁言(第六五種)/周憲文
第四十七章 重修臺灣府志弁言(第六六種)/周憲文
第四十八章 鄭成功傳弁言(第六七種)/夏德儀
第四十九章 清一統志臺灣府弁言(第六八種)/夏德儀
第五十章 鄭氏關係文書弁言(第六九種)/吳幅員
附:鄭氏關係文書暨石井本宗族譜校勘記
第五十一章 領雲海日樓詩鈔後記(第七十種)/周憲文
第五十二章 臺灣日記與稟啟弁言(第七一種)/周憲文
附:臺灣日記與稟啟後記
第五十三章 鳳山采訪冊弁言(第七三種)/周憲文
第五十四章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後記(第七四種)/周憲文
第五十五章 恆春縣志弁言(第七五種)/方豪
第五十六章 天妃顯聖錄後記(第七七種)/夏德儀
第五十七章 清代臺灣職官印錄弁言(第七八種)/夏德儀
第五十八章 臺灣司法債權編弁言(第七九種)/林真
第五十九章 金門志後記(第八十種)/吳幅員
第六十章 臺東州采訪冊弁言(第八一種)/方豪
第六十一章 內自訟齋文選弁言(第八二種)/周憲文
第六十二章 中福堂選集弁言(第八三種)/周憲文
第六十三章 福建通志臺灣府弁言(第八四種)/夏德儀
第六十四章 南明野史弁言(第八五種)/吳幅員
第六十五章 斯未信齋文編弁言(第八七種)/周憲文
第六十六章 左文襄公奏牘弁言(第八八種)/吳幅員
第六十七章 臺灣遊記弁言(第八九種)/夏德儀
第六十八章 番社采風圖考弁言(第九十種)/夏德儀
第六十九章 噶瑪蘭志略後記(第九二種)/夏德儀
第七十章 斯未信齋雜錄弁言(第九三種)/周憲文
第七十一章 劍花室詩集弁言(第九四種)/連震東
第七十二章 張文襄選集弁言(第九七種)/吳幅員
第七十三章 哀臺灣箋釋弁言(第一○○種)/夏德儀
第七十四章 欽定平臺灣紀略弁言(第一○二種)/周憲文
第七十五章 臺灣縣志後記(第一○三種)/方豪
第七十六章 澎湖臺灣紀略弁言(第一○四種)/周憲文
第七十七章 明季三朝野史弁言(第一○六種)/夏德儀
第七十八章 臺風雜記弁言(第一○七種)/夏德儀
第七十九章 彰化節孝冊弁言(第一○八種)/夏德儀
第八十章 臺灣海防檔弁言(第一一○種)/吳幅員
第八十一章 思文大紀弁言(第一一一種)/夏德儀
第八十二章 續補明紀編年弁言(第一一四種)/吳幅員
第八十三章 魯春秋弁言(第一一八種)/周憲文
第八十四章 諸蕃志弁言(第一一九種)/周憲文
第八十五章 臺灣通志弁言(第一二○種)/夏德儀
第八十六章 續修臺灣府志弁言(第一二一種)/周憲文
第八十七章 使署閒情後記(第一二二種)/楊雲萍
第八十八章 徐闇公先生年譜後記(第一二三種)/夏德儀
第八十九章 鳳山縣志弁言(第一二四種)/李騰嶽
第九十章 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弁言(第一二五種)/周憲文
第九十一章 清朝柔遠記選錄弁言(第一二六種)/周憲文
第九十二章 臺海見聞錄弁言(第一二九種)/周憲文
第九十三章 臺灣通志弁言(第一三○種)/周憲文
第九十四章 李文忠公選集弁言(第一三一種)/周憲文
第九十五章 續明紀事本末弁言(第一三三種)/吳幅員
第九十六章 海外慟哭記弁言(第一三五種)/周憲文
第九十七章 罪惟錄選輯弁言(第一三六種)/周憲文
第九十八章 黃漳浦文選弁言(第一三七種)/夏德儀
第九十九章 臺灣府賦役冊弁言(第一三九種)/吳幅員
第一百章 續修臺灣縣志弁言(第一四○種)/周憲文
第一百零一章 張蒼水詩文集弁言(第一四二種)/周憲文
第一百零二章 新竹縣采訪冊弁言(第一四五種)/周憲文
第一百零三章 窺園留草後記(第一四七種)/黃典權
第一百零四章 臺灣中部碑文集成弁言(第一五一種)/劉枝萬
第一百零五章 明季荷蘭人侵據澎湖殘檔弁言(第一五四種)/夏德儀
第一百零六章 清初海疆圖說弁言(第一五五種)/吳幅員
第一百零七章 鄭氏史料初編弁言(一)(第一五七種)/夏德儀
第一百零八章 鄭氏史料初編弁言(二) /周憲文
第一百零九章 苗栗縣志弁言(第一五九種) /周憲文
第一百一十章 東山國語弁言(第一六三種)/夏德儀
第一百一十一章 清聖祖實錄選輯弁言(第一六五種)/吳幅員
第一百一十二章 雅言弁言(第一六六種) /周憲文
第一百一十三章 清世宗實錄選輯弁言(第一六七種)/吳幅員
第一百一十四章 鄭氏史料續編弁言(第一六八種)/夏德儀
第一百一十五章 南明史料弁言(第一六九種)/夏德儀
第一百一十六章 櫟社沿革志略弁言(第一七○種)/吳幅員
第一百一十七章 淡水廳築城案卷弁言(第一七一種)/劉枝萬
第一百一十八章 淡水廳志弁言(第一七二種) /周憲文
第一百一十九章 臺案彙錄乙集弁言(第一七三種)/夏德儀
第一百二十章 清代官書明臺灣鄭氏亡事弁言(第一七四種)/夏德儀
第一百二十一章 臺灣彙錄丙集弁言(第一七六種)/夏德儀
第一百二十二章 爝火錄弁言(第一七七種)/吳幅員
第一百二十三章 臺案彙錄丁集弁言(第一七八種)/夏德儀
第一百二十四章 臺案彙錄戊集弁言(第一七九種)/夏德儀
第一百二十五章 清職貢圖選弁言(第一八○種)/吳幅員
第一百二十六章 臺灣府輿圖纂要弁言(第一八一種)/吳幅員
第一百二十七章 朱舜水文選弁言(第一八二種)/吳幅員
第一百二十八章 聖安本紀弁言(第一八三種)/夏德儀
第一百二十九章 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弁言(第一八四種)/吳幅員
第一百三十章 臺灣地輿全圖弁言(第一八五種)/吳幅員
第一百三十一章 清高宗實錄選輯弁言(第一八六種)/吳幅員
第一百三十二章 清仁宗實錄選輯弁言(第一八七種)/周憲文
第一百三十三章 清宣宗實錄選輯弁言(第一八八種)/周憲文
第一百三十四章 清文宗實錄選輯弁言(第一八九種)/周憲文
第一百三十五章 清穆宗實錄選輯弁言(第一九○種)/吳幅員
第一百三十六章 臺案彙錄己集弁言(第一九一種)/夏德儀
第一百三十七章 法軍侵臺檔弁言(第一九二種)/吳幅員
第一百三十八章 清德宗實錄選輯弁言(第一九三種)/周憲文
第一百三十九章 清先正事略選弁言(第一九四種)/吳幅員
第一百四十章 福建通志列傳選弁言(第一九五種)/夏德儀
第一百四十一章 流求與雞籠山弁言(第一九六種)/吳幅員
第一百四十二章 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弁言(第一九七種)/吳幅員
第一百四十三章 清季外交史料選輯弁言(第一九八種)/吳幅員
第一百四十四章 福建省例弁言(第一九九種)/夏德儀
第一百四十五章 臺案彙錄庚集弁言(第二○○種)/夏德儀
附:臺案彙錄庚集後記
第一百四十六章 半崧集簡編弁言(第二○一種)/吳幅員
第一百四十七章 潛園琴餘草簡編弁言(第二○二種)/吳幅員
第一百四十八章 籌辦夷務始末選輯弁言(第二○三種)/吳幅員
第一百四十九章 法軍侵臺檔補編弁言(第二○四種)/吳幅員
第一百五十章 臺案彙錄辛集弁言(第二○五種)/夏德儀
第一百五十一章 戴案紀略弁言(第二○六種)/吳幅員
第一百五十二章 陳清端公年譜後記(第二○七種)/吳幅員
第一百五十三章 雅堂文集弁言(第二○八種)/夏德儀
第一百五十四章 野史無文後記(第二○九種)/夏德儀
第一百五十五章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弁言(第二一○種)/吳幅員
第一百五十六章 臺灣旅行紀弁言(第二一一種)/吳幅員
第一百五十七章 魂南記弁言(第二一二種)/吳幅員
第一百五十八章 海濱大事記弁言(第二一三種)/吳幅員
第一百五十九章 清稗類鈔選錄弁言(第二一四種)/夏德儀
第一百六十章 後蘇龕合集弁言(第二一五種)/黃典權
第一百六十一章 臺灣輿地彙鈔弁言(第二一六種)/吳幅員
第一百六十二章 鮚埼亭集選輯弁言(第二一七種)/夏德儀
第一百六十三章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弁言(第二一八種)/黃典權
第一百六十四章 廣陽雜記選弁言(第二一九種)/吳幅員
第一百六十五章 碑傳選輯弁言(第二二○種)/吳幅員
第一百六十六章 清史講義選輯弁言(第二二一種)/周憲文
第一百六十七章 臺灣兵備手抄弁言(第二二二種)/夏德儀
第一百六十八章 續碑傳選輯弁言(第二二三種)/吳幅員
第一百六十九章 臺灣詩薈雜文鈔弁言(第二二四種)/吳幅員
第一百七十章 藏山閣集選輯弁言(第二二五種)/吳幅員
第一百七十一章 清會典臺灣事例弁言(第二二六種)/吳幅員
第一百七十二章 臺案彙錄壬集弁言(第二二七種)/吳幅員
第一百七十三章 臺案彙錄癸集弁言(第二二八種)/吳幅員
第一百七十四章 清經世文編選錄弁言(第二二九種)/吳幅員
第一百七十五章 清耆獻類徵選編弁言(第二三○種)/吳幅員
第一百七十六章 吳光錄使閩奏稿選錄弁言(第二三一種)/吳幅員
第一百七十七章 漳州府志選錄弁言(第二三二種)/吳幅員
第一百七十八章 泉州府志選錄弁言(第二三三種)/吳幅員
第一百七十九章 行在陽秋弁言(第二三四種)/周憲文
第一百八十章 幸存錄弁言(第二三五種)/周憲文
第一百八十一章 籌辦夷務始末選輯補編弁言(第二三六種)/吳幅員
第一百八十二章 崇相集選錄弁言(第二三七種)/吳幅員
第一百八十三章 東明聞見錄弁言(第二三八種)/周憲文
第一百八十四章 閩事紀略弁言(第二三九種)/吳幅員
第一百八十五章 青燐屑弁言(第二四○種)/周憲文
第一百八十六章 吳耿尚恐四王全傳弁言(第二四一種)/周憲文
第一百八十七章 江南聞見錄弁言(第二四二種)/周憲文
第一百八十八章 清史稿臺灣資料集輯弁言(第二四三種)/吳幅員
第一百八十九章 明亡述略弁言(第二四四種)/周憲文
第一百九十章 島噫詩弁言(第二四五種)/陳漢光
第一百九十一章 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弁言(第二四七種)/吳幅員
第一百九十二章 遇變紀略弁言(第二四九種)/周憲文
第一百九十三章 述報法兵侵臺灣紀事殘輯弁言(第二五三種)/吳幅員
第一百九十四章 研堂見聞雜記弁言(第二五四種)/周憲文
第一百九十五章 清奏疏選彙弁言(第二五六種)/吳幅員
第一百九十六章 東華選錄輯弁言(第二六二種)/吳幅員
第一百九十七章 中日戰輯選錄弁言(第二六五種)/吳幅員
第一百九十八章 浙東紀略弁言(第二六八種)/周憲文
第一百九十九章 崇禎長編弁言(第二七○種)/吳幅員
第二百章 崇禎記聞錄弁言(第二七二種)/吳幅員
第二百零一章 東華續錄選輯弁言(第二七三種)/吳幅員
第二百零二章 清史列傳選弁言(第二七四種)/吳幅員
第二百零三章 明季北略弁言(第二七五種)/周憲文
第二百零四章 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弁言(一)(第二七六種)/馮用
第二百零五章 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弁言(二)
第二百零六章 光緒朝東華續錄選輯弁言(第二七七種)/吳幅員
第二百零七章 清季臺灣洋務史料弁言(第二七八種)/吳幅員
第二百零八章 甲乙日曆弁言(第二七九種)/吳幅員
第二百零九章 臺灣詩鈔弁言(第二八○種)/吳幅員
第二百一十章 通鑑輯覽明季編年弁言(第二八一種)/吳幅員
第二百一十一章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弁言(第二八三種)/吳幅員
第二百一十二章 李文襄公奏疏與文移弁言(第二八五種)/吳幅員
第二百一十三章 雪交亭正氣錄弁言(第二八六種)/吳幅員
第二百一十四章 使琉球錄三種弁言(第二八七種)/吳幅員
第二百一十五章 明經世文編選錄弁言(第二八九種)/吳幅員
第二百一十六章 臺灣對外關係史料弁言(第二九○種)/吳幅員
第二百一十七章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弁言(第二九一種)/吳幅員
第二百一十八章 清代琉球記錄集輯弁言(第二九二種)/吳幅員
第二百一十九章 琉球國志略弁言(第二九三種)/吳幅員
校後記/吳幅員
序/周憲文
第一章 臺灣割據志卷頭語(第一種)/周憲文
第二章 臺灣鄭氏紀事後記(第五種)/周憲文
第三章 閩海紀要弁言(第一一種)/周憲文
第四章 東征後記(第一二種)/周憲文
第五章 靖海紀事後記(第一三種)/夏德儀
第六章 治臺必告錄弁言(第一七種)/周憲文
第七章 臺灣志略弁言(第一八種)/夏德儀
第八章 陽台筆記後記( (第二十種)/夏德儀
第九章 巡臺退思錄弁言(第二一種)/夏德儀
第十章 海紀輯要弁言(第二二種)/夏德儀
第十一章 閩海紀略弁言(第二三種)/周憲文
第十二章 海上見聞錄弁言(第二四種)/夏德儀
第十三章 賜姓始末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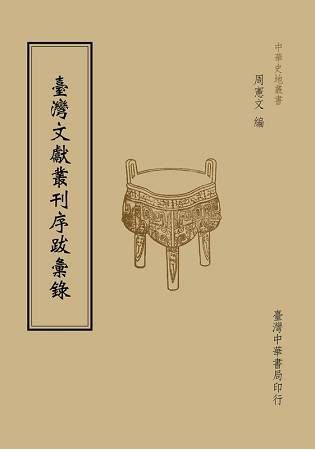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