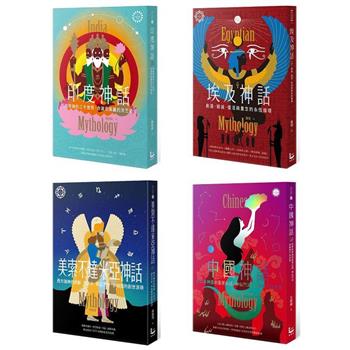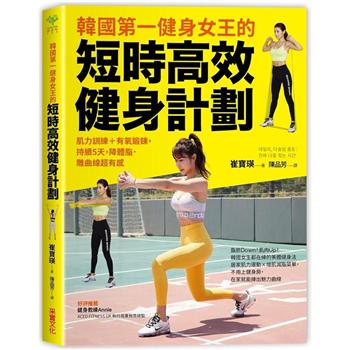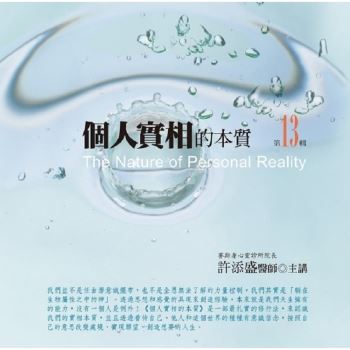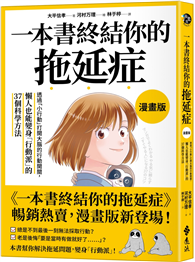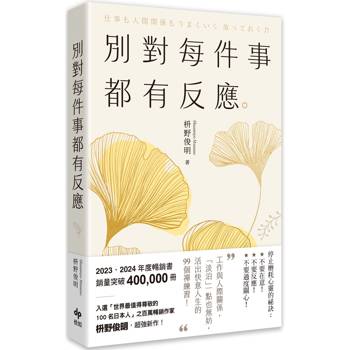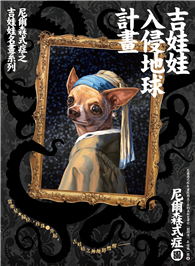§遺忘之歌 鄭炯明
有一天,當我無法
再想念你的時候,請不必驚訝
我是不由自主地
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卻找不到出口
我不記得你是誰
我不記得我的帽子放在哪裡
我不記得聽過你的歌聲
我不記得我們曾共度
一段美好的時光
我要請你原諒
經過長時間精神和肉體的折磨
我深深體會
遺忘,無法使人完全忘記痛苦
也無法使人幸福
坐在公園的椅子上
我們默默地互看一眼
幾棵高大的印度紫檀
隨風飄落滿地的黃色花瓣
但願我能永遠記得你
(2018/10/08)
§才藝出眾的旅阿台灣詩人音樂家 劉安慶
林問語女士,出生於台灣,在台灣讀完大一時隨父母移民阿根廷。接著在阿根廷完成醫學院的學業成為醫師。由於父母親是基隆愛樂合唱團成員,因此自小酷愛音樂,在阿根廷追隨有名的聲樂家學習聲樂。
因此,她會彈鋼琴、作曲、填詞,並且也寫詩。目前從事於聲樂演唱的事業,經常受邀前往世界各地演唱。她在返台期間也曾擔任基隆愛樂合唱團的指導老師。
一群旅阿台灣友人在2010年左右成立「阿根廷台灣文化協會」,2012年編撰了世界上第一部由民間自發的《阿根廷台灣人移民史》(於2012年10月在台北舉辦新書發表會),林問語女士負責為該協會譜寫〈阿根廷台灣人移民史〉史歌,並且由基隆愛樂合唱團在台灣演出。
最近有機緣趁林問語空閒停留在阿根廷的時候,一起和友人聚餐,席間受到眾人的鼓舞,飯後她即席演唱了一首她的詩作,名叫〈歸來吧!這時晚霞滿天〉。她的才藝精湛真的令人驚歎,她說有空時也寫詩。
藉由《臺灣現代詩》篇幅,推薦這位優秀作家,希望讀者喜歡。
§歸來吧!這時晚霞滿天
文:林問語
圖:蘇翎崴
媽媽的懷抱裡,
沒有止不住的淚水;
爸爸的肩膀上,
遍是摘得到的星月;
小時候的時候,
時刻盼望著放學回家,
踩著一路的七彩霞光。
回眸凝望,
在山的那一邊,
可愛的家園,
歸來吧!孩子,
這時晚霞滿天…
遊子的胸襟中,
沒有追不到的理念;
青春的翅膀上,
滿是握得到的契機;
少年郎的夢想,
殷切努力著灌溉茁壯,
踏著漫沒的夜露曙光。
低頭徘徊,
在海的另一岸,
瀾濤港邊,
歸來吧!孩子,
這時晚霞滿天…
(2018/08/27 於Bs.As.阿根廷)
§來不及邀約 蔡秀菊
去年十一月七日上午,接到陳師母(許玉蘭女士)打來的電話,她問我台中文學館是否有什麼花的特展?她說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派人來找她索取結婚照片,說要使用於花博的相關特展,我立刻想起這是配合台中國際花博的「花愛•文學特展」,於是約了巫凱琳於九日開車載師母去台中文學館參觀。
師母在特展室內看到當年和陳千武老師的結婚照,非常愉快地敘述和陳老師相戀過程。陳老師是家中長子,下有二弟四妹,母親擔心她的身體瘦弱,無法承擔大家庭長媳的責任,初始反對這門婚姻,但是她心意已定,最後母親也只好答應。師母笑盈盈地敘說陳年往事,讓人感受到文學的愛情召喚,果真力量無限!師母除了反覆咀嚼文學家丈夫的幸福之愛,也不忘感謝公婆的悉心照拂。她說平日忙於教職,還好有婆婆承攬許多家務事,丈夫及公婆也幫忙照顧三個孩子成長,這一生都過著幸福的日子。師母以如此善體人意、珍惜幸福的心情,接待所有與陳千武老師交往的文學家、親朋好友、後生晚輩等,讓人倍感溫馨。
陳千武老師有一首著名詩作〈生命的鼓手〉「時間。遴選我作一個鼓手╱鼓面是用我的皮張的。╱鼓的聲音很響亮╱超越各種樂器的音響╱鼓聲裡滲雜著我寂寞的心聲╱波及遠處神祕的山峰而迴響╱於是收到迴響的寂寞時╱我不得不,又拚命地打鼓……╱鼓是我痛愛的生命我是寂寞的鼓手。」如果陳老師用他的皮拉成鼓面,師母就是敲打生命之鼓的鼓手,兩人合力敲出節奏有致的生命之歌。
我開始接觸詩人團體是參加「’95亞洲詩人會議台灣日月潭大會」,蒙陳千武老師推薦加入笠詩社,此後得以密切參與詩社活動。一九九六年八月,跟隨陳千武老師及其他詩人前輩參加於群馬縣前橋市舉辦的「第16屆世界詩人大會」,跟陳老師的互動隨之增加,經常至陳老師家請益,師母都在旁一起閒話家常,彼此自然而然更加親近。
多次拜訪陳千武老師府上,聽他論述現代詩理論,尤其以台灣人志願兵到南洋作戰經驗寫成的《獵女犯》(改版後易名《活著回來》),故事精采令人百聽不厭。我開始對陳老師的詩作、詩論和小說充滿興趣,於是下功夫將他的作品逐一賞讀和比較他人評論做成筆記,有系統地書寫閱讀心得。後來師母將她的日文自傳『玉蘭の移り香』借我閱讀,方才曉得原來陳千武老師的詩人風采和南洋作戰經驗,深深擄獲伊人芳心。
陳千武老師和日韓兩國詩人交往密切,是東亞詩人交流的重要推手。重要的國外文學交流活動,都有師母隨行照顧後生晚輩。一九九七年四月五日至七日,我有幸參加日本『こだま』兒童詩誌發行十週年紀念會,除陳千武夫婦外,另有趙天儀、賴洝和我就讀小學的女兒王松玉同行,因此和『こだま』主編保坂登志子建立形同姊妹的情誼。日後保坂登志子偕夫婿保坂陽一郎訪台,也曾帶她的女兒和孫女來台,我都有機會和陳千武夫婦一起陪同他們拜會詩人及安排參觀旅遊。
一九九八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八日,跟隨陳千武夫婦遠至日本岩手縣,參加由北上市「現代詩歌文學館」主辦之第二屆東亞詩書展,首站在千葉縣與當地詩人交流,第一次認識日本千葉縣『吠』詩刊社長山口惣司,後來由陳老師推薦加入該詩社,成為外國人社員,我的《司馬庫斯部落詩抄》,由賴洝前輩協助翻譯逐期發表於該詩刊。日韓詩人常來台拜訪陳千武老師,幸好有在東京出生、小學畢業後舉家返台繼續完成中學教育的師母幫忙接待,可說是紅花綠葉,相襯得宜。
二○○四年五月十四日至十六日,陳千武老師率團參加於日本千葉縣東庄町召開之「第三回東亞文化交流會」,當時我剛好在新竹縣尖石鄉的司馬庫斯部落進行碩士論文研究,徵得大會同意邀請司馬庫斯部落頭目Icyeh Sulung、長老Yuraw Icang出席盛會。大會主席『吠』詩刊社長山口惣司安排第一場活動讓我們介紹「司馬庫斯部落」,賴洝前輩擔任即席翻譯。頭目和長老的泰雅語古調和歌謠深深打動日本詩人的心,會後橫濱大學榮譽教授小海永二不斷誇讚司馬庫斯部落頭目維護族群傳統文化的用心,並透過陳千武老師傳達想去司馬庫斯部落拜訪的心願。當年十月初,小海永二夫婦來台,我設法安排他們夫婦於十月五日至八日上山,因為我不諳日語,所以由陳師母陪同隨行翻譯。八月底不巧遇到艾利颱風侵襲,司馬庫斯部落聯外道路中斷,十月五日,頭目的弟弟Ikit和我們一行四人在新竹火車站會面之後載我們上山,司馬庫斯二號橋仍未修復,車子必下切溪谷再爬升到對岸道路。當時只有我們四人是外來訪客,生態旅遊全部停擺。
我們四人受到部落的熱情招待,搗小米、介紹泰雅族的傳統打獵方式、演唱泰雅古調和歌謠,十月六日晚上參加教會家庭禮拜兼台日交流座談會。Icyeh頭目帶我們踏查Koraw生態,我也陪小海永二夫婦和師母前往巨木群,走到臭味溪。有師母一路陪同解說,讓小海夫婦對司馬庫斯部落留下深刻印象。三位長者都上了年紀,還能忍耐長途山路顛簸,更能入境隨俗跋涉山路,不需要我特別為他們操心適應問題,不愧是體貼的長輩。翌年十月八日至十日,我組團陪同小海永二夫婦二度拜訪司馬庫斯部落,小海夫婦從部落出發走完司立富瀑布行程,毅力與耐力令人欽佩。小海永二教授於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離世,夫人小海伸子捎信告訴我,兩趟司馬庫斯部落之旅,是他們畢生難忘的經驗,小海教授的告別式特別選用在司馬庫斯部落拍攝的照片。我想如果沒有陳師母陪同到司馬庫斯部落,透過師母的翻譯,小海夫婦就無法深刻感受到泰雅文化蘊藏的豐富生命力。
二○一二年四月三十日陳千武老師過世,之後師母白天獨居老家,傍晚再自行搭公車去兒孫家過夜。由陳千武、趙天儀前輩催生的台灣現代詩人協會同仁,有空閒時也會和師母聯絡,閒話家常。賴欣擔任理事長期間,協會有活動都會邀請師母參加,看到師母愉快的笑容和健朗的腳步,同仁也覺得寬心。
去年十一月九日陪師母參觀台中文學館「花愛」特展之後,一直想找時間邀她共進午餐,卻因農歷年前忙著大掃除而耽擱下來,想在過年前約師母時,連打數日電話竟然無人接聽,後來聯絡上師母的家人才知道她發生意外,一時錯愕不敢置信。如果早幾天聯絡師母,說不定她就逃過一劫,我為這種怠惰拖延感到十分自責。來不及邀約的懊惱,只能說給自己聽了。
(2019/04/23)
§山谷中流水和岩石的邂逅――再讀吉蓮‧克拉克詩作
楊 笛
從傳統到現代,從西方到東方,有些價值隨著時間正在流逝中;
但那些可以存留至今的,或許可以從這些女詩人的作品中找到,
屬於東方和西方的共同珍貴價值,因為她們所述說的不僅是詩,
更是人。
一、前 言
吉蓮‧克拉克(Gillian Clarke, 1937-),威爾斯民族女詩人,身為威爾斯的女兒,肩負族群文化傳承,以及詩文閱讀和創作的教育責任。因為她作品甚多,內容更富有文化傳承和鄉土情感的價值,值得與愛詩人再次分享,因此朝著地誌詩(topographical poetry註)的概念分享她的二首詩。
地誌詩(topographical poetry)主要描述地方或區域,具體地描繪特定的鄉村城鎮、山嶺、溪流、等等;除了寫景,詩人的默想思緒,針對風土民情和人文歷史的回顧、批判和展望,這些都可融入作品中。地誌詩的書寫可以展現詩人對於土地的情感反應,就像認同、肯定、憂心、守護等,因此這類的詩作可以突顯並建構本土區域的特性。(鄭琮墿,2016)
克拉克為身為威爾斯原住民的知識分子,藉由詩作追溯社區生活的地理和人文樣貌,也不乏族群神話傳說在詩文中,意在加深自我族群意識;試圖建構屬於威爾斯原民文化空間的同時,也與日漸衰微的人文藝術傳統做聯結;這種聯結對詩人和讀者,是一種「返回本源」進而「開創新局」的珍貴過程。
二、詩作賞析
◎Valley
In water-memory the river turns
always the same way at the boulder
and the bridge.
An ess of current at the land’s shoulder,
The falling back of a sleeve where light burns
Otter silk below the ridge.
A million million years of water-work
to make this place. A whispering seepage
through lion grass on fire
under snow . A stream’s gleaming back
lifts from the mist and marshy weep
as flood meets deep and secret aquifers.
Dwyfor and Glaslyn, green-black rivers
of the north tumbling boulders for the slate.
A rumour of ice, flood-fingers in sodden earth.
The bell of an old glacier in the rock’s seam
So it splits clean at a tap of light.
Weather works the mountain to the bone
with the let juices of rain, the rising sea’s erosion,
a river’s gravity, flood’s cold reflection,
a valley cut by water over stone.
◎山 谷
沿著河岸和橋樑,
屬於「水的故事」正被傳說著,
正如往常流過的河水一樣。
路肩的水流滑落到水門的防護網,
在哪裡陽光將山脊下水獺的皮毛,
照得閃閃銀亮。
千萬年以來的流水工程,
創造了這個地方。
呢喃的水聲滲透到堆雪底下,
讓野草撩起火源。
當洪水碰接到深層的含水層,
水源因著霧霾和沼澤的溢漿反射出光芒。
鄰近二個小鎮
北方的河水呈現黑綠漸層,
因著岩片和漂礫傾瀉而下,
在腐爛的泥漿中,冰塊飄動的響聲和大水的入侵,
在石頭縫隙中可聽到冰河碎片的輕碰聲,
在陽光的照耀下,很果斷的裂開了。
氣候改變山谷原有風貌,
海平面因而上升。
水的重力、水患無情的沖刷,
水和石頭間的密切碰撞,
碰撞出今天山谷的模樣。
——楊笛 譯
這首詩陳述典型的地景形成過程,是克拉克表現地誌文學的佳作。她觀賞本土雕塑家Meical Watts的琉璃和岩片雕刻展後,聯想到土地與人的關係,水流和岩石的碰撞如何造成水工程的建立,從百萬年前到今天形成今日的山谷。使用細膩生動的語言,來描述景觀成形的細節和過程。
詩人猶如一個生態紀錄片的口述者,談論到大地的景象,好似詩人與土地融合,參與每一次河流和岩塊的相遇和碰撞,為在大自然演變中所經歷的變動,作了客觀、理性的見證,同時藉由地理的更變,來反思威爾斯故鄉的改變,顯示詩人對家鄉土地的緬懷。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臺灣現代詩:第58期的圖書 |
 |
$ 237 ~ 238 | 臺灣現代詩:第58期
作者:《臺灣現代詩》 主編 出版社:台灣現代詩人協會 出版日期:2019-06-15 語言:繁體/中文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臺灣現代詩:第58期
1990年代黃明川導演以三部電影劇情長片《西部來的人》、《寶島大夢》、《破輪胎》,探討自我認同、軍中樂園、政治宗教神話,受到電影圈、當代藝術與評論界的熱切討論。黃明川導演長期聚焦於台灣當代藝術人文紀錄片,本協會舉辦黃明川導演作品「《櫻之聲》紀錄片放映暨座談會」,該片記錄了台灣「跨語世代」多位重要作家的身影,藉此探討如何建構台灣文學的特色。
台灣現代詩人協會創會前輩陳千武先生的夫人許玉蘭女士,不幸於今年三月往生,失去如此親切的長輩,著實令人不捨。本期特別以「許玉蘭女士紀念專輯」以示哀悼。
「我畫(i Paint)畫會十周年詩╱畫展」於2019年2月17日在臺中港區藝術中心舉行開幕式,共展出83件畫作,91首賦詩,畫會與詩社同仁豐沛的創作力由此可見一斑,本期刊出部分詩畫以饗讀者。
本期刊載黃明川導演作品「《櫻之聲》紀錄片放映暨座談會」,探討台灣「跨語世代」多位重要作家的身影,藉此探討如何建構台灣文學的特色。
歡迎旅阿台裔詩人林問語聲樂家詩人加入《臺灣現代詩》作者陣容,對威爾斯詩人吉蓮•克拉克有深入研究之楊笛,特別介紹吉蓮•克拉克地誌詩之特色。其他日、韓、英、西語詩譯介均深具特色,值得閱讀收藏。
作者簡介:
台灣現代詩人協會成立於2000年7月,並於2005年3月發行《臺灣現代詩》季刊,於2019年6月,已出刊至58期,堂堂邁入第十五年。本協會除定期發行機關詩誌外,也成功地舉辦多項大小活動,以及在全臺北中南各地深入大學院校,與授課老師或詩社合作舉辦「作品合評」、「現代詩座談會」,並先後承辦二屆臺日韓的「東亞詩書展」、三屆「亞細亞詩感想祝祭」。本協會另發行《十年詩萃》、《2017亞細亞詩萃》華、韓、日、英四語詩選集,頗受各界好評。
章節試閱
§遺忘之歌 鄭炯明
有一天,當我無法
再想念你的時候,請不必驚訝
我是不由自主地
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卻找不到出口
我不記得你是誰
我不記得我的帽子放在哪裡
我不記得聽過你的歌聲
我不記得我們曾共度
一段美好的時光
我要請你原諒
經過長時間精神和肉體的折磨
我深深體會
遺忘,無法使人完全忘記痛苦
也無法使人幸福
坐在公園的椅子上
我們默默地互看一眼
幾棵高大的印度紫檀
隨風飄落滿地的黃色花瓣
但願我能永遠記得你
(2018/10/08)
§才藝出眾的旅阿台灣詩人音樂家 劉安慶
林問語女士,出生於台灣,在...
有一天,當我無法
再想念你的時候,請不必驚訝
我是不由自主地
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卻找不到出口
我不記得你是誰
我不記得我的帽子放在哪裡
我不記得聽過你的歌聲
我不記得我們曾共度
一段美好的時光
我要請你原諒
經過長時間精神和肉體的折磨
我深深體會
遺忘,無法使人完全忘記痛苦
也無法使人幸福
坐在公園的椅子上
我們默默地互看一眼
幾棵高大的印度紫檀
隨風飄落滿地的黃色花瓣
但願我能永遠記得你
(2018/10/08)
§才藝出眾的旅阿台灣詩人音樂家 劉安慶
林問語女士,出生於台灣,在...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詩」「畫」兩字向被合體形容美好的景物和情境,就像「詩情畫意」及「如詩如畫」,也常為文人雅士攪拌調混,稱道「詩中有畫」或「畫中有詩」—「詩」「畫」似乎一直如此親密相映。
我畫畫會從2011年第一次台中市文英館的展覽起,即與台灣現代詩人協會合作,同時併陳雙方的「詩」「畫」創作,開展詩與畫的對話;詩不是畫的圖說,而畫也不是詩的插圖,兩種作品不拘泥表現的內容是否有一定的交集,這種嶄新的展覽形式頗受佳評。
畫會成員來自不同領域,作品展現獨特風格,媒材運用廣泛,除油彩、膠彩、壓克力及複合媒材等,更擴及數位藝術...
我畫畫會從2011年第一次台中市文英館的展覽起,即與台灣現代詩人協會合作,同時併陳雙方的「詩」「畫」創作,開展詩與畫的對話;詩不是畫的圖說,而畫也不是詩的插圖,兩種作品不拘泥表現的內容是否有一定的交集,這種嶄新的展覽形式頗受佳評。
畫會成員來自不同領域,作品展現獨特風格,媒材運用廣泛,除油彩、膠彩、壓克力及複合媒材等,更擴及數位藝術...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臺灣現代詩》第58期目錄
◆卷頭語
詩畫合奏十年╱袁國浩
◆詩創作
遺忘之歌╱鄭烱明
黑的 在哪裡╱賴 欣
正午過大笨鐘╱陳銘堯
雨點╱靜靜喝一杯╱旅 人
一行詩(5)╱令和賦詩一首╱永 井
瞳的連作(5) ╱葉宣哲
寫給小孫女波妞╱蔡榮勇
古典玫瑰園――寄畫家黃騰輝兄╱林盛彬
暗夜瘋狗浪╱顧台安
有一種聲音╱袖 子
從傷心流到幸福時光╱秋的接力賽╱柯 七
唱歌給自己聽(11) ╱蔡秀菊
生命之歌╱林俊樑
力量╱和 希
秋靜╱江 昀
高美濕地的召喚╱李益美
森田家的愛(1)╱王...
◆卷頭語
詩畫合奏十年╱袁國浩
◆詩創作
遺忘之歌╱鄭烱明
黑的 在哪裡╱賴 欣
正午過大笨鐘╱陳銘堯
雨點╱靜靜喝一杯╱旅 人
一行詩(5)╱令和賦詩一首╱永 井
瞳的連作(5) ╱葉宣哲
寫給小孫女波妞╱蔡榮勇
古典玫瑰園――寄畫家黃騰輝兄╱林盛彬
暗夜瘋狗浪╱顧台安
有一種聲音╱袖 子
從傷心流到幸福時光╱秋的接力賽╱柯 七
唱歌給自己聽(11) ╱蔡秀菊
生命之歌╱林俊樑
力量╱和 希
秋靜╱江 昀
高美濕地的召喚╱李益美
森田家的愛(1)╱王...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