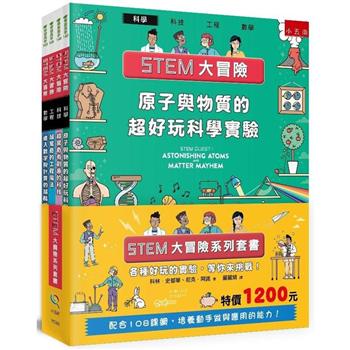圖書名稱:她們的名字
無法忽視的精采!轟動倫敦書展,100萬美金天價售出版權
一出版便空降《紐約時報》暢銷榜,售出全球英、法、義等20國版權!
TriStar影業買下電影版權,將由美劇「醜聞」女星凱莉‧華盛頓主演
Goodreads超過4萬讀者評價,Amazon網路書店5顆星好評推薦
榮獲紐約公共圖書館與《柯克斯評論》2018年最佳圖書!
《今日美國報》《華盛頓郵報》《出版家週刊》等國際媒體盛讚
知名主播/主持人 夏嘉璐
小說家 倪采青
人氣作家 螺螄拜恩 心有戚戚推薦
我能得到想要的幸福,
只要我放棄自己的名字,成為他人的女兒、妻子與母親……
為了你真心所愛,你願意付出多少?以及,犧牲多少?
若你問布魯克林這些時常在公園聚會的女人,回答可能是:
法蘭西:「我不確定,但我希望可以阻止為了愛情變愚蠢的十八歲的自己。」
可蕾:「一切,只求讓遠離我四年的寫作靈感回來。」
妮爾:「嗯,我等不及銷假回去上班。」
史佳麗:「只要能和他在一起,我願意不惜一切代價,就算只有一夜也好。」
薇妮:「我不知道。」
她們的聚會說著能透露的私事,表現自己最完美的模樣,偷偷羨慕著彼此的生活,
──噢,忘了說,她們只認識四個月。
在一個燠熱的七月四日晚上,她們相約去新潮酒吧喝一杯放鬆,
神祕美麗的單親媽媽薇妮原本不想赴約,
但大家積極幫她找好保母,盛情難卻下,她勉為其難出了門,
可等她深夜回到家,卻發現:嬰兒床上空空如也,她的小孩不見了!
只剩呼呼大睡的保母,和完全沒有被破壞、上了鎖的門窗。
大家驚愕又愧疚,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想幫薇妮找回孩子,
不料在一連串令人心驚膽戰的追查過程中,
她們的真實生活也逐漸被揭露──包括亟欲遮掩的幽暗祕密。
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她們的婚姻飽受考驗,友誼更開始四分五裂……
作者簡介
艾米‧莫洛伊Aimee Molloy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其著作《However Long the Night》曾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她也與其他作者合著了數本非小說類書籍。
《她們的名字》是她的第一本小說。由世界最大出版公司之一HarperCollins 以百萬美金天價搶下版權,甫出版即空降紐約時報排行榜。目前已授權二十國,包括英國、法國、韓國、義大利、荷蘭和西班牙等。
TriStar 影業已取得電影版權,將由美劇「醜聞」的女星凱莉‧華盛頓主演兼製片。
現在跟丈夫和兩個女兒住在紐約布魯克林。
譯者簡介
康學慧
英國里茲大學應用翻譯研究所畢業,從事專職翻譯多年。現居於寶島後山的小鎮,沉醉於書香、稻香與米飯香。譯作包括《冷情浪子》、《最好的妳》、《小謊言》(春光)、《謎蹤系列》(果樹)等。



 共
共  艾米是一個長度單位。1 Em=1018米。
艾米是一個長度單位。1 Em=1018米。 2020/04/08
2020/04/08 2020/04/05
20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