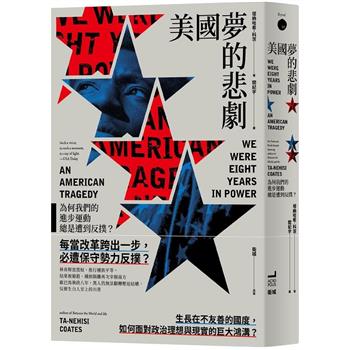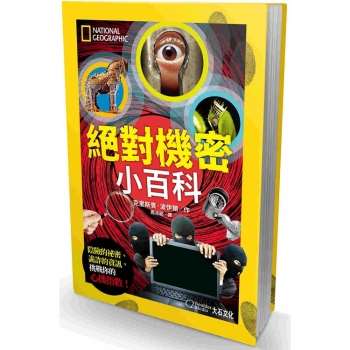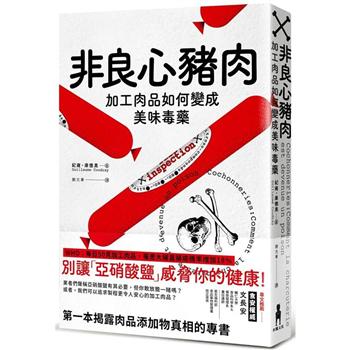第一章 洞房
彥信輕輕打了個呵欠,示意要就寢了。
在秦嬤嬤的指示下,春意和潤雨上來為初晨除去釵環,又服侍著她到屏風後換了件半透明的紅色繡牡丹紗衣,紗衣下雪白絲滑的肌膚和鴛鴦戲水的肚兜若隱若現,穿了比不穿還要誘人,初晨皺起眉頭,指著另一件厚實些的絲袍道:「穿那件。」
春意還未答話,秦嬤嬤不容置疑地道:「就穿這件,這件最合適。」
初晨惱怒地瞪起眼睛,卻發現秦嬤嬤不慍不火地望著她,寸步不讓。初晨淡淡地道:「有些冷,再給我披上件外袍吧!」這回秦嬤嬤倒沒有再說什麼。
初晨才走出屏風,彥信便四仰八叉地倒在床上,懶洋洋地對丫頭道:「備好熱水巾帕,王妃自會服侍本王,妳們退到一旁。」
秦嬤嬤看向初晨一眼,一臉的殷切。
這是要看她的表現了。初晨假笑著迎上去:「王爺,臣妾為您寬衣。」
「唔。」彥信閉著眼伸長了腿,擺出一副安然等她服侍的愜意樣。
初晨正想找個藉口,就聽周福家的媳婦讚道:「哎呀!王妃真是少有的賢惠啊!真不愧是出身於百年世家的貴女。」幾個丫頭婆子連連稱是。
好!她忍!初晨暗自咬牙,為了今後的生存大計,忍。
她心不甘情不願地蹲下為彥信脫鞋、脫襪,剛鬆了口氣,彥信又道:「有勞愛妃了,今天走了太多路,腳有些疼。」
「那王爺的腳泡個熱水吧?」初晨忙上道地建議。
早有丫頭遞過裝滿熱水的銅盆,彥信不客氣的將腳放進了盆裡,假意抱歉地道:「愛妃嬌貴,恐怕沒有做過這些粗活,若不會做、太辛苦,就不要勉強了。」
「不辛苦,服侍王爺是臣妾的本份,也是榮幸。」初晨咬著牙擠出一個笑,趁著沒人注意,在彥信腳上狠狠掐了一下。
彥信猛然坐起身來,貼在她耳邊曖昧地道:「不要挑逗我,我知道妳的意思了,一會定不讓妳失望。」
見初晨滿面通紅,狼狽地縮回手,他心情大好地笑起來。初晨強忍著怒火,面無表情地服侍他洗漱完畢,才得空坐了下來。
秦嬤嬤在床上鋪了一張白綾,嚴肅地道:「王妃真不愧是幾百年的名門望族教出的小姐,很是賢惠得體。服侍丈夫是妻子的本份,更何況王爺身份高貴,老奴先前還擔心王妃出身嬌貴,難免驕矜,做不來這些服侍人的事情。現在看來,王妃做得極好,老奴放心了,對先后也有個交代,老奴這就告退了。」
言罷,她便帶著一幫嬤嬤丫頭靜靜地退了下去。
房裡終於只剩下二人,彥信收起嬉皮笑臉的樣子,沉默地望著初晨。
初晨不敢去看床上的百子千孫大紅被和那刺目的白色,只顧垂頭緊張地揪緊了衣角,突然間眼前一暗,身子一輕,便被彥信騰空抱在了懷裡。
「您做什麼!放開我!」初晨大急,只拚命捶打著彥信的胸脯。
彥信不語,輕輕將她放在床上,俯身上前,用貓盯老鼠般的神色盯著她看。
初晨被他看得毛骨悚然,順著他的目光一看,只見自己的外袍不知何時已被扯開,裡面的紗衣、雪肌和鴛鴦戲水的肚兜通通一覽無遺。
她慌張地伸手去拉衣襟,彥信卻眼明手快地握住她的手。退無可退,初晨緊張地嚥了口口水,目光四下亂瞟,不敢去看彥信。
彥信沉聲一笑,微微瞇了眼:「害怕了?我還以為妳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呢!」
初晨也想猖狂地笑,可是她只擠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表情。她已經是他的妻子,大家都是明白人,她從來就不指望他會大發善心放過她,掙扎只不過是徒勞和自取其辱而已。
彥信顯然對她的順從和安靜很滿意:「我很高興。」他溫柔地把頭伏到她的胸前,說不出的繾綣纏綿。
有什麼東西硬硬地抵著初晨的背,讓她很不舒服。初晨不自在地推了推彥信的頭,低聲道:「床上不平整,有東西。」
彥信起身將她輕輕抱開,含笑拉著她的手往被窩裡探去:「妳看這是什麼?」
百子千孫大紅被裡縫著兩根硬硬的木條和一些乾果。
初晨垂著眼道:「我不知道。」
彥信拉著她的手細摸那兩根木條:「這是筷子,這些乾果是棗子、蓮子、桂子、花生。」
筷子,快子,初晨的臉不由得又紅又熱。
彥信見她害羞,溫柔地揉揉她的頭髮:「晨晨,妳這樣乖巧我很高興,以後只要妳聽我的話,我一定會讓妳過得很幸福。」
不等初晨回答,他便捧了初晨的臉溫柔地吻下去。
她的夫君不是因為娶了她而高興,而是因為她的乖巧和順從,初晨閉上眼,強忍住心裡那勃發的酸澀。
她知道她不應該心存幻想,但是她不由得的就是想哭,她也想要一個愛她疼她知她的夫君。
彥信開始脫她的衣服,動作沉穩有力,毫無任何羞澀之意或任何停頓。
是誰說怕到極致就不會害怕了,實際上她除了極度的害怕還是害怕,初晨緊閉著眼,微仰下巴,猶如獻祭的供品,微微顫抖著,任人宰割。
彥信突然停住動作,道:「妳何不卸下這鐲子?」
初晨睜開眼,看著蘇縝送她的那只玉鐲在紅燭的照耀下閃著盈澤溫潤的光,便小心翼翼地看著彥信的臉色道:「這是我從小最喜歡的鐲子,從來就沒有取下來過的。」
好在彥信並未在意,注意力很快轉移到她的腳上:「妳的腳真美。」
他拿起她的腳在燈下細細地看,表情沉迷而驚嘆。蘭若女子都是天足,初晨的腳天生就小巧玲瓏,雪白粉潤,細緻迷人。
彥信看了一回,突然俯身低頭,輕輕吻上初晨的腳。
初晨又酥又麻,又怕又急,她緊咬著唇,掐緊掌心,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讓自己縮腳或蹬他一腳。
從腳趾開始,彥信火熱溫濕的吻細細密密地落遍了初晨的全身,二人的衣服不知何時早已褪盡,長髮糾纏在一起。初晨僵著身子微微戰慄著,不敢去看彥信。
彥信遊動的手掌和靈活的舌尖熟稔地描畫著她身體的每一處曲線,奇異的酥麻感和電流在她全身遊走,全然陌生而讓人驚悸的感覺讓她喘不過氣來。
她想哭,又想喊,還想逃走,卻清晰地知道自己不能哭,不能喊,不能逃走,也逃不掉。
「不要怕,我的心肝。」彥信的聲音喑啞低沉,眼神迷離,表情顯然有些不耐,仍耐心地摟過她,與她面對面、額頭抵著額頭,低聲咕噥:「不要怕,我不會傷害妳的,妳真美。」
他在她的唇間溫柔碾磨,手指輕動,一手撫在胸前那柔軟的豐盈上輕巧揉捏著,一手已探至她最隱密之處,在那瓣核花蕊間來回的摩裟,當感覺到她的身體因為放鬆而柔軟,並慢慢變得濡濕溫暖時,他才滿足地嘆息了一聲,用力挺身。
「唔……」初晨的眼淚因為劇烈疼痛而不可抑制地流下來,她抽泣著弓起身子,試圖抓住點什麼緩解疼痛。她害怕地看著彥信,卻不敢開口求他。
彥信溫柔地輕吻著她的臉頰、脖子和肩頭,不停輕撫她的身體,聲音溫柔低沉:「不要怕,一會兒就好,妳乖,妳讓我很高興。」
話說得好聽,他的動作卻是毫無停滯,堅定而沉著。
不知為何,他越溫柔,初晨越是淚流不止,甚至抽泣出聲。彥信嘆了口氣:「很疼嗎?」
初晨淚眼朦朧地使勁點頭。
彥信停頓了片刻,又動作起來,低聲道:「女人都要疼這一回的,再忍忍就好了。放鬆,放鬆……」
初晨緊緊抓住他的肩頭,哽咽出聲,又漸漸平息下來。
很久之後,初晨背對著彥信躲在被子裡,任彥信怎麼喊也不肯露出臉來。
儘管她不願承認,但事實就是事實,剛才有那麼一瞬間,她產生了一種極度怪異的感覺,她似乎很迷戀彥信帶給她的這種奇異而動人心魄的感受,而且當時她滿腦子想的都是他好看的臉孔、健壯迷人的身體、溫柔的聲音和深邃的眼神。
她沒有做到她事前所想的那樣不為所動。儘管她一再提醒自己,這個人心裡只有權勢和利益,永遠也不會有她的一席之地,他只是她暫時的主人和安全的保證。可那一瞬間,她被他的溫柔體貼所打動,什麼都忘了,還生出不該有的幻想。
初晨責怪著自己做了不該做的事情,有了不該有的念頭。
彥信怎麼喊她也不應,只得伸手摟住她嘆氣道:「睡吧!不要胡思亂想了,明日我們還要進宮見駕呢!」
初晨小心地往裡面挪了挪,不露痕跡地離他遠一些,盡量不與他的身體有所接觸。
可她不過才往裡面挪了一下,彥信就跟著擠了過來,赤裸溫熱的身子緊緊貼著她的背,手不安份地在她身上遊走,那火熱堅硬的昂揚再次緊抵著她的臀部。
初晨不敢再動,只能僵著身子裝睡,良久才聽得彥信低低嘆了一聲,只把手放在她腰上,並沒有進一步行動的意思。大抵是不會再來了,初晨迷迷糊糊地睡去。
半夜時分,初晨被一種奇異的感覺驚醒,睜開眼,只見半明半暗中,一雙亮晶晶的眼睛緊盯著她,她嚇了一跳,隨即低聲抱怨:「做什麼?嚇死我了。」
彥信伸手緊緊抱住她笑道:「我今天真的很高興。」
他今夜總是反覆向她宣告他很高興,初晨心裡一陣亂跳,是因為娶了她嗎?難道他其實是喜歡她的?也許她的境遇比她想像的要好?那是不是意味著,她可以爭取更多的權益?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花影重重 2的圖書 |
 |
$ 213 ~ 225 | 花影重重02
作者:意千重 / 譯者:芊心 出版社:欣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08-18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20頁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花影重重(2)
意千重最具起伏情感的描寫,帶著些許落寞,些許惆悵,和些許期待……
你的溫柔令人貪戀、令人心神迷醉,我想我是中了你的毒……
彥信風流成性,王府中美人如雲。大婚第三天,初晨正式面對彥信的大小姬妾。只見二十多位的絕世佳人恭謹地向她請安,唯獨彥信的寵妾朱彩陽一身縞素地姍姍來遲,還態度倨傲,分明是蓄意挑釁。初晨為了立威,毫不猶豫地將朱彩陽關入柴房,待彥信發落。彥信卻完全沒為朱彩陽說情,眾人便明白新王妃在他心中地位無人能及,但初晨卻沒被打動。「怎樣妳才滿意?」彥信皺眉。初晨半開玩笑地道:「全攆出去了我才滿意。」初晨這一答卻也有幾分認真,她想試探彥信究竟能為她犧牲多少,有沒有可能是真心喜歡她……
作者簡介:
意千重
著名網絡小說家,每篇作品在起點中文網都達五百萬的點擊率,為起點中文網超人氣作家。其作品類型主要為古代言情、穿越、重生、宅鬥、現代言情、玄幻仙俠。篤信好人好報,卻被逼到盡頭;逼到盡頭,她終於頓悟,對待惡人,善心永遠多餘。幸福,需要拚搏捍衛!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洞房
彥信輕輕打了個呵欠,示意要就寢了。
在秦嬤嬤的指示下,春意和潤雨上來為初晨除去釵環,又服侍著她到屏風後換了件半透明的紅色繡牡丹紗衣,紗衣下雪白絲滑的肌膚和鴛鴦戲水的肚兜若隱若現,穿了比不穿還要誘人,初晨皺起眉頭,指著另一件厚實些的絲袍道:「穿那件。」
春意還未答話,秦嬤嬤不容置疑地道:「就穿這件,這件最合適。」
初晨惱怒地瞪起眼睛,卻發現秦嬤嬤不慍不火地望著她,寸步不讓。初晨淡淡地道:「有些冷,再給我披上件外袍吧!」這回秦嬤嬤倒沒有再說什麼。
初晨才走出屏風,彥...
彥信輕輕打了個呵欠,示意要就寢了。
在秦嬤嬤的指示下,春意和潤雨上來為初晨除去釵環,又服侍著她到屏風後換了件半透明的紅色繡牡丹紗衣,紗衣下雪白絲滑的肌膚和鴛鴦戲水的肚兜若隱若現,穿了比不穿還要誘人,初晨皺起眉頭,指著另一件厚實些的絲袍道:「穿那件。」
春意還未答話,秦嬤嬤不容置疑地道:「就穿這件,這件最合適。」
初晨惱怒地瞪起眼睛,卻發現秦嬤嬤不慍不火地望著她,寸步不讓。初晨淡淡地道:「有些冷,再給我披上件外袍吧!」這回秦嬤嬤倒沒有再說什麼。
初晨才走出屏風,彥...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