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三杯茶》的作者葛瑞格・摩頓森大力推薦!
「卡蜜拉‧賽迪基扣人心弦的故事,充分顯示,為一己之所愛,我們甘願付出一切。」
──Greg Mortenson‧author of Three Cups of Tea
熱心慈善事業好萊塢女星 安潔莉娜.裘莉誠懇推薦!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有許多默默無聲的英雌,她們對抗苦難,她們鍥而不捨,她們為人們創造了希望。《塔利班與女裁縫》就是在為這些偉大的女性發聲。本書保證令你為之動容,並展現了阿富汗難為外人所知的一面。」
──Angelina Jolie
「在塔利班的統治之下,一個女孩,堅忍不拔,蘭心蕙質,為了養活一家人,默默地開創了一番事業。Gayle Lemmon以一支巧筆,優美、典雅而深情地寫活了卡蜜拉。這本好書振聾發聵,提醒人們,除非擁抱婦女的創意、勇氣及靈活,並接納她們的積極參與領導,阿富汗才能在未來興旺發達。」
──蒂娜.布朗(Tina Brown)‧《戴安娜紀事》(The Diana Chronicles)作者
「《塔利班與女裁縫》讀來有如一部偉大的小說,但卻是真人真事;展讀本書,從第一句起就扣人心弦,並帶領讀者穿越多重領域的邊界,包括文化的、地理的、知性的,以及最重要的,情感的。一本必讀的好書。」
──穆罕默德.伊爾艾朗(Mohamed El-Erian)‧《大衝撞》(When Markets Collide)作者
「一則獻身鄉土建設的故事,其大智大勇讀來令人鼓舞。經歷多年的深度採訪……Gayle Lemmon心血所到之處,巨細靡遺,寫活了喀布爾在塔利班統治之下的氛圍。」
──《克科斯評論》(Kirkus Revie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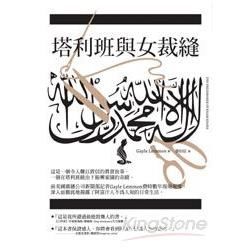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