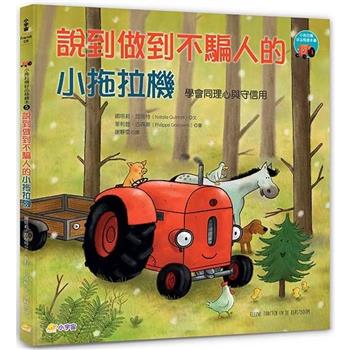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蔣勳談梵高:燃燒的靈魂的圖書 |
 |
$ 599 | 蔣勳談梵高:燃燒的靈魂
作者:蔣勳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04-01 語言:簡體書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蔣勳
蔣勳,生於西安、成長於臺北,著名畫家、詩人與作家。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蔣勳談梵高:燃燒的靈魂
本書從向日葵、自畫像、星空到麥田群鴉, 帶讀者破解曆久不衰的梵高傳奇。從年少到自殺身亡, 從割耳到抑鬱受創, 細說37年不斷掙扎的人生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