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版的《百年孤寂》!
●榮獲「柑橘獎」最佳新人提名!
●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
●亞馬遜網路書店當月最佳選書!美國獨立書商協會每月選書!
肚中有蠢動,房裡有鬼魂,家族有秘密,湖底有怪物。
萬事萬物,就像層層交疊的羊皮紙,刮得愈深,便揭露愈多層……
對葳莉.陽光.厄頓來說,生活不但沒有燦爛豔陽,相反地,根本是烏雲密佈!原本是考古系優等生的她懷了教授的私生子,被綽號「沒卵巢潑婦」的教授夫人當眾摑耳光,只好很不光彩地逃回家鄉坦柏頓。不巧那天瀲鏡湖上卻浮現出巨大的湖怪屍體,小鎮一夕之間聲名大噪。葳莉在湖怪被吊到岸上後摸了牠一下,只感受到無止盡的悲傷……
壞事來時總沒完沒了,葳莉發現曾是嬉皮的母親如今成了虔誠的教徒,還和「牛奶牧師」談戀愛;接著又驚聞姊妹淘罹患紅斑性狼瘡!難道世界真的要分崩離析了?就在她覺得整個人快要瀕臨毀滅之際,母親卻冷不防地揭露隱藏了一輩子、關於她身世的真相,也讓葳莉決定振作起來,重新挖掘出那些幾乎早已隨風而逝的駭人秘密……
本書是美國新銳作家蘿倫.葛洛芙的出道處女作,以富含詩意的優雅文筆,融合了歷史、謀殺、鬼怪和家族醜聞,讓人既感嘆於命運的深邃幽暗,又不禁被恆常不變的愛所感動,也難怪連閱書無數的故事大師史蒂芬.金都大為驚豔!
作者簡介
蘿倫.葛洛芙Lauren Groff
美國紐約庫柏鎮人,她的故鄉正是小說場景坦柏頓的原型。出道作《坦柏頓暗影》不但登上紐約時報、北卡獨立書商協會等全美暢銷排行榜,並入選亞馬遜網路書店當月最佳選書和美國獨立書商協會每月選書,更讓她贏得「柑橘獎」最佳新人的提名。她的短篇小說作品散見於《大西洋月刊》、《犁頭》等文學刊物,亦曾被收入《美國最佳短篇小說》選集、「手推車獎」選集。她目前定居在佛羅里達州的蓋恩斯維爾。
譯者簡介
謝佳真
自由譯者,譯有《峰與谷》、《測謊機男孩》、《大象的眼淚》、《女祭司》、《紐約公寓》、《錯得多美麗》、《潘朵拉處方》等。賜教信箱:oggjbmc@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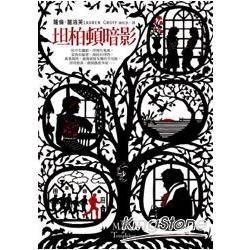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