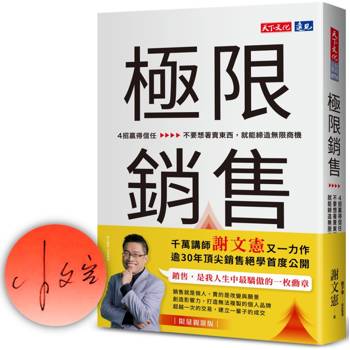在二○○九年國際法蘭克福書展上對《血紀》的介紹
孔令平的《血紀》三部曲,全書共一百多萬字;是史詩式的展現了作者一家在極權中國的困難圖卷;是作者被打成右派之後九死一生的親身經歷、所聞所見,極具震撼性,是中國的《古拉格群島》。
此書未曾面世已轟動,二○○九年參與此書編輯的荊楚先生,被廣西新聞出版局局長秦某、桂林新聞出版局局長陳某等中共宣傳部門官員約談,警告如敢出版,將報復其妻子和孩子。而且聲稱此書的出版,將影響中國的穩定,有關人等將治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孔令平父母都是一介書生,對抗日救亡和建設新教育有過貢獻。孔祥嘉,在一九五一年鎮反中,被抓進監獄並蠻橫的拒絕通知家屬,也拒絕向家屬提供判決書。直到一九八二年,四川省公安廳才在發了一紙共三十二個字的《來信來訪通知》中說他一九五六年死在獄中。
一九五七年孔令平和母親方堅志先後以替父親翻案而打成右派分子,年幼無知弟弟於一九六七年被不明不白殺害。母親因忍受不了非人虐待而投塘自殺(未果),孔令平也幾乎被處死。
《血紀》再現了毛澤東一手製造的大躍進、全民煉鋼、人民公社、高產衛星、社教運動、一打三反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所發生的場景,以及人們被活活餓死、被鬥爭、被打死的心驚場面。《血紀》描述被監督勞動的飢寒交迫和所受非人虐待:遭打罵、戴內圈有倒刺的小銬、吊打繩捆,關禁閉、陪殺場等,還要在飢餓中服苦役。記錄了他們被打死、捆死、踢死、自殺死,以及為活命逃亡被擊斃,餓死在途中的真人真事……
《血紀》也記載難友們在暴力的侮辱、摧殘下,奮起反抗的故事: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皮天明等烈士們將作為中華民族的靈魂,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國家不幸作家幸,一生在苦難的血淚中浸泡的孔令平,終於在把嘔心瀝血的《血紀》貢獻出來了。這不朽《血紀》三部曲也將使它的作者成為不朽的人物;孔令平又是幸運的作家。
武宜三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