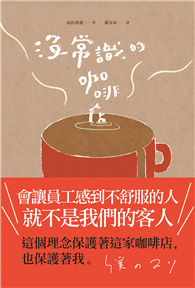一九六六年五月,我們在成都參觀前後,中共內部的「宮廷」較量,以「社會主義教育」的形式拉開了序幕。毛準備多時,利用青年學生的盲目輕信,將全國人民對中共的不滿正在轉嫁給「資產階級司令部」!
不識其陰計的彭真們果然上當,拋出了《二月提綱》,並且揪起了二月鎮反運動!當然全國的紅衛兵運動,一些往這個運動中鑽的毛孩子們,輕易上當,充當毛澤東發動的宮廷政變槍手,就在預料中了。
「文化大革命」就這樣開始。在邊遠的鹽源小城同全國一樣,鹽源農場組織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組,派往各所屬的勞改中隊。
這些工作組顯然並沒有弄清楚「二月提綱」骨子裡要賣什麼藥,只憑他們的本能,跟著黨中央的決定走。按照他們對中共運動的理解,照例是抓一批反革命向中央交差。
六隊是農牧場重點關押反革命份子的中隊,派赴的「社教工作組」陣營特別龐大,由五名科級幹部組成!
六月初正是農場栽種的農忙季節,為了「保證」學習,場部規定下午五點鐘便按時收工。收工回來後,組織我們學習一系列中共中央的「文革」檔案:《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
全隊集中收聽了播出的(中共中央委員會)通知後,便以「你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為題,組織了全隊人員的分組討論。
然而這些年,備受折磨害怕中共那套「放長線釣大魚」欺騙的農六隊流放者,大家都以沈默來回答。第一天的分組討論,會場上冷了場。
已經失去了民心,甚至失掉了中共黨心的毛澤東。由於獨裁本性使他不可能吸取教訓退位禪讓。相反的,從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開始,到一九六四年,經過了將近五年的準備,一個反對黨內反對派的陰謀終於拋了出來。
《五一六》通知已經攤牌,李培連十天以前的那番講話還響在我的耳際。雖然我的心裡堵得慌,幾次想痛斥文化大革命的險惡動機,可是又覺得應當再觀察一下,到口邊的話被我吞了回去。
第一節:宮廷政變.我對文革的看法
第二天場部派出的工作組,再次作了動員,講到了這次「文革」的「偉大」意義,重申這次運動與以往任何學習都不同!宣佈了會場三大承諾:
暢所欲言,各各抒己見;對於在開會時公開發表的意見不抓辮子,不作記錄;保證不作秋後算帳。農場的社教工作組組長,政工處蒯處長,見全場依然同前一天一樣冷清,便指名點姓要我和陳力分別在兩個組進行「發言」,並向我們提出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的保證。
這幾年承蒙共產黨的「教育」,讓我明白,毛澤東發動的每一個運動都預先把「革命」對象作了界定,不管你對運動持何種「態度」,只要被劃為挨「整」範疇,是一定逃不掉的。
(一)激辯
我清楚的看到,本次運動挨打的對象是中共內一批對三面紅旗不滿的人,其中不乏「海瑞」式的「直臣」,他們並沒有成熟的政治主張,但畢竟在當時較能體察民情,深知毛那套理論帶給大陸的災難,儘管這些人壓迫過我們,與我們本無共同點!但為推翻獨裁勢力,仍有必要同他們聯合。何況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想到這裡,我從凳子上站起來,向蒯處長提出要求「我的發言不作記錄,不負法律責任。」
在得到他的點頭應許後,我開始了我的長篇發言:
「首先,《五一六》通知中一個提法值得在場的人認真思考。」我的開場白吸引了在場兩百號人的注意力,全場鴉雀無聲。
「我們知道,我們國家的名字叫人民共和國,毛主席不是說,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比以往資產階級共和國更進步更民主的國家嗎?這叫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共和國。」
「中共領導人不是說,共產黨的領袖人物都是在革命運動中產生的嗎?何嘗有培養接班人一說?那是只有在封建時代皇帝廢立太子時,才可以說,自己在培養繼位人。而在培養繼位人中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才是封建宮廷之爭。現在這樣說等於承認所謂人民民主專政不過是皇上的專政,許諾給人民的民主權力全是假話!」
「掛共產主義的羊頭,賣一貧如洗的狗肉的北京領導人,面對年年歉收,到處餓死人的局面,卻偏要說形勢從來沒有這樣好,逼著老百姓贊三面紅旗好,這不是指鹿為馬麼?」
坐在我對面的周學祝舉起了手,可惜,蒯處長沒有理會他。
於是我接著將歷史追溯到九年以前,從五七年毛澤東打壓知識份子,封人之口的反右運動,講到「三面紅旗」; 從人民公社和社教運動,講瞎指揮下的一場浩劫;從放衛星到大寨運動,講違背社會正常的運行規律帶來全國大幅歉收;從大煉鋼鐵講強徵民間勞力,煉得一堆廢鐵,勞命傷財。結果造成大飢荒,餓殍遍野,國家元氣大傷。
「老百姓最初懷著模糊不清的希望,以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會給他們帶來共產主義的繁榮,半信半疑地跟著他的部署走!煉鋼煉鐵,成立人民公社,辦公共食堂。」
「結果疲憊不堪的農民從原先的窮困走到了飢餓和死亡!於是大家才明白毛澤東不是神人,他只不過像『燕山夜話』裡,用一個雞蛋的家當落地破碎的泡影,哄了大陸老百姓。」
「歷史終於走到了今天,走到了連他當年的親密戰友都無法相信的絕境中,走到了共產黨領導核心都無法維持統一的一九六六年。因此,任何有現實感的人都應當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毛澤東排斥黨內持不同意見者發起的宮廷政變!」
我斬釘截鐵的為我長達半個多小時的發言作了結論。
也許,「宮廷政變」這麼一說在當時確實語出驚人,令主持會場者出乎意外,大家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好像提出了一個他們沒有想到,也不敢想的問題,讓他們開了竅。使他們「發聾振聵」了。
突然,坐在我對面的周學祝霍地站起身來,向蒯主任遞了一個諂媚的眼色說:「我認為孔令平藉學習會在公開宣揚三家村言論,應該給予批判,還要讓他自己消毒!」
周學祝這人因背是駝的,我們叫他周駝背。李培連因為此人也是右派,具有大專文化程度,平常很擅打「小報告」,所以指定他任我們這個特殊學習班的組長。看來,經過兩個月的辯論學習,對他這種找機會都想從狗洞中爬出高牆的人,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現在他也許看到,他面前又是一個很好的「立功贖罪」的機會,豈能放過?
被人猛然提醒,蒯主任顯得侷促,一面應和道:「對,大家要對孔令平這種藉學習討論,進行放毒的言行加以批判。」
但是,我卻不動聲色的坐在那裡,提醒蒯主任在我發言前所許諾的條件。周駝背見我坐著不動,便走過來拽我站起來,一邊說:「毛主席說的凡是毒草就要批判,你今天明明用報紙上正在批判的話在這裡放毒,哪有不消毒的。」
我並不示弱,順著他來拉我手的力量輕輕一送,便將他送出了兩公尺外,跌倒在地上。
被這出奇不意的一推所惱怒。周駝背一邊從地上爬起來,一邊拼命的狂喊:「反改造打人啦!反改造打人啦!」並再次向我撲過來。頓時我們倆扭成一團,會場中立即哄鬧起來,蒯主任連忙叫人將我們拉開。
正在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鄧揚光從圍牆的拐角處冒了出來,自從李培連接手農六隊的管教工作後,他便從六隊消逝了幾個月。今天突然露面,想必與工作組的派駐有關,說不定他便是工作組的總指揮。
他走到我面前,我才發現他的手上提著一付手銬,身後還跟著兩名武裝士兵。沒問任何話,我便被那兩個士兵按倒在地,反剪著雙臂,戴上了一付沒有任何活動空間的土手銬。看來,他早已準備好了。
陳力和劉順森們一齊發出怒吼聲:「還講理嗎?動不動打人!」
鄧揚光將身子轉向陳力,冷冷的說道:「你少囂張一點,我們對你們這樣頑固不化的份子,有的是辦法。」
今天的鄧揚光把他在古柏的那兇惡的面孔重顯出來。在他的指揮下,我和陳力被兩名士兵連推帶搡地關進了東北那一排,靠崗樓下最角落裡的兩間房間,那裡當時是用來堆放糧種的臨時倉庫。
我和陳力罵不絕口,直到被重重地摜在那屋裡,鎖上大門以後,工作組驅散了圍觀的流放者。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血紀:從文革到平反的圖書 |
 |
$ 528 ~ 540 | 血紀: 從文革到平反
作者:孔令平 出版社:新銳文創(秀威代理) 出版日期:2012-12-1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90頁 / 16*23 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血紀:從文革到平反
本書取材於作者的親身經歷,反映出中共統治中國半個世紀的歷史一角,既是個人一生不幸的記錄,也是那個時期的歷史悲劇。
中國是世界的一部份,中國人是人類的一部份,組成這個時代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也許都在想,自己這一生為什麼而生存;為什麼而奮鬥?任何人在回憶自己一生時,是想為自己樹碑呢,還是想真實總結過去,拿出一點對人類有益的教訓以告誡後代?
作者簡介:
孔令平。
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生於南京古樓醫院,十八歲考入重慶大學機械製造系,二十歲時因父親“殊連罪”被劃為右派送勞改,二十三歲時被南桐法院判處十八年徒刑勞改。
一九七九年平反回重慶,一九八○年在重慶二十四中任教,一九八四年由重慶大學出面第二次落實政策到重慶專用汽車廠工作至退休。
章節試閱
一九六六年五月,我們在成都參觀前後,中共內部的「宮廷」較量,以「社會主義教育」的形式拉開了序幕。毛準備多時,利用青年學生的盲目輕信,將全國人民對中共的不滿正在轉嫁給「資產階級司令部」!
不識其陰計的彭真們果然上當,拋出了《二月提綱》,並且揪起了二月鎮反運動!當然全國的紅衛兵運動,一些往這個運動中鑽的毛孩子們,輕易上當,充當毛澤東發動的宮廷政變槍手,就在預料中了。
「文化大革命」就這樣開始。在邊遠的鹽源小城同全國一樣,鹽源農場組織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組,派往各所屬的勞改中隊。
這些工作組顯然並沒有弄清楚...
不識其陰計的彭真們果然上當,拋出了《二月提綱》,並且揪起了二月鎮反運動!當然全國的紅衛兵運動,一些往這個運動中鑽的毛孩子們,輕易上當,充當毛澤東發動的宮廷政變槍手,就在預料中了。
「文化大革命」就這樣開始。在邊遠的鹽源小城同全國一樣,鹽源農場組織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組,派往各所屬的勞改中隊。
這些工作組顯然並沒有弄清楚...
»看全部
作者序
在二○○九年國際法蘭克福書展上對《血紀》的介紹
武宜三
孔令平的《血紀》三部曲,全書共一百多萬字;是史詩式的展現了作者一家在極權中國的困難圖卷;是作者被打成右派之後九死一生的親身經歷、所聞所見,極具震撼性,是中國的《古拉格群島》。
此書未曾面世已轟動,二○○九年參與此書編輯的荊楚先生,被廣西新聞出版局局長秦某、桂林新聞出版局局長陳某等中共宣傳部門官員約談,警告如敢出版,將報復其妻子和孩子。而且聲稱此書的出版,將影響中國的穩定,有關人等將治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孔令平父母都是一介書生,對抗日救亡...
武宜三
孔令平的《血紀》三部曲,全書共一百多萬字;是史詩式的展現了作者一家在極權中國的困難圖卷;是作者被打成右派之後九死一生的親身經歷、所聞所見,極具震撼性,是中國的《古拉格群島》。
此書未曾面世已轟動,二○○九年參與此書編輯的荊楚先生,被廣西新聞出版局局長秦某、桂林新聞出版局局長陳某等中共宣傳部門官員約談,警告如敢出版,將報復其妻子和孩子。而且聲稱此書的出版,將影響中國的穩定,有關人等將治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孔令平父母都是一介書生,對抗日救亡...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文化大革命
第一節:宮廷政變•我對文革的初論
(一) 激辯
(二) 夜深沈
(三) 最後一點「理性」
第二節:加刑——第二次判
第三節:文化的浩劫——人權的厄運
(一)鑽死角的災難
(二)「算總帳」
(三)第三次絕食
(四)鬥爭潘朝元
(五)王氏膏藥
第四節:牢卒子們的內鬥
(一)林扯高鬧劇登臺
(二)「好人」打「好人」
(三)高歡和童管教
(四)紅衛兵墳
第五節:軍事管制——打人狂潮
(一)「請罪」及打人風
(二)我被打昏的體驗
(三)大搜查
(四)為一張畫像被打得半死
(五)打中了
(六)賠殺
(七)「狗」也挨...
第一節:宮廷政變•我對文革的初論
(一) 激辯
(二) 夜深沈
(三) 最後一點「理性」
第二節:加刑——第二次判
第三節:文化的浩劫——人權的厄運
(一)鑽死角的災難
(二)「算總帳」
(三)第三次絕食
(四)鬥爭潘朝元
(五)王氏膏藥
第四節:牢卒子們的內鬥
(一)林扯高鬧劇登臺
(二)「好人」打「好人」
(三)高歡和童管教
(四)紅衛兵墳
第五節:軍事管制——打人狂潮
(一)「請罪」及打人風
(二)我被打昏的體驗
(三)大搜查
(四)為一張畫像被打得半死
(五)打中了
(六)賠殺
(七)「狗」也挨...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孔令平
- 出版社: 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12-12-16 ISBN/ISSN:978986591522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90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