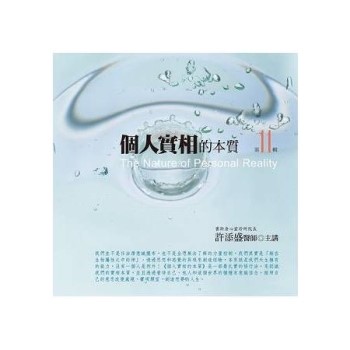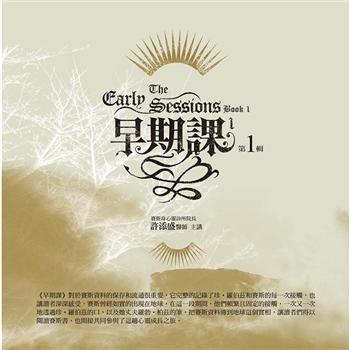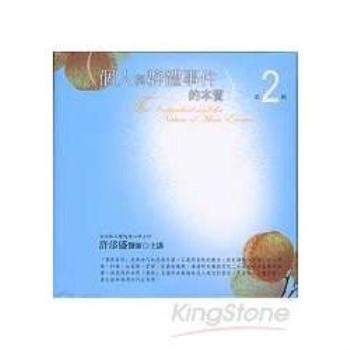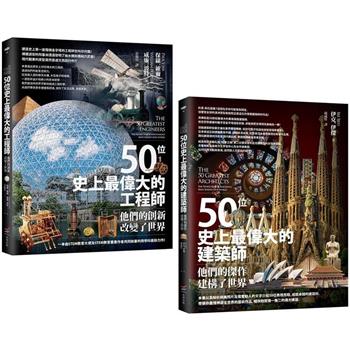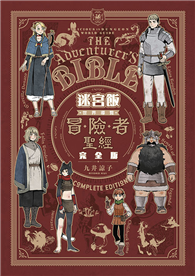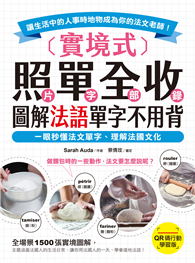序
搶救真相義不容辭、刻不容緩
從上世紀末開始的採訪算起,這個文本的成稿過程時斷時續,前後經歷數十年,居然「跨世紀」。起先,這個家庭的榮辱盛衰,是作為這個時代劇變中,個體命運的個案,進入我的視線的。在往後的歲月中,我從陳將軍當年的戰友溫啟明先生、王應錚夫婦諸前輩及其女兒陳維莉女士那裡,瞭解到許多有別於流行敘說的「獨家新聞」:據台灣原中統局的檔案資料記載,刺丁案的指揮人是中統陳彬將軍(又名陳彬昌)。一九三九年九月,原中統上海區的兩個副區長蘇成德、胡均鶴叛變投敵,區長徐兆麟僥倖逃脫,中統僅在上海就有四十餘人被捕,上海江蘇一帶組織幾乎被一網打盡。在組織解體的嚴重關頭,原中統香港組的少將組長陳彬臨危受命,「一九三九年冬,陳彬奉命調回上海,任中將級站長」。陳彬到上海後,即與已深入虎穴的鄭蘋如等會合,組成鋤奸小組,實施暗殺行動,可惜功虧一簣。李士群暴斃後,中統安插在李身邊的隱蔽戰士陳彬,隨即又接受新的潛伏任務,南下廣州,再次潛伏於敵營,任廣東省海防副司令。一九四五年春,陳彬成功策反廣東海防司令及其部下,刺殺了日寇華南派遣軍特務機關長柴山醇後,不幸壯烈犧牲;抗戰勝利後,殺害陳彬的「兇手依法被判處死刑,國民政府頒發陳氏(按,即陳彬)遺屬撫恤金十年,子女就學讀書免費,併入祀抗日烈士紀念
堂,以慰忠魂。」
陳彬將軍「刺丁」失手後,又奉命潛伏蘇州,而正巧我的童年是在抗戰後期的蘇州度過的。童年時的我,愛聽大人們茶餘飯後的閒談,於是淪陷區的群魔狂舞、亂世中的種種怪象、各路英雄梟雄奸雄的名字,統統進入了我的記憶中。汪偽特工大頭目、偽江蘇省主席李士群被毒死的新聞,曾是蘇州人的熱門議題。在熱議李案的那些日子裡,家裡的大人們每天都會在茶餘飯後交流著從坊間聽來的最新信息。記得有一天,二舅剛進門還沒坐下就說:「呵,醫生化驗結果,李士群嘴唇上找到幾十種毒菌,哪有不死之理……」。二舅眉飛色舞的神態至今記憶猶新。那時我就聽說過陳彬的名字,這位奉命潛入敵營的臥底將軍,深得李士群的重用,其時側目而視者有之,相爭攀附者也有之。有一位顧醫生一度經常出入我家,後來難覓蹤跡,聽二舅媽說,這是因為顧太太在牌桌上結識了李士群的親信陳彬的夫人,並與陳太太結拜為姐妹,所以不屑再與我們平常人家來往。而後,在李士群暴死後,陳彬就突然人間蒸發,只留下陳太太還在蘇州,但已門庭冷落,太太圈的麻將桌上也難覓其蹤跡……常言道,童年的記憶像刻在石板上的花紋,但怎麼也不會想到,幾十年後的巧遇,會再喚醒上述那些沉睡的童憶。
這世界真小,一九五○年我在上海江灣中學住宿,週末到家母的宿舍度假。家母施瑋,又名施雅媛(一九二二~二○○二),浙江南潯人,南潯中學高材生,略有文采,深得當年任教於潯中的詩人徐遲青睞。徐遲的髮妻陳松女士是家母同班同學、閨中密友。抗戰勝利後,徐遲隨南潯中學校長林黎元先生到蘇州向校友募捐,曾在我家租賃的皇宮後二號暫住,林、徐下榻在二樓面對果園的主臥室裡。後來在一份南潯中學復校捐款人的名單上,我看到了家母的名字。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我在南潯中學附屬小學住讀,徐遲先生的大女兒徐律是我童年的玩伴。南潯解放後,徐遲因姐夫伍修權的關係全家遷京,我們就失去了聯繫。抗戰時期,古鎮南潯慘遭日寇蹂躪,外公帶全家六口到鄉下避難,於是家母遭遇了那場決定她一生命運的婚姻。外婆說,我出生在蘇州小豬弄。一九四五年,任職於忠義救國軍的家父曾祥禧因在汪偽軍中策反事敗,被昔日的拜兄弟沈某某殺害。而我隨外婆住在二舅家,家母則到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求學。輟學後到蘇州私立立達小學任教,一九四八年到上海霍山路國民小學任職。解放前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與何祥芳(其女後來任上海市政協主席)等編在同一小組,何的丈夫陳雲濤解放後任上海師範學院(今上海師範大學)院長,家母在世時,每年總會去新康花園何家與他們相敘。家母以樸素而真誠的激情迎接解放,五十年代初,被任命為上海提籃橋區(現已併入虹口區)惠民路小學校長,借宿在學校的辦公樓裡。
一天大舅來訪,聽見家母神秘地對他說,李士群時期在蘇州炙手可熱的陳彬的太太,現在這裡做教員,要不是公安局來指認,根本認不出鉛華洗盡後的陳太太,與當年的華麗富貴判若兩人……一晃又是八年過去了,一九五八年我曾向家母打聽陳彬女兒的消息,家母這才向我透露了一個本不該透露的秘密:一九四九年後,陳彬夫人溫斐的親友幾乎全部離開大陸,惟夫人溫女士一人帶著女兒留在上海,公安認為疑點頗多,疑似特嫌。
公安在溫家周圍佈置了居委會積極分子監控,同時也經常到溫女士任職的小學瞭解情況。而作為該小學校長、共產黨員的家母,就無法避免地成為公安隨訪的首選對象。家母為人正直,把溫女士在教育第一線敬業盡責的實際情況如實彙報。而公安提醒,要看透假象後面的本質,等等。由於家母不願昧心編造並不存在「特嫌」證據,因此無法滿足公安的要求。不久,家母調至外區任職,一九五八年溫女士被送安徽勞動教養,隨即,病逝農場。從陳彬遺屬的家變中,折射出時代大變遷中個人的渺小和小人物在命運面前的無力、無助、無奈。正如家母所說,在五○年代初遇溫女士時,面對眼前這樣一個平凡無奇的小學教員,很難相信四○年代與她同城而居時,在蘇州城裡所流傳的有關她如何耀眼奪目的各種故事。真是「昔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上世紀八○年代以後,原先在保密的理由下被掩飾的資訊,也逐漸浮出水面。據一份權威資料透露,當年曾與陳彬共事的胡鈞鶴,經潘漢年推薦、饒漱石批准,五○年代初出任上海市公安局情報委員會主任,兼情報專員。這位四朝(國共日汪)特工,把他在國民黨中統局、日汪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等機構任職時的資訊積累,作為立功贖罪的資本。據說,提供了上千條有價值的線索,協助抓獲了四百多名潛伏特務,破獲了上百部國民黨的地下電台,成千上萬人因此被審查、監禁。也許出自秘密使命的工作需要,也許另有其他私人的原因,總之,當年陳彬奉命潛伏在李士群身邊時,陳彬家和胡鈞鶴家兩家過從甚密。胡鈞鶴太太趙女士是東北抗日英雄趙尚志的妹妹,還有後大椿(汪偽糧食局長,因向蘇北輸送糧食物資而被汪槍決)的夫人等四人結為四姐妹……雖然沒有證據顯示胡鈞鶴的上千條線索中包括有關陳彬、後大椿及其遺屬的資訊,但據陳彬女兒陳維莉女士回憶,她當年為其母謄抄所謂交代材料時,時常出現一些日偽高層人物的名字,所以當二十一世紀熱播、熱演的諜戰文本中再現上述名字時,就喚醒了她沉睡數十年的記憶。然而人在做,天在看,許多事情不以當事者的主觀願望為轉移,胡鈞鶴雖提供了數量驚人的舉報材料,卻於一九五四年入獄,三十年後始獲平反,享受離休幹部待遇,也算善終。最可憐的莫過溫斐女士,一九五八年被不明不白的莫須有的理由:「曾幫助中統特務陳某管理賬目等問題……」,(摘自一九八○年六月三日中共上海市虹口區唐山學區小教總支給陳維莉的信)被開除公職,病死安徽農場。
這些年來,面對已經搜集的資料,多少次翻出來後,又無奈地重新放回去。直到先烈陳彬女兒陳維莉女士大病初癒,在其子女的強烈推動下才促成文本的定稿。即使如此,直到交印前的最後一刻,由於各種原因,不得不抽下有關先烈遺屬遭遇的部分資訊,擬以後專論補敘。因為現在的文本不是個人空間裡的親屬家史,而是公共空間裡的大時代、大事件、大格局的歷史敘事,任何人物和事件的格局,只能作為宏大敘事的構成要件而存在。在這裡,個人和家庭的變遷,不過是歷史激流中一個稍縱即逝的水泡而已。
當然,對受損的具體個體來說,每一次的付出卻是絕對的,所以也是痛苦的。然而,整個歷史長河不就是那無數水泡破碎後的總匯嗎?困難的抉擇在於:宏大敘事就必須忽略鮮活生動的個體的感受?能不能把「私小說」式的抒情從狹小的私密空間中解脫出來,融入大事件的紀實性的公共場域之中?其實,這裡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零和選擇,難道在這大事件的宏大敘事中,私人空間裡的各種元素就不能成為構成的部件而存在嗎?若要完整地敘述真實的歷史背景中的真實的歷史細節,社會時代的大格局本來就是無數個人、家庭小格局的總和,而個體的命運惟有融入時代大格局之中,才會發現其真正屬於私我的價值。
如果沒有溫啟民、王應錚等前輩們對歷史真相的直言不諱、仗義執言,就不可能有現在的這個文本。可惜由於種種延誤,兩位前輩已無法目睹文本的問世。當年,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的老人公寓裡,溫先生的回憶、在台北和上海對王先生的多次採訪過程中,我都意識到,自己正在做的不是一般意義的拾遺補缺、輯佚鉤沉,而是打撈真相、搶救歷史,因為這個案件的每一個構成要件,無不與大時代的脈動息息相關。
成稿過程中,得到眾多前輩、同輩、後輩的支持,謹在此向一切關懷過本書稿的朋友們,致以最真誠的謝意,恕不一一具名。同時文本藉鑒引述了各種已有的成果,特此致謝。最後,為使今天的讀者能瞭解當年諜戰的原生態實景,所以又把相關的人物生平、機構變遷,事件背景等史料收為附錄。由於這部分資訊本屬大眾共享的公共資源,故不再分別注明,謹在此對所有資訊來源一併致謝。
最後,特向南開大學姚錫佩學姐、台灣的蔡登山先生及秀威資訊所有關心過拙著的朋友致以真摯的謝意!
因為正是學姐的關懷和出版家們的敬業,才使失落了七十多年的真相再次重見天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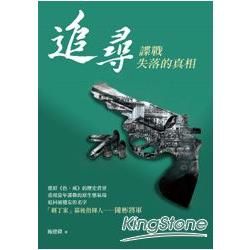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