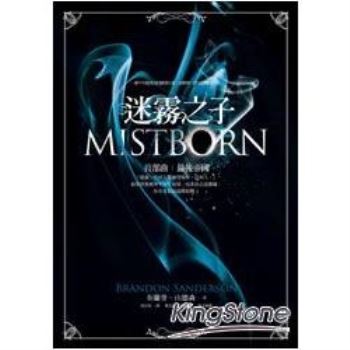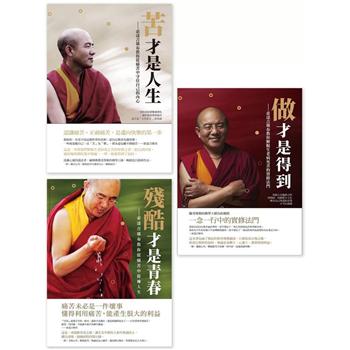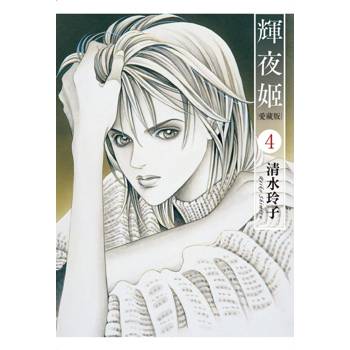縱使僅僅想望─讀《遷徙家屋》
我只是想著航行
如果有島
〈壁紙之五、拼圖時代〉
先提一則小故事,這是作者親口所述,消息來源正確可靠而不八卦。他的母親曾經殷切地請人為孩子算命,得到的斷語是──「離家愈遠,成就愈好」。當時我忍俊不住笑了出來,在這個與家鄉宜蘭一線之隔的花蓮暫時安頓,跟台灣地圖對角的高屏相比,似乎不是個能讓他功成名就的好選擇。然而,更讓我深深忖度的是,不曉得他的母親懷著怎樣的心情對他解釋這一切?用什麼表情如何目送他離開家,註定的──而且越遠越好,讓他在這個世界浪遊冒險。另一方面,必須遠離母土的孩子,他被催促著踏上旅程,要去哪裡?哪裡適合逗留?當他閉眼回望故鄉,是嘆息?是憂鬱?
往後我從他的詩中所能讀到的,似乎都與這則小故事相關,那是來自他者言說的力量,來自相命師、他的母親、語音和文字的綑綁,就像一錘定音的宿命預言孕育他的靈魂。自此,在生命的造句裡,停泊化約為頓號,除非銜接下一個辭彙,否則這行詩將永遠匱乏。我們無法就詩句裡歸結他流浪的原因(事實上,追究也只會落入神秘論的擺布),不只是廣義的人生如旅,當他將自己的護照蓋上王離兩個字,當出走成為一種符號性的執拗,靜止與移動之間已難辨清距離。
也因為如此,王離的宅居成為了最大的諷刺與驚喜(你總能在即時通訊網路清單裡看見他的蹤影,手機可以噗浪),我一點都無法將他歸類為旅者,當然,這是就現實意義、背包客意義而言的,如果他是,我寧可一廂情願地揣測這些詩行會蘊涵更多離散的性質,無依的氣味,甚或孤獨的決斷,然而作品中實際流露出來的安全感和飽滿卻美好的像充滿期盼的心,你開始知道,旅途只是隱喻:
在唱片架抽走一張清單
寫著搖滾和詩
抽走上揚的語音
就到了巴黎
在睡眠的河裡抽走一段
沾附脂肪的和弦
〈那似乎抽走了什麼〉
如果肉體被脂肪束縛,感官的移形就是減肥刀,縱使僅僅想望,想望仍可稱為一種疏離的手段,至少疏離有個對象,提供僭越的可能,但王離始終刻意保持間距,足以問候的方式袖手旁觀,不致成為被威尼斯的斯洛可風感染瘟疫的奧森巴哈。或許生作一個網路時代的詩人,要像韓波、波特萊爾那樣流離,除非命格出奇無以致之,於是,異鄉在王離的筆下,只能寄託於詞彙的能動:
一染畫
一乾雨
一濕樹葉
一紋水
一靨睡眠
〈壁紙之二、五十種異鄉〉
詩人從無法不孤單的生存狀態分身,操作直覺式的瞬間移動,渴慕即是碰觸,描摹即是抵達,從神話到左岸,驛站到廣場,足不出戶(面對電腦總是無奈的)反而幫助──也可稱之為逼迫,他的心靈滋長、構建一幅巨大而有機的地圖,詩人如同采風信使,放任想像考察古今的情境──透過詩──翻譯成迴旋的音節:〈壁紙之一、植物的睡眠〉、反覆的禱詞:〈女伶〉,退一進二的舞步:〈夢遊者〉。
她奔跑,他騎在馬上
她是無韁的戰車
他射了三箭因此
她落入河中,身體
流出金黃的樹汁
沒成黑夜」
〈吉普賽一〉
海洋、港口、航道、吉普賽……王離的詩往往戛然而止,終於不像終點的段落,好比被槍擊過的歌曲,被敲門聲打斷的夢境,裂痕音律偶爾使得誦讀成了苦差事,但無損其意義的生長與收納,我想,整冊《遷徙家屋》就是一雙遺憾與缺陷的紅舞鞋,坐臥難安的強迫症演示。當他驅策自己前進,同時也入魔般地推測下一個、下下一個停頓點,揣摩當地的氣味草香、壁紙的顏色線條、行人的面孔姿態,如此反覆,再重來。不只異國情調的挪移,在作者行旅的過程中,放逐與落腳的慾望雙生並蒂,回應了家屋這個小角落,一個可供靈魂投身的宇宙。
旅行的帳棚恆在
他們重複他的旅程
流沙攪亂歷史
從深處□娠新的歲月
再成為旅人
掩埋底層的殘骸提供了
深邃沃黑的養分
〈旅者〉
也許可以這麼說,面對未曾託運上輸送帶的行李,他的意念佯裝小叮噹的任意門,並賦予它時光機的功能,藉著我們熟知的意象,將白居易、月桂、山櫸、人魚,描述為一種「疑似」的現代,企圖創造嶄新的寓言故事,回到傳述的起點,書寫仍未被詮釋困住的自由狀態,讓教訓、價值判斷、批評、感想全都隱身,保留純粹的敘事:很久很久以前,曾經……
我不怎麼在乎故事的真實與否,但那流浪漢繪聲繪影,越說越是激動,幾乎都要湊到我身上來了,我急忙把他推開,有點狼狽地想保持距離,但他灼熱的眼神堅定地看著我,像是我的態度足以肯定或否定他的人生。
〈漫行者之二、香水女郎〉
世界充滿了框架,特別對於詩人而言,連身分都曖昧不明的情況下,失落感如同窗簾,為自己的房間遮蔽出巨大的陰影焦慮,勉強透進來的殘光彷彿可供指認真實,然而線索竟少得可憐(我該如何彰顯鹿之所以是鹿的本質?我的做法是否將鹿變成馬呢?)就像每個願意獻身文字的人那樣,想替自己定位,又不甘受限,註定?如果是註定就好了。在收編與解放的戰爭裡,詞彙仍然是唯一且永恆的武器,詩人所能作的,就是持續掏洗詞彙,鬆開它為語言造就的自身,讓休止符產生音頻,然後超越它。
昨天他與明年的那人見面了
記憶是無謂的
存在也是
世界開始時
所有人都是死者
〈輪迴〉
那年當我們欣喜與苦楚並存地為了各自的作品長途跋涉,不時藉著網路確認彼此存在,緩解苦悶的孤獨,度過不寐的夜相約早餐,我從蟄居的學校宿舍,他從賃租鄰近小村的套房,雙眼血絲地來到同一張餐桌,四面曠野,陽光正烈,進行中的一切都是那麼幽微而彰然若揭,沒有人願意掃興的提起有關進度的問題,因為說實在,我們都應該好好睡,睡一場無夢的大眠。沒意料到,原來他的精神已經跑得那麼遠,只消一種溫度、一片畫面、一點聲音,就讓他易地而處,想必記憶、想像與現實無窮無盡的傾軋,肯定使他疲倦,最後才得以輕輕地,悄悄地告訴自己,其實我的本身,就包含了所有尚未成行的旅行計畫:
總是說看見之後
便身在其中
〈燈〉
還有別的選擇嗎?身處於可見的世界,卻始終存在於不可見的他方,我想,王離的距離感是摺好的紙飛機,他的房間是象徵的收集冊,幼發拉底河的源頭可能是葛萊美,愛情比星球更遙遠。王離是殼,去向才是蝸牛的軟體,與其說詩人馱著他的世界,不如說,世界向詩人索求更美好的解釋,所以催促他作一位纜線的鋪設員,一切的連結都從不熟知的地境開始,走著走著,疆界不再如此明確,聲音漸漸變得可以觸摸,顏色只是感覺……王離能抵達的極限,無非是他所去過的地方,那些場景,都在意象生成的瞬間被經歷,被訊息化,並且表面被貼上「我只是看起來這樣」的標籤,畢竟,他只是想說一個故事,讓情節領他出去,讓他發現,永遠的完結是不存在的,甚至是一張唱片,都可以藉著描摹,去到描摹以外,那個與己無干的家。
我們聽起弦樂
了解離開和返回的意義
〈三十年後她加了弦樂〉
何俊穆
2010.7.18
佯知者旅遊指南
這不是詩的世紀。在我這個外行眼裡,詩甚至在讀者反應理論之外,詩人不期待也不在乎讀者的反應,讀者更無所謂詩的解讀,對於詩該平白或是晦澀曖昧各有支持,可是一旦要聊起詩來,這些討論都煙消雲散,詩不可解的迷思甚囂塵上。這種恐懼於是乎被隱藏起來,人們討論詩人多受矚目的身分,一些言不及義的推薦關於主題或是風格形式幫不上什麼忙,到底讀者買的這本詩集,由於不期待它的實用價值,就只好轉換成象徵意義。無怪乎上世紀末Rita Dove鼓吹美國的詩人寫點散文,讓讀者有機會更親近詩人一些,才不會越形孤獨。
所以如果得說點王離這本詩集《遷徙家屋》什麼,如果要說有什麼特殊之物被投擲到詩意的行列,我想是花鳥山水或者是宮宇樓台(當然這也意有所指)。如果你要我提供你一條閱讀的路線,我們必須注意到所謂詩意的往往是具有綿長的歷史,那些字詞之所以有魅力是因為他們早就出現過,是因為他們魂魄附著在人類的生活史。也因此王離的《遷徙家屋》乍看之下或許與旅遊文學是相關,但事實上我們會注意到一些長久統治我們想像的文學想像、歷史暴力的華麗偽裝,甚至是包曼言下現代生活「朝聖者」的身影,穿梭這本詩集裡頭。如果意象本身有他自身傳承的大歷史,這本詩集的想像必是建立在冰與火[1],火焰的一端。其實我也想問為什麼不是濕的?
這本詩集的意象集合,不屬於流離(disporia),也不屬於逃亡,事實上大多數是聚焦於當代的旅遊想像。但這也是我的疑惑之處,為什麼這本詩集的版圖與沙漠相離不遠,這樣的氣味換了許多地名、小島仍沒人讓發現旅房外的懷石料理或者大溪地曾經激起上世紀初藝術家永恆意義,或者妖豔氣息的泰國人妖。旅行的意義在這裡,更值得我們注意,也許我們正在閱讀的是一種移植過後的舶來品,有種更深層的基因一直在激起我們對詩歌的想像。
為什麼荒原如此重要,為什麼沙之女得是在沙中誕生慾望的形體,為什麼牧歌乃充斥異教徒般的愛,為什麼愛之詩乃想突破階級的差距,為什麼古老的阿拉伯的懸詩穿越時空而來,競技般的愛,乃一次又一次激起羅曼史,就在這一場綠洲夜宴的詩歌比賽從未來叫喚他的子嗣。我覺得這本詩集是在這樣的系譜內,漫長的雜交派對內[2]。〈植物的睡眠〉彷彿驚恐中幻變成樹,那更被疏離的現代空間內,壁紙上的森林圖樣在某個瞬間像火焰:
世界以無法理解的緩慢
崩毀於幾秒
窗內是我們的靜止
平貼並爬行著
你是山櫸而我是月桂
爬行並拼貼著
我漸漸摸清楚了你的脈搏
自從你的第二葉與我的第三瓣交錯
慾望空間的誕生,通常是從主體的穿越所造成的,比如Ashbery另一首詩〈房間〉:「我經歷過的房間乃是房間曾經的夢∕確實,那些沙發上的腳印都是我的∕早初年紀∕狗橢圓形的肖像是我∕時而閃爍,時而噤然無聲。」或另一首詩〈一些樹〉[3]這是這本詩集也一直頻繁出現的內在,在另一首王離的詩〈親愛的維多利亞〉:
在妳的王朝沉睡前假如
輕吐氣息
就植了一株樹
卸下繁複的衣裝
便生產了沃土
……
妳容許野鴨踏著妳奔跑嗎?
他們將因此健壯
假如妳容許他們飽餐
妳身上的蘆葦
或者妳有一片廣闊的草地
可以牧羊
這些詩都猶如岩盤大陸是虛實有無的肉身,像沙女的變化無常──這樣的想像,夏宇Salsa中也這樣寫過:「我還是願意偷偷自己是沙丘∕被某個晚上的狂風捲走∕第二天早上成為另一種形狀∕我也同意我們必須行動∕然後在行動裡找到動機。」夕陽與沙的命題是在一連串征旅之中對於危厄象徵意義的馴化。但無論如何變化,愛就像一席間詩人彼此的競技,如沙漏的腰,或如肚皮舞般前進的沙丘,猶如一些阿拉伯的懸詩,甚至是中世紀的牧歌來觀看這裡頭男性觀點如何將戰爭轉化成充滿蜜的言語,思想的交鋒又如何包覆為身覆薄紗的舞者或把裸男速寫成曼妙女郎,彷彿蒙娜麗莎之下所隱藏的達文西自畫像。也無怪乎王離也在〈燈〉中召喚了如此幻景:
稍遠些則撐圓了塔
為夜禱蒙上紗
或者是彎曲的吹管
織就絲毯,載音符掛上
墨黑的被絨
〈與鬼魂對話〉更直接向我們說明了這一切的旅遊想像的源頭。
終於她到了陌生的地方
是水和沙的起點
另外兩個她等著歡慶春天
她們身上只有葡萄藤
和些許貝殼
潮汐湧成清晨
風也自吹著
也許也不該如此驚訝,畢竟田曉霏也考察過華語世界的天堂與地獄是如何在中世紀藉由僧侶傳播到中土來。希臘詩歌常說著記憶是謬思的母親,〈去國與鄉人〉:
日復一日
我們記憶的國度漸趨完美
逸事與過往人物
是它的居民
精緻的詞藻與禮儀
仍擁有權力,在那兒
我們是彼此的先知
也是信徒
這本詩集正是詩人本身記憶的國度,只是這個記憶我以為是拜倫式的,是試圖激昂的,是想要運用旅遊文化中的帝國想像,是有關於征獵,有關於汛洪期後,沃土上農務的重整,從酒神(聲音)轉變成更為卑微的日神(意象)(或是以他的乳齒排成一幅落日迎接羸弱的夜那位少年)的口吻:
(我失去了聲音
然後是體態
接著是他),讀者應該反覆疑問是他還是她,是她還是他,國王還是女伶,遺忘還是記憶。也更要注意這本詩集想試圖運用敘事手法的決心〈吉普賽2〉:「攤出隨意繪製的一副牌∕開始抽取排列∕為我們講解故事∕洗牌然後有新的人物∕不斷延伸的土」這本詩集是相當有意識在結構上採用敘事,這裡的牌即暗示著旅房,從夢中不斷穿越而來的各種形象,正如德勒茲在討論《愛麗絲夢遊仙境》,投影在身體表面所形成的幻象會往更深層的冒險而去,每首詩就是旅人喪失在時空維度的故事。另一方面誠如《遊客的凝視》所說的,懷舊情懷自十七世紀產生以來似乎已成為當代社會中的一種流行病。遺產可能是偽造的歷史,想像早就安排好了,詩中的某些場景可能是不稀奇的,但一切早被說過千百萬次的,是詩的主體,乃小說的裂片。[4]
我不怎麼在乎故事的真實與否,但那流浪漢繪聲繪影,越說越是激動,幾乎都要湊到我身上來了,我急忙把他推開,有點狼狽地想保持距離,但他灼熱的眼神堅定地看著我,像是我的態度足以肯定或否定他的人生。
當代的詩意建立在像《Phantoms of Nabua》[5]這樣的作品對一開始場景出現在現代化後螢光燈的某個空地,突然雷所點燃的火球傳遞到最後終於燒毀了布幕,投影機在遠端看來像鬼魅一般投射著家鄉的想像。《遷徙家屋》既不講遷徙也沒談到家屋,只是意圖在描述那些鬼魅的影像,我們輾轉可能繼承了某種漫遊者的宿命,某種文學傳統仍在統治著我們,在不斷被繼承的想像裡面。
[1]〈冰與火〉乃是佛斯特詩作,援引的世界觀乃是北方寒冷南方燠熱的歐洲想像,但如果以台灣為中心,為什麼旅遊想像不能是濕熱的東南亞呢?這是我疑問這本詩集一點都不濕,反而是乾熱的火焰遍布詩中。甚至沒有遊學的打工少年,這可能隱含著一種刻意的主題選擇。而這裡的火,以Gaston Bachelard來說,屬於連結生命與火苗形象的雙重性。
[2]懸詩,阿拉伯六、七世紀早期詩歌的代表,對後世詩歌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阿拉伯人每年要到麥加朝覲天房,朝覲前,在麥加附近進行集中活動,並舉行賽詩會,詩人朗誦自己的作品,獲勝的詩用金水抄寫在麻布上,掛到古廟的牆上,宛如一串明珠掛在脖子上,人們稱之為懸詩。
[3]這些樹令人驚奇:每一棵∕都與鄰樹相連,似乎言語∕是一次靜止的表演∕偶然地做出這樣的安排∕今晨我們相會∕遠離這個世界,似乎∕心有默契∕你和我∕突然變成了這些樹。
[4]這本詩集的敘事得力於王離另一個小說創作者的身分。
[5]Phantoms of Nabua,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錄像作品。
印卡



 共
共  2011/09/09
2011/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