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第一本抵制中國的著作!引爆全球矚目!引發中國警戒!
一個家庭如何身體力行,以自己的力量與中國對抗?
前經建會主委陳博志、台大國企系教授盧信昌 專文導讀
經濟學家朱雲鵬 強力推薦
文茜的世界周報 CNN 時代雜誌 強力背書
大國崛起=大難臨頭?路熱烈討論!各大媒體和電視台強力報導!
大國崛起,大難臨頭?
從蝦子、牙膏、毛巾、輪胎到玩具,「中國製造」正在全世界引爆爭議。一度以超級低價搶攻世界的中國產品,如今讓無數消費者又是憤怒,又是焦慮。憤怒的,是中國不斷以超低價奪走其他國家基層勞工的工作權,焦慮的,是廉價產品背後糟糕的品管,所可能對你我健康所造成的危害。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中國製造?假如生活中沒有中國製造,會是什麼模樣?我們會因此而被迫花更多錢,還是這壓根是不可能的任務?本書作者決定身體力行,啟動這無數人都想要做、卻遲遲沒有開始的行動!而這趟勇敢的行動,最後引領這家人、以及全世界,得以重新看待與思考中國製造的未來…
作者簡介
Sara Bongiorni
得獎無數的資深財經記者。曾經主跑國際貿易,並曾於2002年榮獲美國財經編輯與記者協會(Society of American Business Editors and Writers)的年度商業寫作大獎。長期觀察中美貿易與中國的崛起,Bongiorni憂心著中國製造無遠弗屆的影響力。2005年,她決定大膽嘗試過著沒有中國製造的生活,並完成了這本備受矚目的《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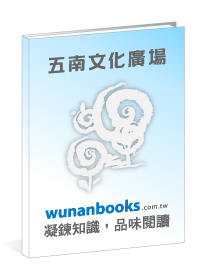
 共
共 









光從聳動的書名來看,就對這本書很有興趣;中國,真是令人又愛又恨的國家…。它的地大物博令人羡慕,但它的不友善及自大狂,更讓人討厭! 相信有很多人,不只是我,早已如作者一般身體力行,力拒中國商品進入家門,但這不是件容易的事,早些年前,「中國製造」就已經讓各大賣場淪淊,凡舉任何生活用品,大部份(95%以上)都是那刺眼的Made in CHINA,最近幾年,更變本加厲的入侵百貨公司各大部門!其實,撇開政治立場不談,在商言商,我們真正不喜歡的,是中國不斷以超低價奪走其他國家基層勞工的工作權,而焦慮的,是廉價產品背後糟糕的品管(有毒棉被、有毒醫療器材、有毒奶粉、有毒食品…幾乎沒有一樣東西可以讓人安心使用),對你我健康所造成的莫大的危害,台灣一般百姓所得還不差,實在有必要檢討:這樣低價但品質有問題的東西,真的是我們要的嗎? 美國距大陸遙遠,他們的人民也漸漸感受到工作權不保,甚至有些擔憂中國的入侵;反觀台灣,大陸近在咫尺,台商一窩蜂往對岸設廠,本國老百姓失業率不斷上昇,政府不積極思考因應之道(人民素質、政商法令、國家未來定位…等),反而鼓吹加速與對岸聯結,一眛自我催眠如此即能擺\脫不景氣,殊不知這實在有如飲鴆止渴…。 最近二年,反觀大陸目前的種種作為(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及規定企業必需提撥一定比率之勞工訓練成本,取消租稅優惠…等),它們也想加速擺\脫低成本低附加價值的勞動力方式,轉型為高附加價值的勞動力,此舉已導致許\多勞力密集企業出走往更低成本的國家移動,這是很正常的經濟現象,所以不必擔憂,真正應該小心的是:它不斷以不正當的手段併購(或想染指)各國的重要企業(尤其國防、能源、重工業、高科技等產業),這種拿著大把鈔票想往人臉上砸,短時間內取得別人智慧結晶的如意算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