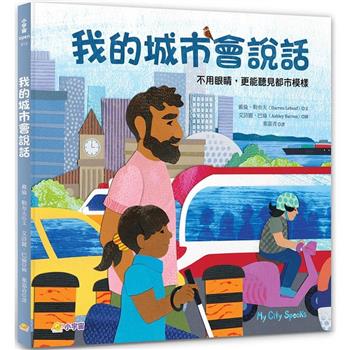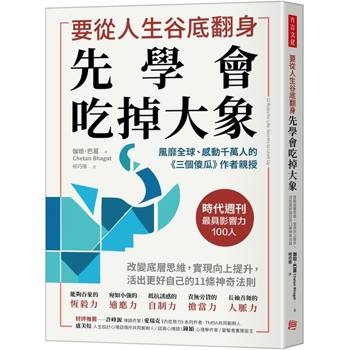七百七十五萬點閱率!晉江原創網 年度排行榜作品!
邁向未知的旅程,踏上神秘的國度,
勇往直前,永不屈服!
嗨!誰叫我是世界之王的小弟。
可惱阿!永瑞你居然連叫聲舅舅都那麼吝嗇,果然是傳自你老爸納蘭錫若的好種,小氣!
(最可惡的是居然可以跟那個冰塊臉貼臉,還親切的喊他皇帝舅舅,搞清楚誰家住得比較近好唄。)
『龍頭大銀票』見票立即支付五百萬兩白銀
這…這…有這等好東西怎麼不早點拿出來,辛苦了大半輩子,還□不到這個零頭,財神九真有你的。
(我又不是要給你的,你在高興什麼,我是擔心有一天你要跑路沒有盤纏,怕你連累我的女兒及外孫,跟你沒干係。)
千里迢迢來西北為國效力,到了為國捐軀的重要時刻,怎麼你大將軍王也會臨陣膽怯退縮呢!真是有辱英雄之名。
(喂!誰跟你說為國捐軀是這樣用的,虧你還是內閣大學士。再者,你說的獻身是出賣肉體,爺我不幹!)
嘴裡說不幹,還不是偷偷在後花園賞花、曬月亮。
作者簡介
八喜
本名黎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畢業。2001年開始寫作至今。著有《南北朝風雲》、《蘭陵長歌》。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