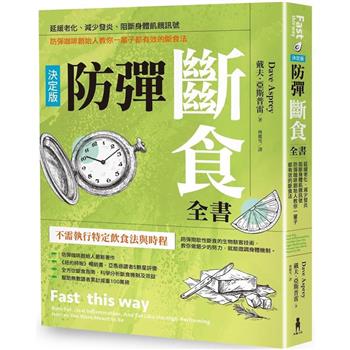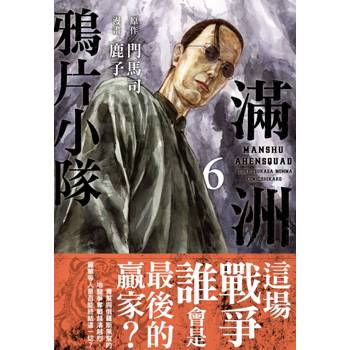一個還活在七○年代「無仁義之戰」的黑幫份子
一個拒絕參與波斯灣戰爭的士官
一個莫名奇妙替人背黑鍋的議員秘書
三個性格迥異的人被聚集在銀座一間高級俱樂部裡
他們的任務就是和一名退休的老警察共同策劃
重新改造這個冷漠的社會,對不公不義之事發出怒吼
展開一場充滿熱血與歡笑之「義理的逆襲」
阪口健太,通稱槍健。他殺了敵對的黑道老大,因而在監獄服刑十三年六個月又四天。大河原勳,通稱軍曹。因為堅決反對出兵波斯灣,隻身一人引發軍事政變,最後自殺未遂。廣橋秀彥,通稱小秀。他原本是某位議員的秘書,為收賄事件背黑鍋,成為這名議員底下一顆被犧牲的棋子。這三名個性鮮明、價值觀互異的男子,在某個機緣下,聯手結黨,挑戰欺騙他們的大惡人!淺田次郎惡漢小說的顛峰之作!
作者簡介:
淺田次郎(1951- )
本名岩戶康次郎,出生於東京,為舊士族家子弟。因為受到三島由紀夫自殺的影響,而加入自衛隊。期滿退役之後,曾從事過各行各業,因此積累許多豐富的人生經驗,而這些也成為筆下的最佳題材。早期以創作散文為主,由於熱愛寫作,儘管從事服飾業,仍創作不輟,一九九一年以文章<被拿到還得了!>初試啼聲。
初期作品多以「惡漢」題材入文,因此被稱為「惡漢小說」,(所謂惡漢小說(picaresque novel)是源自十六世紀西班牙,對騎士小說中理想主義的反諷,故事內容多描寫惡人如何冒險犯難、對社會極盡辛辣諷刺)於一九九二年始發表「金光閃閃系列」、《惡漢小說英雄傳》、「監獄飯店系列」等等。
一九九五年以《穿越時空.地下鐵》一書得到吉川英治文學新人賞;以中國清朝宦官為舞台的時代巨作《蒼穹之昴》,一九九六年入圍直木賞(一九九七年出版《誰殺了珍妃?》,為本書續篇);隔年以《鐵道員》榮獲直木賞的肯定。
從新選組系列小說中獲得靈感,構思二十年,創作《壬生義士傳》,二○○○年獲得第十三回柴田鍊三郎賞,也被稱為淺田版新選組。
自稱是「小說的大眾餐廳」,認為「寫作是最大的愛好」,作家生活十四年以上,出版超過七十冊的著作,至今仍保持對執筆的熱情。小說中濃厚的人情味是其主要特徵。
譯者簡介:
高詹燦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畢業。現為專職日文譯者,譯作有《祕劍.柳生連也齋》、《蟬時雨》、《隱劍秋風抄》、《光之國度》、《孤劍不折》等書。
章節試閱
反叛者
平靜的早晨。駐軍地陽光普照,心情無比舒暢。一等陸曹大河原勳心想,像極了二十年前的那一天。
他命值完勤務的警衛隊在重迫擊砲中隊的走廊上排好隊伍,向中隊長報告。當大河原一曹準確地一百八十度轉身向後,下達解散命令後,他喚住年輕的中隊長。
「中隊長大人,請問波灣戰爭的情勢近來如何?」
畢業於防衛大學的三等陸佐,多所顧忌地環視周遭,將大河原拉進中隊長室。
「我說軍曹……」中隊長反手關上房門,開口說道。自衛隊裡當然沒有軍曹這樣的階級,那是大河原一曹的綽號。因為他不管怎麼看,都像晚了半世紀才出生的老士官,雖不知道是誰替他取這個綽號,但確實取得相當貼切。
「今天師團長和師團司令部的幕僚來到隊上。」中隊長悄聲說。
「在下知道。剛剛在下才親自在大門前迎接。怎樣嗎?」
「既然你知道,說話就應該更小心才是啊。」
「中隊長大人,在下關心國際情勢難道有什麼不對?」
中隊長一副莫可奈何的模樣,仰天長嘆。
「我指的不是那個。拜託你別再用『在下』、『中隊長大人』和我說話了。」
「是。在下大河原一曹一時疏忽。不,是我一時疏忽。那我再次向您詢問,不知波灣情勢如今有何進展?」
中隊長一臉不耐煩地解開腰帶,拋在桌上。
「這我哪知道啊,就由他們去吧。對了,軍曹,你最近怪怪的。是不是身體不舒服啊?」
「不。」軍曹挺直腰桿。
「在下非常健康。中隊長大人,您剛才說『就由他們去吧』,這句話可是肺腑之言?」
「當然是肺腑之言啊。因為我沒有你那種危險思想。」
「危險思想?這句話請容在下問個清楚。堅決反對自衛隊派兵至波斯灣,為何是危險思想?」
「當然危險,而且是危險之至。由自衛隊員口中說出舊思想,就是危險。你連這個都不懂嗎,蠢蛋。」
「蠢蛋?」
「沒錯,蠢蛋。你乾脆搭時光機回到五十年前去算了。這麼一來,也許歷史會改變,瓜達爾卡納爾島(Guadalcanal)之戰也會戰勝呢,哈哈哈哈。」
軍曹光一個晚上便會長出滿臉青色鬍渣,外加粗大的濃眉、威嚴十足的氣勢,確實很像半個世紀前的軍人,他以這副面貌轉頭面向中隊長。駭人的氣勢,令中隊長不自主地後退。
「你……你想幹嘛!」
「中隊長大人是個孬種。」
「我孬種?有種你再說一遍!一旦有戰事,我就算粉身碎骨也不怕……」
「要在下說幾遍都行。中隊長大人是個孬種,不配為日本國民。身為軍人,一旦有戰事,捨身為國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不必講得一副很了不起的模樣。順從政府的意思,想要破壞和平憲章,這就是孬種。」
軍曹的軍靴發出響亮的踩踏聲,站在中隊長面前。
「等等,軍曹。你冷靜一下。自衛隊出兵海外,原本就是正當防衛行動的一環……」
「昔日的滿洲事變、出兵中南半島,也都宣稱是正當的防衛行動。此種防衛根本就是侵略的別名。」
「可是,中東是我國經濟的命脈……」
「滿洲國昔日也說是日本的命脈。」
「等等,大河原。你冷靜一下。」
「在下很冷靜。您的想法愚弄著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在下將代表兩百萬國軍英靈與國民之民意,痛毆中隊長大人。此乃替天行道。」
話還沒說完,軍曹已朝中隊長的臉揮出一記重拳。軍曹在空手格鬥技方面,連隊裡無人能出其右,中隊長被他一記右拳紮實地擊中臉部,身子整個飛向屋內角落。
軍曹按照軍事教練的動作,恭敬地行了一禮,軍靴的腳跟發出叩的一聲清響,順時鐘轉身向後,神色自若地走向走廊。聽聞有狀況發生,成群擠在門前的隊員們,被他威風凜凜的氣勢震懾,紛紛開道讓路。
由於警衛隊剛繳回槍械,中隊的彈藥庫鐵門仍未關閉。軍曹走進彈藥庫,掌管武器的陸士長顫抖著向他行禮。
「準備好六四步槍和實彈、手槍子彈、五顆手榴彈,以及繩索。」
掌管武器的陸士長臉色發白,拒絕受命。軍曹從腰間的槍套裡取出手槍,門外的人潮紛紛後退。
「你要死在市谷的彈藥庫裡,還是死在阿拉伯的沙漠裡,現在是決定的關鍵時刻。一切責任由我來扛。快交出來!」
照他說的去做──從中隊辦公室衝出的資深陸曹朗聲喊道。軍曹的腳下旋即擺滿了武器。
「好,你退下。」軍曹語畢,立即將六四步槍的拉柄往後拉,檢查槍膛,接著裝上彈匣,解除保險裝置。手榴彈一排掛在肩章上。他將繩索斜披在肩上,右手持手槍,左手持步槍,霍然起身。
「武器的保養狀況大致良好,繼續作業。」
軍曹身穿沒輪值時的非正式軍裝,英氣逼人,像針鼹般全身攜滿武器,步向走廊,現場黑壓壓的群眾全都不敢出聲。
「喂,鋼盔借我。」
他朝一名從對面營內班探頭的隊員說道,旋即遞來一頂鋼盔。軍曹在襯盔外戴上鋼盔,深戴至眉際,繫上環扣。
「大河原,你想幹什麼?」
資深陸曹撥開人群,向他喊道。軍曹轉頭朝他瞄了一眼,以他平時沉穩的軍人口吻說道:
「在下要直接向師團長陳情。日本政府錯了。在下身為一等陸曹,不能讓在下帶領的一兵一卒白白犧牲。其他事就有勞您費心了。」
軍曹在走廊上昂首闊步,走上階梯。
望著他離去的重迫擊砲中隊隊員,以及聚集在樓梯平臺和二樓走廊的第四中隊隊員,個個呆立原地。
然而,幾乎沒人將它當作一件重要的事件看待。對他們而言,這比出兵波斯灣還難以理解。早已見識過軍曹此等怪異行徑的人們,都會想起秋季勞軍旅行時,軍曹表演武田節舞的模樣。眾人一致認定,那一板一眼、引人發噱的舞蹈,是軍曹自成一派的表演方式。換句話說,大河原一曹的存在,在已經形同公務員的自衛隊中,與其說具有象徵性,不如說他是塊記念碑還比較貼切。
軍曹走上二樓,筆直地走在第四中隊的走廊上,朝位於營區西邊的連隊總部而去。
「喂,重迫擊砲中隊的大河原軍曹不知道要做什麼呢?」
在走廊上接受軍曹敬禮的第三中隊副隊長,看著軍曹從身邊走過,思忖了一會兒後,笑著朗聲如此喊道。營內班的大門不約而同地打開,閒得發慌的隊員們個個湧向走廊。
「聽說要向師團長表演武田節呢。」
「不,好像是要從屋頂進行沿繩下降的示範表演。」
「不是突擊隊員緊急集合嗎?」
和二十年前的那天一樣,全部都一樣──軍曹在行走的同時,於心中暗忖。
那名男子綁架方面總監,頭綁白色頭巾,出現在一號館的陽臺上時,當時眾人也同樣是這番話語。沒半個人認真思考事情的嚴重性。眾人在一旁吹口哨、拍手、喝倒采,但誰也沒料到這名男子竟然在數分鐘後切腹自盡。當時在陽臺下朗讀宣告文,淚流滿面的我,年僅十九。我一直在等待。這二十年來,我等的就是這天。
當時大河原一曹突然發現自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一時為之愕然。
他沒換內褲!儘管心中暗叫不妙,但已然太遲。而且內褲不僅只是髒污而已。如果那是一般店內賣的白色內褲倒還好,但他現在身上穿的,是情人節那天,歌舞伎町的酒店小姐送他的星條旗緊身內褲。
他全身冷汗直冒。當初原本計畫在執行完勤務後洗個澡、刮鬍子、換件內褲後,再展開行動。但偏偏平時就很看不順眼的中隊長說了那些不該說的話,結果只好割捨計畫中的這一部分。內褲的事,他壓根兒就忘了。
軍曹繼續往前走,對自己的疏忽深感後悔,咒罵「熱帶酒店」裡的小姐明美──竟然送星條旗緊身內褲給自衛官,未免太沒常識!特別是他自己,在擔任警衛勤務時,竟然穿這種內褲,實在沒有操守可言。
結果他完全感受不到葉隱精神。如果內褲的花紋是太陽旗的話就好了……可是,仔細一想,太陽的圖案實在不適合當內褲的花紋。如果太陽擺正面,充滿猥褻;若是擺後面,又活像猴子。
軍曹現在身陷窘境,進退維谷。既然身穿星條旗內褲,他的犧牲肯定會引來嚴重的誤解。進是死,退也是死,英帕爾戰役(Battle of Imphal)一定就像這樣,軍曹一面走一面思忖。
從連隊長室傳來幕僚們的笑聲,不知道有什麼事那麼好笑。
「報告,我是重迫擊砲中隊的大河原一曹。有事參見師團長。」
「大河原,你那是什麼模樣。」
一名資深的庶務班長見狀上身後仰,如此說道。軍曹瞪視著他們每一個人,以此代替回答。
他這股氣勢充滿自信。他身高一百九十公分,胸圍一百三十五公分,魁梧的身材猶勝席維斯史特龍,足以與阿諾史瓦辛格匹敵。而且他在連隊內,是令人驚嘆的空中突擊隊員、刺槍術五段的高手、徒手格鬥術特別等級,還在夜校取得珠算三級的資格。
人牆倏然後退。
「進來吧。」室內傳來連隊長的聲音。
「是。」
軍曹打開門。坐滿會客室的幕僚們,一見他這身打扮,頓時不約而同地起身。
他們狼狽的模樣,讓軍曹明白了一件事。斬殺奸臣軍務局長永田鐵山,深受軍曹敬重的相澤三郎中校,想必就是像我這樣。然而……現場眾人實際聯想到的人物,卻是八墓村裡的殺人狂。
「大河原,你……你這是幹什麼?你這身奇怪的裝備……是在做戰鬥訓練嗎?是這樣沒錯吧?哈哈哈。」
連隊長立刻站在師團長面前打圓場,但看得出他臉上露出焦急的神情,像是在訴說著「在這麻煩的時候,偏偏來了個麻煩的傢伙」。軍曹反手關上大門,加以上鎖。
「這不是訓練。」
語畢,他右手執起手槍,左手將六四步槍架在左腰上,幕僚們驚叫連連,紛紛趴在地上。躲在書桌後頭的連隊長,露出一對惶恐不安的眼珠,向軍曹說道:
「你知道你現在在做什麼嗎?」
「我知道。」
師團長命百般不願的副官擋在前頭,自己縮在連隊旗下方,向他說道:
「等一下,有話好好說。總之,你先和連隊長談談吧。」
「不,我是特地前來向師團長陳述我的意見。」
「我並不認識你。」
「就算閣下不認識我,我卻對閣下知之甚詳。換言之,我是在閣下的一聲命令下,便會立即喪命的第一師團所屬之普通連隊隊員。只因為不認識我,就不和我對話,這樣有違民主國家的原則。」
「那你就說來聽聽吧。」
「我希望您能阻止政府派兵波斯灣。」
「這怎麼可能!」一名趴在地上,雙手抱頭的幕僚說道。
「在憲法下不被認同,四十年來就像被當作私生子般的隊員們,如今卻想以和平的名義殺害他們。這是悖離人倫的行徑,我無法服從。」
「說什麼人倫!你現在的行為根本就是犯罪!」
連隊長配合軍曹的威嚇如此說道,一會兒站起,一會兒坐下,猶如打地鼠遊戲般。
「我明白。但道德倫理比法律優先,這是人盡皆知的道理。我確信沉默才是背叛,所以今日才有此舉。希望您能給我答覆。否則我將以死會見九泉下眾英靈。」
伏臥在會客室的地板上,面面相覷的眾幕僚中,有人喃喃低語道:
「竟然說要會見九泉下眾英靈?這傢伙腦袋有問題啊。」
住口!軍曹厲聲斥喝,執起手槍掃射。在瀰漫的煙硝中,現場鴉雀無聲。
「英靈不是戰爭的象徵,是和平的代表。你們就是因為不具備這種國際性的常識,才會被國際社會孤立。」
師團長惴惴不安地從屋內角落爬出。
「大河原一曹是吧?可是你要了解,自衛隊有文官統治的原則,我們這些自衛官……」
「這我知道。那些文官打算以隊員們的鮮血,來彌補他們差勁的外交所捅的婁子。」
「為和平流血,不正是我們的使命嗎?你說是不是?」
「既然這樣,就由您來流血吧。閣下對自衛隊員根本一無所知。如今求職雜誌氾濫,您知道是什麼樣的年輕人選擇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嗎?他們大多是在這只重學歷的社會中無法謀生、稚氣未脫的青年,那些東大畢業的官員們所犯的錯,不該以他們的鮮血來洗濯。」
「我懂了,你是共產主義者對吧。」
幕僚從地上抬起頭,如此說道。軍曹再次將步槍夾在腋下,朝窗戶掃射。南面的玻璃窗被轟成碎片。
「我沒有那種偏執的思想。」
「是嗎?我倒覺得你的想法很偏執呢……」
師團長朝那名說話的幕僚猛搖頭,使了個眼色。
「真是遺憾。師團長和各位幕僚們,原來也都是身穿軍服的文官。」
走向吹來陣陣宜人春風的窗邊一看,可以望見有輛白色吉普車帶隊,後頭跟著數輛巡邏車,朝這裡急馳而來。軍曹感到沮喪,和二十年前那天一模一樣。駐軍地的警務隊一認定有事發生,便馬上打一一○報警。自衛隊完全沒有軍隊的主權,甚至沒有主張正當權利的能力。
「我明白了。你說的都很有道理。你的想法,我會透過陸軍幕僚部傳達給防衛廳長明白。」
「此話當真?」
「當然是真的。武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來,你先冷靜一下。」
老奸巨猾的師團長這番話,令軍曹的憤慨急速冷卻。他對善惡的區分相當敏銳,但卻不懂得判別真假。
「是嗎?您真的明白我的想法?」
「嗯,我當然明白。既然我明白了,你就別輕舉妄動吧。」
「不,我已決定要為國家犧牲。我將血染連隊長室,請容許我冒犯的行為。」
軍曹內心剎那如明鏡般清澈。他端坐地上,擺好武器與繩索,接著將貼身的一封「致內閣總理大臣」的陳情書擱在上頭。
「驚擾各位了。因為這件事一生只有一次機會,若是沒能成功,煩請幫我了斷性命。」
他將手槍抵向太陽穴,緩緩扣下扳機。
──要是當時他閉上眼睛,故事應該就到此為止了。
然而,他模仿二十年前那名男子,遙拜皇居,從容就義,這種浪漫主義引來了悲劇。
他昂首望向右前方一點鐘方向,望見在方面總監房間屋頂翩然飛舞的太陽旗,執槍的手登時不聽使喚。
因為他驀然想起自己身上穿的內褲,既不是太陽旗花紋的內褲,也不是軍方配給的白色內褲,而是酒店小姐贈送的星條旗緊身內褲。而且已連穿了五天,每次上廁所,都會發出熏人的臭味。
伴隨著一陣劇烈的衝擊,扳機擊發。
他昏倒在地,那群幕僚低頭望著他,在逐漸模糊的意識下,他望著他們那猥瑣、卑微、令人唾棄的公務員嘴臉。
「真令人吃驚!頭蓋骨留下好長一道彈痕,好一顆堅硬的石頭!」
「簡直就是日本藍波!他的頭這麼堅硬,連鋼盔都可以不用戴了。」
「要幫他了斷嗎?反正留下他也是個麻煩。」
「不,用不著這麼做。」
「不過,要是留下後遺症,日後半身不遂,那也可憐呢。」
「這傢伙半身不遂,正好跟正常人一樣,哪會可憐啊。」
大門開啟,耳邊傳來凌亂的腳步聲。軍曹在腦中冷靜地思考,這就是死亡嗎?但他一直等待,眼中始終不見耀眼的太陽升起。不久,猶如沉入無底深淵般,深沉的黑暗到來。
反叛者平靜的早晨。駐軍地陽光普照,心情無比舒暢。一等陸曹大河原勳心想,像極了二十年前的那一天。他命值完勤務的警衛隊在重迫擊砲中隊的走廊上排好隊伍,向中隊長報告。當大河原一曹準確地一百八十度轉身向後,下達解散命令後,他喚住年輕的中隊長。「中隊長大人,請問波灣戰爭的情勢近來如何?」畢業於防衛大學的三等陸佐,多所顧忌地環視周遭,將大河原拉進中隊長室。「我說軍曹……」中隊長反手關上房門,開口說道。自衛隊裡當然沒有軍曹這樣的階級,那是大河原一曹的綽號。因為他不管怎麼看,都像晚了半世紀才出生的老士官,雖不知...

 2 則評論
2 則評論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2009/10/19
2009/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