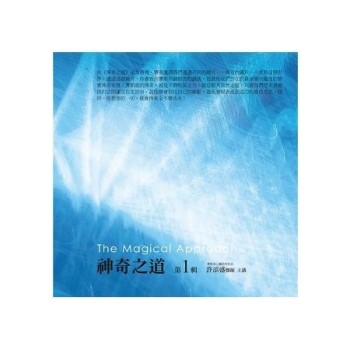本書集結了作者的四篇文章,學術性較强,主要涉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變遷、縣制的起源、縣鄉亭裏制度以及有關《聖諭》和《聖諭廣訓》兩部專著的探討。有純粹考證性的文章,也有概括性總結性的文字,還有以材料和分析為主關於古代專著的討論等。
自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開始,統治者歷來都追求長治久安的目標。雖然秦朝二世而亡,唐代最長也不足三百年,但就整個中華民族的體系而言,却在不斷打破久安的情况下,總體上保持了長治的過程,其秘訣就在于制度的設計。美國政治學者福山說:「歷史,就哲學的意義而言,的確是一種發展,或曰進化,或曰現代化,即制度(institutions)的現代化。」中國歷史的變遷乃在于長治久安局面的不斷被打破,而後又不斷被重構,不斷改進國家組織以及教育安定百姓的工作,從而使長治久安的局面得以重複出現。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長治與久安的圖書 |
 |
$ 264 ~ 360 | 長治與久安
作者:周振鶴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6-24 語言:繁體書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長治與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