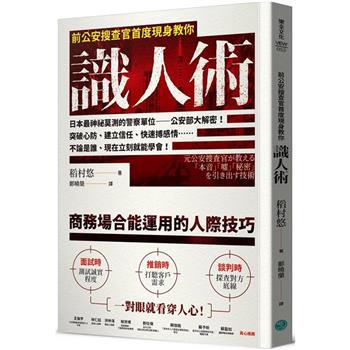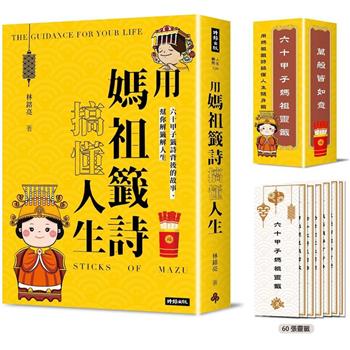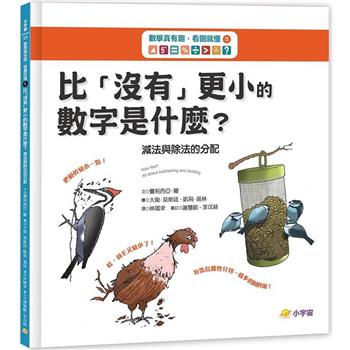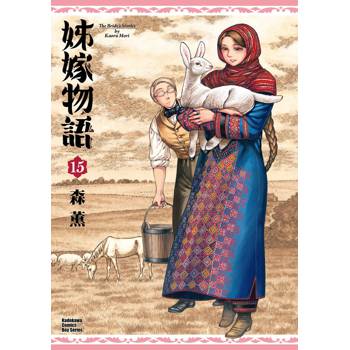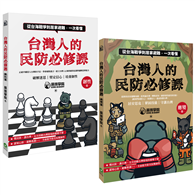阿里山人的阿里山故事,
感受「我們都是一家人」的特殊山林文化!
曾經昂揚,卻不敵雷火焚身的阿里山神木;
以及林場出差人員,找尋家的溫暖的各種俱樂部……
為了家計,一次可擔起五、六十斤重物的女挑夫;
越洋而來,與當地女子發生短暫異國情緣的年輕背包客;
以及因為時空更迭、角色遽變,數十年後重逢,只能淚眼相對的台、日阿里山人……
這些發生在阿里山的故事,有著特殊的阿里山氣味,是身為阿里山人的攝影家陳月霞,在重返阿里山尋訪其人文歷史與自然生態之後,最深切真實的描述。在這些故事當中,我們看到的不再只是觀光的阿里山,而是那份夾雜著多元文化面貌的山林神髓,以及阿里山人在面對生活考驗,歷經時代與環境變遷之後,所淬鍊出的共同特質與記憶,情感飽滿而動人,帶領讀者從「心」認識阿里山的山林文化。
本書特色
1.不是觀光的阿里山,而是生活的阿里山。
2.神木、樹靈塔、姊妹池、火車、森林等知名的阿里山代表,最真實深入的背後故事。
作者簡介
陳月霞
出生於阿里山沼平。
長年從事攝影、寫作及兩性、親子、社區、環保、自然教育等工作。1987年,於台北春之藝廊舉行「植物之美」攝影個展。1997年,進行「認真的女人最美麗」廣告拍攝。
曾任阿里山高峰山莊莊主、勵馨基金會台中站顧問、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理事、台灣民族誌影像學會理事、行政院新聞局中小學優良課外讀物評審委員。
現為台中市社區婦女成長協會理事長、台灣生態研究中心協同負責人、台灣生態學會理事。
著有攝影集《植物之美》、《自然之美》;植物圖文集《認識老樹》、《童話植物》、《大地有情》、《森抹遠綠---大阿里山植物親子解說手冊》;兩性暨親子教育散文集《這一家》、《跟狐狸說對不起》;兩性散文暨論述集《聰明母雞與漂亮公雞》;《阿里山永遠的檜木霧林原鄉》、《火龍119》等書。
目前正進行阿里山人文歷史長篇小說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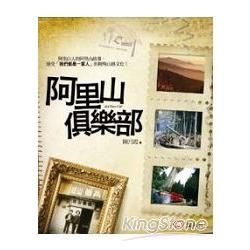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