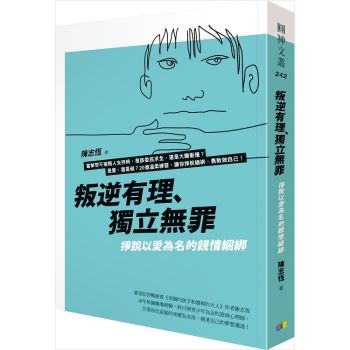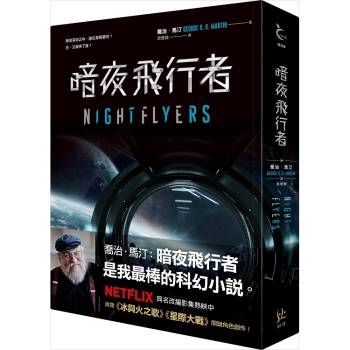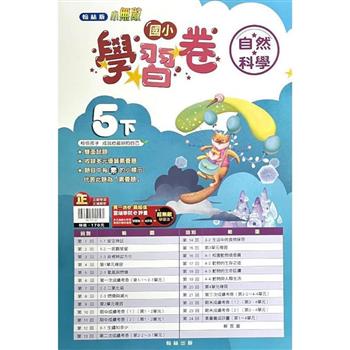阮義忠推薦序
我可能是阮璽所認識的人當中,最後一個知道他在拍照的。身為他的父親,我一直勸他不要碰攝影,因為壓力會太大;我也以為他不會在藝術領域發展,他從小討人喜歡、得人信賴,最適合從事公關或是業務推廣。
記得他在讀大學時,有一回很慎重地給我看他的畫。我翻了幾張,跟他說:「這還只是塗鴉,任何人在空想時,拿個筆都能畫得出來。你如果想表達心中的感覺,就要好好練基本功,從觀察開始,把眼睛所見用手勾勒出來。能夠把看到的畫真,才能把想到的畫美。你別看老爸畫的插圖只是隨意幾根粗細不等的線條,背後其實是從小按部就班的苦練。」
那席話很可能澆熄了阮璽的繪畫熱情,但幸好沒阻擋他對美與藝術的追求。父子倆各有所愛,我那大量的藏書與黑膠唱片他很少去翻,在這方面極少受我影響。他自己買喜歡的書和音樂,穿的、用的更是跟我不同路。他對好設計品特別感興趣,而且喜歡跟人分享。熱愛蘋果電腦,便找了個銷售工作,還收集該品牌各個時期的原型;喜歡丹麥、瑞典的傢俱,便當起了二手北歐傢俱店的店長。
從小我對阮璽便沒什麼特殊要求,只希望他健康、快樂,告訴他要做一個誠實的好人,忠於自己、善待別人,能這樣,一輩子就算沒白過。他在當電腦業務員時,有一天我跟他母親去百貨公司的專櫃找他,工作環境讓我看了嚇一跳,很難想像在那麼吵雜、窄小的空間站一整天、吃兩個便當是什麼滋味。用餐、上洗手間還得抓緊空檔,趁沒客人時盡快解決。那時我才曉得,他吃得起苦,為了喜歡的事,可以克服環境,把苦變樂,這還真是天生樂觀的人才辦得到。
大概是因為我比較嚴厲,阮璽基本上很少跟我談學業、服役、或工作的情況,有事只會跟他母親說。每次問他:「最近怎麼樣?」他的回答總不外乎「還好」、「可以」、「OK」,讓我難以分辨其中的差別。他也一直沒讓我知道他在拍照,直到有一天,說要帶我和他母親去一間他所吃過最棒的臭豆腐店。
那一帶我已多年沒興趣前往,況且住家附近就有一攤難得好吃的臭豆腐,酥炸、麻辣任人挑,想不出臺北有哪家會勝過。不過,他的好意讓我非常開心,即使是不怎麼樣,也無妨。
果真不怎麼樣,可是,吃完他又說了:「附近有家我朋友開的咖啡館很不錯,要不要去坐坐?」這我就更不以為然了,多年來我只喝自己烘焙的咖啡,但依舊覺得開心,而且他母親興頭特別大。
果然又不怎麼樣,而且竟不供應搭配的甜點!我特地去附近便利商店買了一包巧克力,回到座位時只見他母子倆頭靠著頭在看些什麼。坐定,老伴才說:「兒子拍了些照片,你幫他看看,給點意見。」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阮璽記取了多年前的教訓,費心安排,希望我在比較輕鬆、愉快的心情之下看他的作品。一看之下,不得不說「好!」。所有照片都是他用手中那台iPhone拍的,而且沒整理出來給我看的還很多。原來他幾乎天天拍照,已拍了快兩年。我這也才明白,他每天騎著那輛拉風的英國手工打造摺疊式腳踏車上下班,是在幹嘛,為的就是能在大街小巷穿梭、拍照。
我拍照超過四十年,寫過兩本介紹世界攝影大師及新銳的書,辦過十多年國際性的攝影雜誌,在大學教了二十五年攝影,閱歷算豐富了,但阮璽的作品讓我充滿了觀看的新鮮感,每張照片都躍出一種生氣勃勃的熱情。臺北的大街小巷,處處向他展現著活潑、幽默的一面,平凡事物在他的鏡頭下顯得活力十足。
攝影自有史以來,幽默的視角就比較少見;紀實攝影趨於沈重,觀念攝影則不是太冷感就是過度自憐。阮璽所拍的照片充滿溫度,構圖又嚴謹,實在是讓我意外。我從前勸他不要走攝影這條路,擔心他會籠罩在父輩的陰影之下,現在看來,我是多慮了。如今我倒是樂意聽到有人說:「你兒子拍得比你好!」
阮璽的所有作品都是用手機拍的,手機攝影的方便使許多人的創作態度改變,依靠軟件求取特殊效果,在取景時誇大前景深、故意不經意地框取特寫,藉以表現純圖像的趣味;結果,卻讓人愈看愈沒感覺。攝影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會表現出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微妙關係。本來毫無淵源,但在快門按下的那一剎那,就彷彿有了血緣。阮璽在街頭拍了許多擦身而過的人,他們的側身或背影傳達了與空間組成的一種特殊氛圍,故事性很強,彷彿是影像小說的極短篇;他也愛拍動物,無論禽鳥、狗或貓都帶著令人莞爾的靈性,生動而喜氣,溫暖又令人回味。
我與阮璽相處最密切的時光,就是在寫《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銳》以及籌備《人與土地》展覽的那陣子。當時他讀幼稚園,不想上課,整天跟著我。那兩本書原是《雄獅美術》的專欄,每個月得交一篇。我總是坐在臺北民生東路巷內的「芳鄰餐廳」,在同一張桌上從白天寫到晚上,直到他母親下班來會合。給他幾張紙、一支筆,他就乖乖地坐在旁邊塗鴉,畫累了就自己跑到隔壁公園玩耍。
籌備《人與土地》展覽時,他是第一個觀眾。我將所有照片在一座25:1的展場模型上擺來擺去;他問:「為什麼要分成四個單元?成長、勞動、信仰、歸宿是什麼意思?」我一一說明,但實在不曉得如何對小孩解釋「信仰」,只有這麼回答:「無論發生什麼事,爸爸媽媽都是愛你的,而你也會愛爸爸媽媽。永遠不變的愛,就是信仰。」當時他似懂非懂地點頭。二十七年後的今天,他不但要開個展,還要出版攝影集。這讓我明白,我的話他聽進去了。現在,我只希望阮璽和我一樣,把攝影也當成信仰。
──攝影家 / 阮義忠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院喜.Happiness in a Courtyard的圖書 |
 |
$ 202 ~ 432 | 院喜.Happiness in a Courtyard
作者:阮璽 / 譯者:李彥儀、洪慧珍 出版社:可口智造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1-24 語言:繁體書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院喜.Happiness in a Courtyard
阮義忠獨子,初聲之作──
結合傳統攝影精神與當代敘事思維,用幽默的視線記錄城市。
臺灣第一本正式出版手機攝影集/ 兩年7O張作品精選+中英雙語創作訪談
攝影名家阮義忠專文側寫/ 設計師王志弘推薦 / 空白地區workshop主編
把手機攝影認真當成一回事,它可以比你想像的做到更多
Take cellphone photography seriously. It can do a lot more than you can imagine.
攝影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會表現出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微妙關係。本來毫無淵源,但在快門按下的那一剎那,就彷彿有了血緣。阮璽在街頭拍了許多擦身而過的人,他們的側身或背影傳達了與空間組成的一種特殊氛圍,故事性很強,彷彿是影像小說的極短篇;他也愛拍動物,無論禽鳥、狗或貓都帶著令人莞爾的靈性,生動而喜氣,溫暖又令人回味。──攝影家/ 阮義忠
作者簡介:
阮璽,1981年生於臺北,喜愛音樂、藝術與設計。2O12年起以手機進行攝影創作,現為臺北藝術聚落「空場」阮義忠攝影工作坊經營人。作品曾刊登於《杭州都市報》、攝影雜誌《秘境》專文介紹。《院喜.Happiness in a
Courtyard》是他的第一本攝影集。
展覽:《院喜.Happiness in a Courtyard》臺北空場 / 臺南新光微藝廊個展(2O15)「空場」藝術聚落開幕聯展(2O14)、《臺北建城130週年》攝影特展聯展(2O14 )。
編者介紹:
彭星凱.一九八六年生,空白地區工作室負責人、黑文化出版總編輯、學學文創講師。裝幀作品逾百本,曾獲臺北書展金蝶獎銀獎╱銅獎╱榮譽獎(兩件)、APD亞太設計年鑑收錄。著有散文詩集《不想工作》。
推薦序
阮義忠推薦序
我可能是阮璽所認識的人當中,最後一個知道他在拍照的。身為他的父親,我一直勸他不要碰攝影,因為壓力會太大;我也以為他不會在藝術領域發展,他從小討人喜歡、得人信賴,最適合從事公關或是業務推廣。
記得他在讀大學時,有一回很慎重地給我看他的畫。我翻了幾張,跟他說:「這還只是塗鴉,任何人在空想時,拿個筆都能畫得出來。你如果想表達心中的感覺,就要好好練基本功,從觀察開始,把眼睛所見用手勾勒出來。能夠把看到的畫真,才能把想到的畫美。你別看老爸畫的插圖只是隨意幾根粗細不等的線條,背後其實是從小按部...
我可能是阮璽所認識的人當中,最後一個知道他在拍照的。身為他的父親,我一直勸他不要碰攝影,因為壓力會太大;我也以為他不會在藝術領域發展,他從小討人喜歡、得人信賴,最適合從事公關或是業務推廣。
記得他在讀大學時,有一回很慎重地給我看他的畫。我翻了幾張,跟他說:「這還只是塗鴉,任何人在空想時,拿個筆都能畫得出來。你如果想表達心中的感覺,就要好好練基本功,從觀察開始,把眼睛所見用手勾勒出來。能夠把看到的畫真,才能把想到的畫美。你別看老爸畫的插圖只是隨意幾根粗細不等的線條,背後其實是從小按部...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阮璽 譯者: 李彥儀、洪慧珍
- 出版社: 可口智造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1-24 ISBN/ISSN:978986902721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08頁 開數:20x20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