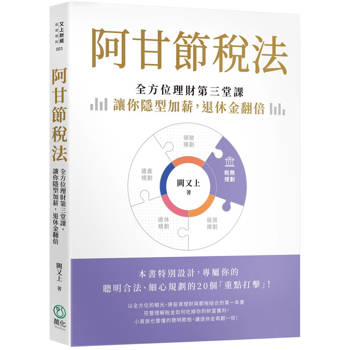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這本名著中寫道:「上帝絕不一般地觀察人類。」上帝一瞥人類,就能分清「人人互相接近的相似點和人與人互相疏遠的差異處」。上帝不須區分中國人、台灣人或者美國人。上帝能區分每一個人。人類沒有上帝的大能,總是把一個相似的群體歸類地描述,把它納入在一個「模式」中。這雖然容易簡單化,但這是人類智力軟弱無力的一個不得已的策略。
不同文化的民族差別細微,與他們的共同點相比,這種差別幾乎不值得一提。他們都有智慧,能用語言交流,能發明創造。他們都有共同的人性,有幾乎相同的欲望:追逐美色、美味和舒適,而且都不會停止去實現永無止境的欲望。他們都有攻擊性,都會進行暴力犯罪和戰爭。即使在不同文明互相隔絕的時期,他們幾乎英雄所見略同地創造了貨幣、交易制度、國家,也都有妓女、小偷、強姦犯、統治者……不同的文化之間幾乎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礙。中國西部少數民族的婦女可能不識字,沒有見過西方人,但她們編織的工藝品能為西方人接受,其中的美能被西方人所欣賞。日本的漫畫無論是純情的題材或色情的題材,在中國都能找到市場。
承認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差異不會存在困難,這往往被理解成人類在時間跨度上的變化。但一些人不喜歡「國民性」這個詞,認為世界上美國人、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的區別並不重要,他們都是現代人。人們容易承認個體之間的差異,而不願正視群體之間的差異。文化身份容易與「種族歧視」聯繫在一起。在提及一個國家的國民性時,人們總是小心翼翼,害怕招致責難和批評。
文明人確實對野蠻人表現得過於偏激,把他們視為低人一等的動物。他們忽略了野蠻人和文明人的共性。野蠻人可以與文明人通婚,可以生育後代,而且生育的後代不是怪物,而是正常的人。在文明人的生活環境裡,「野蠻人」同樣可以成為音樂家、科學家、詩人、將軍、國王……從生理和智力上,種族之間可以存在細微的差異。有些種族容易對酒精產生依賴,容易出現酒鬼。有些種族在某一方面可能表現出略微超過平均水準的「天賦」。但有一點幾乎是肯定的:種族之間後天的文化差別比先天的稟賦差別更重要、更具有決定性。
十八世紀的美國人與英國人就有差別,雖然他們都是同一個種族,但他們已經不是同一個民族。顯然,中國人與美國人的差別比英國人與美國人的差別更大,這不是因為他們的種族差異,而是因為他們的文化差異。美國的黑人與白人的差別遠遠比美國的黑人與他們的非洲同胞小。
驢與馬在外觀上有明顯的不同,但驢與馬的基因差異不到2%,它們交配還能產出騾子。上帝不過是用一些細微變化就製造了世界的豐富多彩。
人類文化的細微差異也會導致人類社會的截然不同。人類進入工業文明後,不同文化群體在經濟上的差距越來越大。在十九世紀,發達國家,除了日本,都在基督教社會。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重新洗牌,日本和歐洲仍然從廢墟上崛起。除了新加坡、香港、台灣、韓國等少數地區改變了命運,落後的地區依然落後。群體差異比個體差異更重要。一個中國人在日本可以創造出不俗的業績,在日本奮鬥的中國人證明了這一點。但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國社會和由日本人組成的日本社會竟會有天壤之別。
不管中國人高興不高興、接受不接受,台灣人與中國人不同。台灣在歷史上幾乎沒有受到中國中央政權的控制,除了幾個短暫的時期,台灣走的是一條與中國不同的道路。台灣是獨特的。台灣沒有共產主義革命,沒有「反右派」、「文革」這類「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台灣的吏治遠沒有中國腐敗。台灣在經濟發展中沒有表現出「中國特色的」環境破壞、貧富懸殊。台灣已經在民主、自由、地方自治上逐步成熟。
不管台灣人高興不高興、接受不接受,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差別較小。甚至與香港人、新加坡人相比,台灣人更接近中國人。新加坡人、香港人說的漢語只有在中國留學的外國人的水準。台灣的國語與中國的「普通話」完全一樣,中國人與台灣人交流幾乎不存在障礙。台灣的文化產品對中國人幾乎沒有隔膜,幾乎看不到台灣特有的痕跡。鄧麗君的情歌、瓊瑤的言情小說、柏楊的雜文表現出的是中國味而不是台灣味。
2006年,台灣流行從中國大陸傳過去的一句順口溜:「不到台灣,不知道文革還在搞。」這雖然是一個笑話,卻反映中國文化在台灣已經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1980年代,柏楊寫的《醜陋的中國人》在中國大陸捲起了一陣旋風,這本書中引用的事例多取自台灣。
在中國這個中央集權的大國,如同這個國家過去的大家族,人與人互相牽制,社會改良的機會和個人的活力受到制約。「中國是大海,它能使流入其中的每一件東西都帶上鹹味。」即使在海外經過洗禮的中國人,回到祖國,也會恢復從前的狀態。
顯然,台灣人不甘把自己的命運與中國大陸聯繫在一起。正因為脫離中國大陸,才使得台灣沒有像新疆、西藏一樣經歷文革之類的磨難。如果台灣是中國中央政權統治的一個省,它比已經設省的海南島好不了多少。現在,海南島做為中國最大特區,享受著優惠政策,2006年人均GDP為11049元(人民幣),至少比台灣落後三十年。正因為脫離中國大陸,台灣有獲得尊嚴的可能,也不用為中國在世界帶來的麻煩「背書」。
在中國作家巴金的小說《家》中,主人公覺慧從腐朽墮落的家庭出走意味著覺醒和新生。覺慧知道這個家庭是「無可挽救的了」,他感到「這舊家庭裡面的一切簡直是一個複雜的結,他這直率的熱烈的心是無法把它解開的」。他毅然出走,尋找自己的生活道路。如果有台灣人還留戀中國這個「家」,本書可以幫助這些人瞭解這個「家」是什麼樣子。善良的人們都不希望台灣與中國大陸一起「爛掉」,就像善良的巴金不希望他的主人公「爛」在家裡一樣。
台灣離中國大陸越遠越好。地理上台灣不能與中國大陸拉開距離,但在文化上可以。這方面,新加坡是一個好的榜樣。作者在這本書中沒有顧及對中國人的描述可能讓台灣人看到自己的影子。作者寧願招致台灣人的批評,只是希望台灣離中國大陸越遠越好。這樣的台灣才會獲得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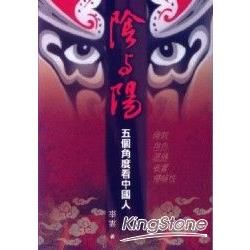
 共
共